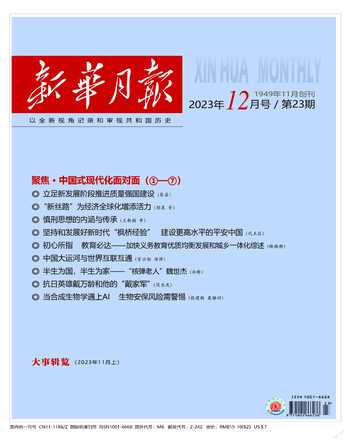慎刑思想的內涵與傳承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法系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優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們傳承。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等等,都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智慧。”慎刑思想具有深厚的內涵,對后世刑事司法制度產生深遠影響。慎刑思想有哪些值得提倡和深化的內容,對現在的刑事司法活動有哪些啟發?專家學者對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特邀嘉賓:
霍存福 沈陽師范大學教授
顧 元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羅慶東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副廳長
主持人、文稿統籌:王新穎 崔議文
問題一:什么是慎刑思想?
霍存福:慎刑,也叫慎刑罰,或者慎刑辟。來源于周初輔佐周成王的周公旦。他說:周文王是“明德慎罰”的(《尚書·康誥》),甚至殷商從商湯到帝乙這些君主,也都是“明德慎罰”的(《尚書·多方》)。后世講慎罰不多了,更多的是講慎刑,逐漸成為一個比較通行的概念。在發展過程中,人們不斷對慎刑思想做深入挖掘。明朝呂坤曾講,《周易》刑罰四卦,“曰‘致刑,曰‘明慎,曰‘明罰,曰‘無敢折獄,皆慎也”,都是講“慎”的。呂坤又說,《周易》里另有兩句話和《尚書》里的三句話,“曰‘緩死,曰‘赦過,曰‘不留獄,曰‘欽恤,曰‘寧失,皆仁也”,都是講“仁”的。這里的“慎”和“仁”,可能有一定的關聯,像“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便是“慎”和“仁”并行。
慎刑可以算作一個比較重要、相對核心的法哲學概念。其起源早,歷史長,涉及的范圍大,關涉問題多,從立法到司法、執法,都有涉及。可以這樣理解慎刑,即慎刑應該是一個刑法理念,是一項制刑原則,是一個程序機制,還是一種司法倫理。
顧元:慎刑是儒家法律觀的核心思想,是其法律主張最為簡潔、明達的表達。慎刑的基本意涵就是要求立法機關在制定法律、司法機關適用法律時皆需審慎。一般認為,慎刑思想萌芽于虞舜時期。有關的文獻記載可溯源至儒家經典《尚書》。《尚書·大禹謨》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即疑罪應予從寬處理,而論功行賞有疑問的,則從重辦理;寧可不按常法行事,也不可錯殺無辜。這是現代法治“疑罪從無”的先聲,也是慎刑思想的淵源。《尚書·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唐孔穎達疏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在具體適用上采取“附從輕,赦從重”的原則,即施刑從輕條,赦罪從重條,以示對疑罪之寬宥。
《尚書》進一步提出慎刑的主張和舉措:“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大禹謨》)”主張罪止己身,罪責自負,刑罰不及于子孫,獎賞施及后代;對過失的犯錯,無論多大都予以寬宥;對故意的犯錯,無論多小都予以刑罰。《康誥》中也已明確區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強調在定罪量刑時,考慮行為人的主觀動機。
西周統治者在總結桀紂覆滅歷史教訓基礎上,提出“彰明德教,慎用刑罰”。這是慎刑思想的首次闡釋。孔子進一步提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措手足”,主張德禮教化百姓,并將中庸之道融入刑罰理念,堅持刑罰適宜,反對濫用酷刑。孟子提出慎刑戒殺,天下定于“不嗜殺人者”的觀念,反對連坐。荀子主張“刑不過罪”,反對族刑。
西漢賈誼繼續闡發賞疑從有、罪疑從無的慎刑觀念:“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無辜也,寧失于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大政》)”在“約法省刑”原則指導下,漢文帝、景帝進行了廢肉刑的歷史性刑制改革。

慎刑概念明確使用見于《漢書·平帝紀》:“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灑心自新之意也。”此后逐漸普遍使用。如《元史·張懋傳》記載:“懋惡衣糲食,率之以儉,慎刑平政,慮之以公。”
羅慶東:我國古代就提出“明德慎罰”“慎刑”這樣較為先進的理念,并且成為主流法律思想,進而在立法、司法上都有一些相應的制度措施,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慎刑思想比起古代同態復仇、血親復仇的野蠻做法和酷刑、不人道刑罰,是相當大的進步,體現了經濟社會和司法文明的發展趨勢。此外,慎刑思想還對司法官員提出了較高要求,這里面既有對法官本身素質的要求,又有回避、復審、追責等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的相關制度設置,這就抓住了制度成敗的關鍵是“人”這個核心問題。
問題二:古代慎刑思想的具體表現有哪些?
霍存福:我國古代在闡述慎刑思想時,把好多方面的內容都賦予到這一大概念下面。比如,首先在態度上,“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只敢全力做好其他的政務工作,不敢輕易去“折獄”,這是一種司法態度。其次,在制度上,“罪疑從去”或者“疑罪從赦”,是仁,也是慎刑。大理寺在明清時負責案件的復核或復審,這就和“慎”的要求相契合了。另外,清朝還有熱審減刑制度,也屬于慎刑的制度化要求。再次,對司法官的要求,“惟良折獄”,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折獄,反對那種能說會道的人去折獄,佞人很可能“聘口辯”而折服人。
此外,理解慎刑的表現,還需要再補充一點,慎刑和濫刑、淫刑相對。與濫相關的,還有枉濫、冤濫,冤、枉都指以無罪為有罪、以小罪為大罪,明顯是背離了“刑稱罪”的罪刑法定原則,也就是沒能慎刑。實際上,慎刑是有標準的,是有底線不能背離的,這就是“刑稱罪”。如果背離了罪刑相適應原則,則是濫刑。
顧元:慎刑思想的主要體現是恤刑。《尚書·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恤”乃憂念之意,是“唯恐查之不審,施之不當也”。朱熹認為,“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中國古代社會在恤刑方面有很多制度的安排。譬如,歷代皆有老幼廢疾減刑、免刑的法律規定,成為中華法系的一大傳統。唐律對老幼廢疾者,分三種情形實行減免刑罰:一是70歲以上、15歲以下以及廢疾者,犯流罪以下,收贖。二是80歲以上、10歲以下以及篤疾者,犯反逆、殺人罪應處死刑的,上請;盜竊及傷人者,收贖;其余犯罪皆不論。三是90歲以上、7歲以下,雖犯死罪,不加刑。
就古代恤刑的制度設計及其實踐而言,死刑復奏制度是最典型的體現。漢代就有錄囚制度,并開始規定對某些死刑案件收歸中央核定。魏晉南北朝時期,死刑復奏逐漸制度化,至唐太宗時期進一步法律化,將死刑執行中的三復奏改為五復奏。唐以后歷代建立了嚴格的死刑復核(奏)制度。
為慎重審判和刑罰,中國古代的會審制度也頗具特色。唐代建立制度化的會審制度“三司推事”,由大理寺、刑部、御史臺三大司法機關的長官大理寺卿、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重大疑難案件。此外,還有朝廷派出的大理寺司直(或評事)、刑部員外郎、御史臺御史組成的“小三司”,會同審理地方重大案件。這種會審形式為后世繼承發展。明代確立朝審制度,每年霜降后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同公、侯、伯等會審死刑案件。除此之外,明朝還有三司推事、九卿會審、大審、熱審等會審形式。清代則有秋審與朝審兩種死刑復審形式,被稱為傳統的“正當程序”。各省死刑案件,分“立決”“監候”兩種。立決案件由原審機構立即執行,監候案件則列入秋審程序。秋審審理的對象是各省上報的斬監候、絞監候案件,每年秋八月上旬在天安門金水橋西由九卿、詹事、科道以及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等重要官員會同審理。秋審被視為“國家大典”,專門制定《秋審條款》,作為秋讞大典的法律依據。秋審案件經復審程序后,分情實、緩決、可矜、可疑、留養承嗣等情況處理。京城的監候案件則列入朝審,一般于霜降后十日舉行,其方式和內容與秋審類似,被告人被準許上堂為己聲辯。經秋審、朝審,罪犯被免除死刑的比例相當高。
慎刑在傳統立法和司法中可謂無所不在,貫穿始終。譬如,不太為學界所關注的夾簽聲請,亦為清代慎刑的極好例證。夾簽聲請是指在審理情節重大的案件時,若案情中具有較為顯著的“情有可原”情節,可由相應的司法官署在依法擬斷時夾簽注明可矜可憫的情節,請求皇帝予以最終裁決。作為審判中申請減等處罰的特殊司法程序,夾簽存在于清代刑事審判逐級審轉復核過程中,為審視刑事犯罪中的情理要素提供了合理合法的申訴渠道和制度保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夾簽就是司法中對情、理、法進行綜合考量權衡以實現“情法允協”的一種慎刑制度。
羅慶東:我國古代慎刑思想的表現是多層面、多角度、多方面的。首先,從國家治理層面來看,是把“德主刑輔”思想用來作為治理國家的一個理念和方略,其中就包括了慎刑思想。其次,從立法層面看,慎刑思想在立法上也是有很多體現的。比如,刑罰的體系設計為笞、杖、徒、流、死,有輕有重,由輕及重,輕者居多,根據行為的危害程度不同,分別適用不同的刑罰,實際上蘊含了慎刑的導向。再次,從司法層面看,慎刑思想要求在認定犯罪時要查清事實證據,反復推敲,遵循“賞疑從有、罪疑從無”的理念。在具體量刑時,講究“三赦三宥”,強調用刑慎重不濫。審判方面有多重程序,特別是對死刑的適用有較為嚴格的制度,甚至是由皇帝來親自審批,體現了對個人生命的尊重。
問題三:如何認識慎刑思想與刑法謙抑性理念?
霍存福:從學術話語中國化,或者說我們發展的中國道路選擇方面來說,我還是建議把慎刑概念傳承、固定下來,并發掘其時代內涵,讓其繼續有生命力。從學術進步的角度講,我也贊成謙抑原則的使用,并且提倡其與慎刑的比較研究。無論理論來自中國還是外國、東方還是西方,我們必須有更強的包容性。不過,我主張把中國式的概念用得更多一些,這樣更符合中國人對于正義、公平等要求的細節,更符合我們實際的期待和真正的需求。
顧元:刑法謙抑性與慎刑存在著歷史聯系,兩者的內涵、價值追求以及功能作用有相同之處。但我不認為慎刑思想的往昔“榮光”已不復存在,甚至在當下僅被作為域外謙抑理念的本土“注腳”。因為現代社會是民主法治社會,法律以保障人權為第一要義,慎刑當然是其題中之義。
謙抑性原則,又稱必要性原則,指立法機關只有在該規范確屬必不可少、沒有可替代刑罰的其他適當方法存在的條件下,才能將某種違反法律秩序的行為設定成犯罪行為。現代刑法追求維護正義、保障自由的價值,其制定、適用到執行無不滲透著慎刑理念。刑法制定遵從謙抑性原則,立法者要遵從實際,只有在某一行為沒有除刑罰外的其他法律能有效規制時,才可結合社會生活條件及客觀情況認定為犯罪行為;司法適用應遵從罪刑相適應原則。謙抑性原則旨在嚴格限制刑法的適用,特別是要限制刑事強制措施,強調適用不起訴制度;貫徹疑罪從無原則,充分保障人權;抵制嚴刑峻法,減少重刑的適用。同時,刑罰的輕重絕非衡量慎刑的最終標準,評價慎刑的標準應為“合理”,在謙抑之下充分發揮刑法預防功能。
刑事立法應始終保持謙抑和必要的積極,因此,應精確把握新領域涉罪行為及認定等問題,規范和監督司法機關依法行使職權,防止刑事立法“過猛”而引發犯罪圈“異常擴張”。《老子》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基于經濟社會發展和法治建設實際,我國犯罪結構和刑罰結構的輕緩化乃必然結果。
慎刑思想直接體現著法律的寬和與謙抑,蘊含著深刻的治世之道。現代刑法的謙抑性,在思想上與傳統慎刑有諸多契合之處。慎刑既體現了整體的“人民”主體觀念,又反映了具體的“個人”權利要求,尤其蘊含著對被告人人權的保障和尊重。
羅慶東:慎刑思想和刑法謙抑性理念不但有歷史聯系,而且聯系很緊密,謙抑理念可以說是慎刑思想的發展和完善。有學者認為,慎刑思想倡導刑法的緊縮與清簡,刑罰的慎用與節制,它與近現代意義的刑法謙抑精神有相同之處。有國外學者就認為,謙抑主義來源于中國古代的慎刑恤刑思想。恤刑原則的一個重要體現是對特殊的犯罪人群施以寬宥,對弱者采用強制性措施時要有所寬待,如不戴戒具,不一概拘押。可以說,慎刑思想和謙抑理念是從不同角度來談問題,二者的價值追求、思想主導實際上都是一致的,相比之下,慎刑思想具有鮮明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特征。
在討論慎刑思想對當今司法工作、檢察工作的啟發作用時,要重點把握好以下幾點:一是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法治思想,特別是要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做好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傳承的重要指示精神,使慎刑思想得到揚棄,不斷賦予其時代性。二是要貫徹落實憲法關于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定,履行好司法機關、檢察機關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神圣職責。三是要秉持刑法是最后一道屏障,刑事手段是最后一個制裁手段選擇的理念。對于進入刑事程序的案件,也要看罪行的輕重、社會危害程度以及認罪悔罪態度等來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以及追究刑事責任的輕重。四是要充分發揮檢察機關職能作用。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秉持客觀公正立場是法律對檢察官的明確要求,檢察機關和檢察官進行司法活動、履職盡責時,特別是在指控證明犯罪過程中,既要履行好懲罰犯罪的職責,也要履行好防止殃及無辜的責任,做到不枉不縱。為了防止錯案發生,還要注重更多發揮律師作用,注重聽取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意見,同時注重聽取被害人的訴求,實現辦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問題四:對我國古代的慎刑思想如何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顧元:慎刑思想具有顯著的現代適應性和深厚的生命力。傳承慎刑思想,對我國法治建設發展的意義重大。
其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根源,體現了我國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慎刑思想,是傳統慎刑在當代的鮮明呈現與深化。古人主張慎刑是從儒家中庸主義思想出發予以論證的,如南北朝時期西魏名臣蘇綽說:“刑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歷代的治國理政多以寬猛相濟作為基本政策,以突出刑法的打擊犯罪和治理功能,同時盡可能緩和社會矛盾,做到張弛有度。慎刑是寬緩化刑事政策的要求,我國將寬嚴相濟作為刑事政策,既是對傳統法文化的弘揚,亦有利于推進現代法治進程。寬嚴相濟是黨領導推進刑事犯罪治理的一項基本原則,契合現代法治理念和發展方向,也是構建中國特色輕罪治理體系的關鍵要素,應從頂層建構、體系重塑、規范適用等方面一體推進,不斷豐富發展刑事司法和犯罪治理新方案,以更好實現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之結合。
其二,死刑改革。傳統慎刑思想在新中國刑事司法中得以延續,主要表現為“少捕少殺”原則。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制度是“少殺”原則的具體化。我國死刑復核程序與死刑核準權統一行使制度,則體現了刑事政策中的慎殺原則。死刑改革在近年來取得很大進展,立法和司法上逐漸嚴格限制死刑適用范圍。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逐步減少死刑適用罪名以來,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項、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9項罪名的死刑,特別是在經濟領域死刑罪名已經大幅減少。
其三,訴訟程序防錯糾錯機制改革。我國刑事訴訟法經三次修改,強化辯護一方的訴訟權利,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訴訟并展開辯護;改變庭審方式,增強訴訟中的對抗性;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遏制非法取證行為。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力圖增進庭審實質化,解決庭審流于形式問題。這些刑事訴訟程序的改革,有利于加強偵查權與司法權正當行使,提高辦案質量。此外,刑事訴訟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五個階段的結構設計,以及各司法機關之間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有利于保障司法權力的有效行使,強化司法人權保障,防止國家刑罰權誤用和濫用,防止冤錯案件。
其四,法律職業改革。為保證司法公正和提升辦案質量,我國從2002年開始實行統一司法考試制度,后改為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制度,嚴格把好辦案人員任職資格關。另外建立司法官員額制,在任職資格上建立起分流、淘汰機制。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契合古人“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的理想。
就檢察工作而言,檢察機關應立足于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以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為基本的角色定位,行使好職權,在審查起訴、審查批捕、偵查司法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案件、監督民事行政案件等方面把好法律監督關。從慎刑的角度看,檢察機關的角色極其重要,舉足輕重。譬如,檢察機關應著力監督法官的審判活動是否合法、法院作出的生效判決和裁定是否合法;監督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是否合法;監督監獄、看守所等監管活動是否合法;監督罪犯是否符合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等刑事處罰變更的條件。
總之,傳承慎刑思想,應當結合新時代發展,把握核心內涵,加強制度的銜接配合。
羅慶東:慎刑思想的內涵和傳承與刑事檢察工作聯系十分密切。在刑事檢察工作中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要以刑事檢察工作現代化助推檢察工作現代化、政法工作現代化,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根據刑事檢察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最高檢提出,要著力構建三個體系,就是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中國特色輕罪治理體系、刑事訴訟制約監督體系。
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是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需要。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等政法機關一道承擔著指控犯罪的責任,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特別是認罪認罰案件的訴訟過程中承擔著主導責任,案件質量能不能過得硬,把案件辦成“鐵案”,最后靠證據,所以要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其中就包括落實非法證據排除、證據裁判等原則要求,也包括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建設,等等。
構建中國特色的輕罪治理體系,要求我們既要注重辦案,也要注重社會治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建設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20多年來,我國刑事犯罪的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刑事案件里面,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占了絕大多數,也就是說,多數是輕罪案件。嚴重暴力犯罪案件下降,但整體刑事案件發案量在上升,其中更多的是輕罪案件。同時,近年來出現的一些新型犯罪,包括網絡犯罪、金融領域犯罪等,是根據這些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通過立法把那些新型的危害社會的行為規定為犯罪,總體來說,法定刑相對比較輕,需要在打擊的同時做好防范工作。近年來,檢察機關一直在積極探索開展輕罪治理工作,結合案件辦理,發現同類社會管理問題時,向有關部門提出檢察建議,推動社會治理,取得了良好效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輕罪治理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認罪認罰案件的適用率已經穩定在80%以上,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的比率也超過90%,法院采納量刑建議率很高,被告人一審判決以后上訴率很低,這就說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功效已經彰顯出來,緩和了社會矛盾,提高了司法效率,修復了社會關系,推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刑事訴訟制約監督體系構建是刑事訴訟規律和我國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應當遵循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要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做到敢于監督、善于監督、依法監督、規范監督,同時更要注重自我監督。
最高檢黨組明確提出,讓求真務實、擔當實干成為檢察人員鮮明的履職特征。這對檢察官的政治素質、業務素質、紀律作風建設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我們要按照最高檢的部署和要求,不斷加強隊伍建設,真正擔當起新時代刑事檢察工作職責。注意全面準確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切實做到依法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相濟、罰當其罪。始終堅持嚴的一手不動搖,堅決嚴懲危害國家安全、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犯罪,保持嚴的震懾力度,切實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同時要規范寬的一面,對輕微犯罪、主觀惡性不大的犯罪等,依法落實寬的政策,發揮好寬的教育作用,減少社會對抗,增進社會和諧。堅持嚴格依法辦案、公正司法,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公平正義,前提是依法,核心是公正。所有監督辦案都應遵循法律規定和法的精神,以嚴格公正司法,實現公平正義,維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當事人合法權益。
(摘自《人民檢察》2023年第17期。王新穎、崔議文為該刊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