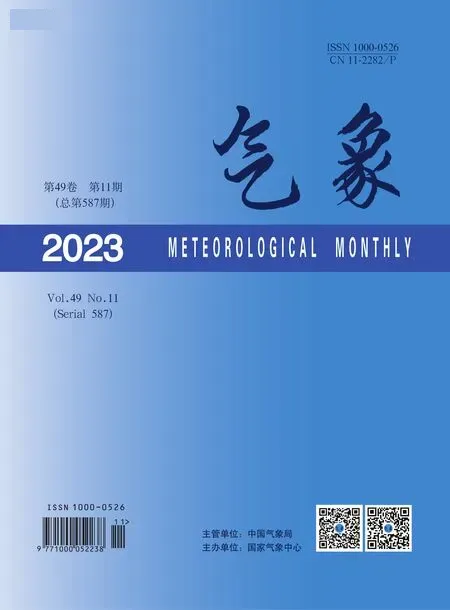多個超級單體風暴誘發的EF3級強龍卷特征分析*
張桂蓮 李一平 江 靖 常 欣 霍志麗 仲 夏 郭炳瑤 賈克寒
1 內蒙古自治區氣象臺,呼和浩特 010051 2 赤峰市氣象局,內蒙古,赤峰 024000 3 錫林郭勒盟氣象局,內蒙古,錫林浩特 026000
提 要:2021年6月25日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發生了歷史罕見的EF3級強龍卷,導致6人死亡,大量建筑物等嚴重損毀。利用常規高空和地面觀測、區域自動氣象觀測站、FY4衛星云圖、河北省張北CB型多普勒雷達等觀測資料,以及NCEP(1°×1°)逐6 h再分析資料對這次強龍卷過程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此次龍卷發生在前傾槽不穩定層結環境背景下,較強的對流層中低層條件不穩定(850 hPa與500 hPa溫度垂直減溫率約為7.7℃·km-1)、低層豐富的水汽、中等強度的對流有效位能和強的0~6 km垂直風切變為超級單體風暴形成提供了有利環境背景。此外,0~1 km風矢量差為8 m·s-1,抬升凝結高度為1.0 km,為超級單體龍卷的發生提供了相對有利的環境條件。與地面干線伴隨的輻合線觸發了產生龍卷的母風暴,隨后演變為超級單體,其雷達反射率因子呈現典型的鉤狀回波、低層暖濕氣流入流缺口、低層弱回波區和中高層回波懸垂,以及中等強度的中氣旋等特征;龍卷的生成和消亡過程中有三個超級單體風暴相繼形成,都呈現為孤立的對流風暴形態,龍卷發生在其中一個超級單體鉤狀回波的頂端,在前側上升氣流和后側下沉氣流交界處,雷達分析的基于中氣旋強度演變的龍卷可能起始時間和路徑與現場調查時間十分吻合。除了強龍卷,這系列超級單體還產生了大冰雹和直線型對流大風(雷暴大風),強回波中心自低到高明顯傾斜,最大反射率因子高達65 dBz,徑向速度圖上除了有中等強度的中氣旋,還存在明顯的中層徑向輻合,超級單體風暴形成時垂直累積液態水含量(VIL)值高達73 kg·m-2,VIL密度達到4~5 g·m-3,這些雷達回波特征指示大冰雹的存在,而中層徑向輻合是雷暴大風的雷達回波特征。
引 言
龍卷是強對流中產生破壞力最強的小尺度災害性天氣,能在短時間內造成重大人員和財產損失,龍卷通常分為超級單體龍卷(或稱為中氣旋龍卷)和非超級單體龍卷(或稱為非中氣旋龍卷)(Wakimoto and Wilson,1989;俞小鼎等,2006a);對國內龍卷的研究已經有許多成果,鄭永光等(2021)對中國龍卷研究進展進行了深入分析,王秀明等(2015)、鄭媛媛等(2015)、黃先香等(2019)、徐芬等(2021)分別對中國東北龍卷的環境特征、東部沿海地區的10次臺風龍卷過程、珠江三角洲臺風龍卷的活動特征、江蘇龍卷時空分布進行了區域性研究;中國的強龍卷主要分布在江淮、兩湖平原、華南、東北和華北東南部等平原地區,具有在某地頻發的特征(范雯杰和俞小鼎,2015),例如2016年6月23日發生在江蘇鹽城阜寧的EF4級龍卷(鄭永光等,2016;張小玲等,2016),2019年7月3日遼寧開原EF4級龍卷(鄭永光等,2020;張濤等,2020),2019年4月13日廣東徐聞強龍卷(黃先香等,2021);從誘發我國龍卷的天氣系統而言,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臺風天氣背景產生的臺風龍卷,例如2015年10月強臺風彩虹螺旋雨帶中衍生龍卷對廣東的影響(王炳赟等,2018),另一類是低渦、高空槽、切變線等天氣背景下產生的西風帶龍卷(俞小鼎等,2006b;刁秀廣等, 2014;鄭艷等,2017)。
內蒙古對短時強降水、雷暴大風、冰雹等強對流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對龍卷的研究罕見;2016—2020年內蒙古出現了3次龍卷,如2016年赤峰市龍卷、2020年包頭市、錫林浩特龍卷,均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因此加強內蒙古龍卷的研究非常必要。本文對2021年6月25日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由多個超級單體風暴誘發的EF3級強龍卷特征進行分析,以期對內蒙古龍卷的預報提供一些參考依據。
2021年6月25日14:00—15:00(北京時,下同),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千斤溝鎮發生龍卷風天氣(以下簡稱“6·25”龍卷),伴隨短時強降水和冰雹,龍卷導致6人死亡,14人受傷,磚木結構房屋倒塌200余間,部分牲畜被砸死。25日錫林郭勒盟氣象局對太仆寺旗龍卷進行了初步現場調查,26日由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災害天氣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氣象中心、內蒙古自治區氣象局、錫林郭勒盟氣象局、太仆寺旗氣象局組成的四級聯合現場調查組開展龍卷過程調查,通過無人機航拍等影像資料,獲得寶貴的龍卷災情信息。
1 資料和災情調查
1.1 資 料
本文選取資料為2021年6月25日內蒙古氣象信息中心提供的全區1134個加密自動氣象站觀測資料,中國氣象局衛星中心提供的FY-4可見光云圖和云頂亮溫(TBB)以及河北省張家口市張北多普勒雷達(CINRAD/CB型)資料,NCEP的FNL(1°×1°)逐6 h再分析資料以及聯合調查組提供的災情調查資料。
1.2 災情調查
2021年6月25日14:10—14:40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千斤溝鎮出現龍卷,伴隨雷電、短時強降水和強冰雹天氣。距離受災點最近的氣象站為建國村和千斤溝鎮區域氣象站(距離為15 km),建國村區域站為氣溫、降水兩要素站,龍卷經過前后氣溫明顯下降,從14:00的20.5℃下降到11.5℃,下降幅度為9.0℃;14:00—15:00的小時降水量為26 mm,14:00—16:00的累計降水量為31.6 mm,并伴有雞蛋大小的冰雹(目擊者描述)。龍卷發生地有風塔,但剛剛組裝未投入使用,因此沒有探測到龍卷經過時的極大風速;千斤溝鎮六要素區域站14:00—15:00極大風速從8.2 m·s-1增至11.9 m·s-1,極大風速出現在14:22,同時風向突變,由西南風轉為西北風;氣壓偏低,后略有上升,從14:00的836.8 hPa上升至15:00的837.5 hPa;14:00—15:00 的小時降水量為15.3 mm,13:00—16:00的3 h累計降水量為23.6 mm。
依據《龍卷災害調查技術規范》(全國氣象防災減災標準化技術委員會,2017),對錫林郭勒盟太卜寺旗千斤溝鎮“6·25”龍卷風進行調查,根據現場調查,結合航拍影像和目擊者描述,本次龍卷風于25日14:10左右生成于馬坊子村西馬坊西北側,途經東馬坊、建國村大營子,14:40終止于建國村三級地東南2 km左右,路徑全程為13 km左右;受災寬度為50~200 m;依據《龍卷強度等級》(中國氣象局,2019)強度定級為強龍卷風三級,相當于EF3級強龍卷。
根據龍卷風起點處目擊者描述,25日14:10左右天氣突變,太仆寺旗馬坊子村村頭西北方天空出現漏斗型云狀,后逐漸與地面相接,地面出現黃色塵土,呈螺旋狀快速經過村頭由北向東南移動,后又向正南方移動,接地寬度為50~150 m;龍卷所經之地大量樹木折斷,并有明顯扭曲旋轉特征,部分大樹連根拔起,最大直徑達52 cm,沿途樹木成片擼頂,大多樹木倒伏方向和龍卷移動方向基本一致,有多處樹木向內側成氣旋倒伏,具有龍卷獨有的樹木倒伏特征。14:20左右龍卷進入建國村,瞬間天昏地暗,磚混結構房屋倒塌,農機車吹翻損毀、移位,汽車移位至破損墻上、機動三輪車拋到農田,沿途變壓器損毀嚴重,直徑20 cm的電線桿被折斷,并伴有雞蛋大小的冰雹,冰雹把挖掘機駕駛室擋風玻璃打碎,1 min 后龍卷向東南方向移動;據建國村三級地農民講述,龍卷在建國村三級地東南2 km左右處減弱消失,龍卷消失處位于太仆寺旗與河北省沽源縣交界處河北一側。
2 前傾槽下大尺度環流背景
由6月25日08:00高空綜合配置圖(圖1)可見,在蒙古國和內蒙古河套地區(40°~50°N、110°E)850 hPa 有高空槽,500 hPa、700 hPa高空槽位于其下游內蒙古中部、華北東部地區(40°~50°N、110°~115°E),即850 hPa高空槽落后于700~500 hPa高空槽,高空槽隨高度具有明顯的前傾結構特點,且700~500 hPa西風槽重疊,系統較為深厚,非常有利于強對流的產生;太仆寺龍卷(圖中三角代表龍卷中心)位于700~500 hPa高空槽后的位勢高度大梯度區內,該區域為下沉運動區;與850 hPa槽前西南氣流上升運動區疊置, 龍卷發生地850~500 hPa均位于濕區,上游為干區,有干冷空氣侵入,并有干線(露點鋒)維持。綜上所述,此次太仆寺龍卷是發生在前傾槽結構的大尺度環流背景下,上冷下暖的不穩定層結,且上游有干冷空氣入侵,冷暖空氣交匯,易發生雷暴大風和冰雹等強對流天氣(孫繼松和陶祖鈺,2012)。

注:三角代表龍卷中心,下同。圖1 2021年6月25日08:00高空綜合配置圖Fig.1 High-altitude comprehensive configuration at 08:00 BT 25 June 2021
3 龍卷發生的中尺度環境條件
對于雷暴(深厚濕對流)生成,大氣靜力不穩定、低層水汽和抬升觸發機制,這三個要素是雷暴生成的充分必要條件(假定微物理條件自動滿足)(Do-swell et al,1996;俞小鼎,2011);除這三個要素外,水平風垂直切變大小決定雷暴的組織程度和生命史長短(Weisman and Klemp,1982),下面從這四個方面分析超級單體風暴發生、發展的環境條件。
3.1 低層水汽豐富
6月25日11:00比濕和風沿41.79°N(龍卷中心為41.79°N、115.49°E)剖面顯示(圖略),龍卷中心800 hPa以下比濕為10~12 g·kg-1,高于內蒙古中部強對流層低層比濕8~10 g·kg-1的標準,且為西南風,風速不大,普遍為4~6 m·s-1,800 hPa 以上均為西北風,水汽整體呈現上干下濕的層結分布;大氣低層高相對濕度有利于龍卷對流風暴的下沉氣流不會太強,從而有利于近地面垂直渦度的增強(Doswell and Evans,2003;Schultz et al,2014);25日14:00(圖2a)龍卷中心800 hPa以下比濕仍為10~12 g·kg-1,且為西南風,但風速明顯增至6~10 m·s-1,其上游(112°~114°E)風向也從11:00的西南風轉為西北風,濕度明顯下降,比濕從11:00的6~8 g·kg-1下降至2~4 g·kg-1,表明有干冷空氣入侵,干冷空氣強迫暖濕空氣抬升,有利于鋒生;800 hPa以上仍維持西北風,但風速也明顯加大,400~300 hPa高空西北風風速達32 m·s-1。中空干冷空氣入侵并疊加在西南暖濕氣流之上形成強的高低空垂直風切變區是強風暴系統發展和維持的重要因素。

圖2 2021年6月25日14:00(a)比濕(陰影)和風場(風羽)沿41.79°N剖面, (b)500 hPa高度場(黑線,單位:dagpm)、溫度平流(填色)和850 hPa風場(風羽)Fig.2 (a) Vertical profile of specific humidity (shaded) and wind field (barb) along 41.79°N, and (b) geopotential height (contour, unit: dagpm), tempreture advection at 500 hPa (colored) and wind field at 850 hPa (barb) at 14:00 BT 25 June 2021
3.2 有利于龍卷生成的不穩定層結
中高層較強干冷空氣疊加在低層暖濕氣流上,使得大氣溫度垂直遞減率增大,造成低層空氣負浮力加大,有利于地面強對流天氣特別是冰雹、大風類的強對流天氣出現(許愛華等,2014)。
25日11:00(圖略)500 hPa溫度平流和850 hPa風場上,龍卷中心區域850 hPa為4 m·s-1的西南風,500 hPa位于冷暖溫度平流交界處,其上游有明顯的冷空氣,冷平流中心強度為-35×10-5℃·s-1;14:00(圖2b)在內蒙古中部850~500 hPa 冷暖氣流同時加強,850 hPa有西南風、東南風、東北風、西北風形成的氣旋式環流中心,并有“人”字型切變線維持,500 hPa冷空氣東南下,且冷平流中心正好經過龍卷中心,龍卷中心區域850 hPa仍為西南風,但西南風風速增至6~8 m·s-1,500 hPa溫度平流和850 hPa風場配置上,龍卷中心區域500 hPa冷平流疊加在850 hPa西南暖濕氣流之上,垂直溫度遞減率加大,上冷下暖不穩定層結加強,有利于強對流天氣的產生,龍卷在14:00之后生成并爆發。
25日14:00 850 hPa假相當位溫θse(圖略)在華北地區為顯著高能區,龍卷中心位于高能區后部θse梯度區;14:00θse沿龍卷中心41.79°N剖面顯示(圖3a),龍卷中心700 hPa以下θse分布呈近似倒“Ω”型,850 hPa以下θse呈高能舌分布,龍卷中心θse為346 K,θse隨高度減小,且垂直遞減率高;θse是表示溫度和濕度的特征量,低層高能高濕,有利于強對流的發生。
25日11:00龍卷中心850 hPa與500 hPa溫度差ΔT(850-500)為29℃ ,而14:00(圖略)隨著500 hPa冷平流和850 hPa西南風同時加強以及午后太陽輻射的共同作用,ΔT(850-500)高達33℃,明顯大于內蒙古中部雷暴大風、冰雹等強對流ΔT(850-500)為28℃的標準;850 hPa與500 hPa溫度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表示對流層中低層環境溫度垂直遞減率,也就是條件靜力不穩定度的大小,ΔT(850-500)差值越大,表示大氣層結越不穩定,有利于對流天氣的產生(吳芳芳等,2013);14:00溫度垂直減溫率約為7.7 ℃·km-1,大于美國顯著龍卷垂直減溫率(Craven and Brooks,2004),14:00龍卷爆發。
強龍卷爆發通常需要有超級單體風暴產生的環境條件,其有利條件是較大的對流有效位能(CAPE)和強的深層(0~6 km)垂直風切變(鄭永光等,2017)。25日11:00龍卷中心CAPE值(圖略)只有800~1000 J·kg-1, 14:00(圖3b)CAPE的強度和范圍在華北地區迅速躍增,龍卷中心CAPE值高達1200~1400 J·kg-1,大于內蒙古中部強對流CAPE值1000 J·kg-1的標準,龍卷發生地并不位于CAPE最大值區域,而是在CAPE最大值后側梯度區。
25日14:00(圖略)0~1 km垂直風切變并不大,只有4~6 m·s-1,而0~6 km垂直風切變卻一直較大,在08:00—11:00為18~20 m·s-1,14:00(圖略)高達20~22 m·s-1,高于內蒙古中部強對流0~6 km垂直風切變18 m·s-1的標準。強的垂直風切變有利于對流風暴的加強和維持,水平風垂直切變大小決定雷暴的組織程度和生命史長短(Weisman and Klemp,1982),F2/EF2級以上龍卷通常出現在強垂直風切變環境下(Johns and Doswell,1992;俞小鼎等,2012);CAPE值和0~6 km垂直風切變越大,發生龍卷的可能性越大(Markowsi and Richardson,2010),這次太仆寺龍卷環境條件滿足了以上兩個條件。

圖3 2021年6月25日14:00(a)θse沿41.79°N剖面,(b)CAPE值分布Fig.3 (a) Vertical profile of θse along 41.79°N, (b) CAPE at 14:00 BT 25 June 2021
探空曲線反映了探空站及其附近一定范圍內氣象要素的垂直分布,對距離龍卷中心最近的河北省張家口探空資料進行分析(表1),25日08:00沙瓦特指數(SI)、抬升指數(LI)、最有利抬升指數(BLI)分別為-0.36℃、-0.41℃、-0.8℃,而CAPE、下沉對流有效位能(DCAPE)均不高,分別為125.3 J·kg-1、8.4 J·kg-1,0~1 km、0~3 km垂直風切變分別為8.3 m·s-1、15.2 m·s-1,但K指數為35.1℃,ΔT(850-500)為22.8℃,特別是0~6 km垂直風切變為21.2 m·s-1,達到強的垂直風切變,抬升凝結高度(LCL)也很低,只有1.038 km;用14:00的2 m溫度、露點溫度等對08:00的探空資料進行訂正,14:00(表1)CAPE躍升為1312.9 J·kg-1、BLI減小至-4.2℃,不穩定條件進一步增強,較強的CAPE和0~6 km垂直風切變以及較低的LCL為午后龍卷天氣的發生提供了有利的熱力和動力不穩定條件。

表1 2021年6月25日張家口站主要環境參數Table 1 Main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t Zhangjiakou Station on 25 June 2021
3.3 與地面干線伴隨的輻合線觸發產生龍卷的母風暴
在對流不穩定條件下,對流初始活動需要邊界層輻合線、地形和海陸分布、重力波(俞小鼎等,2012)等觸發機制。此次太仆寺龍卷是由超級單體風暴誘發生成,與地面干線伴隨的輻合線觸發產生龍卷的母風暴。
25日14:00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南部有中尺度輻合線生成(圖4a),其后緩慢向東南移動,不斷觸發對流系統產生,14:30移出內蒙古境內,隨后進入河北省;14:00(圖4b)在內蒙古和河北交界附近有西北風和西南風構成的中尺度輻合線,同時中尺度輻合線附近有干線維持,干線北側干冷空氣不斷侵入,地面露點溫度只有2℃,而其南側由于西南暖濕氣流不斷輸送,露點溫度為16℃,干線南北兩側干濕梯度非常大,表明干線兩側的冷暖氣流顯著加大,干冷空氣和暖濕氣流交匯,有利于龍卷超級單體風暴誘發生成。

圖4 2021年6月25日(a)14:00—14:50中尺度輻合線演變, (b)14:00 2 m露點溫度(數字,單位:℃)和10 m風場(風羽)Fig.4 (a) Evolution of the mesoscale convergence line from 14:00 BT to 14:50 BT, and (b) 2 m dew point temperature (number, unit: ℃) and 10 m wind filed (barb) at 14:00 BT 25 June 2021
4 孤立的對流單體形成龍卷
6月25日13:45(圖5a)FY-4衛星云圖上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南部太仆寺旗附近有一個孤立近似圓形的中尺度對流系統(MCS),在其西南側有三個排列成一線的TBB≤-52℃冷云區,表明對流發展旺盛;14:00(圖5b)MCS面積逐漸增大,三個排列成一線的TBB≤-52℃冷云區合并成一個面積較大的冷云區;14:10左右龍卷爆發,14:15(圖5c)孤立近似圓形的MCS仍繼續維持,TBB冷云區范圍進一步增大,龍卷爆發在TBB梯度區,而此時雷達回波反射率強度高達60 dBz;符合孤立分散的單體對流更易于生成龍卷以及產生EF2級以上龍卷的對流模態,其中一類為相對獨立的單體聚集成圓形或橢圓形的離散單體,最大回波可達50 dBz的統計研究(Grams et al,2012)。14:20(圖6)可見光云圖上有白亮的圓形對流單體,在龍卷爆發處TBB梯度大值區云頂非常粗糙,有明顯上沖云頂,表明有深厚對流發生;在對流云團西北側上風方向邊界齊整,而對流云團東南側下風方向有明顯云砧,垂直風切變強,有利于對流風暴龍卷的形成;15:00(圖5d)MCS主體進入河北沽源,雖然也有龍卷但沒有產生明顯危害。

圖6 2021年6月25日14:20 FY-4可見光云圖Fig.6 Visible cloud image of FY-4 satellite at 14:20 BT 25 June 2021
5 多個超級單體風暴誘發龍卷
5.1 多仰角的超級單體風暴垂直結構
此次龍卷在25日14:12爆發,距離龍卷發生地最近的是河北省張家口市張北多普勒雷達,位于龍卷中心西南方向約100 km處。對張北雷達0.5°、1.5°、3.4°、4.3°不同仰角基本反射率因子(圖7)進行分析,0.5°仰角(圖7a)有中心強度為60 dBz的強回波,在強回波移動方向右側有倒“V”型缺口,強的上升氣流導致了“V”型缺口;低層1.5°仰角(圖7b)有弱回波,低層弱回波對應的3.4°仰角(圖7c)、4.3°仰角(圖7d)有強回波及回波懸垂,回波強度高達60 dBz、中高層有回波懸垂和傾斜的強中心,有利于組織化對流的發展。
25日14:00張北雷達1.5°基本徑向速度圖上有明顯的±15 m·s-1氣旋式切變速度對(圖8a),且14:06(圖8b)、14:12(圖8c)雷達連續兩個體掃仍有氣旋式速度對維持,速度對距離張北雷達中心為100 km,滿足中氣旋判據,為中等強度的中氣旋(俞小鼎等,2006a),該風暴為超級單體風暴,表明此次太仆寺龍卷由超級單體風暴誘發而成;國內大量研究認為,許多龍卷發生時伴隨中氣旋,且中氣旋底高很低(張小玲等,2016),此次龍卷也具有這個特點。
垂直累積液態水含量(VIL)從14:00到14:12(圖略)有明顯躍增,VIL中心值高達73 kg·m-2,VIL密度為6.1 g·m-3(>4 g·m-3),表明有直徑超過 2 cm 的大冰雹(Amburn and Wolf,1997),產生龍卷的超級單體具有大冰雹的回波特征,同時也產生了大冰雹,與龍卷實際調查有大冰雹相吻合。
6月25日14:48張北雷達1.5°仰角反射率因子圖上(圖9a),在內蒙古太仆寺旗和河北沽源有兩個渦旋鉤狀回波,近似經典超級單體;1.5°仰角在鉤狀回波處有明顯弱回波,2.4°(圖9b)、3.4°(圖9c)、4.3°仰角(圖9d)在弱回波上有強的回波懸垂,且隨高度強度明顯加大,3.4°、4.3°仰角回波懸垂中心強度高達65 dBz以上。

圖7 2021年6月25日14:00張北多普勒雷達(a)0.5°,(b)1.5°,(c)3.4°,(d)4.3°仰角反射率因子Fig.7 Doppler radar reflectivity factor in Zhangbei at elevations of (a) 0.5°, (b) 1.5°, (c) 3.4°, and (d) 4.3° at 14:00 BT 25 June 2021

圖8 2021年6月25日(a)14:00,(b)14:06,(c)14:12張北多普勒雷達1.5°仰角基本徑向速度Fig.8 Doppler radar basic radial velocity in Zhangbei at 1.5° elevation at (a) 14:00 BT, (b) 14:06 BT, (c) 14:12 BT 25 June 2021

圖9 2021年6月25日14:48張北多普勒雷達(a)1.5°,(b)2.4°,(c)3.4°,(d)4.3°仰角反射率因子Fig.9 Doppler radar reflectivity factor in Zhangbei at elevations of (a) 1.5°, (b) 2.4°, (c) 3.4° and (d) 4.3° at 14:48 BT 25 June 2021
6月25日14:42(圖10a)、14:48(圖10b)張北雷達1.5°仰角基本徑向速度圖上,連續兩個體掃,同樣有明顯的±15 m·s-1氣旋式速度對,速度對距離張北雷達中心約為100 km,表明有兩個中氣旋,14:42—14:48又有兩個超級單體風暴生成,龍卷發生在鉤狀回波頂端,在前側上升氣流和后側下沉氣流交界處,這符合龍卷超級單體風暴概念模型(Lemon and Doswell,1979);雷達分析和現場調查時間十分吻合,此次太仆寺龍卷為三個超級單體風暴誘發而成,這在內蒙古中部地區極為罕見。
5.2 超級單體風暴的垂直剖面結構
張北雷達14:00反射率因子沿徑向方向垂直剖面圖上(圖11a),低層有弱回波區、較大的反射率因子梯度區、5~6 km處有回波穹隆,回波穹隆之上有強的回波懸垂,懸垂正上方60.5 dBz強回波中心高度接近9 km,大于55 dBz的強回波高度已經伸展到13 km以上,高懸的強回波也是大冰雹的預報指標;剖面結構表明超級單體風暴內反射率因子從低到高向低層入流一側傾斜的特征,極強的傾斜入流和上升運動迫使較大直徑的冰粒在超級單體風暴中不斷生成,有利于大冰雹的生成。
張北雷達14:06基本徑向速度沿垂直徑向方向垂直剖面圖上(圖11b),風暴單體(水平方向1.2~2.2 km)低層2~4 km高度處有偏北風斜升入流,與圖11a 反射率因子剖面圖中低層反射率因子大梯度區方向一致;垂直方向上6~12 km有明顯的中層徑向輻合(MARC),厚度大于6 km,中層徑向輻合通常可作為地面大風預警指標(俞小鼎,2006a),一般MARC出現10~30 min之后,地面會出現大風(Schmocker et al,1996);8~9 km高度上存在±12.5 m·s-1的氣旋式切變速度對,超級單體風暴內具有明顯的旋轉特征,這種顯著的中層徑向輻合通常在地面有強的出流氣流,造成地面強風的生成,這也是龍卷產生的重要原因。

圖10 2021年6月25日(a)14:42,(b)14:48張北多普勒雷達1.5°仰角基本徑向速度Fig.10 Doppler radar basic radial velocity in Zhangbei at 1.5° elevation at (a) 14:42 BT, (b) 14:48 BT 25 June 2021

圖11 2021年6月25日張北雷達(a)14:00反射率因子,(b)14:06基本徑向速度垂直剖面Fig.11 Cross section of (a) reflectivity at 14:00 BT and (b) basic radial velocity at Zhangbei Radar at 14:06 BT 25 June 2021

圖12 2021年6月25日張北雷達14:42(a)反射率因子,(b)基本徑向速度垂直剖面Fig.12 Cross section of (a) reflectivity and (b) basic radial velocity at Zhangbei Radar at 14:42 BT 25 June 2021
張北雷達14:42反射率因子沿徑向方向垂直剖面圖上(圖12a),同樣低層有弱回波區、較大的反射率因子梯度區以及位于其上的回波懸垂,大于55 dBz 強回波高度伸展到9 km左右;不同于14:00,弱回波區左側有強回波墻,其高度在2~8 km,最大反射率因子高達64 dBz,這種近乎接地的強回波墻往往伴有大冰雹的落地和地面強風的生成。
張北雷達14:42基本徑向速度沿徑向方向垂直剖面圖上(圖12b),超級單體風暴低層2 km高度以下有明顯的輻散,與圖12a反射率因子剖面圖中回波墻接地造成大風結論一致;垂直方向上3~11 km處有明顯的中層徑向輻合,厚度高達8 km,8~9 km高度上有±12.5 m·s-1速度對,這種顯著的中層徑向輻合同樣指示著地面有強的出流氣流,造成地面強風。
綜上所述,反射率因子和基本徑向速度垂直剖面均有利于大冰雹和強風的生成。
6 結 論
通過對2021年6月25日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太仆寺旗EF3級強龍卷進行分析,結果表明:
(1)太仆寺龍卷發生在前傾槽結構的不穩定層結大尺度環流背景下,龍卷爆發于700~500 hPa高空槽后的位勢高度大梯度的下沉運動區與850 hPa槽前西南氣流上升運動區疊置區域內。
(2)較強的對流層中低層條件不穩定(850 hPa與500 hPa溫度垂直減溫率約為7.7 ℃·km-1)、低層豐富的水汽、中等強度的對流有效位能和強的0~6 km垂直風切變為超級單體風暴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環境背景。此外,0~1 km風矢量差為8 m·s-1,抬升凝結高度為1.0 km,為超級單體龍卷的發生提供了相對有利的環境條件。
(3)龍卷爆發在一個孤立的近似圓形的中尺度對流系統MCS內的云頂亮溫梯度區,該區域云頂非常粗糙,有明顯的上沖云頂,表明有深厚的對流發生;在對流云團西北側上風方向邊界齊整,而對流云團東南側下風方向有明顯云砧,垂直風切變強,有利于對流風暴龍卷的形成。
(4)與地面干線伴隨的輻合線觸發了產生龍卷的母風暴,隨后演變為超級單體,其雷達反射率因子回波呈現典型的鉤狀回波、低層暖濕氣流入流缺口、低層弱回波區和中高層回波懸垂,以及中等強度的中氣旋等特征。
(5)龍卷的生成和消亡過程中有三個超級單體風暴相繼形成,都呈現為孤立的對流風暴形態,龍卷發生在其中一個超級單體鉤狀回波的頂端,在前側上升氣流和后側下沉氣流交界處,雷達分析的基于中氣旋強度演變的龍卷可能起始時間和路徑與現場調查時間十分吻合。
(6)除了強龍卷,系列超級單體還產生了大冰雹和直線型對流大風(雷暴大風),強回波中心自低到高明顯傾斜,最大反射率因子高達65 dBz,徑向速度圖上除了有中等強度的中氣旋,還存在明顯的中層徑向輻合,超級單體風暴形成時垂直累積液態水含量值高達73 kg·m-2,其密度達到4~5 g·m-3,這些雷達回波特征指示大冰雹的存在,而中層徑向輻合是雷暴大風的雷達回波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