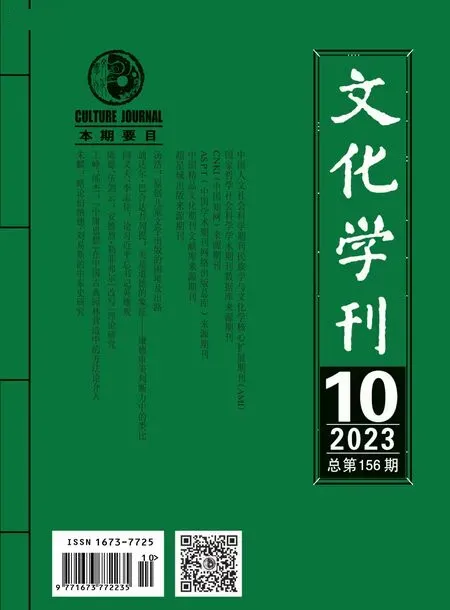文化產業關聯與效應測度分析
顧歆瑜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當前,我國文化產業正在從快速發展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文化產品日益豐富,市場規模不斷擴大。 但由于起步較晚等原因,我國文化產業仍存在效率低、結構不合理等問題。 因此,為提高文化產業發展效率,增強我國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本文對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效應進行了測度與分析,以期能夠為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政策的提出有所助力,進而推動 “文化+” 戰略思想的實現。
二、文獻綜述
20 世紀40 年代,阿多諾和霍克海默首次提出 “文化產業” 的相關概念。 自此國內外學者為提高文化產業競爭力,對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多方面探究,而文化產業關聯效應作為推動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和結構轉型的重要動因,成為了文化產業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當前,學界主要通過投入-產出模型對產業間的關聯效應進行研究。
David Thorsby(2004)[1]通過CGE 模型研究了文化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并對其發展路徑進行了分析,得到文化產業具有較強關聯性的結論。 趙云(2016)[2]計算文化產業內部15 個部門與其他部門間的影響度和感應度。 由研究結果可得,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應發展文化產業并使其成為支柱性產業。 黃思源(2013)[3]、王葉軍(2015)[4]、林峰(2015)[5]、張秀峰和康軍(2016)[6]、孫智君和江燕(2017)[7]、李偉舵等(2018)[8]、劉曉玲等(2021)[9]分別對我國不同地區的文化產業關聯效應進行了分析,得到文化產業的影響力和感應度與其他產業相比都相對較低,更依賴自身產業內部消耗的結論。 應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大資源整合力度,提升文化產業集聚發展水平。
綜上所述,當前學界對文化產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文化產業與第一、第二、第三產業關聯度的研究,且合并部門的標準未進行統一,無法精確反映文化與不同部門間的產業關聯程度。 本文依據《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2018)》將文化產業分為文化制造業和服務業兩部分,并分別對全國和各地區的文化產業數據進行前向關聯分析、后向關聯分析和各行業對文化產業的波及效應分析,以期能夠為國家文化產業效率的提高和結構的轉型提出有益的建議。
三、全國文化產業關聯分析
產業關聯度可分為前向和后向關聯度。 基于現有研究,本文采用直接消耗系數(aij)和完全消耗系數(bij)衡量產業的后向關聯效應,即進行拉動力分析,用直接分配系數(hij)和完全分配系數(wij)對產業的依賴性及前向關聯效應進行衡量,系數越大,產業間的關聯程度越強。 各指標的計算公式如下:
由bij構成完全消耗系數矩陣(B),用公式可表示為:
其中,Xj表示j 部門的總投入,xij表示j 部門產品在生產中對i 部門產品的直接消耗量,Xi表示i 部門總產出,I 為單位矩陣,W 為系數wij構成的完全分配系數矩陣。[1]
筆者測算了文化產業與其他產品部門間的直接分配系數(hij)和完全分配系數(wij),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由直接消耗系數結果可知,對文化產業直接拉動作用最大的是剔除文化產業后的制造業。2012 年和2017 年對文化制造業直接后向關聯最為緊密的前五個產業相對穩定。 文化服務業和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業的排位有所上升,表明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文化制造業對第三產業的直接拉動作用逐漸變大。 對于文化服務業而言,除其自身外,受文化服務業直接拉動作用最大的為剔除文化產業后的制造業,2012 年和2017 年的直接消耗系數分別為0.0933 和0.0802。 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業排名上升幅度最大,文化產業直接通過產業鏈帶動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業發展的作用大大增強。

表1 2012 年、2017 年文化產業對其他產品部門直接消耗系數表
同理,測算其他部門對文化產業的直接消耗系數及完全消耗系數可知,制造業對文化制造業的直接拉動作用最強,文化制造業在2012 年及2017 年的完全消耗系數均大于1。 除制造業和文化制造業外,對文化制造業拉動作用較強的產業為采礦業、水電熱燃業、交通運輸以及倉儲和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其完全消耗系數均大于0.1。 而文化服務業對其他部門的拉動作用則相對較小,除制造業外,其余部門的完全消耗系數均小于0.1,表明文化服務業對其他行業的后向關聯效應較小,其在產業鏈中對其他行業的拉動作用仍需增強。 此外,直接消耗系數與間接消耗系數對文化制造業拉動程度相對較高的產業部門基本相同,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對文化制造業依賴程度最高,僅次于文化制造業自身。 文化服務業對于其他行業的完全消耗系數均小于0.1,且對其依賴程度最大的為文化服務業本身。 這表明其余行業對文化服務業的依賴程度較小,文化服務業自身相對而言較為薄弱。
筆者測算了文化產業與其他產品部門間的直接分配系數和完全分配系數,并對文化產業的前、后向效應進行了對比分析,可以得出文化產業的后向關聯效應強于前向關聯效應的結論,即文化產業對上游產業的拉動作用強于下游產業,對其他產業有較強的輻射作用,但產品需求方面的潛力還有待深挖。 除文化產業本身外,對文化產業拉動作用最強的是剔除文化產業后的制造業,說明文化產業的發展主要依賴于其自身以及制造業的不斷推動,而文化產業的拉動作用則對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和科技服務業等第三產業部門而言相對更強。文化制造業同其他產業部門間的關聯效應較大,說明文化制造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而文化服務業前向和后向關聯系數均相對較小,文化產業在產業鏈中對其他部門的拉動作用有待增強。
同時,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間還存在波及效應產生的間接效應,可用影響力系數(KB(j))和感應度系數(KF(i))來衡量,基于此,本文分別對2012 及2017 年文化制造業和文化服務業對其余國民經濟部門的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力系數進行測度,結果如表2 所示。

表2 2012 年、2017 年各產業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
由表2 中的計算結果可得,2012 年文化制造業影響力系數為0.9537,小于社會平均影響力1,僅次于剔除文化產業后的制造業;感應度系數為0.6219,對其他部門的推動作用遠大于社會平均水平,且在產業部門中位列第一。 隨著文化制造業的逐漸發展,2017 年文化制造業的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均已大于1,分別為1.8104 和1.3426,文化制造業對其他產業部門的推動和拉動作用都較為顯著。由此可得,文化制造業推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對文化服務業而言,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相對較小,2012 年和2017 年均未超過1,但同2012年相比,2017 年的數值均有所提高。 這表明文化服務業對我國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還不強,但我國已在通過優化產業資源配置等政策支持促進文化服務業的發展,以期能夠充分發掘文化服務業的潛力從而推動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四、文化產業波及效應的地區比較分析
為更好地了解文化產業的地區發展狀況,本文選取北京、吉林、河北、湖南、上海、廣東、陜西、甘肅、四川、云南十個地區對其文化產業的波及效應進行進一步研究,以期能夠對我國產業的合理布局和轉型升級提出更加具有針對性的建議。
地區間的對比結果表明(如表3 所示),[2]文化產業的波及效應大致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動規律相同,經濟水平越高,文化產業越發達,對其他產業的拉動作用越強,呈現出 “高影響力、低感應度” 的特點。 然而,北京市和上海市為滿足地區發展需要,將多數制造業外移至周邊地區,其文化制造業在經濟結構中所占比重相對較低,對其他產業的拉動作用較其他發展水平相近的地區而言較弱。 而陜西省經濟發展水平雖相對薄弱,但由于其豐厚的歷史底蘊和特殊的經濟結構,陜西省文化產業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對其他部門的帶動作用相對更強。就文化服務業而言,各地區的文化服務業對其他產業的影響和波及作用均相對較弱,這說明各地區的文化服務業的潛力仍需進一步深挖,應加強對其產業結構的優化配置,并制定相應政策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充分發揮文化服務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表3 各地區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測算結果
五、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1. 文化產業是我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各產業之間的聯系緊密。 我國文化產業具有 “高影響力、低感應度” 的特點,即文化產業對其他產業的需求拉動作用較大,受其他產業的供給影響程度相對較小。 同時,文化制造業的影響力、感應度系數較大,文化服務業較小,但二者均隨時間發展表現出上升趨勢,說明我國文化產業在不斷以平穩有序的狀態穩步發展。
2.通過對各地區文化產業的波及效應進行測度和對比可得,其他國民經濟部門與文化產業間的關聯程度同時受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的影響,且同樣呈現出 “高影響力、低感應度” 的特點。
(二)政策建議
1.加速文化產業內部結構改革,提供有針對性的政策支持,放寬產業準入要求,促進文化服務業發展。
2.促進文化產業創新模式建設,優化 “文化+” 思維,發揮 “互聯網+” 優勢,加快文化產業信息化建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競爭力。
3.加大資源整合力度,完善產業融合發展機制,制定文化產品新業態標準體系,建立產業融合發展示范基地,實現文化產業鏈的不斷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