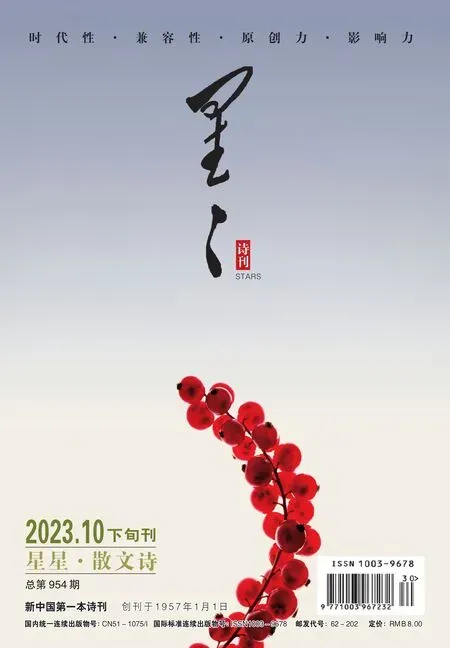燈臺是個虛詞(組章)
劉曉娟(內蒙古)
秋后事
有時耕牛犁,有時鐵牛犁。
懸于犁尖的萬頃良田,半種稻麥,半植桑麻。
沒有比莊稼更值得信任了,不同于遠方梅子林,不同于畫中餅。
大囤滿小囤流是秋后事。
興安小伙娶回心愛的興安姑娘,添丁進口,也是秋后事。
燈臺是個虛詞
把電線比做牧鞭,把架線人比做牧人,牧場離地三尺。
舉起鞭子。
一揮,黑暗落荒而逃;再揮,光明落地生根;揮到第三下,就把一個自帶微光的實詞,放牧成了虛詞。
虛詞之虛由書生演繹。夜讀中,為安放添香紅袖,需要一而再地,從童謠里賒借燈臺。
不用刻意安排事由,偷油吃那只小耗子,改行竹籃打水。
在烏蘭毛都草原,做個牧草人
不牧羊,不牧牛,也不牧馬。一心只做,牧草人。
翻雪山火山,跨無形溝壑,一棵接一棵,把草,往內心深處趕。
一坡。一嶺。一河灘……直到趕夠八千平方公里,直到趕出另外一個,烏蘭毛都。
風來躬身。雨來洗塵。向土地行叩拜禮,把肉體摁進水里,搓洗出清白骨骼……我遲遲未做的事,草都替我做了。
我知道我不是第一個得這片草原加持,虛構廟堂超度自己的人。
也不會是,最后一個。
勒勒車懷想
鄉村博物館里,參觀者圍在勒勒車前各抒己見。
有人認為樺木車身和樺皮拱棚,就是一棵移動的樹。
有人認為車輪吱扭扭轉過一圈,就是東胡、鮮卑、柔然、契丹、蒙古……這些游牧民族半部史書。
“勒勒車上的慢時光,適合愛情。”是唯一引起共鳴的結論。
——卻不適合迎接愛情結晶。傷者自揭傷疤。
從難產女人到醫院三十多公里草原路,需要一頭牛一輛車,用一整天時間,一步一個泥窩丈量。
需要搭上,母子,兩條命。
如果放在今天,就不至于……余音未落,我看見有人潛回義務講解員巴特爾體內。
我看見路網通達,牧人家代步的車子,隨便哪一輛,都能日行八百里。
從荷花到荷花燈
日薄西山。
在微山湖紅荷濕地,你想起土琵琶,動人的歌謠,鐵道線,飛車志士……
沒有人注意,被晚霞加冕,十三萬畝荷花已經悉數變成了荷花燈。每一盞荷花燈都配得上一個五體投地之禮——僻靜處,你反復躬身。
你反復躬身的另一個原因在于:生與義不可得兼。
你不敢保證,舍生,取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