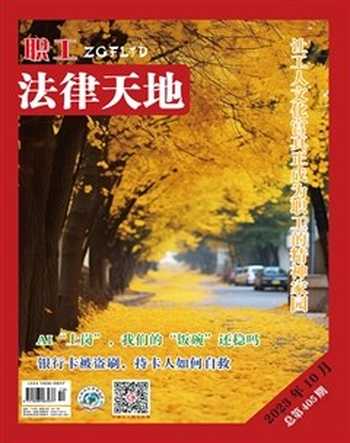微信聊天作證的打開方式
顏梅生
“老板已經在微信聊天中承認拖欠我工資,為什么法院卻不支持我索要欠薪的請求?”手持判決書的鐘女士滿臉疑惑地問筆者。其實,類似的疑問并非個別,而出現問題的關鍵,在于他們并不知道微信聊天作證的正確打開方式。
微信作證,應當明確雙方身份
【案例】何女士在個體戶王先生處上班時,因王先生經營不善,無法及時向何女士支付工資。何女士離職時,王先生也沒有出具欠薪條。2019年8月初,王先生經營狀況好轉,不好直接開口的何女士便通過微信向王先生發了一條短信:“請你在本月底之前,將20000元欠薪付給我。”王先生回復:“可以。”到期后,但王先生并未兌現,何女士遂以微信截屏為憑提起了訴訟。不料,王先生卻一口否認,何女士的微信聊天記錄中的對方并非是他。
【點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與之對應,何女士要想使自己的主張成立,無疑必須舉證證明“對方”就是王先生。經何女士申請,法官當庭通過王先生的微信號,確認即是王先生的手機號碼。王先生承認了欠薪的事實,并支付了何女士的欠薪。
微信作證,內容不得剪接刪改
【案例】因為謝先生一直欠薪不還且拒絕出具欠薪條,江先生于2019年7月1日向謝先生發了一條微信短信:“因父親遭遇車禍,急需錢醫治,請你在半個月內,將15000元欠薪付給我。”謝先生回復表示要求推遲3個月。江先生不同意,質問謝先生到底付不付?謝先生最后回復:“我不是已經?”其意思是該說的都說了。不料,江先生不小心刪去了中間的內容,只剩下最初問話和謝先生的最后回話。而當江先生以微信聊天記錄為憑提起訴訟時,謝先生卻一口咬定,其回復的意思是自己已經付清欠薪,江先生無權繼續索要。
【點評】微信信息作為視聽資料類的證據,因存在易剪接、刪改的特性,決定了對其效力的認定,必須考慮兩個方面:微信聊天記錄的位置是否出現變動,發出(收到)的短信是否仍在微信中;微信聊天記錄的內容是否完整,與其他證據是否矛盾,能否確保待證事實真實可靠。正因為本案所涉微信聊天記錄已被刪改,無法反映雙方就欠薪問題的全過程,自然也就無法證明謝先生承認欠薪的事實。
微信作證,應當符合證據要素
【案例】張女士于2019年11月5日向法院起訴稱:其曾在彭先生經營的超市上班,后因彭先生拖欠其9000元工資而離職,但彭先生一直沒有向其出具欠薪條。今年2月,其與彭先生微信聊天時,彭先生承認了欠薪的事實。但微信聊天記錄顯示,張女士雖然提到過欠薪一事,但彭先生并沒有回答其對于張女士是否欠薪、尚欠多少。而彭先生在答辯狀中表示,自己并沒有拖欠張女士的工資。
【點評】證據的采信必須符合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要求,用作證據的微信聊天記錄同樣不能例外,即必須做到來源符合法律規定,內容清晰明確且相對完整,能夠反映想要證明的事實,必須與待證事實之間存在某種聯系。正因為在張女士提供的微信聊天記錄中,彭先生并沒有認可欠薪、欠薪多少,意味著微信聊天記錄與欠薪的事實完全沒有關聯,加之彭先生事后明確否認,微信聊天記錄自然不能作為認定彭先生欠薪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