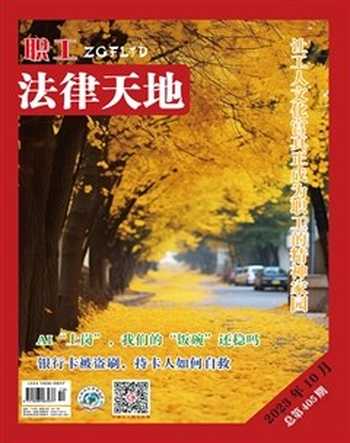雙重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構建探索
董思然
雙重股東代表訴訟指子公司權利被侵犯利益受損后,該公司及母公司股東怠于或者拒絕起訴時,母公司股東取得的對侵權人起訴的權利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的情形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連續一百八十日以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書面請求監事會或者不設監事會的有限責任公司的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監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的情形的,前述股東可以書面請求董事會或者不設董事會的有限責任公司的執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監事會、不設監事會的有限責任公司的監事,或者董事會、執行董事收到前款規定的股東書面請求后拒絕提起訴訟,或者自收到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訴訟,或者情況緊急、不立即提起訴訟將會使公司利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前款規定的股東有權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該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明確了提起股東代表訴訟的原告必須是利益直接受損的公司股東而排除了其他主體。
2022年《公司法》修訂草案二審稿一百八十八條在現行《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條基礎上增加一款作為第四款:“本條第一款、第二款所稱的董事會、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監事會、監事,包括全資子公司的董事會、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監事會、監事”,這一規定體現了我國構建雙重乃至多重股東訴訟代表制度的決心。該規定雖然擴大了雙重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被告范圍,但要求母公司必須對子公司“全資”控股,且未對原告資格、前置程序等作出詳細規定。
一、雙重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確立的意義
鼓勵投資、提升市場活力是公司法律制度的重要使命,在現代公司法制度的促進下,公司設立的門檻不斷降低,公司主體數量急劇增加并出現了復雜的公司鏈接結構。在簡單的公司形態下,股東訴權是平面化的,但在復雜的集團化公司形態下,平面化制度設計必然會帶來訴權的疏漏,對投資活力的負面影響不言而喻。雙重股東代表訴訟制度在確定股東雙重代表訴權的同時,也對權利的行使做出了諸多的限制,避免母公司股東對此權利濫用而對子公司的經營造成不必要的干擾,形成對社會資源的浪費。
二、雙重股東代表訴訟的適用前提
我國公司法并無母公司的概念,而是用《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條所規定的控股股東概念代替。母子公司關系可因控股關系形成,但母子公司還可由非股權控制比如公司之間簽訂的合同及人事安排等形成。普通股東代表訴訟股東提起訴權的前提是必須具有股東身份,雙重股東代表訴訟具有衍生性的特點,且股權控制導致利益受損的傳導性要大于非股權控制,因此非股權控制下母公司股東并不可以提起雙重股東代表訴訟,在此要求上與普通股東代表訴訟保持一致即可。
在確定母公司必須對子公司控股的前提下,還須進一步明確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控制力度是否要做出限制。控股可分全資控股、絕對控股和相對控股。《公司法》修訂草案二審稿第一百八十八條要求將母公司為全資控股作為母公司股東提起雙重股東代表訴訟的前提。限制在全資控股關系范圍內,有多種原因。一是考慮減少母公司股東濫用訴權從而干涉子公司正常經營的可能性,防止實踐中大量出現母公司股東動輒行權導致子公司或者母公司疲于應付的情形;二是在絕對控股、相對控股的情形下,子公司除母公司外必然存在其他股東,其他股東完全可以提起普通股東代表訴訟來維護子公司的利益從而消除母公司股東利益受損危境。但若采取此種規則也存在漏洞:母公司在子公司其他股東存在的情形下,其他股東不一定能夠對其形成牽制,如其他股東因持股期限和持股比例不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從而不具備普通股東代表訴訟的原告身份;或者母公司和子公司其他股東之間惡意串通,利益交換,子公司其他股東對子公司利益受損視若罔聞,則母公司股東的權益救濟便陷入無門之境。建議適當放開此項限制要求,詳細列舉母公司股東雙重代表訴權可以啟動的情形而取代“一刀切”的范圍限制。
三、雙重股東代表訴訟的原告資格
為了限制普通股東代表訴訟的權利濫用,我國《公司法》對不同的公司形式作出了不同要求,對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的持股期限和持股份額不做限制,起訴時具有股東身份即可;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提起代表訴訟必須滿足連續180日以上持股且持股份額必須達到單獨或合計1%以上的條件。若起訴時已不具備股東身份,則不可提起代表訴訟;即使子公司利益受損的事實發生于股東持股之前,此受損狀態持續至股東持股條件滿足后,股東依然可提起股東代表訴訟。
雙重股東代表訴訟是否可以沿用普通股東代表訴訟關于持股期限和持股比例的規定?此處可分公司形式進行探討。若母公司與子公司均為有限責任公司,則母公司作為有限責任公司提起普通股東代表訴訟并無持股時間和期限的限制,母公司股東提起雙重代表訴訟也不必要作出限制;若母公司與子公司均為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提起普通股東代表訴訟條件受限,母公司股東提起雙重代表訴訟受限也未嘗不可;若母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是有限責任公司,母公司提起普通股東代表訴訟不受限,母公司股東提起雙重股東代表訴訟受限是否合理?
為了限制母公司股東濫用訴權對子公司日常經營活動造成干擾,對母公司股東持股期限和持股比例作出限制在保障與普通派生訴訟制度鏈接的前提下更好地實現了防止濫訴的功能。若母公司是有限責任公司,子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提起普通股東代表訴訟會受到持股期限和持股比例的限制,但母公司股東提起股東代表訴訟卻不受限。在此情況下,就持股比例而言,母公司持股比例可輕易達到1%的比例,不提起或不能提起普通股東代表訴訟時才會觸發母公司股東雙重代表訴權,母公司股東持股比例不受限反而迎合了雙重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確立意義;但在持股期限上,母公司持股期限不滿足連續180日的要求,無法提起普通股東代表訴訟,但母公司股東持股期限卻滿足法律規定的要求,此時卻易造成濫訴的結果。若遇緊急情況要求母公司股東等待母公司持股期限屆滿后,母公司不行使普通股東代表訴權的情形下母公司股東再提起雙重股東代表訴訟,極易造成子公司利益損失進一步擴大的結果,從而致使雙重股東代表訴訟進入形同虛設的局面。
對于以上情形,可參考后續的前置程序進行制度設計,若非緊急情況,母公司股東在母公司持股期限達到法律規定的180日后母公司怠于行權方可提起雙重股東代表訴訟從而防止母公司股東訴權濫用;但若遇緊急情況,可設置“緊急豁免”直接賦予母公司股東提起雙重股東代表訴訟的權利,不再需要等待母公司的持股期限滿足法律規定的要求。綜上,母公司股東提起雙重股東代表訴訟在持股期限和持股比例上可與母公司提起普通股東代表訴訟制度保持一致,但當母公司為有限責任公司,子公司為股份有限公司時,在持股期限上應進行更加詳細的制度設計。
四、雙重股東代表訴訟的被告范圍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權益,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本條第一款規定的股東可以依照前兩款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他人的范圍既包括其他股東,也包括實際控制人、利害關系人等人員,只要對公司實施不法行為而公司怠于起訴的,都屬于被告的范圍。那么雙重股東代表訴訟是否也將上述侵犯子公司利益的主體均列入被告范圍還是將此范圍限縮?
以目前公司組織架構而言,發生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侵犯公司利益的概率較大,職業經理人制度在某些公司并未建立成熟。若股東雙重代表制度的被告范圍做此限縮,會導致母公司中小股東無法實現權益救濟的情形。雙重股東代表訴訟的被告范圍和普通股東代表訴訟保持一致,不僅將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納入其中,也將實際控制人、控股股東、利害關系人等主體納入其中方可周全。但需要注意的是,子公司有可能是基于商業判斷原則為公司長久利益考慮而怠于起訴,這種情況下允許母公司股東對公司外部人提起雙重股東代表訴訟又將子公司陷入被動境地,此處應設置子公司以具備商業判斷原則的正當理由阻斷母公司股東提起雙重股東代表訴訟的程序。
五、雙重股東代表訴訟的前置程序
在公司權益損害不緊急的情況下,股東必須提出書面交叉請求,在窮盡內部救濟、履行前置程序的基礎之上,方可提起普通股東代表訴訟。這種制度充分尊重公司的獨立人格,公司權益受損為公司內部事宜,理應由公司相關組織機構以公司的名義提起訴訟維護公司的權益。另外,股東往往并未實際參與公司經營,對公司日常經營活動及財務狀況不甚了解,若無此種前置程序的設置股東直接提起訴訟在舉證及訴訟策略上可能對公司不利,也容易造成訴訟資源的浪費。雙重股東代表訴訟也應設置前置程序避免濫訴造成的不利結果。雙重股東代表訴訟要設置的前置程序比普通股東代表訴訟要復雜,不僅要尊重子公司獨立的法人資格,也要為母公司提起普通股東代表訴訟留出空間,當母子公司均怠于起訴時母公司股東再行提起訴訟。
在請求順序上有四種選擇:先請求子公司再請求母公司;先請求母公司再請求子公司;同時向母子公司提出請求;向子公司提出請求,同時僅向母公司進行書面通知。若分別請求母公司、子公司,等待時間較長,子公司利益有進一步損失的風險。有學者認為,向子公司提出請求,同時僅向母公司發出通知即可,這是因為子公司怠于起訴往往是由于母公司的授權而導致的,向母公司提出請求多此一舉,毫無用處。但雙重股東代表訴訟不可繞過普通股東代表訴訟,否則后者的設置便失去意義,也剝奪了母公司、子公司其他股東在急于追究侵害人責任時的訴權。第三種請求順序相對更為妥當,同時向母公司、子公司提出請求,適用同一等待期同時計算,若母公司在等待期滿前或當時表示將提起普通股東代表訴訟,則等待期滿時母公司即可行權。此時,母公司股東無法提起雙重股東代表訴訟;反之,母公司股東可通過母公司的態度直接判斷母公司是否放棄行使普通股東代表訴權,等待期滿母公司股東可提起雙重股東代表訴訟。另外,我國《公司法》允許普通股東代表訴訟制度在緊急情況下前置程序可豁免。考慮到母公司掌控子公司情況下利益損失的急迫性,雙重股東代表訴訟也應做此制度設計為母公司股東提供更強有力的保障。
(作者單位:山東司法警官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