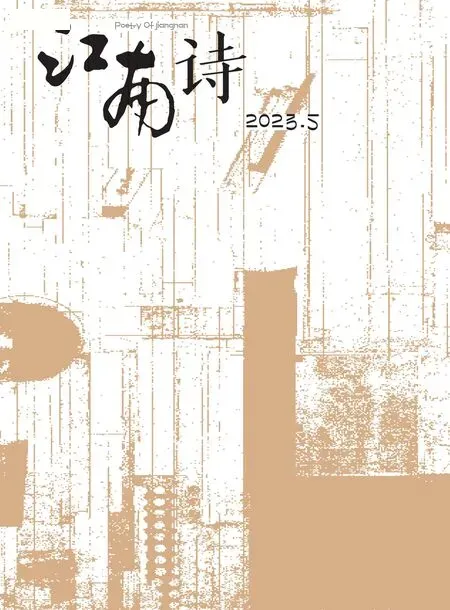蟋蟀之歌(三首)
田雪封
立 夏
1
又刮風了,帶來了雨,
整個河南都籠罩在陰郁中。
我的房間,一個建筑工放飛的紫色氣球,
它的腦袋隨夜風搖動,就要被黎明摘走。
其間的人,仍然在沉睡,如躺在搖籃里。
窗前的一株歲月梧桐,被狂風所彈奏,
為痛苦的回憶伴舞的大長腿,
冠狀枝葉,展現出音樂那持續轉幻的形狀。
2
下雨了,又下雨了,敲打著窗子。
黑夜里,我看見一只只雨滴做成的小手;
在無數男人有力大手中流轉,
仰天躺下,或者翻過身子,
趴下,像匹白馬,扭回頭,
金色的長巤遮住半邊臉,
看腫脹的太陽,朝它的肉體,
發泄怒火;
冬天的樹,一個倒栽蔥的女人,
兩條腿在半空踢蹬,她的頭
吸收著無邊的泥土,長發在黑暗底部飄動。
3
從夏天到夏天,你一直在試圖收攏
指縫間流失的沙子,試圖
重新把它們握在手掌中,
啊,那份松軟、光滑、沁涼和顆粒微小的喜悅。
就像一棵白楊樹的三個枝杈,
你同時生活在過去、現在和未來。
4
又是夜晚,雨聲大作。
誰在外面敲打窗玻璃?
而窗子內卻久久沒有回應。
誰用右手食指指關節敲打墻壁,
桌面,床頭柜?而另一面沒有回應。
誰在從內向外敲擊窗玻璃?
卻遲遲不見有誰推開一道縫,
臉像月亮,躬身邀請……
雪世界
只剩下樹,枝條壓低,
一張拉開的彎弓。
只剩下記憶、煙霧、路程
和時間遮蔽的身體。
只剩下邁進誘惑的凌亂足跡,
上一個季節的落葉,覆蓋的空間。
只剩下風吹草動,
被一陣異響吸引的貓,
寫下的一首梅花詩。
只剩下雨刮器豎立,
野兔支棱著長耳朵,
在靜靜聆聽黑夜。
只剩下眼珠骨碌碌轉動。
只剩下腳下被白顏色墊高,
松軟,富麗,一張嘴唇
剛好夠到另一張嘴唇。
只剩下在積雪的毛毯下的翻滾。
蟋蟀之歌
1
一個即使在白襯衫、紅領結、藍西褲、
黑皮鞋的雄壯的合唱隊中
也能將自己的膽怯
和不足的底氣暴露無遺的人——
一個踏不準節奏,
總是與時代不合拍的人,
五音不全,顫抖,偷了東西一樣慌張,
發聲不是太提前,
就是太錯后,就像收割后的麥田里
孤零零生長的一根麥苗。
2
一座農家小院,
一支由眾多卻看不見的
星星點點生命所唱的歌,
草窠間,瓦礫中,落葉下,空氣里,
盡管每一個聲音都是那么細小、
微弱,可他們匯成了龐大的軍團,
鋪天蓋地,
多么讓人心驚:這支蟋蟀之歌,
誕生于地球上的第一個黎明,
與時間的洪流一樣兇險,
沖垮一道道人世堤壩,從來不曾被打斷過。
3
我那逐一
從虛無縹緲之處
凝聚而成的肉身
落在大地織工
蟋蟀
編織的細密
又富有彈性的巨網上。
世界晃悠了幾晃,復歸于平靜。
4
無數個黑夜,
迎來了唯一的早晨,
而萬物尚未醒來。
隔著兩條腿的籬巴墻,
只有那位衛兵,
仍然保持著忠誠,
挺直腰身,朝你致意。
5
二十二點半,
七樓窗外,一聲蟬鳴。
干燥,單調,無起伏,
就像伸向天空的一根木棍,
它要敲落最高枝頭的梨。
它要緩緩展開一面白旗,
我踴躍的想象,在下面聚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