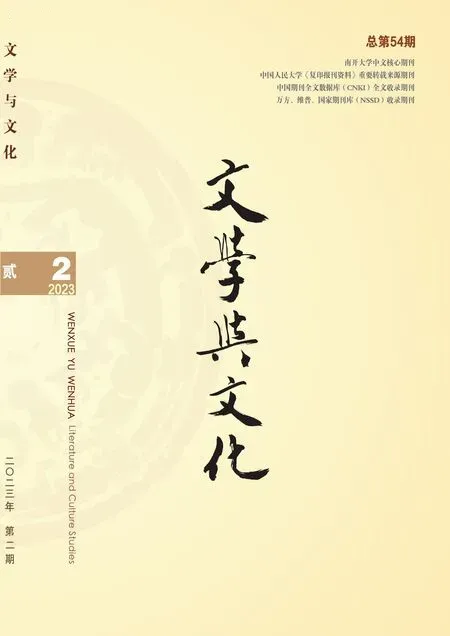當代都市生活想象與智慧山空間文化
高迎進 張清瑩
內容提要:本文以天津智慧山及其“那山街區”轉型為分析對象,試圖窺見國內“新技術產業園區”這一新興城市空間的內部運行機制及文化生產結構。可以看到的是,對于“新知識階層”與“消費者”無法調和的焦慮導致了智慧山以“平滑美學”為主要特征的景觀化轉型,在這種轉型中,為了“配套”而進行的規劃以反客為主的方式取代使用空間的人擁有了主體性。作為智慧山的轉型結果,“山丘廣場”以隱喻的方式向我們訴說著被放逐了主體身份的“白領階層”的異化生存狀態。
一 智慧山及其轉型
智慧山文化產業示范園(簡稱智慧山)于2012年底創立,坐落在天津市南開區遠離核心商業區的華苑住宅群,隸屬于濱海新區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以南開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為基礎的科技文化創意產業園,如今已經走過了十年時間。
智慧山的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2012年之前的準備期、2012年至2016年的全面建設期和2017年之后的商業提速期。這樣的分期不僅體現在硬件設施建設、整體設計方面,更是植根于天津乃至中國整體發展的社會歷史語境中。智慧山開始準備籌建的時間點,也是美國制造全球通貨膨脹背景下,中國著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以求經濟軟著陸的時間點。2009年,天津市撤銷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設立天津市濱海新區作為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重要組成部分。濱海新區是中國科技驅動類型“園區經濟”的縮影,智慧山的社區轉型更是園區經濟多途徑“二次創業”的有效實踐。
需要指出的是,智慧山的自我命名在十年中經歷了從“科技園”到“那山街區”的轉變。這種轉變是基于現實情況的妥協,是成功的商業轉型,也構成了智慧山的兩種看似融洽卻無法兼顧的愿景:智慧山從致力于吸引創新人才的“共同富裕”式道路——在這種道路中,智慧山試圖希望借助政策優勢,投資“80后”創業者來復制中國互聯網初代企業的超預期收益——走向了“致力于為更廣大的,隨著互聯網科技崛起的數字中產階級群體創造消費場景,吸引消費行為”的“賣家”道路。
這種轉變得以形成的基礎,表現為一種調和了創業主體與消費主體的廣告話語。創園初期,智慧山旨在服務具有創新創業潛力的“新知識階層”,同時創造不同種類的文化消費空間作為配套設施——這個“新知識階層”在智慧山內部刊物《智慧報》中被描述為“由新知識階層所構成的新型企業家”、“中國第六代財富創造的主體”,是“中國經濟由‘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時代轉型中……最活躍的力量。”①來源網址:http://www.visionhill.cn/OwnerViewdoc.php?cid=1&uid=318。而在2022年智慧山宣傳視頻中,“新知識階層”被涵蓋在一個新的概念中:
智慧山通過……吸附白海青新(白領、海歸、青年、新階層)夜間消費群體,形成開放、活躍、創意、科技的特色夜間經濟消費氛圍。
對空間使用目標人群從“新知識階層”到“白海青新”的修改,看起來像是一種“穩定中的微調”。隨著中國互聯網新動能崛起的互聯網企業創立者(也就是“創富主體”)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我們想象中“有理想、有追求”的,“買手沖咖啡的高品質生活者”,但正如我們在第二部分中所詳細闡述的那樣,對于“新知識階層”與“消費者”的調和基于某種科技樂觀主義,這種樂觀主義的無法落地使得“既要又要”的智慧山落入了一種始終無法實現自身的焦慮之中。而最終,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以2016年星巴克開業為起點,以2017年5月那山廣場建成為重要標志,智慧山從“共同富裕”式道路轉向了“賣家”道路,從深耕創新走向了提振消費。
智慧山文化生產的根本動力來自于這種無法實現自身的焦慮。在下面的章節中,我們嘗試梳理智慧山的初創愿景與轉型細節,并試圖挖掘這樣一個新興城市空間為何無法實現自身,又如何注定被消費符號所改寫,成為韓炳哲意義上“只要求點贊,不允許反思”的“平滑空間”。
二 硅谷愿景與技術樂觀主義
如果想要探討作為新技術產業園的智慧山,我們需要回到這一形式的發源地——也就是硅谷的故事中來②作為補充的是,智慧山內部刊物《智慧報》創刊期刊登了一篇以“運營城市未來,打造天津硅谷”為題的企業創始人專訪,并在首頁印有這樣一段話:“從美國硅谷到中國硅谷:關于知識創造財富的奇跡,美國的硅谷,或可成為全世界最好的榜樣。對天津而言,濱海高新華苑核心區的高速發展,正復制著與美國硅谷極其相似的時代夢想。同樣是依托世界級的城市群,同樣是聚集著世界500強及數千家創新企業,同樣是知名高校環繞,同樣是形成了數萬知識精英的行業規模及數十個高新行業的完整產業鏈。如果說中國的硅谷在中關村,那么,濱海高新華苑核心區則無疑是天津的硅谷,天津新知識階層最密集的地方。”(來源網址:http://www.visionhill.cn/OwnerViewdoc.php?cid=1&uid=318)。在這一部分中,我們將嘗試通過溯源硅谷來說明這樣一個問題:轉型之前的智慧山何以注定是“無法成為它自身”的城市空間。智慧山對兩種目標群體概念“創業主體”與“消費主體”的拼合并非異想天開,而是可以追溯自硅谷本身特質的雙重性。這種拼合的無法實現,其背后是“生長的硅谷”與“建造的硅谷”,或者說“不可復制的硅谷”與“可復制的硅谷”之間的對立。需要承認的是,“新技術產業園”這樣一種城市形態從一開始就帶有某種“復制”的動機與目標,但維持硅谷內部張力的調和機制本身恰恰是不可復制的。這種不可調和所帶來的焦慮與搖擺是轉型之前的智慧山始終無法回避的問題,因此其“那山街區”轉型正是對于這種焦慮的回應。
(一)硅谷反對硅谷:硅谷的內部張力
硅谷是美國高新技術的搖籃,這個美國加利福尼亞北部的產業區以研究和生產以硅為基礎的半導體芯片得名。英特爾、蘋果公司、谷歌、臉書、雅虎……硅谷的互聯網公司改變并持續塑造著這個世界。與此同時,“硅谷”的名字也已成為世界各國高科技聚集區的代名詞。當我們將硅谷等同于“創新高科技產品/超高利潤互聯網公司”時,硅谷背后的具體性和不可復制性卻因此被忽視,“硅谷”仿佛是一個可隨處發芽的科技種子,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能結出相似的果實。我們往往習慣將硅谷視為“可復制的成果”而非“自然生長的結果”,正如柄谷行人在《作為隱喻的建筑》中所說,建筑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表現形式即“意味著通過將一切‘生成’看作是‘制造’從而與‘生成’構成對抗的姿態”①[日]柄谷行人:《作為隱喻的建筑》,應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1頁。。
但硅谷并不是易于復制的對象。有趣的是,在這個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所指認的擬像社會中,硅谷反而擁有了獨一無二的“原作”地位——世界各地的“硅谷”都只是作為贗品的硅谷而已,幾乎在任何程度上都沒有與之比肩的能力。回溯硅谷的歷史時我們會發現,硅谷在其誕生時就存在著兩股相對抗的力量。一方面,來自20世紀60年代全球的嬉皮士運動帶來了反對權威、反對主流的民粹主義聲音,大量的工程師持有無政府主義立場并認為個人計算機的出現打破了“大公司”也即全球化資本的壟斷局面,終止了計算機被用作權力壓迫工具的狀況。這種觀念以帕洛阿爾托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 of Palo Alto)、家釀計算機俱樂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及后期計算機展覽會(the computer fair)的創建為重要標志,以信息的自由共享為核心價值觀;另一方面,以比爾蓋茨(Bill Gates)反對徹底共享(開源精神),堅持發明付費為代表,硅谷催生出了一批擁有巨額財富的億萬富翁,他們代表著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商業發展模式,這里充滿了背叛、惡意競爭和幾乎赤裸的叢林法則,而硅谷的崛起也直接助力了美國在后冷戰時期所建立的全球霸主地位。因此,當我們使用“硅谷”這個概念時,我們需要首先關注其中所蘊含的雙重屬性。
(二)技術樂觀主義與霸權政治
硅谷的雙重性被復雜的社會歷史語境所包裹,這種語境所攜帶的“生成性”使得后繼者無論如何復制硅谷的模式都似乎不得要領。究其核心,是因為硅谷的調和機制——基于啟蒙理想的技術樂觀主義與美國在全球的技術壟斷、軍事掌控與金融霸權是全球資本主義分工體系的一體兩面。換句話說,只有穩定地站在全球資本主義分工體系的剝削端,美國才有可能保有一個蓬勃發展的硅谷。作為佐證的是,硅谷背靠斯坦福大學,其早期投資很大程度上來自軍方與政府。硅谷之父弗雷德·特曼(Frederick Emmons Terman)與軍方有密切交往并獲得了豐厚的經費贊助,20 世紀50年代之后的仙童半導體公司,因為市場需求量有限,早期產品主要服務于美國國防部。此后,國防部一直維持對硅谷的巨額訂貨,直到21世紀初期,國防部的訂單仍占硅谷總訂單的40%。
與之相對應的是,當美國霸權受到威脅時,硅谷的危機一定首當其沖。當下發生在硅谷的事情不僅證明了在云數據時代硅谷及全球新技術產業園的注定衰落,更印證了我們的觀點:隨著全球保守主義的崛起,硅谷得以健康發展的土壤也在逐漸流失。隨著時任世界首富馬斯克在2022年10月底成功收購推特,這個硅谷第一個宣布可以永久居家辦公的公司僅用郵件通知就裁掉了推特總部的一半員工。②信息來源:https://mp.weixin.qq.com/s/mi0I6gqbIqBe7rEkFCD3mg。直至今天,硅谷的裁員浪潮仍然在繼續,2023年3月的硅谷銀行危機也至今余波未平。
需要說明的是,啟蒙理想下的技術樂觀主義與美國霸權的綁定與其說是一種啟蒙傳統的新面貌,倒不如說是一次“幽靈重現”。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在《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中曾經指出:“在8和9世紀,理性和自由被視為等價之物。弗洛伊德的個體觀念和馬克思的社會學說,都曾因假設自由和理性的相符而得到加強。”①[美]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周曉虹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導言”第9頁。但這種啟蒙理想在現代社會被工具理性所異化。科技的樂觀主義源自理性和自由的等價,那是一種對于“我們可以通過理性獲得自由”的信仰。但事實上,理性被工具理性所窄化從而走上了非理性的道路,最終導致了20世紀前半葉的種種災難與啟蒙理性自身的破產。
(三)智慧山作為園區經濟的縮影
正如我們在上一部分中所說的那樣,美國在全球的技術壟斷、軍事掌控與金融霸權是硅谷之所以為硅谷的基石。也就是說,在這種意義上,只要中國依舊處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被剝削狀態,如智慧山一樣的眾多“中國硅谷”就永遠不可能像“原生”硅谷一樣調和其中的雙重性。
“中國硅谷”的典型是走出了聯想、京東和百度的北京中關村與孕育了華為和騰訊的深圳。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承認,智慧山所在的濱海新區并不屬于此列。但恰恰因為如此,智慧山代表了中國在數量上占大多數的“沒那么發達”的產業園區的真實樣貌。根據2018年版《中國開發區審核公告目錄》,我國共有2782個開發區。在國家經濟戰略語境下,產業園區“既是區域經濟發展、產業調整升級的空間承載形式,又是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標志”②引自賽迪產業報告,來源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h6FjJIhSlW-1zSGemGc8BQ。,這些開發區在改革開放的40年間,在不同階段以多種方式完成了為經濟發展賦能的重要作用③賽迪產業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園區經濟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土地、政策與人口紅利驅動階段、要素匹配與服務驅動階段,投資、技術、人才、創新與模式驅動階段與“數據化、信息化、知識化、智能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階段。。從90年代開始,國家戰略充分發揮了硅谷“可復制科技種子”的一面,以“黑貓白貓”的結果決定論邏輯,試圖通過建設科技橋頭堡來擺脫中國制造/世界工廠路線——濱海新區正是這一階段園區經濟的產物。而在智慧山謀求發展與轉型的這十年,大多數“沒能拔得頭籌”的產業園區也正在以“二次創業”為口號,謀求新的發展路徑。④“二次創業”口號出現在包括濱海新區在內的眾多產業園區新聞中,如《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九年奮飛筑新城 二次創業再起航》、重慶“兩江新區全面開啟‘二次創業’”、江西“積極推動園區‘二次創業’”(來源均為人民網)等。智慧山的轉型,是園區經濟“二次創業”浪潮的縮影。
三 “白領”與智慧山的社區景觀轉型
在這一部分中,我們試圖闡明,當“新知識階層”和“白海青新”之間注定無法調和時,智慧山進行了自覺的轉向——“那山街區”是智慧山對于其社區屬性的商業行動,是對于話語整合實體的自覺。智慧山通過一系列的活動,使得不可量化的“社區”可以成為可量化的“資源”,完成了從“硅谷科技園”到“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園區”的社區景觀化轉型。這種轉向有賴于在智慧山工作的上班族所形成的“社區空間”,但同時放逐了其主體性的地位,抹除了其與普通都市消費者之間的差別。在這里,科層制體系里被壓抑的、真實的“個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抽象的文化身份,人們不再是“從事某種具體勞動的人”,而是“消費文化產品的都市潮流青年”,智慧山空間從被動的日常生活載體變成了文化身份的召喚者。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景觀”(spectacle)是德波意義上的否定性的消費景觀。也就是說,權力對于主體的控制與剝削不以福柯借用邊沁環形監獄概念所描述的“隨時可能被觀看”的形式出現,恰恰相反,剝削來自主體的“觀看”行為本身。通過觀看,主體被異化為“觀看的目光/注意力/流量”,認同于觀看的對象并通過對象建構自身的欲望。
(一)白領
項飆在《全球獵身》中曾經這樣描述在硅谷工作的印度互聯網公司工作者:“與我們通常設想的大大相反,軟件開發和軟件服務是高度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在編程、測試和檢錯(排除程序設計中的錯誤)的階段尤其如此。大多數被獵身到海外的印度IT工人正從事這些沉悶乏味、單調且收入偏低的所謂‘驢活’。”①項飆:《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王迪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頁。飛速擴張中的硅谷在全球招募“IT工人”以轉移低技術含量附屬工作的行為,正如互聯網加速發展時期,在全國招募“互聯網民工”以實現低技術工作“外包”的國內互聯網企業。在智慧山工作的人,不是野心勃勃的、可以開辟新賽道完成“顛覆性創新”的創業者,而正是項飆意義上的“IT工人”,是“坐在辦公室中的流水線工人”,他們承擔著科技公司總部分擔出去的一部分職能,并換取一份體面的薪水。
這種狀況是由智慧山的公司集群性質所決定的。智慧山的經營狀況良好,雖然對于旗下入駐企業有嚴格的要求與決定性的話語權,但一直不缺候補入駐與想要參觀學習的企業主。2022年,完美世界、搜房、北京中外建建筑設計有限公司、360等多家智慧山園區企業營業額過億。
與營業額形成對比的是,智慧山園區內企業呈現出鮮明的“天津分公司”特征。園區第一批入住的企業大概可以分為三類:互聯網創業公司、以高校創業為主體的高精尖制造業、配套金融企業。而在這當中,只有天津象形科技有限公司(經營狀態:吊銷)是在天津成立的互聯網創業公司。十年后的今天,智慧山產業集群已經形成穩定的規模,但“天津分公司”的性質并未發生改變。
這樣的企業入駐選擇也印證了“創業主體”與“消費主體”之間的不可調和:智慧山似乎想要借用資本市場的投資行為來為互聯網企業助力,從而達成投資方與企業雙贏的局面,但是在風險評估問題上,這種投資又顯得過于保守——投資成熟企業在天津建立分公司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保證了利益最大化,同時在結果上拒絕了“孵化”行為。也就是說,這種“天津分公司”的布局在投資行為上講是理性的,但并不利于智慧山成為企業創新的發源地。
在智慧山工作生活的大多數人,就像米爾斯所描述的“白領階層”那樣,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體系中依附于科層制的體系,為更大的體系打工,在獲得較高社會地位和承認度的同時,并沒有獲得同舊時代企業主那樣豐厚的報酬,他們沒有安全感(家園)、沒有身份(消費趣味),對權力極端服從,因此缺乏政治立場甚至干脆對政治缺乏興趣。他們“除了那個塑造了他又企圖將他控制在其異化目標之下的大眾社會外……沒有任何文化的基礎可以依托。……這種孤立無援的處境為印刷品、電影、廣播和電視等流行文化提供了絕好的虛構素材。”②[美]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第8頁。正如我們在下一部分將要詳細梳理的那樣,白領階層對于自由的逃避與對于時尚流行文化的追求助推了智慧山的社區化轉型,并最終導致了其自身主體性的喪失。
(二)“那山街區”轉型
智慧山在轉型過程中使用了大量的“社區”元素,不再強調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空間定位。2020年智慧山獲批“濱海新區智慧山文化創意園”,并從這一年開始舉辦各式各樣的青年文化“市集”。在這樣的語境下,一家飯店如果生意紅火,就會被稱為“贏得了社區伙伴的民心”①來源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5jCDP0wVCY2jHsoqHC1ofA。。智慧山的日常空間使用主體,似乎不再是那些曾經被寄予巨大期望的白領階層,而是一群創造文化產品并以此為生的潮流人士(或者說潮流文化的創造者),他們熱情好客,期待著所有客人的到來(并進行消費)。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更加能夠理解智慧山在宣傳視頻中所提到的“城市文化會客廳”②引用自企業內部資料。愿景。智慧山給人一種“深藏不露”的感覺——雖然在表面上是普通且無聊的寫字樓,但在各個角落處充滿了令人驚喜的視覺刺激——智慧山利用了由白領階層形成的社區概念,但放逐了社區中最主要的白領階層的“會客廳主人”位置,不由分說打開了他們會客廳的門。
通過對于“社區”概念的挪用,智慧山的主體從白領階層轉換為本應處于“配套設施”位置的小商戶,會客廳主人的目標從“出賣勞動力”轉換為“賣出文化產品”。在這個過程中,智慧山幾乎自然而然地構建了某種“家園”的形象,一種有關消費文化的、大眾參與其中的想象的共同體,人們在這里以共同的消費品味為紐帶,獲得了歸屬感。這種形象經由互聯網媒體(智慧山及其商家在大眾點評、小紅書等app上投入了大量的廣告)的放大構成了有效的、對于都市消費者的召喚:“來吧,這里就像自己家一樣。”
(三)智慧山的頂層設計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智慧山并不遵循完全的商業資本邏輯,而是具有類似“城市中的鄉土社會”的形態。當然,正如上文所說,我們所討論的居民并非企業中出賣勞動力的白領階層,而是作為空間實際主人的小商戶。如果我們把后者比作“智慧山村”的村民,那么智慧山的公司法人代表及頂層行政部門則是這里的“城市鄉紳”。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曾經指出,在表面的人的理性之下,城市由資本驅動,以資本增殖為最終/唯一目的,因此良好的社區如果沒有干預和控制就會由于資本的無限擴張產生“自我毀滅”的傾向③[美]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金衡山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本來繁榮、充滿多樣性的空間里,最賺錢的店鋪不斷擴張并形成壟斷,吞并那些利潤低卻構成了社區多樣性的店鋪,于是多樣性被打破,空間逐漸變得單一。尤其是像銀行/保險這些不會對社區產生實際價值的公司,往往會出于保守的目的選擇在這種已經發展好的地方立足并擴張,最終造成街區空間的衰敗。
與此相對的是,智慧山解決了資本盲目擴張的問題,保持了權力頂層的理性,保證了這里商戶集群的多樣性,不會由于資本理性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糟糕局面。與其說智慧山是商業集群,倒不如說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想象的“小企業主共同體”。智慧山對于入駐商家有嚴格的篩選標準(或者說,必須遵守某種“村規”)——經營者要“有追求,不是純粹營商賺錢;品牌有調性、產品品質有保障、出餐健康口味好;商鋪空間有水吧休息區、空間裝修風格舒適有設計感;善于或積極營銷品牌……”④引用自企業內部資料。在這樣的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中,每一家店、每一個店主都是“有故事”的——比如“半半咖啡店”的主人林修毅是一個話很少但是技術精湛的“手藝人”,文具店“KOLOFO 開樂福”則是2008年來中國的伊朗設計師“阿鯉叔叔”的夢想店鋪等。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智慧山甚至參與了一些非常具體的事情——“餐廳內有好大一束花”的“最美螺獅粉店”“三十三吉”,甚至店名都是智慧山決策層親自確定的。
四 平滑美學與文化身份召喚
(一)平滑美學
韓柄哲在《美的救贖》開篇向我們描述了一種統治當下流行文化的“平滑美學”:“平滑不會造成什么傷害,也不會帶來任何阻力。它要求的是‘點贊’。平滑之物消除了自己的對立面。一切否定性(Negativitat)都被清除。”①[德]韓炳哲著:《美的救贖》,關玉紅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頁。平滑是一種人造的完美狀態,平滑的商品盡可能少地體現出人為加工的痕跡(就如同韓炳哲作為例子提出的蘋果手機和杰夫·昆斯②美國當代藝術家,以“氣球狗”(Balloon Dog)等作品聞名。韓炳哲認為,杰夫·昆斯的作品“無需評判、解讀、注釋、自省和思考,并且刻意保持天真、平庸、絕對放松、卸下武裝、忘記憂愁的狀態,沒有任何深度、奧妙和內涵”([德]韓炳哲:《美的救贖》,第3頁)。杰夫·昆斯在2019年創下在世藝術家的成交價新紀錄。[Jeff Koons]作品那樣),人造品因為平滑獲得了某種自然的特性,在平滑美學所支配的商品社會里,人與技術的關系徹底代替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而在這種關系中(和人一直在試圖反抗自然、改造自然相比),商品要求人的順從和不反抗,要求人們只發出一聲“哇哦”的贊嘆就足夠了,因為這里是“一個供人享樂,擁有絕對積極性的世界,是一個沒有痛苦、不會受傷、無罪的世界”③[德]韓炳哲著:《美的救贖》,第7頁。。
在這一節中,我們試圖探討智慧山何以是“平滑美學”的實踐,其如何以消費行為為核心構建起了一個閉合的符號結構。具體而言,對于智慧山來說,一切有意義的行為都是收費的,其志在消除的“否定性”,就是那些“不買不賣”,甚至還會在路過時說一句“這有什么好逛”的人。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不買(咖啡、音樂現場和劇場門票)、不賣④需要說明的是,盡管白領階層在這里出賣自己的勞動時間,但只要其沒有將獲取的勞動報酬用于消費,就仍然是的結構剩余。,那么他/她在這個街區里就會成為意義結構的“剩余”。作為例證的是,每當智慧山舉辦市集活動,一定會圈出明確的圍墻并在入口處進行收費(這種行為保證了不會有路人指出市集本身“皇帝的新衣”的特征);而我們在智慧山的宣傳物料中,也幾乎看不到以“不買不賣”姿態出現的“閑逛者”。
需要指出的是,收門票的行為也意味著空間公共性的消失。場所的公共性并非與商業活動相抵觸,相反,正如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公共領域的結構性轉型》中所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直接產生自咖啡廳這樣的消費場景當中;切爾·克勞斯·奈特(Cher Krause Knight)在《公共藝術:理論、實踐與民粹主義》(Public Art:Theory,Practice and Populism)中也將商業廣場視為公共藝術發生的場所之一,但智慧山收取門票的行為直接切斷了公共性賴以生存的可及性(avail?able)。同時,咖啡、啤酒市集在事實上壓縮了咖啡廳和小酒館的空間,人們不再可能在這樣的消費空間中坐下彼此交談,而只能以隔絕的方式分別觀看作為景觀的“中產階級食物博覽會”。
(二)時尚作為盔甲
在智慧山,所有的商鋪店面都是以視覺景觀的方式呈現出來的“美好生活樣板”(比如之前提到的最美螺螄粉店,再比如被稱為“智慧山氛圍感之王”的咖啡店“105 CAFé&KITCHEN”)。飲食店面穿上文化的外衣,劇場和音樂現場以文化工業最典型的形式,空間內所有的符號都在使盡渾身解數喚起人們的消費沖動。
在智慧山,一切都是“潮流”的、“時尚”的。喬納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在《知覺的懸置》中指出,時尚“是一個保護性的能指之盾,一個反射性的盔甲,被仔細地安排來掩蓋社會的和心靈的柔軟之處”①[美]喬納森·克拉里:《知覺的懸置》,沈語冰、賀玉高譯,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7年,第93~94頁。。當主體被異化為注意力,主體無法被整合為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笛卡爾式的觀看主體,年輕人唯有披上時尚的外衣才得以確立自身——“我是愛喝咖啡的,愛看脫口秀的……”基于文化工業的休閑愛好成為整合自身的唯一方式,除此之外,“我無法回答我是誰”。
導演李一凡在2019年的電影《殺馬特我愛你》中描繪了“殺馬特”們在東莞石排公園聚會的場景,他們聚在一起夸贊彼此的造型,討論做頭發和保養的技巧,交朋友或者談戀愛。而在平時的生活場景中,這種打扮給人一種“強硬不好惹”的感覺,“這樣子才不至于我很脆弱、很容易被人欺負,因為那種感覺太孤獨了”。這與米爾斯對于白領階層對于流行文化的渴望幾乎是完全一致的。換句話說,在智慧山消費文化產品并借以界定自身的消費者,與“殺馬特”們擁有相似的心理結構。
不管在哪一種場景中,人們都是通過消費行為(而非自身在勞動中所處的位置)來界定自身。智慧山借由消費景觀承擔了其園區內的“意識形態建構”或者說“認同文化編織”的作用,使得這里的人們得以形成穩定感與認同感,這是對于白領階層主體身份的征召,但同時也是對于白領階層真實創傷的壓抑。一方面,智慧山似乎順應了“年輕人的需求”,呈現了如音樂現場、脫口秀俱樂部、咖啡店、生活方式用品店等諸多城市青年文化符號,給了年輕人“擺脫壓抑,在上班之余盡情狂歡、盡情滿足自己”的抵抗路徑;但另一方面,這種消費只不過提供了一種抵抗的幻象,或者說一種抵抗的規定渠道——你只能通過這種方式去抵抗,而不能通過其他的更加現實激進的方式去抵抗。
(三)市集和山丘廣場的竹子
2023年1月,智慧山第一場市集活動以“咖啡年貨節”為主題——想要進入年貨節需要購買門票,但天津并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年貨節”需要顧客交費才能進入。②年貨節活動信息來源:https://mp.weixin.qq.com/s/rYB8KB8IYhiOXIYjDVEqBw。“交錢”這個行為首先意味著獲取視覺景觀的主動性——人們需要付出金錢才能擁有購買的權力。在年貨節里,人們不是為了“買實惠”,而是“看新奇”,咖啡及周邊產品仿佛是擺放在博物館里的藝術陳列,“看商品”行為本身成為像度假一樣的休閑體驗,人們甚至不需要購買商品本身,只需要購買“買商品的體驗”就可以了。在這個過程中,商品不再需要展現誘惑的姿態,它被膜拜,被供上神壇。
需要指出的是,和東南沿海地區可以免費進入,甚至還有諸多促銷方式的咖啡市集(如上海白玉蘭廣場“啡”常IN集③網址來源:https://mp.weixin.qq.com/s?_biz=MjM5MTE2ODE4Mg==&mid=2651906293&idx=1&sn=9898afb1292732 97b18520eff488110d&chksm=bd5de32c8a2a6a3a0d2a40c9ed85c05ce39b56d156f12cea6b4b1ab5588a7dc9536cfbe77420&scene=27。、嘉興月河咖啡市集④網址來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1852624617296418&wfr=spider&for=pc。、東莞市咖啡文化節⑤網址來源:https://finance.sina.cn/tech/2023-03-18/detail-imymfchs4535548.d.html。等)不同,智慧山市集與其說是為了提振消費促經濟,倒不如說是通過“認同文化編織”來保穩定。盡管天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終高于平均,甚至2022年在31個省份中排名第五⑥網址來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6735819448444885&wfr=spider&for=pc。,但就城市來說,天津甚至無法與東南沿海城市相提并論⑦2020年至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十城市排名都沒有天津且差距較大。——因此,居住在市郊產業園區的年輕人,幾乎無法將精品咖啡文化當作速溶咖啡這樣的普通日常品來消費⑧作為補充的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常年穩居第一的上海被稱為“咖啡之都”,在這里咖啡作為青年文化符號反過來也暗示著上海的經濟發展水平。。
咖啡市集的目的與其說是賣咖啡,倒不如說是在販賣“可以買咖啡的高消費人群”的想象性身份。盡管智慧山已經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面前做出了選擇,但這種召喚話語在白領階層中間仍然是有效的。在智慧山生活的人,他們一旦接受了“白海青新”的指認,就接受了智慧山所提供的身份標簽與幻想中的職場圖景,認可了自己“互聯網創新者”與“都市潮流文化消費者”之拼貼身份的召喚。
這種想象身份的話語,是對于白領階層真實處境的改寫,也是對于其創傷經驗的遮蔽。在這里生活的大部分白領階層注定不能與核心崗位程序員一樣獲得令人羨艷的高工資,也無法在高度異化的科層制體系中獲得自身的主體地位。
智慧山的故事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不僅向我們展示了園區經濟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其自身的內生活力,也向我們展示著在這個過程中的個體困境。在這種意義上,“山丘廣場”作為智慧山的轉型結果以隱喻的方式向我們訴說著被放逐了主體身份的“白領階層”的異化生存狀態——浙江安吉面積超過3500平米的竹子經過工業流程變成近35 萬片竹條,繼而變成山丘廣場的過程正是現代社會中人不再作為主體的隱喻。山丘的存在向我們不斷訴說它不曾說出的內容——在商業景觀背后,組成那山的已經異化的竹子向我們展示著每一個在這里出賣勞動時間的個體的困境:深度介入科層制體系,卻依舊需要假裝自己在森林,假裝自己可以從包裹自身的商業景觀中重獲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