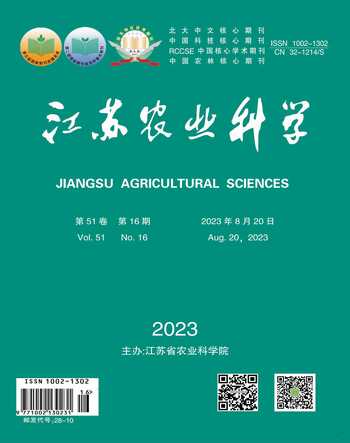長(zhǎng)三角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文化景觀基因及其設(shè)計(jì)利用
周之澄 徐媛媛 周武忠



摘要:鄉(xiāng)村景觀是鄉(xiāng)村自然風(fēng)貌、風(fēng)土文化與村民生產(chǎn)、生活狀態(tài)的最直觀體現(xiàn),也是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重要載體。當(dāng)下長(zhǎng)三角鄉(xiāng)村景觀建設(shè)中存在如“大拆大建”、盲目模仿城市化做法、文脈傳承不受重視等問題,導(dǎo)致了江南鄉(xiāng)村田野景觀的衰退。長(zhǎng)三角區(qū)域內(nèi)的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具備良好而典型的文化景觀元素,其長(zhǎng)時(shí)間積累的文化景觀基因值得設(shè)計(jì)利用,同時(shí)也應(yīng)以之為中心構(gòu)建鄉(xiāng)村景觀價(jià)值共創(chuàng)整體設(shè)計(jì)框架。鄉(xiāng)村建設(shè)需要通過系統(tǒng)挖掘文化景觀基因以彰顯鄉(xiāng)村地格,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獨(dú)具在地原真性的特色鄉(xiāng)村景觀,并在此過程中著力培養(yǎng)專業(yè)鄉(xiāng)村設(shè)計(jì)師。減少對(duì)鄉(xiāng)村景觀的“建設(shè)性破壞”,恢復(fù)適地自然景觀基礎(chǔ)、延續(xù)人文景觀脈絡(luò),圍繞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文化景觀基因設(shè)計(jì)具有場(chǎng)所記憶的在地“鄉(xiāng)愁”景觀,是倡導(dǎo)鄉(xiāng)村美學(xué)、引領(lǐng)鄉(xiāng)村景觀有機(jī)更新的有效途徑。
關(guān)鍵詞:農(nóng)業(yè)遺產(chǎn);鄉(xiāng)村景觀;整體設(shè)計(jì);景觀基因;鄉(xiāng)村地格
中圖分類號(hào):F323.4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1302(2023)16-0255-10
收稿日期:2023-04-22
基金項(xiàng)目:上海市藝術(shù)科學(xué)規(guī)劃項(xiàng)目(編號(hào):YB2021G08)。
作者簡(jiǎn)介:周之澄(1988—),男,江蘇江陰人,博士,講師,碩士生導(dǎo)師,研究方向?yàn)榫坝^規(guī)劃設(shè)計(jì)、地域振興設(shè)計(jì)。E-mail:13913995008@163.com。
通信作者:徐媛媛,博士,主要研究方向?yàn)槁糜我?guī)劃設(shè)計(jì)與管理。E-mail:ivy0226@126.com。
自聯(lián)合國糧農(nóng)組織(FAO)于2002年啟動(dòng)“全球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評(píng)定工作后,我國各地對(duì)“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概念的認(rèn)識(shí)與保護(hù)利用工作越來越重視,僅長(zhǎng)三角地區(qū)就已有4處全球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27處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這些重要的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絕大多數(shù)疊合了江南文化烙印,具有較高的生態(tài)文化和景觀美學(xué)價(jià)值。
隨著“鄉(xiāng)村振興”與“長(zhǎng)三角一體化”相繼上升至國家戰(zhàn)略的高度,目前江南地區(qū)(本研究中主要指江、浙、滬、皖的部分相鄰區(qū)域)的鄉(xiāng)村景觀建設(shè)在經(jīng)濟(jì)、文化等多個(gè)方面發(fā)展位居前列的長(zhǎng)三角區(qū)域也再度受到較高關(guān)注,“新時(shí)代美麗鄉(xiāng)村”“特色田園鄉(xiāng)村”“鄉(xiāng)村振興示范村”等抓手多條線并行,其成效有目共睹。但在發(fā)展過程中,曾經(jīng)城市化進(jìn)程中“大拆大建”的“跨越式”做法也在一些鄉(xiāng)村地區(qū)顯出了端倪,江南鄉(xiāng)村田野景觀的質(zhì)量大大衰退。生態(tài)上,對(duì)鄉(xiāng)土物種不夠重視,盲目引進(jìn)的外來動(dòng)植物品種破壞了原生景觀體系,影響了鄉(xiāng)村生態(tài)系統(tǒng)穩(wěn)定性,而城市景觀元素的過度介入也會(huì)使景觀系統(tǒng)的運(yùn)維脫離鄉(xiāng)村實(shí)際,使地域性原生景觀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生產(chǎn)上,不重視作為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根基的第一產(chǎn)業(yè)農(nóng)業(yè),丟棄了“精耕細(xì)作”的重農(nóng)傳統(tǒng),導(dǎo)致大面積的耕地拋荒。在景觀設(shè)計(jì)方法上流于對(duì)江南園林和城市景觀的簡(jiǎn)單模仿,江南園林的文化深意遭到忽視,江南鄉(xiāng)村的文化-景觀融合度不高。雖然通過仿古建筑的復(fù)建或是在景觀改造時(shí)運(yùn)用有代表性的地方元素能使鄉(xiāng)村景觀煥然一新,但資源同質(zhì)化利用所引發(fā)的“萬村一面”問題極易造成鄉(xiāng)村景觀的建設(shè)性破壞。如何挖掘江南地區(qū)的“鄉(xiāng)村空間基因”,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江南鄉(xiāng)村新景觀,成為當(dāng)下鄉(xiāng)村建設(shè)行動(dòng)過程中的當(dāng)務(wù)之急[1-3]。
不少學(xué)者在如何傳承鄉(xiāng)村文化景觀方面做過探索,保持鄉(xiāng)村自然生態(tài)性的研究成果較豐富,但多從江南建筑、出土文物等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視角提取表皮景觀元素,鮮有從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內(nèi)在精神提取鄉(xiāng)村文化基因,對(duì)鄉(xiāng)村景觀進(jìn)行整體設(shè)計(jì)。鄉(xiāng)村地區(qū)的景觀個(gè)性在于如何傳承地格,依據(jù)在地的自然地脈和歷史文脈,保護(hù)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自然性和歷史文化的原真性,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具有“鄉(xiāng)村性”的特色景觀。而針對(duì)“鄉(xiāng)村性”的文化原真性,本研究試從長(zhǎng)三角地區(qū)現(xiàn)有的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中梳理、提煉“江南鄉(xiāng)村文化基因”,為鄉(xiāng)村特色景觀營(yíng)造提供借鑒[4-10]。
1 長(zhǎng)三角區(qū)域的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
1.1 “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發(fā)展脈絡(luò)
知名度較高的農(nóng)業(yè)遺產(chǎn)認(rèn)定類型一般是指聯(lián)合國糧農(nóng)組織(FAO)的“全球重要農(nóng)業(yè)遺產(chǎn)”(GIAHS)和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主導(dǎo)的“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2012年3月,原農(nóng)業(yè)部下發(fā)了《關(guān)于開展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發(fā)掘工作的通知》,標(biāo)志著我國正式啟動(dòng)“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發(fā)掘工作;迄今已認(rèn)定6個(gè)批次(圖1)。《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確立了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歷史性、系統(tǒng)性、持續(xù)性、瀕危性、示范性、保障性6個(gè)方面的主要標(biāo)準(zhǔn),在認(rèn)定實(shí)踐中,又追加了傳承歷史年限、核心保護(hù)要素、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特色、鄉(xiāng)土社會(huì)系統(tǒng)、保護(hù)傳承意識(shí)等新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并明確了“創(chuàng)新保護(hù)與利用機(jī)制”。
1.2 長(zhǎng)三角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分布關(guān)鍵詞
截至2021年公布的第六批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江、浙、皖3省共入選27項(xiàng)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表1)。浙江省在江南地區(qū)的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遺產(chǎn)資源中占據(jù)優(yōu)勢(shì)地位,有14項(xiàng)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上榜,這得益于浙江省一直以來的卓越鄉(xiāng)村保護(hù)與建設(shè)工作,對(duì)相關(guān)資源與鄉(xiāng)村文化環(huán)境的保存十分重視,山脈連綿的自然環(huán)境反而令浙江對(duì)賴以生存的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以及隨之衍生的文化生活方式視若珍寶;江蘇省僅有第二批次未能入選,其余5批共計(jì)8項(xiàng)名單,溫和的東亞季風(fēng)氣候、大量的平原平坦地形以及豐沛的河流水系資源為江蘇鄉(xiāng)村提供了優(yōu)越的農(nóng)業(yè)發(fā)展環(huán)境;同為農(nóng)業(yè)大省的安徽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資源較好,雖然可能因?yàn)樵缙诘牟恢匾暼毕?批名錄,但也共有5項(xiàng)入榜,且資源類型多樣;在江南地區(qū)地位舉足輕重的上海市因?yàn)檩^高的城市化率,也因?yàn)楦劭诔鞘袣v史上復(fù)雜的變化影響,目前并沒有資源入選,但如青浦、金山等地都有大量的鄉(xiāng)村區(qū)域,青浦區(qū)更是作為目前長(zhǎng)三角生態(tài)綠色一體化示范區(qū)先行啟動(dòng)區(qū)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預(yù)見地會(huì)在將來為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與利用工作做出更大努力。
在3省27項(xiàng)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中,有4項(xiàng)同時(shí)也名列“全球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名錄,分別是江蘇興化垛田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tǒng)、浙江紹興會(huì)稽山古香榧群、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tǒng)。就鄉(xiāng)村景觀元素而言,僅此4項(xiàng)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就可謂“田、水、林、魚、蠶桑”等經(jīng)典江南“魚米之鄉(xiāng)”的文化景觀要素十分齊全,同時(shí)也包含了江南大部分平原區(qū)域少見的山脈元素,體現(xiàn)了有限資源條件下的農(nóng)業(yè)文化智慧與特質(zhì)性景觀生成。
從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發(fā)展與文化景觀成因的視角分析,其關(guān)鍵詞之一是“特色農(nóng)耕”:興化垛田基于大面積水域的塊狀田地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田地耕種,因其獨(dú)特的少陸地多水系地貌、穿行期間的水鄉(xiāng)小舟與顏色鮮明的黃色油菜花群形成異于他地的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與文化景觀,并隨之易于衍生出休閑旅游、特色農(nóng)產(chǎn)品等產(chǎn)品服務(wù)體系;青田稻魚則在傳統(tǒng)田地耕作基礎(chǔ)上最大化利用水稻田溝渠的有利條件,使稻田養(yǎng)魚與水稻種植相互平衡形成二極穩(wěn)定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在平地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呈現(xiàn)出了田地、水溝相映成趣而欣欣向榮的生產(chǎn)場(chǎng)景。
關(guān)鍵詞之二為“源遠(yuǎn)流長(zhǎng)”:無論垛田、稻魚還是香榧群都已歷經(jīng)超過千年歷史,蠶桑更是漢文化經(jīng)久不息的代表,這些發(fā)源于古代原始農(nóng)作“耕漁蠶桑”經(jīng)典農(nóng)業(yè)模式的產(chǎn)業(yè)經(jīng)過長(zhǎng)時(shí)間的多方檢驗(yàn),產(chǎn)業(yè)模式與景觀形態(tài)成熟而穩(wěn)定,對(duì)鄉(xiāng)村環(huán)境的適應(yīng)力極強(qiáng),在新時(shí)期也同樣會(huì)具備蓬勃的生命力。同時(shí),如果根據(jù)農(nóng)作基本形態(tài)將垛田視為基礎(chǔ)種植、青田稻魚視為種植加養(yǎng)殖、古香榧群為林果培育,桑基魚塘則在產(chǎn)業(yè)方面更為復(fù)雜,是“一種具有獨(dú)特創(chuàng)造性的洼地利用方式和生態(tài)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模式”,集成了塘基種桑、蠶桑絲織、水塘養(yǎng)魚等內(nèi)容,突出塘桑蠶魚互補(bǔ)的零污染生態(tài)自平衡循環(huán)利用理念,其所呈現(xiàn)的文化景觀形態(tài)也更為復(fù)合。這也是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傳承與創(chuàng)新利用的價(jià)值所在,關(guān)鍵在于如何妥善運(yùn)用其資源要素,合理轉(zhuǎn)化為可視、可觸、可用而異質(zhì)性的新型鄉(xiāng)村文化景觀體系[11]。
2 長(zhǎng)三角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典型景觀
2.1 長(zhǎng)三角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景觀類型
江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是基于江南地理與氣候條件,根據(jù)一個(gè)特定區(qū)域內(nèi)鄉(xiāng)村人群歷史性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活動(dòng),長(zhǎng)時(shí)間人地互相作用關(guān)系所形成的一整套農(nóng)業(yè)文化活動(dòng)系統(tǒng),包括了物質(zhì)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內(nèi)容。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是人類活動(dòng)與自然環(huán)境共同生成的結(jié)果,研究其所形成文化景觀的文化元素,首先應(yīng)該從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2個(gè)方面分析其主要類型,再根據(jù)每個(gè)案例的具體情況層層深入。27項(xiàng)長(zhǎng)三角區(qū)域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中,有幾種較為典型的自然景觀基礎(chǔ)條件,包括江南文化景觀意象中最有代表性的河流水系,江南地理環(huán)境中多丘陵地帶的山地景觀,代表喬木植被豐茂的林木與林果景觀;以及基于人地農(nóng)耕互動(dòng)、盛產(chǎn)糧食的代表性半自然土地景觀(包含低矮灌木、草本植物作物等),由于農(nóng)耕民族田間種植的基本屬性而將田地景觀視為江南地區(qū)自然景觀基底的一種;人文景觀則根據(jù)其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形式、主要產(chǎn)出及地方族群等因素各有異同(表2)。
根據(jù)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申報(bào)材料與官方描述,江南地區(qū)27項(xiàng)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所在地的主要自然景觀基礎(chǔ)類型,涉及山地景觀的“山”元素遺產(chǎn)有浙江云和梯田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等共11項(xiàng),“林”元素遺產(chǎn)有江蘇泰興銀杏栽培系統(tǒng)等共13項(xiàng),“水”元素遺產(chǎn)有安徽壽縣芍陂(安豐塘)及灌區(qū)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等共10項(xiàng),“田”元素有江蘇啟東沙地圩田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等共11項(xiàng)(表2),4種自然景觀基礎(chǔ)類型分別占比41%、48%、37%、41%,相對(duì)而言分布比較均勻,并沒有如大眾印象中江南水鄉(xiāng)“魚米之鄉(xiāng)”的“水”“田”2種元素占據(jù)景觀的絕對(duì)主導(dǎo)地位,這恰恰與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篩選標(biāo)準(zhǔn)中對(duì)自然與人文環(huán)境二者發(fā)展適應(yīng)性的強(qiáng)調(diào)較為吻合,關(guān)注的是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史中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立足的根本,在于人類應(yīng)對(duì)自然環(huán)境的適應(yīng)性與改造智慧;當(dāng)然也從側(cè)面說明了江南地區(qū)自然景觀資源的豐富度。
2.2 “山-林-水-田”的景觀基礎(chǔ)格局
山地景觀是唯一在27項(xiàng)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中都沒有單獨(dú)支撐景觀基底的自然景觀類型,11項(xiàng)包含“山”元素的遺產(chǎn)都有其他自然景觀元素發(fā)揮作用。山脈地形是地殼變化的直觀產(chǎn)物,與人文景觀尤其是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農(nóng)業(yè)文化的關(guān)聯(lián)度相對(duì)較低,甚至在許多時(shí)候都是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障礙;但山地決定地形基本條件、高差以及地塊基本形態(tài),是景觀設(shè)計(jì)中的基礎(chǔ)地形要素之一,同時(shí)山地通常伴隨著“林”元素較為豐茂的植被體系,往往也被視為物產(chǎn)豐富的景觀意象。例如在安徽黃山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統(tǒng)中,獨(dú)特的高山森林生態(tài)環(huán)境自成體系,并因農(nóng)業(yè)活動(dòng)形成了森林-高山茶園-森林-村落田園的立體農(nóng)業(yè)景觀體系,林地形成高低錯(cuò)落的防護(hù)林與隔離緩沖帶,茶園建于高山之中,村落田園間或山林中,整體上山地決定群落景觀形態(tài)、林地提供豐富的植被資源。因此山地景觀仍然是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中重要的基礎(chǔ)自然景觀類型,“山地”突出的是因物理高差在景觀視覺層面上所帶來的沖擊感,是地形起伏的韻律性,而非“山石”所體現(xiàn)的堅(jiān)實(shí)物質(zhì)性。
林木景觀類型是農(nóng)業(yè)活動(dòng)的重要分支——種植行為的產(chǎn)物,與“田地”景觀的區(qū)別在于其主要為喬木樹種的種植。林木景觀因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導(dǎo)向而多以“林果”景觀形式呈現(xiàn),同時(shí)也受花卉的文化景觀審美意象影響,時(shí)常形成林木、花卉、果實(shí)的三相景觀結(jié)構(gòu)。江蘇泰興銀杏栽培系統(tǒng)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在平原地形上進(jìn)行銀杏樹的人工栽植,從而形成單一樹種規(guī)模化林木景觀。同樣屬于單一“林”元素自然景觀分類的還有江蘇吳江蠶桑文化系統(tǒng)、浙江安吉竹文化系統(tǒng)、浙江黃巖蜜橘筑墩栽培系統(tǒng)、浙江桐鄉(xiāng)蠶桑文化系統(tǒng)4項(xiàng),其中浙江黃巖蜜橘筑墩栽培系統(tǒng)與泰興銀杏較為類似,也以單一品種樹種的大規(guī)模種植、果品出產(chǎn)以及相關(guān)文化系統(tǒng)的形成著名,雖兼顧平原與山地的蜜橘種植但筑墩栽培技藝對(duì)地形依賴程度不高;2項(xiàng)蠶桑文化系統(tǒng)除了人工栽植而形成的桑林外,景觀上更多體現(xiàn)的是中華民族蠶桑生產(chǎn)所形成的獨(dú)特生態(tài)系統(tǒng);浙江安吉竹文化系統(tǒng)則通過竹子這一特殊的植物種類呈現(xiàn)出我國文化體系中竹文化的重要沿革,竹林環(huán)境所承載的人文情懷與民族化的主觀意趣是觀景主體,人文景觀意義超越其原有林木景觀生態(tài)體系。
除“山林”元素組合較為常見外,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tǒng)的“林田”元素組合從生態(tài)系統(tǒng)物種多樣化的角度給出了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結(jié)構(gòu)性建議”。樹林與田地的交雜不僅在景觀層次上填滿了喬木、灌木、草本植物高、中、低的視覺組合,從景觀功能上也優(yōu)勢(shì)互補(bǔ),隔離緩沖、光照與土壤養(yǎng)分配給、根莖果實(shí)的復(fù)合產(chǎn)出等,從多個(gè)不同角度豐富了場(chǎng)地景觀元素,增添了文化景觀縱深,江蘇吳中碧螺春茶果復(fù)合系統(tǒng)的茶果間植、安徽銅陵白姜種植系統(tǒng)的外圍防護(hù)林帶、安徽黃山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統(tǒng)高山林地茶園都是很好的例證,充分驗(yàn)證了我國農(nóng)耕文化因地制宜、物盡其用的“整合”思想。“林水”元素組合也有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tǒng)的例子,塘基桑林與湖塘養(yǎng)魚互成表里,農(nóng)業(yè)種植與農(nóng)業(yè)養(yǎng)殖相得益彰,林地種植便于汲取水源、水系養(yǎng)殖易于獲得養(yǎng)分,形成良好的生態(tài)循環(huán)系統(tǒng),主景觀層次上也有樹冠高突、林間疏密與湖塘低洼的組合。
“水鄉(xiāng)”的文化景觀印象分為水景與鄉(xiāng)愁2個(gè)方面,其核心景觀都是江南地區(qū)發(fā)達(dá)的河道水系環(huán)繞的聚居情境,早期是鄉(xiāng)村環(huán)境的田園家鄉(xiāng),后延展至村鎮(zhèn)甚至城市的人類聚落,以民居、古橋、古意街巷等為主要景觀元素,著名的江南水鄉(xiāng)古鎮(zhèn)景觀體系便是沿著蜿蜒河道的排列民居。長(zhǎng)三角三省的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中不乏大面積湖塘蓄積水體的經(jīng)典水文景觀,或?yàn)樘烊换驗(yàn)槿斯ぃ紴橹苓厖^(qū)域的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發(fā)展作出巨大貢獻(xiàn)。江蘇高郵湖泊濕地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安徽壽縣芍陂(安豐塘)及灌區(qū)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及浙江德清淡水珍珠傳統(tǒng)養(yǎng)殖與利用系統(tǒng)是其中的3項(xiàng)典型,共同特點(diǎn)是都以大型集中水體成景為主要景觀形式,但區(qū)別也很明顯:嚴(yán)格意義上而言,芍陂及灌區(qū)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應(yīng)該統(tǒng)計(jì)“水”與“田”2項(xiàng)自然景觀類型,蓄水面積與灌溉面積體量相當(dāng),且“納川吐流,灌田萬頃”的主要景觀風(fēng)貌體現(xiàn)了引水灌田的農(nóng)業(yè)文化,但考慮到其較少見的古代大體量水利工程壯舉以及核心區(qū)域的主體水系景觀,仍然將其視為單一水系景觀元素;德清珍珠養(yǎng)殖系統(tǒng)雖然也有復(fù)合業(yè)態(tài)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行為,但主要依靠并以特有的珍珠養(yǎng)殖系統(tǒng)而著名,所呈現(xiàn)的主要景觀也為優(yōu)質(zhì)淡水養(yǎng)殖水網(wǎng);高郵湖區(qū)域則是結(jié)合了水系與周邊濕地,綜合體現(xiàn)采集漁獵、飯稻羹魚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生活,物種與物產(chǎn)體系都十分豐富、復(fù)合,且舟楫易行。在單一水系景觀元素之外,江南地區(qū)經(jīng)典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自然景觀基底中,水、田相依相生與山間流水的景觀格局較為常見,江蘇興化垛田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浙江杭州西湖龍井茶文化系統(tǒng)與浙江縉云茭白-麻鴨共生系統(tǒng)都屬于前者的類型,異于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意義上的稻田水系,不管是水網(wǎng)垛田、西湖茶田還是茭白所處水生環(huán)境都以水文景觀為多而非田地占據(jù)絕對(duì)主導(dǎo)地位,既有與稻田類似但“田在水中”的田水交混共生環(huán)境,也有傍水而種、便于灌溉的田水依傍景觀關(guān)系;山間流水的景觀體系則多利用山泉水系資源滿足林果、田地灌溉等農(nóng)業(yè)種植需求,安徽休寧山泉流水養(yǎng)魚系統(tǒng)、浙江開化山泉流水養(yǎng)魚系統(tǒng)十分相似,都以山泉資源活水養(yǎng)魚于山林、村舍之間,算是從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角度為山地農(nóng)業(yè)養(yǎng)殖另辟“山水”蹊徑[11]。
田地景觀是典型的農(nóng)耕文化產(chǎn)物。由于我國千百年農(nóng)耕生活的長(zhǎng)時(shí)間熏陶,鄉(xiāng)村與田地已經(jīng)緊密結(jié)合,形成了鄉(xiāng)村景觀的“半自然”風(fēng)貌基礎(chǔ)。田地所代表的種植業(yè)對(duì)于農(nóng)業(yè)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一方面田地景觀類型與其他自然景觀類型都有良好的結(jié)合,由此產(chǎn)生的多種典型鄉(xiāng)村田野風(fēng)貌層出不窮;而另一方面,正因?yàn)樘锏卦卩l(xiāng)村區(qū)域的普遍性,田地作物類型的“特殊性”與“稀缺性”成為田地景觀能夠脫穎而出的決定性因素。田地景觀單一元素遺產(chǎn)資源中,江蘇宿豫丁嘴金針菜生產(chǎn)系統(tǒng)與浙江寧波黃古林藺草—水稻輪作系統(tǒng)都以作物的區(qū)域不可替代性,以及生產(chǎn)、加工、管理等過程的獨(dú)有特點(diǎn)脫穎而出;江蘇啟東沙地圩田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則是在特殊的海陸相接的鹽堿地質(zhì)條件下發(fā)展出的墾荒圩田范式,具備可觀的地理與人文環(huán)境價(jià)值。如上分析,在“水田”元素交匯時(shí),水生環(huán)境、水系景觀占主導(dǎo)的條件異于一般“田地”的土地景觀概念;“林田”景觀打破了田地景觀近地、貼地的景觀視野感,豐富了景觀層次;“山田”景觀則扭轉(zhuǎn)了山體高差與斜度帶來的耕種行為阻礙,形成了如梯田般壯美的景觀畫卷。
表2中列出的僅為長(zhǎng)三角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地較有代表性的生態(tài)景觀類型,多為一項(xiàng)特質(zhì)性元素或2項(xiàng)元素組合,但仍有遺產(chǎn)地景觀類型較為復(fù)合。例如已探討過的安徽黃山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統(tǒng),山地基礎(chǔ)地形與大量林木植被加上農(nóng)業(yè)文化痕跡較突出的茶田,形成“山林田”復(fù)合景觀;村民、茶農(nóng)穿行于山地、林間、田間,農(nóng)林耕作形成田園,再憑借“三大階段、九道手工采制工藝”的“最高超、最精湛、最獨(dú)特的制茶技藝”積累形成了以高山生態(tài)茶園林茶共育和綠色栽培管理技術(shù)體系為代表的人文景觀,結(jié)合而成了自然景觀內(nèi)外高低層次分明、農(nóng)業(yè)景觀立體、人文景觀分時(shí)線性的文化景觀體系。浙江杭州西湖龍井茶文化系統(tǒng)也依托杭州西湖“山水田園”的景觀本底,營(yíng)造出了基于良好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湖畔茶田景觀體系,三面環(huán)山但茶田多存于西湖周邊的平地、緩坡,得益于環(huán)山地形與大面積水域的優(yōu)越自然環(huán)境將3種自然景觀類型很好地結(jié)合在了一起;人文景觀方面同樣以采、制茶工藝為主,但因杭州西湖自古以來的文化藝術(shù)意象添加了如以靈隱寺為代表的禪宗、養(yǎng)生、觀景多元文化,內(nèi)涵與外延都得到了較大延展;也正因?yàn)楹贾菸骱懥恋拿暸c“文化景觀遺產(chǎn)”的入選現(xiàn)狀,想要列名全球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在農(nóng)業(yè)文化梳理與產(chǎn)業(yè)開發(fā)方面還需要做出較大努力。安徽太湖山地復(fù)合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從名稱上就體現(xiàn)了其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的復(fù)合特點(diǎn),背山面水的山地-河谷地形提供了平緩農(nóng)田地形與緩坡林果畜牧空間,水域也被劃分為大、小2種水體,即近自然大面積水體與近村舍水塘式小面積水體以分別發(fā)展水產(chǎn)養(yǎng)殖;“山環(huán)水抱,明堂開闊”的村落聚居原則形成了以防御性民居“大屋建筑”為核心的村莊人文景觀,整體上“山-林-河-田-村-塘”的復(fù)合型土地利用格局體現(xiàn)了安徽太湖山地復(fù)合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在有限生態(tài)條件下充分開發(fā)多種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生活形式的環(huán)境利用智慧,同時(shí)其移民文化與原鄉(xiāng)文化景觀融合的人文景觀特征也較有特色[11]。
3 長(zhǎng)三角地區(qū)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景觀基因
3.1 代表性文化景觀基因
根據(jù)上述分析,“山-林-水-田”4項(xiàng)基本元素構(gòu)成了長(zhǎng)三角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景觀基底,各遺產(chǎn)點(diǎn)的風(fēng)土、風(fēng)景、風(fēng)物、風(fēng)俗的組合形成了其典型文化景觀,并在漫長(zhǎng)的歷史演化過程中固化成“文化景觀基因”。
3.2 “雙遺產(chǎn)”的文化景觀基因體系
與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不同,全球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評(píng)選標(biāo)準(zhǔn)與價(jià)值體系主要聚焦于全球重要性、糧食與民生保障、生態(tài)系統(tǒng)功能、知識(shí)與技術(shù)適應(yīng)性、社會(huì)文化價(jià)值與景觀資源特色6個(gè)方面,主要考慮的是農(nóng)業(yè)文化資源的產(chǎn)業(yè)特點(diǎn)及其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稀缺性和影響力,景觀特色僅作為其中的一項(xiàng)關(guān)注點(diǎn)。但也恰恰是其景觀特點(diǎn)最能體現(xiàn)文化景觀基因的特殊作用。
分析4項(xiàng)“雙遺產(chǎn)”案例,第1項(xiàng)是2005年入選的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tǒng)。自然景觀方面,青田縣屬丘陵山地地貌,基礎(chǔ)地形以低山和丘陵為主,2 228 km2的面積占全縣總面積的89.7%;而 132 km2的平地僅占5.3%,與水域面積基本持平,青田地貌特征呈現(xiàn)“九山半水半分田”格局。獨(dú)特的山林地貌使其稻田以梯田及小型平地空間的形式存在于丘陵包圍之下,因此雖然青田稻魚的主要呈現(xiàn)場(chǎng)景為稻田水系(非大面積水體),體現(xiàn)的是農(nóng)耕文化下“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田地景觀基礎(chǔ),仍然應(yīng)該將山林地貌視為其重要的自然景觀類型。人文景觀方面,青田稻魚在種植與養(yǎng)殖協(xié)作、田間管理及水田漁業(yè)上長(zhǎng)時(shí)間積累而成的一套成熟農(nóng)作景觀體系,和以田魚產(chǎn)品、青田魚燈舞為代表的田魚文化衍生景觀都較為知名;相對(duì)而言其村落文化景觀似乎欠缺辨識(shí)度,但也因田魚共生生態(tài)循環(huán)系統(tǒng)出產(chǎn)豐富、減少化學(xué)依賴的特點(diǎn)滿足村容整潔、生活富裕等鄉(xiāng)村環(huán)境建設(shè)要求。總體上,其鄉(xiāng)村景觀體系都圍繞著田魚文化的“魚”“米”2項(xiàng)關(guān)鍵性要素展開,魚在田中、米魚相合的鄉(xiāng)愁記憶躍然鄉(xiāng)野[12]。
第2項(xiàng)是2013年入選的浙江紹興會(huì)稽山古香榧群。香榧樹林與會(huì)稽山脈組合而成的山林景觀體系以沿山坡而上的香榧樹群為主要景觀標(biāo)志物,形成了“嫁接技藝-林果產(chǎn)物-文化詠嘆”條線式較為簡(jiǎn)單而穩(wěn)定的農(nóng)業(yè)文化架構(gòu),在景觀呈現(xiàn)上以山林元素為基礎(chǔ)、魚鱗坑式梯田為點(diǎn)狀突出;人文景觀價(jià)值則主要體現(xiàn)在傳承超過千年的香榧人工嫁接技術(shù)、豐富的林下作物產(chǎn)出,以及隨之同樣沿襲千年的香榧文化藝術(shù)作品、傳統(tǒng)觀念以及民俗等文化產(chǎn)物。會(huì)稽山脈、香榧樹林與傳統(tǒng)村落融為一體,形成了壯觀的豎向?qū)哟涡跃坝^;“魚鱗坑”石樁梯田圍合的香榧林、針葉林、毛竹林等樹種的山石林帶景觀與生態(tài)涵養(yǎng)功能,香榧、櫻桃、竹筍、板栗、云霧山茶等多種物產(chǎn)以及純屬的手工加工工藝,再加上村落活動(dòng)、祭祀節(jié)慶活動(dòng)等傳統(tǒng)觀念與做法組成的“香榧文化”群體記憶,共同構(gòu)成了浙江紹興會(huì)稽山古香榧群的獨(dú)特文化景觀結(jié)構(gòu)。因此,山脈林地、特有“圍樹”梯田、香榧林下物產(chǎn)以及贊美香榧的文化習(xí)俗是文化景觀元素提取重點(diǎn);而同樣的,在很大程度上被廣袤山勢(shì)地貌弱化的村落景觀也有很大的設(shè)計(jì)突出空間。
第3項(xiàng)是2014年入選的江蘇興化垛田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興化垛田水、田景觀元素較為均衡,在自然景觀方面“七水三土”的大面積河湖水域風(fēng)光較為引人注目,在人文景觀方面行船搖擼、島田耕種的“稻飯漁歌”場(chǎng)景意境深遠(yuǎn)。湖蕩沼澤地的連綿水系在形成長(zhǎng)三角地區(qū)典型水系景觀的同時(shí)也因其洪澇災(zāi)害、陸地少而割裂等天然缺陷給當(dāng)?shù)剞r(nóng)民帶來了不小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阻礙,興化先民圍湖造田,并創(chuàng)造性地在湖中反復(fù)堆積泥渣沙漿,逐漸形成多至兩三畝、小到幾厘的高垛,即為延續(xù)至今的垛田,配合如油菜花等代表性農(nóng)作物,以水上“千島”“千垛”的奇瑰景象享譽(yù)世界。興化垛田水為底、垛田網(wǎng)格狀點(diǎn)綴其間的空間景觀格局十分難得,也是以人為勞作積累,扭轉(zhuǎn)水、土不均衡格局以至水、田分庭抗禮,有效將農(nóng)作劣勢(shì)基礎(chǔ)轉(zhuǎn)化為優(yōu)勢(shì)人文景觀的完美案例,充分體現(xiàn)了江南文化景觀中象征著漁業(yè)養(yǎng)殖與農(nóng)作耕植“魚米水鄉(xiāng)”的“水-田”元素特征,將“水-漁”“田-耕”的人文農(nóng)作景觀良好地結(jié)合在了一起。其自然景觀基底與農(nóng)作文化元素具有十足的元素提取代表性,低洼水系與凸起高田的反差地景符號(hào)有深入挖掘的價(jià)值,其小微灌排工程、聚居建筑與街道景觀形式、橋梁步道等人文景觀也具備相當(dāng)?shù)脑鼗O(shè)計(jì)價(jià)值[13]。
第4項(xiàng)是2017年的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tǒng)。0.4萬hm2桑地和1萬hm2魚塘形成了我國規(guī)模最大,同時(shí)也是“林-塘”相互包圍空間景觀結(jié)構(gòu)保存最為完整的江南水鄉(xiāng)典型生態(tài)農(nóng)業(yè)景觀。蠶桑農(nóng)業(yè)文化系統(tǒng)與魚塘養(yǎng)殖文化系統(tǒng)的組合營(yíng)造出了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的桑基魚塘生態(tài)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模式,對(duì)所處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幾乎零污染使其呈現(xiàn)出最為原生態(tài)的文化景觀。它包括了人工密集種植的桑樹林,蠶的規(guī)模化飼養(yǎng)及蠶絲生產(chǎn)加工,以及以魚塘淤泥、蠶蛹蠶沙、桑營(yíng)養(yǎng)土等為核心的內(nèi)循環(huán)灌溉、排水與給肥系統(tǒng)。
從以上4項(xiàng)升格為全球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案例來看,它們都是復(fù)合的生態(tài)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同時(shí)也具有更優(yōu)質(zhì)的文化景觀基因,可被歸納為:復(fù)合的自然景觀+先進(jìn)的循環(huán)農(nóng)業(yè)技藝+特色的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系統(tǒng)。
4 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導(dǎo)向的鄉(xiāng)村景觀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思路
4.1 圍繞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鄉(xiāng)村景觀價(jià)值共創(chuàng)設(shè)計(jì)
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中蘊(yùn)含著當(dāng)?shù)厝藗儗氋F的生產(chǎn)、生活經(jīng)驗(yàn),同時(shí)也具備保存完好的生態(tài)基底,所體現(xiàn)的由特有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衍生的一系列習(xí)俗、文化等生活模式需要被良好的保護(hù)與傳承延續(xù),應(yīng)以整體全面的眼光看待與核心農(nóng)業(yè)活動(dòng)相關(guān)的“衍生過程”與“副產(chǎn)品”,同樣重視與之緊密相連的民間傳說、文藝表演、工藝美術(shù)等,力求完整地呈現(xiàn)出農(nóng)業(yè)遺產(chǎn)的全貌。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在我國與世界范圍內(nèi)的評(píng)選都以“系統(tǒng)”為單位,充分體現(xiàn)了圍繞同一農(nóng)業(yè)主題下地形地貌等自然景觀基底、人類生活痕跡及人類活動(dòng)本身以及地域族群衍生文化行為等多項(xiàng)生產(chǎn)、生活、生態(tài)內(nèi)容的系統(tǒng)性統(tǒng)一[14-18]。
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對(duì)于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帶動(dòng)作用至關(guān)重要,而其關(guān)聯(lián)性文化景觀則是最為直觀、高效的表現(xiàn)形式。正因?yàn)槲幕坝^脫胎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與生活,以鄉(xiāng)村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為核心,是人類群體行為長(zhǎng)期作用于自然環(huán)境、與自然和諧共存而產(chǎn)生的人文地景,忠實(shí)地記錄了鄉(xiāng)村這一人類聚落的發(fā)展模式,因此才能與地方產(chǎn)業(yè)發(fā)展、人才培養(yǎng)、資源利用等全方位掛鉤。這一現(xiàn)象在江南鄉(xiāng)村地區(qū)這樣自古以來“農(nóng)耕牧漁”經(jīng)典農(nóng)業(yè)模式十分發(fā)達(dá)的地方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
從這些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產(chǎn)生和構(gòu)成的復(fù)雜性可知,要系統(tǒng)傳承文化景觀基因需要在合力保護(hù)遺產(chǎn)系統(tǒng)的前提下,集合能夠?qū)r(nóng)業(yè)遺產(chǎn)地鄉(xiāng)建發(fā)展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核心利益相關(guān)者,遵循價(jià)值共創(chuàng)網(wǎng)絡(luò)主導(dǎo)邏輯,通過在利益相關(guān)者之間建立高聯(lián)結(jié)屬性的充分互動(dòng),形成“價(jià)值主張-價(jià)值創(chuàng)造-價(jià)值共享”的價(jià)值共創(chuàng)整體設(shè)計(jì)思路。通過識(shí)別不同遺產(chǎn)地各利益相關(guān)者所擁有的資源基礎(chǔ)提出整體性的價(jià)值主張,統(tǒng)一思想觀念,形成價(jià)值共識(shí);通過資源的獲取、釋放、整合以及重構(gòu)優(yōu)化和革新價(jià)值內(nèi)容,推動(dòng)價(jià)值創(chuàng)造;基于各類平臺(tái)的合作拓寬價(jià)值共創(chuàng)網(wǎng)絡(luò)中的價(jià)值鏈條,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共享;在這一過程中,資源的流動(dòng)以及利益相關(guān)者的互動(dòng)方式根據(jù)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呈現(xiàn)動(dòng)態(tài)化的迭代升級(jí)。這樣一種動(dòng)態(tài)化的價(jià)值共創(chuàng)整體設(shè)計(jì)模型能夠創(chuàng)新傳承優(yōu)秀文化景觀遺產(chǎn),為建設(shè)美麗新江南創(chuàng)造新的鄉(xiāng)村景觀。
這樣的農(nóng)業(yè)遺產(chǎn)傳承與創(chuàng)新目標(biāo)需要由以下主體參與,首先是業(yè)主方:對(duì)地方條件比較了解,包括擁有者、管理者等,針對(duì)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申報(bào)提出保護(hù)與利用的相應(yīng)需求,但不具備景觀設(shè)計(jì)專業(yè)知識(shí);之后是設(shè)計(jì)與建造師(匠師):掌握鄉(xiāng)村景觀設(shè)計(jì)方法與效果呈現(xiàn)手段,了解實(shí)踐落地流程與做法,但對(duì)地方條件了解不深入;最后是公眾:文化景觀所處江南鄉(xiāng)村環(huán)境的使用者,包括長(zhǎng)時(shí)性使用居民與短時(shí)性使用游客等群體,能夠提出基于自身的經(jīng)驗(yàn)性判斷與意見看法(圖2)。三方共同努力構(gòu)成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傳承、創(chuàng)新、利用全過程的鄉(xiāng)村景觀價(jià)值共創(chuàng)整體設(shè)計(jì)方法。
4.2 重視鄉(xiāng)村景觀設(shè)計(jì)師的培養(yǎng)
長(zhǎng)三角鄉(xiāng)村建設(shè)過程中,鄉(xiāng)村主體退化、缺少地域特色、以農(nóng)業(yè)為主的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發(fā)展艱難等“建設(shè)性破壞”困境的出現(xiàn),原因是多方面的。從設(shè)計(jì)學(xué)專業(yè)視角出發(fā),懂農(nóng)業(yè)、愛鄉(xiāng)村的鄉(xiāng)村設(shè)計(jì)力量缺失是導(dǎo)致鄉(xiāng)村重“建”而輕“設(shè)”、千村一面等問題產(chǎn)生的主要原因。設(shè)計(jì)有助于明確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實(shí)施路徑、有效對(duì)接城鄉(xiāng)資源,城市設(shè)計(jì)與鄉(xiāng)村設(shè)計(jì)有著不同的方法論、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實(shí)現(xiàn)路徑,但在實(shí)踐中,設(shè)計(jì)師常把城市規(guī)劃設(shè)計(jì)的思維生硬地用于鄉(xiāng)村設(shè)計(jì)。
鄉(xiāng)村設(shè)計(jì)的文脈基礎(chǔ)來源于鮮活的鄉(xiāng)村生活,其地格扎根于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環(huán)境。要更好地發(fā)展鄉(xiāng)村設(shè)計(jì),唯有建立科學(xué)的鄉(xiāng)村設(shè)計(jì)教育體系,以《鄉(xiāng)村設(shè)計(jì)定山宣言》等文件與共識(shí)為綱要,加速培養(yǎng)專注的鄉(xiāng)村設(shè)計(jì)師。在鄉(xiāng)村景觀設(shè)計(jì)這一需要知識(shí)與經(jīng)驗(yàn)積累的行業(yè)中,通過農(nóng)業(yè)知識(shí)特別是對(duì)農(nóng)業(yè)遺產(chǎn)知識(shí)的教育培訓(xùn),充分考慮如何將優(yōu)質(zhì)的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資源轉(zhuǎn)化為鄉(xiāng)村景觀發(fā)展的助推動(dòng)力,通過產(chǎn)業(yè)與文化景觀融合發(fā)展的方式,精準(zhǔn)定位鄉(xiāng)村景觀與產(chǎn)業(yè)區(qū)別于城市環(huán)境的特質(zhì),才能使江南文化區(qū)在長(zhǎng)三角一體化與鄉(xiāng)村振興的雙重國策下成為區(qū)域乃至全國范圍內(nèi)的引領(lǐng)者[19]。
4.3 基于農(nóng)業(yè)遺產(chǎn)文化景觀基因的鄉(xiāng)村景觀設(shè)計(jì)實(shí)施路徑建議
從設(shè)計(jì)的角度來研究鄉(xiāng)村環(huán)境的各個(gè)方面,需要整體考慮人工和自然等空間要素,設(shè)計(jì)出使這些要素和諧統(tǒng)一的美麗鄉(xiāng)村,既滿足生產(chǎn)和生活的功能需求,又考慮到環(huán)境安全和生態(tài)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以長(zhǎng)三角區(qū)域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文化景觀基因研究為基礎(chǔ),其基于江南文化地格的鄉(xiāng)村景觀整體設(shè)計(jì)策略可分為以下3個(gè)步驟:
4.3.1 修復(fù)形成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自然地脈
生態(tài)景觀的自然性是鄉(xiāng)村地格的基礎(chǔ),長(zhǎng)三角地區(qū)的生態(tài)景觀基礎(chǔ)并非單一的耕地,但在長(zhǎng)期的發(fā)展過程中,特別是長(zhǎng)三角地區(qū)特定時(shí)期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的高速發(fā)展和快速城市化,令山林景觀被采石等掠奪性開發(fā)方式破壞得遍體鱗傷,廢棄的宕坑與幾近削平的山頭隨處可見,連片的湖蕩被填埋的支離破碎,“退耕還林”還是“退林還田”的爭(zhēng)端也屢見不鮮。因此江南鄉(xiāng)村景觀設(shè)計(jì)的首要任務(wù)是按照“山-林-水-田”的基本格局進(jìn)行環(huán)境生態(tài)修復(fù)。同時(shí)應(yīng)避免城市化的綠化方式、綠化樹種,尊重鄉(xiāng)村的自然肌理與地帶性植被規(guī)律,宜林則林、宜樹則樹、適地適樹,營(yíng)造符合自然規(guī)律的復(fù)合型植物景觀。
4.3.2 延續(xù)形成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歷史文脈
長(zhǎng)三角地理區(qū)域長(zhǎng)久以來積淀所形成的江南文化是我國最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種類之一。在區(qū)域一體化進(jìn)程中,江南文化的特質(zhì)構(gòu)成了長(zhǎng)三角共同的精神家園,江南水鄉(xiāng)的風(fēng)景意象是江南地區(qū)文化景觀的重要表現(xiàn)方面。但由于受文人雅士吟詠江南地區(qū)“杏花春雨江南”的景觀風(fēng)情影響,小橋流水、粉墻黛瓦、水鄉(xiāng)民居、古鎮(zhèn)街巷往往被認(rèn)為是江南的典型文化景觀。但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延續(xù)的景觀基因卻沒有在鄉(xiāng)村景觀建設(shè)中得到應(yīng)有的體現(xiàn)[4-5]。
在表3提煉的長(zhǎng)三角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9個(gè)代表性文化景觀基因中,林下種植、竹林竹海、山泉養(yǎng)魚為自然生態(tài)景觀類型,茶田果園、島式垛田、村莊聚落和農(nóng)業(yè)加工等典型景觀他處也有分布(表2),唯有魚米之鄉(xiāng)、男耕女織這2個(gè)文化景觀遺產(chǎn)基因與江南文化的血脈更加緊密,值得重點(diǎn)加以傳承和創(chuàng)新。
魚米之鄉(xiāng)的文化景觀基因在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tǒng)得到了最佳顯現(xiàn)。聯(lián)合國糧農(nóng)組織的注解從多個(gè)方面闡釋了青田稻魚的景觀價(jià)值:“被森林環(huán)繞的稻田塑造了景觀”,奠定了“山林-田地”式從外到內(nèi)的景觀基礎(chǔ);“由于稻田面積較小,水稻種植者和魚類養(yǎng)殖者在相同田地間共同勞作的合作管理模式至關(guān)重要”,體現(xiàn)了農(nóng)民充分利用資源,彼此之間、與環(huán)境之間和諧共處的農(nóng)業(yè)生存智慧;“稻魚制度被描述為一種文化方式,稻魚系統(tǒng)鼓勵(lì)基本生態(tài)功能、提供多種產(chǎn)品與功能”,說明了青田稻魚在農(nóng)業(yè)物產(chǎn)與文化生活方式上的豐富度。
而正如上面所述,山林景觀元素在系統(tǒng)中基本作為背景式自然景觀存在,其核心文化景觀基因仍然集中在不利環(huán)境條件下“水-田”元素的交融與稻魚共生模式的存續(xù)。因而在尊重其農(nóng)作生態(tài)循環(huán)系統(tǒng)與相應(yīng)衍生文化的基礎(chǔ)上,梯田地貌、田魚產(chǎn)品及其衍生文化活動(dòng)應(yīng)該成為文化景觀元素提取的重點(diǎn),而村落景觀則成為了更有針對(duì)性的設(shè)計(jì)目標(biāo)。在當(dāng)下的鄉(xiāng)村景觀設(shè)計(jì)過程中,于田野上架起河豚魚的雕塑、營(yíng)造大閘蟹建筑、豎起漁舟村標(biāo)雖高效、直觀但卻并不能完全代表魚米之鄉(xiāng)的文化景觀,應(yīng)該把精耕細(xì)作、循環(huán)農(nóng)業(yè)的農(nóng)耕文化傳統(tǒng)滲透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場(chǎng)景中,構(gòu)成原汁原味的新時(shí)代稻作文化景觀。
男耕女織是江南地區(qū)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的經(jīng)典模式,自然也體現(xiàn)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的核心特點(diǎn):自給自足。“衣食”需求中,除了“魚米”,“穿衣”也同等重要,蠶桑絲織文化因而成為我國農(nóng)耕文明中最有代表性的農(nóng)事生產(chǎn)和生活文化之一。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tǒng)和江蘇吳江蠶桑文化系統(tǒng)雖然跨省,但相距僅30~50 km,2個(gè)遺產(chǎn)系統(tǒng)所處太湖流域經(jīng)久累積的灌排水網(wǎng)與圩堤水田系統(tǒng)最能體現(xiàn)江南地區(qū)平原地帶地勢(shì)低洼、水網(wǎng)縱橫、內(nèi)澇外旱的地理特點(diǎn),以及溝渠縱橫、水利發(fā)達(dá)、農(nóng)事基建整體完備的人文景觀風(fēng)貌,根據(jù)南北向與東西向的空間方位特點(diǎn),俗稱“縱浦橫塘”。這兩大以蠶桑文化為主題的遺產(chǎn)人文農(nóng)業(yè)景觀在其景觀體系中占絕對(duì)主導(dǎo)地位,傳承這樣的文化景觀基因等于傳承了這里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和核心鄉(xiāng)村景觀。
近年來受水產(chǎn)效益高于養(yǎng)蠶效益、產(chǎn)業(yè)鏈的后端開發(fā)不足等因素影響,蠶桑絲織文化始終未能形成較為健全的文化景觀與產(chǎn)品體系。事實(shí)上,桑樹的景觀價(jià)值一直沒有得到充分認(rèn)識(shí)和系統(tǒng)設(shè)計(jì)。種桑養(yǎng)蠶不只為織布裁衣,桑樹作為植物中蛋白質(zhì)含量極高的樹種,桑葉可以煲湯炒菜,桑基木耳口感獨(dú)特鮮美,桑葚不僅可以鮮食還是釀酒的高級(jí)原料,因此栽桑不僅可以傳承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景觀基因,也是發(fā)展休閑農(nóng)業(yè)和鄉(xiāng)村旅游難得的“可食用景觀”。
誠然,針對(duì)重要農(nóng)業(yè)遺產(chǎn)的核心景觀資源,結(jié)合環(huán)境的歸屬性和認(rèn)同感,根據(jù)場(chǎng)所精神設(shè)計(jì)鄉(xiāng)愁景觀;根據(jù)公眾的審美信息與景觀基因的匹配,通過對(duì)環(huán)境空間的設(shè)計(jì)傳達(dá)美感的信息;考慮到人們行為的多樣性與審美趣味的多元性,用遺產(chǎn)景觀基因的豐富性創(chuàng)造與之相適應(yīng)的文化景觀多樣性,可以滿足新時(shí)代高品質(zhì)生活的新需求。
4.3.3 突破區(qū)劃限制建設(shè)區(qū)域文化遺產(chǎn)與景觀共同體
鄉(xiāng)村文化的根基在鄉(xiāng)村生活,鄉(xiāng)村生活的根基在食糧,長(zhǎng)三角區(qū)域的基本食糧是稻米。“魚米之鄉(xiāng)”是長(zhǎng)三角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和地理特征的標(biāo)簽,但在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的蘇南地區(qū)稻田面積減少速度非常快。土壤重金屬污染、建設(shè)性破壞等問題在加速破壞長(zhǎng)三角地區(qū)的地脈和文脈,一向以“精耕細(xì)作”著稱的稻作文化傳統(tǒng)也存在斷裂的危機(jī)。稻作及其衍生傳統(tǒng)文化生活方式不僅僅能保證糧食安全,其生態(tài)效益、景觀與防洪防汛等多元價(jià)值體量甚至遠(yuǎn)超經(jīng)濟(jì)價(jià)值。以生產(chǎn)稻米的水稻田、耕織綿延的文化生活以及象征生態(tài)的田林水系為核心景觀元素,圍繞農(nóng)業(yè)遺產(chǎn)優(yōu)先從“水”“田”兩大類型出發(fā)構(gòu)建新時(shí)期鄉(xiāng)村文化景觀體系,創(chuàng)設(shè)如“長(zhǎng)三角國家稻作文化公園”等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區(qū)劃限制的鄉(xiāng)村文化景觀遺產(chǎn)集群,保護(hù)鄉(xiāng)村自然生態(tài)的“原真性”與歷史文化的“鄉(xiāng)村性”,可以喚起區(qū)域內(nèi)全民的共同“鄉(xiāng)愁”記憶,同時(shí)也能搭建起一個(gè)全區(qū)聯(lián)動(dòng)的江南鄉(xiāng)村文化基因保護(hù)與傳承的重大平臺(tái)。
在具體實(shí)施上可借鑒英國經(jīng)驗(yàn),在長(zhǎng)三角地區(qū)劃定“杰出景觀區(qū)域”。針對(duì)具有獨(dú)特自然地景價(jià)值的資源,強(qiáng)化對(duì)鄉(xiāng)村原生態(tài)地質(zhì)地貌、動(dòng)植物的保護(hù);同時(shí)也積極發(fā)掘當(dāng)?shù)貧v史人文資源與自然景觀的聯(lián)系,大力開發(fā)農(nóng)業(yè)、林業(yè)和其他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保證鄉(xiāng)村區(qū)域社會(huì)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充分保護(hù)當(dāng)?shù)鼐用竦睦妗?/p>
5 結(jié)語
“美麗鄉(xiāng)村”的主體是鄉(xiāng)村,鄉(xiāng)村的“鄉(xiāng)村性”直接體現(xiàn)在鄉(xiāng)村景觀風(fēng)貌上,而其中所蘊(yùn)含的能夠傳承鄉(xiāng)村地域文化的核心內(nèi)涵是關(guān)鍵點(diǎn)。新時(shí)期“鄉(xiāng)村振興”工作中“文化”與“產(chǎn)業(yè)”的振興是兩大主要方向,因此以最能代表鄉(xiāng)村特點(diǎn)的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與農(nóng)業(yè)文化為內(nèi)核的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扮演著重要角色,對(duì)于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資源較為豐富的長(zhǎng)三角地區(qū)來說更是如此。“江南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shí)作為長(zhǎng)三角文脈延續(xù)的主體形態(tài),應(yīng)該被當(dāng)作重要戰(zhàn)略資源反映在區(qū)域文化價(jià)值認(rèn)同機(jī)制構(gòu)建的多個(gè)方面[20]。因此,交叉共生而通過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形式存續(xù)的江南文化景觀,尤其是以如“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等典型形式被特質(zhì)化突顯的景觀元素與文化景觀價(jià)值觀念,值得我們?cè)卩l(xiāng)村建設(shè)工作中妥善保護(hù)、合理利用。而無論是田地農(nóng)耕、桑林養(yǎng)蠶,還是水陸共生、山間林下,都因自然環(huán)境基底與鄉(xiāng)村特有產(chǎn)業(yè)充滿了鄉(xiāng)野風(fēng)情而飽具“鄉(xiāng)村性”,可明顯區(qū)別于大眾印象中城市型江南文化景觀“古鎮(zhèn)小橋流水、城市私家園林”的一般印象,在各旅游目的地可視性文化景觀高度同質(zhì)化、城市建設(shè)“千城一面”城市病愈發(fā)常見且鄉(xiāng)村地區(qū)文化景觀系統(tǒng)亟待振興的如今,很有現(xiàn)實(shí)應(yīng)用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王建革. 19—20世紀(jì)江南田野景觀變遷與文化生態(tài)[J]. 民俗研究,2018(2):34-47,157-158.
[2]周之澄,張羽清,周武忠. 長(zhǎng)三角鄉(xiāng)村振興實(shí)踐存在的問題與對(duì)策[J]. 農(nóng)村工作通訊,2021(4):32-34.
[3]張羽清,周武忠. 江南文化與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發(fā)展問題研究[J]. 東方設(shè)計(jì)學(xué)報(bào),2022,2(1):57-63.
[4]張 松. 小·橋·流·水·人·家——江南水鄉(xiāng)古鎮(zhèn)的文化景觀解讀[J]. 時(shí)代建筑,2002(4):42-47.
[5]唐 旭. 簡(jiǎn)談江南水鄉(xiāng)傳統(tǒng)文化景觀的延續(xù)[J]. 廣西城鎮(zhèn)建設(shè),2008(12):63-66.
[6]吳燕妮. 江南地區(qū)地域性景觀設(shè)計(jì)研究[D].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xué),2011:72.
[7]許 悅. 江南園林的文化景觀傳承與發(fā)展[J]. 產(chǎn)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2019,1(12):127-128.
[8]朱志平,王思明. 價(jià)值挖掘與路徑選擇:長(zhǎng)三角地區(qū)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傳承與利用研究[J]. 中國農(nóng)史,2021,40(6):134-146.
[9]王 濤,傅盈盈,嚴(yán)夢(mèng)雨,等. 江南水鄉(xiāng)古橋文化景觀空間解譯與特色認(rèn)知研究——以紹興安昌古鎮(zhèn)為例[J]. 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與科技,2021,32(1):206-210.
[10]周武忠. 新鄉(xiāng)村主義論.世界農(nóng)業(yè),2014(9):190-194.
[11]中華人民共和國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 中國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實(shí)錄[EB/OL]. [2023-04-15]. http://www.moa.gov.cn/ztzl/zywhycsl/.
[12]中華人民共和國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農(nóng)產(chǎn)品質(zhì)量安全中心. 青田田魚[EB/OL]. [2023-04-15]. http://www.anluyun.com/Home/Product/29184.
[13]聯(lián)合國糧食及農(nóng)業(yè)組織. 全球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地[EB/OL]. [2023-04-15]. https://www.fao.org/giahs/giahsaroundtheworld/designated-sites/asia-and-the-pacific/xinghua-duotian-agrosystem/zh/.
[14]苑 利. 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與我們所需注意的幾個(gè)問題[J]. 農(nóng)業(yè)考古,2006(6):168-175.
[15]陳 艷,楊 陽,潘健峰,等. 基于“三生”空間視角的中國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研究文獻(xiàn)分析與評(píng)述[J]. 西南林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2022,6(1):16-23.
[16]徐業(yè)鑫. 文化失憶與重建:基于社會(huì)記憶視角的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價(jià)值挖掘與保護(hù)傳承[J]. 中國農(nóng)史,2021,40(2):137-145.
[17]李 明,王思明. 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什么與怎樣保護(hù)[J]. 中國農(nóng)史,2012,31(2):119-129.
[18]閔慶文. 關(guān)于“全球重要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的中文名稱及其他[J]. 古今農(nóng)業(yè),2007(3):116-120.
[19]周武忠. 東方設(shè)計(jì)學(xué)研究[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xué)出版社,2021:452-453.
[20]劉士林,姜 薇. 長(zhǎng)江文明視域下江南城市發(fā)展與文化傳承[J]. 江西社會(huì)科學(xué),2022,42(4):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