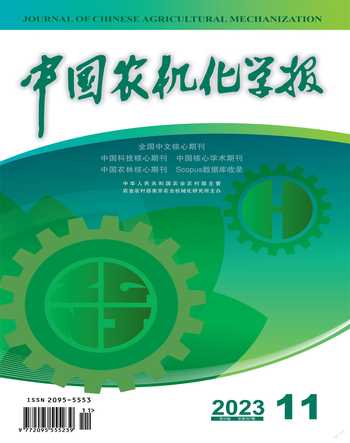目標價格政策對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分析
趙晨曉 趙達君 陳玉蘭



摘要: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棉花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則決定棉花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運用中國12個棉花主產省的棉花投入產出數據,測算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Malmquist指數并對其進行分解,采用Tobit模型估計棉花目標價格政策核心變量及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棉花每公頃收益、棉花產業聚集程度和區域環境投資力度等控制變量對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表明:我國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為1.02,安徽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最高為1.92,湖南地區棉花全要素生產率最低為0.91。目標價格政策對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無顯著影響,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棉花每公頃收益、棉花產業聚集程度和區域環境投資力度則對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正向影響。
關鍵詞: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目標價格;投入產出數據;Malmquist-Tobit模型
中圖分類號:F326.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5553 (2023) 11025808
Analysis of impact of target price policy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otton:
Based on the Malmquist-Tobit model of 12 major cotton-producing provinces panel data
Zhao Chenxiao Zhao Dajun Chen Yulan
(1. Scientific Research Department,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qi, 830012,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2, China)
Abstract: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otton,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determin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tton industry. Based on the input-output data of cotton in 12 major cotton producing provinces in China, the Malmquist index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otton was calculated and decomposed. The Tobit model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core variables of cotton target price polic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cotton income per hectare, cotton industry aggregation degree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ott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hinas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otton is 1.02, the highest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Anhui is 1.92, and the lowest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Hunan is 0.91. Target price policy has no significant indigenous effect on cott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hil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cotton earnings per hectare, cott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egree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intensity have significant indigenous positive effects on cott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Keywords:cott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arget price; input-output data; Malmquist-Tobit model
0引言
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態文明發展理念,綠色農業發展受到各級政府的廣泛關注,我國傳統種植農業開始向生態友好農業加速轉型。十九大報告強調經濟發展要注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概念,倡導加快我國農業綠色發展進程,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重申“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要求。綠色發展和生態振興已成為新時代農業發展的方向,同時我國農業綠色發展也面臨諸多現實挑戰,地膜殘留、化肥農藥過度施用、農業機械使用的二氧化碳排放帶來的農業點源及面源污染,致使農業生態環境持續惡化。農業綠色發展日益受到學術界的熱烈討論,與之相關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
棉花是我國最重要的戰略物資,也是僅次于谷物的第二大農作物,而棉花產業和下游產業聯系緊密,對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重大影響。為了穩定棉花生產并保證棉農基本收益,于2014年開始實施的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以來,棉花單產水平、總體質量以及棉花產業集聚有了明顯提高,政策效果十分顯著。棉花種植生態環境同樣面臨巨大威脅,我國棉花主產區廣泛存在地膜殘留、化肥農藥過度施用、土壤板結、土壤肥力下降等環境問題,嚴重影響了棉花產業可持續發展。
目前針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早期的全要素生產率研究多以特定區域的大農業為研究對象[14],隨后大量研究開始轉向糧食、林果及其他經濟作物等[57]。隨著非期望產出理論在農業經濟研究領域的應用,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成為新的研究熱點,大量學者將環境因素納入非期望產出,運用數據包絡法、超效率SBM等模型使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研究更加科學全面[810]。作為我國最重要的經濟作物,棉花的全要素生產率也得到廣泛關注,初期研究多以一般DEA方法的全國整體、三大棉區以及各棉花主產省區域進行研究[1112],近年來的研究熱點亦開始轉向考慮環境非期望產出因素的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并分析其影響因素。多在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基礎上采用Tobit模型進行估計,研究結論較一致:全要素生產率呈波動趨勢,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棉花人均種植規模、環境投資等對棉花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影響[1315]。
鮮有學者從棉花目標價格政策視角研究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高升等[16]基于時間序列數據分析了目標價格政策前后我國棉花生產效率的差異;王利榮[17]采用新疆、河北、山東、安徽四省區農戶棉花目標價格補貼額度調研數據考察棉花目標價格政策對生產效率的影響,丁建國等[18]采用類似調研數據對新疆不同縣域的目標價格影響進行分析得出相同的結論,目標價格政策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三位學者的研究在指標選取方面稍有局限。主要原因是:從目標價格政策實施過程來看,農戶獲取的每公頃平均補貼金額取決于每公頃產量,而每公頃產量則是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產出指標。當其他條件不變時,每公頃產量帶來每公頃補貼金額增加,亦引發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同步上升,因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和補貼金額間存在內在的產量傳導關系,也就是說采用補貼金額反映棉花目標價格政策對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內生性問題。
棉花目標價格政策在保證棉花生產穩定基礎上是否對該產業的綠色發展造成影響是本文的關注重點。研究選取了我國2005—2021年12個棉花主產省的棉花投入產出數據,測算了各省份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M指數,在控制其他變量基礎上,運用Tobit模型考察目標價格政策對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本文將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實施情況進行分類,將全額補貼的新疆定義為“3”,參照新疆60%補貼的河北、江蘇等9省份定義為“2”,未實施目標價格政策補貼的山西、陜西定義為“1”。將目標價格政策實施情況分為無、部分、全部的定性分類方法來考察目標價格政策對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1棉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度及分析
1.1Malmquist指數
1.2指標選取及變量說明
1.2.1指標選取
中國的棉花產量居于世界首位,主要種植地區有新疆、甘肅、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安徽、江西、江蘇、湖南、湖北等12個省份。本文采用2005—2021年間的面板數據,其數據來源于2006—2022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及各地區統計年鑒、統計局網站,選擇了棉花投入和產出兩類指標。土地投入指標為土地費用,勞動力投入選擇家庭用工天數和雇工天數之和計算,農業資本投入為棉花種植過程中的化肥數量、每公頃農藥費用、農膜費用、機械費用及其他費用[6]。棉花單產、二氧化碳排放量、勞動力投入、化肥投入、農藥投入、農膜投入均采用每公頃平均投入數量,為消除年份間的價格影響,費用類指標均以2005年基期價格水平測算[21],以保證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測算結果的準確性。
期望產出指標為棉花單產,非期望產出為棉花生產過程的碳排放量,具體指標選擇情況如表1所示。
1.2.2非期望產出
1.3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算結果與分解分析
本文使用Deap2.1軟件對中國12個棉花主產省2005—2021年的棉花投入產出數據進行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Malmquist指數測算及分解,并根據結果分析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情況。
如圖1所示,2005—2021年間我國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略有波動且增速度較緩慢,技術效率、技術進步,以及規模效率有略微下降,表明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出現的負增長阻礙了棉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2007—2008年間我國棉花主產區總體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達到峰值為1.359,同年的技術效率也達到最大值1.013。2008—2009年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均達到最大值,二者均呈現“M”型增長。我國棉區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的雙重驅動能提高棉區綠色化發展水平,而技術進步的均值大于技術效率變化,表明技術進步會引起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同時規模效率不高導致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下滑。
從基于時間維度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來看,2005—2010年間我國棉區綠色全要素增長率呈現“W”型波動,隨著2007年首次提出生態發展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上升趨勢推動了棉花產業綠色化發展,但并未能一直保持在增長狀態。2011年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達到1.000,三者呈現波動性變化趨勢。2011—2013年間實施了棉花臨時收儲政策,棉花數量有了明顯的增長,種植規模逐漸擴大,2015年后規模效率由0.868增加到1.024,平均增長率約為3.300%。2019年我國棉花綠色全要素增長率再次達到最大值1.104。2014年取消臨時收儲政策開始實行目標價格改革旨在促進棉農增收。2015—2021年,純技術效率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了反變化關系,規模效率稍有下降趨勢,2021年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達到0.956。
如表3所示,從基于省份維度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來看:西北內陸棉區的新疆和甘肅總體類似,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呈現“W”型周期波動增長趨勢,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平均值分別為1.03和0.98,均在2021年達到最大值1.09和1.49。其中分解結果顯示技術進步呈下降趨勢,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在提高;黃河流域的河北和河南省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在2008年均達到最大值分別為1.73和1.85,山東省在2021年達峰值1.84,陜西在2018年達到峰值1.41,山西省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情況較穩定無明顯變化,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約為1.03;長江流域的江蘇、湖北、安徽省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保持在上升趨勢,峰值分別為1.38,1.34,1.92,湖南省在2015年達到最大值1.30后有了明顯下降,江西省在2011—2019年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連續出現下滑,平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為1.00。
2目標價格政策影響的Tobit模型分析
2.1面板Tobit模型
Tobit模型也叫做受限因變量模型,最早由Tobin提出,其特點為方程含有一定的約束條件,并且為連續變量。M指數測算得到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值為離散變量,本文通過歸一化處理將其變為截斷變量以滿足Tobit模型的條件,模型構建如式(6)所示。
2.2數據來源與指標選取
2014年國家對新疆棉區開始進行目標價格改革,按照逐年制定目標價格的方法補貼;根據查閱其他省份棉花補貼的地方政策,河北、江蘇、安徽、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甘肅九個省參照新疆補貼標準的60%進行補貼;山西和陜西無補貼。棉花目標價格政策旨在穩定棉花生產,注重提質增效保障棉花供給,在棉花播種面積穩定的條件下提高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通過市場交易價格和棉花目標價格補貼確定單位面積補貼標準,棉花種植面積與補貼金額呈現正向變動關系,棉農為保證盡可能獲得多的補貼會增加投入要素提升技術效率,或采納新技術使生產技術由傳統方式走向現代化發展,調整棉花生產結構有助于推廣機械作業提高規模效率,棉花目標價格政策引起技術效率、技術進步、規模效率變動共同影響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改變,但棉花目標價格政策是否是影響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因素是本文考察的重點內容。
國家自2014年開始實施棉花目標價格改革,各地目標價格補貼額度存在差異,本文研究棉花目標價格改革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采用了2005—2021年12省份的面板數據。核心解釋變量為棉花目標價格政策,將無補貼的地區定義為1;將新疆全額補貼定義為3;其他為部分補貼的地區定義為2。通過將棉花目標價格政策定義為分類變量以消除內生性,更好地反映目標價格政策的執行程度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控制變量選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棉花人均種植規模、棉花每公頃收益以及地區環境投資額,參考前人的研究[1719, 2223],本文認為棉花人均種植規模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有正向影響,人均種植規模更加利于開展機械化作業提升規模效率,引起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加;棉花每公頃收益越多棉農可能會增加棉田的投入要素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地區環境投資額表現為地區對農業環境的投資力度,對農業環境污染治理能力越強,農業生產中污染越小,因此預期方向為正。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可能導致農業地位降低,也可能加大對農業科技的投入力度,因此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無法確定。指標選取情況如表4所示。
2.3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5為棉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及影響因素的描述性統計,通過對比發現各省份和年份之間的影響因素存在明顯差異。
在計算時為了便于模型估計,對控制變量的數值取其自然對數處理。
2.4Tobit模型回歸結果與分析
2.4.1多重共線性檢驗
為保證模型估計的準確性,通過VIF檢驗對自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得到VIF的平均值為1.310,結果說明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模型構建良好。
2.4.2模型結果及分析
考慮到模型的穩健性以及異方差和序列自相關的影響,本研究選用Tobit模型為主,最小二乘法、廣義矩估計等方法為參考模型,各模型估計結果無明顯差異,模型估計及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
目標價格政策能正向影響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但影響效果不顯著;控制變量中棉花人均種植規模、棉花每公頃收益、地區環境投資額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正向影響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每提高1%,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會提升2.3%,并且這種正向影響在5%的水平上顯著。
1) 目標價格政策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無顯著影響。這與前人的研究不一致。從產出(期望產出)角度來看,棉農都希望自身的產量值達到最大,目標價格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棉農的投資行為,當投資增加,棉花生產帶來的碳排放量(非期望產出)也會增加,同時降低期望產出,所以目標價格政策產生了溢出效應,使得棉農為了提高收入而增加投資力度,從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得知,產出增長幅度小于投資力度。和沒有目標價格政策的區域相比,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并無顯著差異。
2)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棉花每公頃收益均在1%的水平上對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棉花每公頃收益每提高1%,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分別會提升0.02%和0.03%。二者共同促進了棉花綠色化發展,也關系著土地資源、人力資源科技的合理利用程度,從而提升棉花產區的經濟和生態效益。
3) 棉花人均種植規模能顯著拉動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棉花人均種植規模每提升1%,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會提升0.01%。綠色化發展不能僅憑一家一戶,更需要連片的土地。土地和農用物資的集約能最大化發揮效用,有利于管理人員和科技人員的專業化和精簡,并且統一購入農用物資還可以降低單位成本,以減少投入費用的方式,提高棉花主產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4) 地區環境投資力度越大,棉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越高。這種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性,并且地區環境投資力度每提升1%,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能提升0.03%。碳排放已經成為一個熱點話題,我國的政策大多表現在污染治理和約束碳排放,政府的投資在一定程度上能促進地區采用綠色生產方式,減少棉花生產中的碳排放和污染,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2.4.3穩健性檢驗
本文從以下三方面進行穩健性檢驗:Tobit Ⅳ為隨機刪去一年的樣本重新估計結果;TobitⅤ為刪截因變量上下1%部分作縮尾處理的重新估計結果;Tobit Ⅵ為去除三個部分補貼的省份進行回歸的結果。如表7所示,三種穩健性檢驗結果均與原模型結果相似,研究結果較穩健。
3結論
采用同期目標價格政策實施程度的不同省份面板數據,比相同地區政策實施前后的0-1變量衡量更準確;同時對目標價格政策采用三分類定性變量重新定義,彌補了已有研究中采用農戶補貼金額衡量目標價格政策考察全要素生產效率時存在明顯內生性的問題,更科學地衡量了政策本身是否對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
1) 通過Malmquist指數測算得出我國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均值為1.024,2008—2009年間出現波谷數值0.71隨即開始上升,全要素生產率在2009年出現最大值1.359,2021年出現最小值0.956,2005—2021年間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整體呈現“W”型變動趨勢,表明我國棉業綠色發展狀況在逐漸向好發展但穩定性欠佳。西北內陸棉區中甘肅省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最高為1.49,黃河流域棉區中山東省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最高為1.84,長江流域棉區中安徽省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最高為1.92。綠色實行棉花收儲政策之前呈現“N”型變化趨勢;實行棉花收儲政策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略有降低;實行目標價格政策后稍有上升趨勢但不明顯。純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帶動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規模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未達到最優狀態,遏制了棉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阻礙整體綠色化發展。通過分省測算結果表明,江西省在2010年達到最快增長速度,河南省在2009年出現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劇烈下滑。
2) 目標價格政策的實施未能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顯著提升。目標價格政策在保障農戶基本收益的同時提高棉花單產,農戶更愿意對棉花投資導致增施化肥帶來的非期望產出增多,另外由于邊際效益遞減規律,產出增長幅度小于投資幅度使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更快。本研究采用類別變量反映目標價格的程度,研究結果顯示目標價格政策的執行程度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無顯著差異。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棉花每公頃收益、棉花人均種植規模和地區環境投資力度均對棉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棉花每公頃收益的提升為棉業綠色化發展提供了經濟基礎;擴大棉花經營規模能解決昂貴的人工費用,同時又能為棉農增收提供現實保障;加大環境投資力度能夠約束棉農行為,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參考文獻
[1]劉洋, 吳育華. 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變動: 1995—2005[J].中國農機化, 2008(6): 41-44.Liu Yang, Wu Yuhua.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as agriculture industry: 1995-2005 [J]. Chines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2008(6): 41-44.
[2]劉春明, 陳旭. 我國糧食生產技術效率及影響因素研究——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Translog-SFA模型的分析[J]. 中國農機化學報, 2019, 40(8): 201-207.Liu Chunming, Chen Xu. Study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Analysis of Translog-SFA model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e [J]. Journal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2019, 40(8): 201-207.
[3]余泳澤. 異質性視角下中國省際全要素生產率再估算: 1978—2012[J]. 經濟學(季刊), 2017, 16(3): 1051-1072.Yu Yongze. Estimation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ity: 1978—2012 [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7, 16(3): 1051-1072.
[4]張利國, 鮑丙飛. 我國糧食主產區糧食全要素生產率時空演變及驅動因素[J]. 經濟地理, 2016, 36(3): 147-152.Zhang Liguo, Bao Bingfei. Empirical analysis on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orces of food total factor production in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of our country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3): 147-152.
[5]方國柱, 祁春節, 雷權勇. 我國柑橘全要素生產率測算與區域差異分析——基于DEA-Malmquist指數法[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 2019, 40(3): 29-34.Fang Guozhu, Qi Chunjie, Lei Quanyong. Calculation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itrus in China and the difference of region—Based on the DEA-Malmquist index method [J].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9, 40(3): 29-34.
[6]李學林, 李隆偉, 董曉波, 等. 云南省糧食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研究[J]. 農業技術經濟, 2019(10): 102-113.Li Xuelin, Li Longwei, Dong Xiaobo, et al. A study on decomposition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grain in Yunnan Province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9(10): 102-113.
[7]楊雪, 何玉成, 閆桂權. 碳排放約束下中國大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與分解[J]. 大豆科學, 2019, 38(3): 460-468.Yang Xue, He Yucheng, Yan Guiquan. Growth and decomposition of Chinas soybe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under carbon emissions [J]. Soybean Science, 2019, 38(3): 460-468.
[8]郭永奇, 侯林岐. 中國糧食主產區糧食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度及影響因素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20, 40(19): 223-229.Guo Yongqi, Hou Linqi. Study of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grain agriculture in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of China [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20, 40(19): 223-229.
[9]吳傳清, 宋子逸. 長江經濟帶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度及影響因素研究[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18, 35(17): 35-41.Wu Chuanqing, Song Ziyi. Study on the measurement and affect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8, 35(17): 35-41.
[10]紀成君, 夏懷明. 我國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區域差異與收斂性分析[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 2020, 41(12): 136-143.Ji Chengjun, Xia Huaiming. Study on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on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0, 41(12): 136-143.
[11]岳會, 于法穩. 中國棉花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研究——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分析[J]. 價格理論與實踐, 2019(10): 43-47, 166.
[12]陳玉蘭, 王嬌, 魏敬周. 基于DEA模型下新疆棉區棉花產業運行效率評價[J]. 江蘇農業科學, 2016, 44(7): 558-562.
[13]王曉珍, 鄒鴻輝, 楊拴林, 等. 高技術產業R&D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區域形態及影響因素分析[J]. 現代經濟探討, 2017(7): 1-8.
[14]李丹, 曾光, 陳城. 中國柑橘全要素生產率演進及影響因素研究——基于Malmquist-Tobit模型的實證[J]. 四川農業大學學報, 2018, 36(1): 118-124.Li Dan, Zeng Guang, Chen Cheng. Measuring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itus in China and studying its influence factors—Th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Malmquist-Tobit method [J]. Journal of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8, 36(1): 118-124.
[15]湯杰新, 唐德才, 吉中會. 中國環境規制效率與全要素生產率研究——基于考慮非期望產出的靜態和動態分析[J]. 華東經濟管理, 2016, 30(8): 86-93.Tang Jiexin, Tang Decai, Ji Zhonghui. A study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fficienc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Static and dynamic analyses based on consideration of the undesirable outputs [J].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2016, 30(8): 86-93.
[16]高升, 鄧峰. 目標價格政策對我國棉花生產效率影響評價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指數模型和變系數模型[J]. 價格理論與實踐, 2019(9): 54-57.
[17]王利榮. 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棉花生產效率的影響分析[J].農業經濟與管理, 2021(3): 50-60.Wang Lirong. Effect analysis of target price subsidy policy on cotton production efficiency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1(3): 50-60.
[18]丁建國, 穆月英. 目標價格政策對棉花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分析——以新疆棉區為例[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0, 33(4): 113-120.Ding Jianguo, Mu Yueying. Impact of target price policy on cott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 case study of Xinjiang [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33(4): 113-120.
[19]Hollingsworth B, Dawson P J, Maniadakis N. Efficiency measurement of health care: A review of non-parametric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J]. Health Care Management Science, 1999, 2: 161-172.
[20]Mohtadi H. Environment, growth, and optimal policy design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6, 63(1): 119-140.
[21]王智勇. FDI對中國產業效率的影響——基于1989—2010年地市級面板數據的研究[J]. 當代經濟科學, 2015, 37(1): 87-97, 127.Wang Zhiyong. The effects of FDI on Chinese industrial efficiency—The study based o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pane data from 1989 to 2010 [J].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2015, 37(1): 87-97, 127.
[22]冉啟英, 周輝. 環境約束下農業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 基于SBM-TOBIT模型[J]. 經濟問題, 2017(1): 103-109.Ran Qiying, Zhou Hui. 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under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Based on SBM-TOBIT model [J]. On Economic Problems, 2017(1): 103-109.
[23]Mosier A R, Duxbury J M, Freney J R, et al. Mitigating agricultural emissions of methane [J]. Climatic Change, 1998, 40: 3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