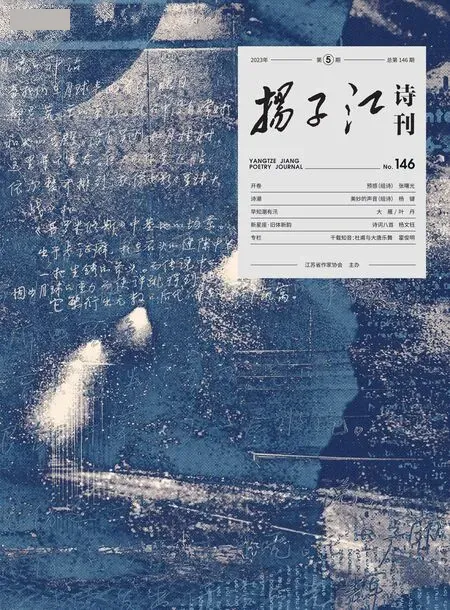激進的創變
——張曙光訪談錄
苗 霞 張曙光
苗霞(以下簡稱苗):從創作年表得知,你從1979 年開始寫詩,至今已有40 余年,在我看來,守望先鋒是你一直不變的立場。初登詩壇時你就以“敘事性”有力抗辯、沖擊當時詩壇浮夸空洞的假抒情的調式。到2017 年的《看電影及其他》,新變始生:敘事性開始弱化,即使某些詩仍有外在的敘事框架,也僅是一種托詞。場景與細節拉長并放大;向內挖掘與向外投射疊合;日常瑣屑的生活經驗和玄學、抽象的純粹思辨混搭。到了2019 年的《雪的色情與謀殺》,則彰顯出一種藝術風格的巨變:無意識狀態下的碎片化寫作。請問,你認可我如此的描述嗎?在你內心,是否還有另一條不同的創作變化線路?
張曙光(以下簡稱張):相比于先鋒,我喜歡前沿的說法。先鋒就我的理解,是無所顧忌地一往無前,與傳統在最大限度上決裂。而前沿則保持了對新事物的關注,態度卻不那么激進,和傳統也會保持著一定的聯系。我們這代人在文化極度匱乏的情況下成長起來,在開始寫詩時情況稍有改變,但遠遠沒法和現在相比。我和其他詩人們一樣,寫詩都是自我教育的結果。盡管自1970 年代末新的東西開始陸續進入中國,但也只是零零散散,無論引進還是研究都談不上系統,寫作只是在螺螄殼里做道場,全憑自我摸索。但這也養成我關注新事物的習慣,不斷求新。當一個人對整體文化缺少了解,對藝術的邊界沒有認識時,又怎么能談得上先鋒?那時的先鋒,充其量是一種姿態,并沒有多大的實質意義。
說到變化線路,你提供的是一種高度概括,實際情況要更復雜些。我在1978 年寫下了我的第一首詩,真正進入寫作是在1979 年,這之前讀過一些古詩詞,現代詩也讀過一些,比如聞一多、艾青的,外國詩人普希金讀得最多也最早,上大學后又讀了拜倫、雪萊,還有戴望舒譯的洛爾迦。1979 年我讀到袁可嘉的一篇關于西方現代派的文章,這是第一次接觸現代派詩歌。我在惶惑之外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后來陸續讀到了《荒原》、葉芝和弗羅斯特等人的詩歌,感到自己的寫作過于陳舊,一直想尋找一種新的寫法。直到寫出了《1965 年》。這首詩后來被稱為敘事性寫作,但里面真正重要的是現代感。到了上世紀90 年代初,我寫下了《尤利西斯》這樣一批詩,這些詩重點不再是敘事而是情境。我試著在語境轉化間做一些嘗試。到了上世紀90 年代后期,又回到了敘事性,但已把這兩個時期的特點結合起來。以后的寫法在這兩種方式間搖擺,直到2018 年,出現了較大的變化,這些或許可以稱作反敘事吧。
苗:我們知道,文學史上有兩種先鋒:一種是“懷舊的”先鋒派,“溫故而知新”,歷史上,每向前一步的進展,往往是伴著向后一步的探本窮源;一種是變革的先鋒派,它對技術革命做出了有力的反應。它不斷地創新和變革,追求一種創造的狂歡。而你無疑是后者,并且是擺脫了“運動”意味的具有個人性的“先鋒”,真正具有“先鋒”的品格。但在當代詩壇,“先鋒”不僅被符碼化,還被庸俗化。就如你詩中的那頂巴拿馬軟帽,可以被安置在任何一個詩人頭上,盡管感覺怪怪的。有人從語言創新的維度,有人從形式技巧創新的維度。但我認為,無論哪一種界定都是以偏概全的,只見枝節不見根底。先鋒首先建立在一種對自身所處時代的敏感性之上,新的想象、新的感知、新的認識是對生活、世界、所處時代中還遠遠沒有顯露出來的歷史的、人心的、勢能的那樣一種潛能的前瞻式表達。先鋒,究其實質,是回應歷史巨變的問題,捕捉大變局中的跡象和歷史變化的信息。結合自己的創作經歷,你如何看待我這種評述?
張:我同意你的評述。人們對先鋒有很多誤解,尤其是容易把創新和先鋒混為一談。這可能是詩歌的現狀過于沉悶,缺少活力,稍有創新,便被當成了先鋒。文學上激進和保守并存,當然并不是先鋒就一定好、非先鋒就一定不好。但先鋒激進而超前,并且與傳統徹底決裂,正是這種看似過激的做法,才會導致文學藝術上的發展,也是走出困境的一個出路。
先鋒是一種態度、一種品格,一往直前而不顧及其他。它總是面向未來,失之偏頗卻能開創潮流。而現在所謂的先鋒在一些人那里只是一種姿態,或一種營銷方式。當然先鋒過于激進了,在矯枉的同時會造成與傳統的斷裂。真正優秀的作家或詩人總是在保持先鋒姿態的同時不忘從傳統中吸取養分,但是如果離開了開創,那么一切都無從談起。我們不妨看看一個多世紀前的創作。如果我沒有記錯,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的情歌》寫于1915 年,《荒原》寫于1921 年,這些詩歌今天我們讀來仍然會感到震撼。還有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寫于差不多的年代,稍晚些的《芬尼根守靈夜》,以及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這些在一百多年后我們仍然沒有能夠達到并且超越。國內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先鋒派,更多是一種姿態。我也算不上先鋒派,這個名稱讓我受之有愧。充其量我只是具有某種先鋒意識。
苗:你的寫作姿態一直是前傾的,古典質素在你詩歌中很少體現。但我通過你的詩外文字如訪談錄、札記、批評、信件等獲知,你關于古典詩歌和古典詩學的學養甚富,并且也有不少極喜愛的詩人,如陶淵明。但這種認知和喜愛并未轉化為你詩歌創作中的認同。請問你是如何看待古典性和現代性的?在詩歌中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
張:在上大學之前,我就讀過很多古典文學作品,我的古代文學修養可能比我的外國文學修養要好,盡管仍然是一知半解。這些閱讀對我一生的影響是深遠的,早已內化成為我的精神氣質。后來我開始大量閱讀西方文學作品,只是作為他山之石,說得好聽些,是為了實現一種世界文學的格局,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彌補我在文化上的缺失。
我認為,一個人的文化氣質決定了他是什么人,而不是靠服裝或其他外在的東西。一些人,包括某些漢學家,都會認為我的詩西化,如果他們真正讀進去,就會發現精神氣質仍然是中國化的。而新詩從一開始就是借鑒了國外詩的形式,以抵消舊體詩的影響。在我看來,無論中外,所有好的東西都應該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都應該繼承。當然,繼承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種自己的詩學體系,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我骨子里是中國人,無論穿西裝、T 恤還是長衫,都改變不了我是中國人這樣的事實,從外形上就不會被認錯。但為什么我穿T 恤不穿長衫?因為除了我是中國人,同時也是一個現代人。現代人的特質我想應該具有一種全球眼光,順應時代的潮流,接受一切有益的東西,而不是死守自身的傳統。至于沒有形成創作上的認同,如果你說的不是內在精神,而只是形式和手法,那么確實是這樣的,甚至有一段時間我要努力排除古典詩在形式和語言上對我的影響。原因很簡單,是為了拋開對古典詩寫作上的因襲,尤其是那些陳腐的東西。古典詩歌所以被新詩所取代,不是因為不夠成熟或完美,而是它不再具有創新機制,也不太可能體現現代性。盡管新詩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還沒有達到古典的高度和完美,但得天獨厚的是它具有創新機制,而且能更好地表達我們現代人的經驗和感受。這一點非常重要。古典詩在形式和技法上無法與這個時代對接,也很難與新詩對接。我們今天讀古典詩,是為了加強我們的文化修養,提升境界和格調,但如果照搬形式技藝或語言,那就未免本末倒置了。
在我的寫作中,確實會透露出一種古典特性,你可以看作是古典主義的影響。簡約、樸素、控制、均衡。這也是很多人不喜歡我的詩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在外在感覺上不夠激烈,這還是用浪漫派的標準來衡量。但這種古典精神使得我的詩很耐讀。我花了三年時間翻譯了但丁的《神曲》,我認為這是我最好的翻譯。如果不是喜歡,以我的性格是堅持不下去的。而且,我也想在翻譯中學到但丁詩藝中的某些東西。記得1986 年看了奧運會開幕式的表演,我深受觸動。那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羅納,會標是米羅畫的。今天看那時的我可能有些像井底之蛙,但我確實被震撼到了。我很喜歡里面充滿想象力和現代感的演出。我當時就確定了我的寫作主張:古典精神,現代技藝。這個想法在很長時間內主導著我的寫作。
苗:最近幾年,碎片化是你寫作的一個顯在特征,環境碎片、意象碎片、幻覺的夢境的碎片、意識的碎片、語言詞匯的碎片、感覺體驗的碎片等,不僅在外部形式我們看到文體的碎片特征,在文本的內部也刻錄著抒寫主體思維上的碎片性。比如2018 寫出的一首詩《復制》,甚至幾乎全是碎片化語詞的拼貼。但一首詩之所以能站立起來,靠的是結構,結構是所有構成的總和,它的動力也正產生于突出和未突出的構成之間的緊張狀態。能談談你創作時的結構意識嗎?
張:人們習以為常地把碎片化當作后現代的一個特征,卻忽略了一種創作手法總是有著現實的依據。現代生活的節奏越來越快,世界也變得復雜而陌生。大量相關的和不相關的信息紛至沓來,包圍著我們。我們對外部事物的認識不是更加完整,而是支離破碎。如果說以往我們認為外部世界是完整的,可能是以偏概全,或是在意識中對它進行了整合,人為賦予它以意義。但事實上我們接觸到的只是一個個不同的碎片。我們的內在體驗也在分裂。既然現實不再是完整的,作為寫作者,他會用這些碎片整合成一個近似自己心目中的現實。而把這些不同時空和維度的內容放置在一個平面,也許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而這正是我想嘗試的。
你提到的《復制》盡管看上去是由一些片斷組成,但還是有一個相對完整的結構。復制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同本雅明的“復制”理論、詹姆遜的“類相”或拉康的“鏡像”有著某種關聯。總之我覺得復制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行為,我們不斷地在復制著自己,也在復制著身邊的一切。在復制中個性不再是唯一的,完全同質化了。我們只是一個個復制品,而且還將無限地繁衍下去。然而這首詩帶有某種游戲的性質,圍繞著我和對我的復制而展開,逐漸向周圍擴散。我和我周圍的一切,乃至整個世界,都會被復制。這可以理解為藝術產生的過程,從自我出發進行復制,并不斷向著周圍擴展。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我有意讓語言或意識具有一種自主性,讓它自身也在不斷繁衍,而進行創作的“我”只是作為一個觀察者,并適當保證不要溢出界限。
苗:在你的創作中,日常生活的表達從未缺失過,這表明你一直試圖在當代生活的背景里傳達個人經驗的深度。但不同的是:日常生活之前作為經驗內容,而今作為形式結構。我認為這種轉變立足于詩歌思維、感覺和想象方式的變化。你能具體談談轉變背后的詩學觀嗎?
張:我以往的寫作重在關注和呈現現實經驗,這在很大程度上要借用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我認為這種日常化更能代表生活的本質,體現我們當下的生存狀況。而眼下我的寫作偏重于碎片化的寫法,這并不是要取消日常生活,或脫離現實,而是通過生活的碎片重新構建一種現實,一種我所理解或認為的更接近本質的現實。把不同層面的日常生活組合在一起,會產生一種奇妙的效果。當然對于同一事物,每個人都可能具有不同的看法,“橫看成嶺側成峰”,也可能是看山是山,或看山不是山。這就造成了一種割裂,也由此說明現實只是每個人理解的現實,并隨著我們的主觀意識而變。“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與“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哪一個更真實?真實又是什么?世界太大,又太復雜,我們所能把握的只是局部,或局部的局部,充其量只是一些碎片。我們都知道瞎子摸象的故事,每個人對感知對象的理解是不同的,有的說大象是蒲扇,有的說大象是繩子、是柱子、是墻。也許每個人的感覺都是實在的,但他們說的是大象嗎?那么把他們的感覺加在一起,是不是能夠還原出大象的原貌?仍然不能,因為缺少必要的結構,即構建。人們往往只看到碎片,卻往往會忽視后面的建構。當然,很多時候這些碎片會有幾個不同的點,向外發散出意義。胡塞爾提出“看”的概念,只要看,不要想。但對于同一事物,每個人看到的可能都不盡相同。不光有視力和視野上的區別。有人根據病跡學的原理,認為梵高的畫在我們看來是偏重黃色,在有黃疸病的梵高那里卻是正常的。單眼的我們看一件東西和復眼的蒼蠅會是一樣嗎?最近大家都在談論的量子理論,這門科學似乎證明了一切都是意識的產物,和中國古人所說的萬物皆備于心高度一致。記得當時有人問王陽明,深谷里的花不為人見,是否還會存在?王陽明回答說當花不被看見時是處于一種寂滅的狀態。我記得是這樣。這其實正像薛定諤那只放在盒子里的貓,處于一種非生非死的疊加態,有待于觀察者的出現而確定。而雙縫實驗證明,觀察者的在場會出現不同的結果。現實與其說是像過去那樣,具有一種整體和客觀性,可以通過作品來再現,不如說,現實是意識的投射,是自我分析的結果。
另一方面,人們的思想觀念隨著技術的進展也有所改變,對事物的感知和審美肯定會發生變化,現實不再是統一的、完整的,而是支離破碎、浮光掠影。這一方面導致了碎片化的產生,同樣,對于意義我們也會產生疑慮。意義的不確定性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在我看來,卡夫卡的小說開創了意義不確定的先河。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這一特點。所謂意義,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強加在作品中的,以便將能指順利地引入所指,用巴特的話講,就是讀者的寫作,是作者將意義放在盤子里端給讀者去享用。但刻意去體現意義,總是顯得過于主觀,且簡單化,是對豐富性的取消。真正好的作品,呈現出的意義總是復雜的、多義的、不確定的,事實上生活就是如此。正如羅蘭·巴特把作品分為可讀的和可寫的,后者能最大限度讓讀者參與進來,在作品里發揮自己的辨析力和想象力,挖掘并賦予意義。正是這些觀念,促使我近年來的詩歌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苗:你一直都有著鮮明的語言自覺意識。早在上世紀90 年代末的《90 年代詩歌及我的詩學立場》一文中你就寫道:“漢語詩歌的局限性在最大程度上是它使用的那種語言的局限性,而詩人們正是要通過對語言自身局限的克服來豐富和發展那一種語言,從而實現它自身的價值和魅力。”綜觀當代詩人在語言上的探索,我認為,具體呈現為如下幾種語言策略:1.清除詞語上的層層油彩抵達原初語義;2.借語境置換深挖語義潛能;3.松綁甚至切斷詞語板滯的語法邏輯;4.詞匯選擇上的雜食性。能談談你在語言上的探索嗎?是否和上述的路徑不一樣,并且在40 余年的創作史中是否呈現不同的語言特征?
張:語言的自覺意識是每個詩人都應該具備的。語言是人類認知和思考的基礎,或者說,語言就是認知和思考本身。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語言是存在的家園。我們棲身在語言中,離開了語言我們什么也做不了。尤其是詩人,受惠于語言,更是對語言負有責任。一味贊揚自己的母語從出發點說也許是好的,但發現母語的局限并在最大程度上去加以修補才是真正負責任的態度。當然做起來很難,但作為以語言安身立命的詩人來說,這是一種責任。你對語言的概括很全面,國內很多詩人都自覺不自覺地在這些方面做出了努力。我在以往的寫作中追求語言的自然質樸,力求在平淡的語言中包含更深的意蘊。概括說,過去我一直堅持使用日常語言,而近年來卻有所改變,即在日常語言的基礎上去除其自然性,而盡力讓語言變得含混而多義,充滿新奇感和陌生化的效應。這一轉變,應該是從2018 年開始,但既然我們談論詩歌語言,我理解詩歌的語言有狹義和廣義的兩種。廣義的詩歌語言應該包含更多的內容。比如,我們說色彩和線條是繪畫的語言,音樂的語言是旋律、節奏、音色和調式,那么,詩歌語言是否應該包括修辭、句式和技法等內容?說詩人要豐富語言,除了我們日常使用的語言外,是否還要包括增加詩歌的技藝?
苗:我發現,你近期詩歌多了一個藝術特征:客觀、審慎的反諷,它常常來源于現實性之各個不相稱層面的并置或沖突。正如你在一首詩中寫的:“就著包子喝咖啡。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發明。”反諷辯證法既是我們的現實處境,又是我們的認知方式。要立足于歷史、思想、文化的維度來理解你的反諷。但是,我們知道,反諷,味道辛辣力道勁爆,極易失控。你又是如何把它控制在詩味之內的?
張:反諷,也許還要加上一點調侃,至少在你提到的這個句子中是這樣。關于就著包子喝咖啡,并非我的創造,而是實有其事。在“喜馬拉雅”平臺上聽到一個談話類節目,里面提到了某著名品牌的飯店里推出了這類套餐,覺得好玩,后來就用到了詩里。在我看來,反諷也是一種解構。人們都說藝術高于生活,但我越來越覺得藝術哪怕是孫悟空,也始終跳不出生活這位如來佛的手掌心。任何想象都不會是憑空產生,都是有著生活基礎的。過去認為卡夫卡小說、荒誕派戲劇還有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里面的情節都是靠作家想象出來的,也許是這樣,但這些肯定都在生活中發生過,只不過被賦予了一種更普遍的意義罷了。說到反諷,數年前,看到一個譯者在譯奧登時說過的話,他說奧登的《美術館》里面有一句“關于苦難,他們從不會錯”,而最初穆旦譯成了“關于苦難他們總是很清楚的”,“從不”或“絕不”同“總是”,有著程度上的不同,其中的反諷意味就削弱或消失了。那位譯者說,這不能怪穆旦,因為那時候的詩人們不懂得反諷。不知情況是否真的是這樣,但反諷直到現在在我們的詩中用得還是很少。反諷是皮里陽秋,表面上不動聲色,卻暗加嘲諷或諷喻。寫作不要太用力,那樣自己累別人看著也累,要像打太極一樣把力量蘊含在看似輕松的動作中。其實中國古典詩一直講究含蓄蘊藉,而現在的詩卻往往都是正面言說,或義憤填膺,或淚流滿面,唯恐別人不知道他的態度,這可以說就帶有了表演性質,而忽略了詩的含蓄,降低了藝術的成色。其實把握了反諷的本質,一切都恰到好處,運用起來并不困難。
苗:矛盾修辭法是你一貫的語言特征和思維方式,但我感覺,這其中還有悄然的不起眼的變化。之前,是以遲疑不決的、試探性的口吻完成正和反、矛和盾的上下、左右、里外的輪轉,而今很多相互悖反的話語卻以鏗鏘昂然的宣判調子出現,是和非是的語氣都是那么堅信不疑。這也是你詩篇中出現得越來越多的句號,每個句號既是有力的結束,又是一種嶄新的開始。你認可我這樣的理解嗎?
張:我認同你的看法。葉芝說過這樣一句話,同別人爭吵產生雄辯,同自己爭吵產生詩歌。也就是說,詩是一種自我矛盾的產物。一首好詩,應該包含著矛盾的特質,這樣才會產生張力。好的藝術作品都是這樣,在卡夫卡和貝克特的小說中,便有這樣的吊詭式的寫法。矛盾和對立產生張力。但這并不玄妙,世界的構成就是這樣。老子說,一陽一陰謂之道也。還說,反者道之動也。至于大量運用句號,可能你說的是對的,當畫上句號時,就意味著這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意義。也就是說,加上句號,會使每個句子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獨立單位,按維特根斯坦所說,每個句子構成了一個圖像。然而在我的詩中,即使是現在,你所提到的那種遲疑不決的、試探性的口吻仍然存在,也許這和直截了當的句號放在一起,起到了一種調節作用。就我個人來說,我始終是矛盾的,對所有事物都在懷疑,都不確定,也許正好符合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一切都是轉瞬即逝,一切既是確定的又是不確定的,難以把握。所謂意義,只是一種人為界定罷了。
苗:有人評定你的詩歌為“城市詩歌”,你是否認可這一稱述?在當代詩壇,是否存在著“城市詩歌”的創作?如有,它們體現在哪些詩人身上、哪些作品之中?如無,那么可以篤定的是:當代詩歌中肯定存在城市話語,畢竟早在現代詩歌初期,郭沫若詩歌中就出現了都市話語,盡管那時的都市描寫還只是一種遠景式的圖像,尚沒有進入生命的日常生活圖景中。這種城市話語發展到今天的脈絡蹤跡,你能具體談談嗎?
張:首先我認可“城市詩歌”的說法,只是這個概念還沒有得到推廣。其次,所謂“城市詩歌”,只是寫作的一種主導性傾向,或者是一種詩學意義上的追求。我在縣城長大,直到讀了大學,才算真正進入城市。我的一些詩作,包括《1965 年》,寫的都是縣城生活。我以為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城市詩歌”代表了一種關注和介入復雜紛紜的現代生活的努力。當然不能說描寫農村或非城市的詩歌就不具有現代意識,但無論如何,城市喧囂的生活和背后所蘊含的都市文化因素更能體現這個時代的本質特征。
關于城市詩歌的發展脈絡,我只知道是從波德萊爾肇始,到紐約派集大成。紐約派比如奧哈拉醉心城市場景,聲稱即使寫一片草葉,也要寫地鐵站旁的,這可以看成是一種宣言。國內的詩歌脈絡我說不太好,似乎并沒有形成城市詩歌的自覺意識,但在一些重要詩人的作品中總是會出現城市的意象,或以城市作為背景。也許這種分類將會引發詩歌對城市生活的進一步思考。
苗:面對你的詩歌,很多固有的批評方式是失效的,比如,重建你詩中的抒寫主體形象就是極其困難的。他總是被碎片化的景觀與物象重重遮掩著,被雜語多音的不和諧語調分化著,被高度心靈化的精神活動抽離著,這種精神活動和個體心靈無關,和自身經驗無關,而是一種內涵廣泛的心境。這樣一來,主體性不是將自身引向聚焦在一起的某種內核,而是沿著相反的方向向外部無限擴張。解構性主體是典型的后現代特征,不同于艾略特的“非個人化”,艾略特作為現代詩歌標識的“非個人化”是棄絕自我,逃避個性,以便作為參與到一種完整的生活中去的前提。分化的主體、碎片化經驗、拼貼方式構成你詩歌創作最顯著的后現代特征。從現代性到后現代性可以歸納成你的詩歌之路嗎?
張:你這樣說是對我寫作的一種肯定,說明它脫離了某些理論套路。批評是量體裁衣,而不是削足適履。詩歌寫作更多是出自感性,審美是詩歌的第一要義。為文學史寫作,或等而下之,為批評家寫作,都算不上是正途。判定一首詩是不是好詩,應該看能否帶給讀者一種心靈的震動,或者說審美愉悅,而不是是否符合某些批評套路。一些批評者習慣了用一些理論或概念去套作品,就像拿著一只玻璃鞋(不是水晶鞋)去套作品的腳。能夠穿上的當然幸運,穿不上的便只好自認倒霉。但有多少批評是從作品本身出發,是從審美出發?這就像把一只蝴蝶的標本當成翩翩飛舞的蝴蝶,或把一位美女放在解剖臺上,卸下一只胳膊,或一條腿,告訴人們,這就是美。有人說美女美在氣質,有人說美女美在姿態,真正的美總是生動鮮活的,所謂活色生香,而不是僵死的標本。藝術不是也不應該按照某種文化觀念去制作,而應該帶有一種異質性。我注定是個大腳怪,更不會砍掉自己的腳趾把腳放進批評的玻璃鞋中。
說到抒寫的主體形象,就如同一個人,總是復雜多樣的。如果我們反思一下自己,就會發現自己就是一個錯綜復雜的矛盾體。過于清晰呈現出的主體形象更有人為設定的意味,帶有某種姿態感。有了姿態感,就很難達到真誠。另一方面,主體形象在我看來,也要作為客體形象來對待,加以觀察和反思。我對解構情有獨鐘。我年輕時迷戀禪宗,盡管現在仍是一知半解,但對我的思維方式影響深刻。而在維特根斯坦和德里達的思想中也能找到禪的某些思想痕跡。當然不能說他們是受到禪宗的影響,而是一種殊途同歸吧。禪宗,也包括東方古代的思想,與當下人們津津樂道的量子物理學有很大的相似處。禪是一種解放、一種超越,我總是覺得與解構也有一些關聯。我在上世紀80 年代初關注現代派,在80 年代中期興趣轉向了后現代,在90 年代后期我開始把關注點放在了一些作家身上。我以為后現代和現代一樣是社會發展的自然產物。從寫作角度講,我喜歡后現代的注重反思、反諷、不確定性和游戲性質。
苗:現代西方藝術繪畫、音樂、尤其是詩歌,對你影響極大,如果要拉出其中具體的名單,應該是長長的一大串。你在隨筆、評論、書信中數次評論闡釋過,具體到你的創作,這種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
張:影響應該是多方面的。比如,杜尚和約翰·凱奇給了我大膽打破藝術規則和邊界的勇氣。畢加索不斷嘗試新的方法、敢于打破自己的氣魄,塞尚對藝術的執著和畫中的厚重感和體積感都讓我敬佩;我從克利那里學到了作品中的稚拙意味、童話色彩和游戲性。從波洛克那里看到了無意識在創作中的重要性,從莫蘭迪那里懂得了格調的高雅,還有菲利普·格拉斯的音樂,我的那首你曾提到的《雪》和《海》就借鑒了他的簡約和不斷重復的手法。說來話長,簡單說,通過他們的作品,我認清了藝術與時代的關聯,并增強了大膽創新和變化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