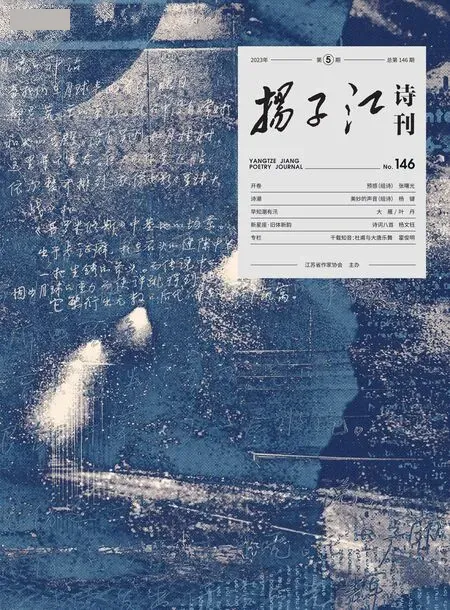詩如何直指本心又立文字
——以王君的小長詩《獻詩》為例
敬文東
一
最素樸的文學常識也許是:在所有形式的語言藝術中,詩依賴語言的程度最深。它一方面必須在“推”“敲”之間二選一,在“到”“過”“入”“滿”“綠”中做抉擇,另一方面正體現在對“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追逐之中。在中國古代,詩不過是詩人“言”說自我之“志”的絕佳工具,有著非常明顯的工具論色彩。工具當然臣服于它的主人。在大多數情況下,古詩僅僅是詩人的內心之“情”與外在之“景”深度交融的產物。它極度依賴語言的加持,但尤其依賴意在“言志”的詩人不斷激發語言的詩性功能與潛能,以便成就詩篇。伴隨著現代社會氣息(或曰現代經驗)的撲面而來,這種美好的景致或“好的故事”終于成為明日黃花,并且很快凋謝,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西渡有一個大膽并且精彩的觀察:現代漢語可以被視作人為造成的語言;它被制造出來的目的,是為了追求現代性。現代漢語大致有兩個來源:日常的口頭語言、對外國語言的漢語翻譯。前一種來源為現代漢語貢獻了最表層的毛發部分,第二個來源則為現代漢語貢獻了既可以又能夠追求現代性的肌理和骨骼。現代漢語的語法體系以拉丁語的語法體系為主要參照對象。作為這方面的經典證據,《馬氏文通》的重要性可謂眾所周知。這的確是一個非同小可的事實:現代漢語接管了拉丁語系的語法體系,也就邏輯性地照單接收了拉丁語系的基本信條。蘭波所謂的“話在說我”是其中的信條之一。另一個更加重要的信條包含在唐·庫比特(Don Cupitt)的言說中:“不是先有經驗,再有語言的表達;不是先有對上帝或者終極者的神秘經驗,再有對上帝或者終極者的表達。而是相反,先有語言,再有經驗;先有關于上帝或者終極者的語言,再有關于上帝或者終極者的經驗。先有基督教的語言,才會有基督教的經驗。”還有一個信條由海德格爾提供:語言的本質無他,唯“語言說”(Die Sprache spricht)而已矣。三個信條相加,獲取的結果很有可能是:現代漢語具有態度鮮明的自我(或曰自我意志)。既然如此,作為一種前所未有的文體形式,新詩——它以現代漢語為媒介——也就不再單方面服從、被動性聽從詩人的隨意驅遣,它有來自本能的自我訴求,它對自己的體貌有很自覺的設想。作為文體的新詩,也就不再可能成為詩人“言”說自我之“志”的純然工具,它要和詩人分庭抗禮。“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更有可能僅僅是古代詩人的風姿,令現代詩人羨慕不已;即使是李賀一類的苦吟派詩人,也莫不將主動權牢牢把控在自己的手中。正是在這種孤絕的境況下,不妨同意也似乎可以同意《李白撈詩》(而非詩人王君單方面)做出的判斷:在詩之死中,必然暗含著詩之生;新詩命運多舛,一路跌跌撞撞、趔趄復趔趄,但到底頑強地存活下來。對此,王君的小長詩——《獻詩》——給出的理由仍然和語言有關:
此刻
物的語言,如“花崗巖的理智”……
二
古詩因景生情,以抒情為方式回應萬物,陳世驤所謂的抒情傳統由此而生。在更大的程度上,古詩僅僅是對一個給定世界的靈魂反應。在古詩的只眼里,萬物莫不是擬人化的,每一件物事都可以和詩人之志相互交流,彼此對話。古人使用的漢語圍繞味覺(或以舌頭為中心)組建其自身。它以感嘆為魂,以舌頭舔舐萬物(或曰品嘗萬物)為認識萬物的根基。這引出了兩個很打眼的結果:第一,面對給定的世界,古詩以品嘗萬物為方式與萬物相往還、打交道,嘗因此成為天人合一在動作上的首選,甚或最佳選擇;第二,與萬物合一意味著古詩必須以抒情為務,抒情的主動權歸詩人所有,作為文體的古詩不具備自我意識,它安于自己的工具地位。這兩個后果決定和導致了作為文體的古詩、詩人與萬物之間的恒常關系。與此大相徑庭的是:新詩用現代漢語——它擁有態度鮮明的自我——說出了只存在于詩中的虛構世界。這個世界不是對給定世界的內心反應,它被現代漢語所發明;在終極的意義上,它與詩人生活的現實世界沒有必然關系。從本性上說,現代漢語不允許新詩僅僅是對一個給定世界的內心震動、靈魂反應。此情此景,正合胡戈·弗里德里希(Hugo Friedrich)的得道之言:現代詩“是自我封閉的構造物。它既不傳達真理,也不傳達‘心靈的沉醉’,根本就不傳達任何事物,而只是自為存在的詩歌(the poem per se)。”心靈對萬物的感悟與萬物自身的運行節奏同步調、共振幅,是古代詩人理解現實世界的經典范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不朽的案例。隨著現代漢語接替古代漢語,現代詩人只有在不斷發明一個、一個又一個新世界(或新現實)的過程之中,才能深入理解那個給定的、唯一的現實世界。王君的小長詩——《獻詩》——對此心有靈犀:
時間的露下在獅子洞的清晨。
遠處是人間,碧空在破繭,此刻
物的語言,如“花崗巖的理智”
一樣寬闊:露消失在眼——
在耳里,卻能再次活過來:
嘰嘰喳喳,一只鳥。
它站起來……它站在它的有限性上,
它從它的靜物的灰塵里獲得了命,
它……升起,歌唱。
上引詩行中特別值得分析和重視的應該是:“此刻/物的語言,如‘花崗巖的理智’/一樣寬闊……”出于小長詩本身的多維性和多義性,對這幾行詩也許可以做出多種理解或解釋,但仍然不妨礙將它理解為現代漢語的倔強、不妥協,以及強大的生產和生育能力。時間的露下在獅子洞的清晨、碧空在破繭、嘰嘰喳喳的那只鳥、站起來的那只鳥、站在自己的有限性上的那只鳥、從它的靜物的灰塵里獲得了命的那只鳥、正在升起和歌唱的那只鳥,如此等等,都是現代漢語發明的新現實,和給定的那個唯一的現實關系稀薄。至少從表面上看,“時間的露下在獅子洞的清晨”“碧空在破繭”等,臣服于超現實主義文學理論提倡的信條——自動寫作。很遺憾,這種看似頗具慧眼的觀察,顯然忘記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線索:現代漢語擁有態度鮮明的自我,它讓這個新現實必須以自身為目的,新現實只為自己而歌。現代漢語聽說過自動寫作(沒聽說過是不可能的),但它終究視自動寫作為無物,畢竟自動寫作的主動權僅僅屬于詩人,在不少駭人聽聞的時刻僅僅屬于詩人的潛意識。沒有任何理由懷疑這個理念僅僅是碰巧,是例外,是一次偶然的美學交通事件。內證比比皆是,《獻詩》在另一處就很明確地寫道:
從白云里誕生了“圓月”這個念頭。
圓月,呼喚出了虛幻中會呼吸的詞:
獅子。獅子的長吟挪動了
林子深處的門閂,
窗戶在內心里還有
一扇更小的窗戶,打開……
念頭的得來,看似源自古詩那般的呼應萬物、吞吐萬物,正所謂“氣之動物,物之感人”,實則是現代語言以其態度鮮明的自我意志,創造性地——但似乎更應該說成自然而然地——貢獻了“圓月”這個極優質但又極平常的念頭。說優質,是因為現代漢語具有卓越的生育性能;說平常,也是因為現代漢語具有卓越的生育性能。在此處,“白云”可以臨時充當現代漢語的隱喻或面具,而圓月這個念頭一旦被白云發明出來,接下來的一切似乎順理成章,但更應該說成現代漢語的生育、生產能力被完好地落到了實處,亦即順現代漢語之“理”而“成章”:比如說獅子的長吟挪動了林子深處的門閂;窗戶在內心里還有一扇更小的窗戶……當然,還有接下來理應到來的一切情景。制造新世界、發明新現實,也許是新詩自身的唯一目的,但絕不是詩人——比如王君——的目標之所在。和普通人理解一個給定世界的方式大相徑庭,諸如王君一類的現代漢語詩人唯有不斷發明新世界、新現實,才能更好地理解那個唯一的現實世界:給定世界的丑陋、不完善,以及它美好的風景、平靜的地平線,才被現代漢語詩人盡收眼底。在現代漢語統攝的時空中,作為文體的新詩、詩人和給定世界之間的關系,大異于作為文體的古詩、詩人與萬物結成的恒常關系。就像鐘鳴曾經感慨的那樣,語境變了,一切都變了。
三
王君對新詩所持有的不同凡響的洞見,并不完全源自以拉丁語系為榜樣的現代漢語,至少還有來自禪宗的影響和輻射。據傳,六祖對他的弟子有一個教誨是這樣的:“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圣對,問圣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李澤厚對此的評論是:“有無、凡圣等等都只是用概念語言所分割的有限性,它們遠非真實,所以要故意用概念語言的尖銳矛盾和直接沖突來打破這種執著。……只有打破和超越任何區分和限定,才能真正體會和領悟到那個所謂的絕對本體。它在任何語言、思維之前、之上、之外,所以是不可稱道、不可言說、不可思議的。”王君對此的理解和李澤厚正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當禪宗的僧人們被問到什么是佛時,《五燈會元》是這樣記載的:僧問云門:“如何是佛?”,文偃答:“干屎橛”。當文偃禪師從意海中一下子蹦出“干屎橛”這個詞兒,我相信他處于一種打破“不落窠臼,不墮理路”的禪思癲狂之中,概念的邊界被奮勇突破了,詞語從意義上被抽離為意識的一個頓斷,空間裂開了,世界成為一種光的形式,自性開始顯露。啪!又一個頓斷,把顯露打了一個趔趄,顯露顯露為非顯——這是一種什么狀態的迷醉和清醒?我沉迷于這種“斷點再生”的“遮語”的思維方式中,保持了寫作上的自嗨和成癮,我希望能走得更遠。
禪宗一向強調不立文字、直指本心。它要求禪者越過語言文字,直接和絕對本體相交通、相往還。但這里邊的吊詭之處顯然是:越過語言文字直接相交于絕對本體,卻又不得不利用、依靠語言文字。相較于李澤厚所謂“故意用概念語言的尖銳矛盾和直接沖突來打破這種執著(亦即對有無、凡圣的執著——引者注)”,禪宗公案里不斷出現的棒喝、看似簡單粗暴的拳打腳踢無疑更上層樓。從表面上看,棒喝與拳打腳踢似乎擯除和棄絕了文字,事實上依然是語言化的,這僅僅因為人是語言的動物。在正常情況下,沒有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個自覺的動作是無目的的。這就是說,棒喝與拳打腳踢并非無意識的產物,恰恰相反,它是高度意識化的,而意識本身就意味著語言。陳嘉映曾經爭辯過,對于人來說,一切視覺的——再比如棒喝與拳打腳踢——都必然是高度語言化的。如果它居然不是高度語言化的,也就不可能進入“萬古長空,一朝風月”所昭示的那種澄明、頓悟之境。更有甚者,棒喝與拳打腳踢一定會給禪者制造某種特定的心境。對于禪者而言,這種心境不僅直接相交通于絕對本體,它本身就是絕對本體。但此處不能、不該也不可以被忽略的是:在語言哲學看來,心境原本就是一個典型、密集的語言事件(language events)。如此說來,看似無法言說的絕對本體并非和語言全然無干,只不過在絕對本體那里,語言似乎突然靜止,突然放棄了飛翔。在此,語言和絕對本體一道,達致了瞬刻即永恒的境界。無論如何,高度語言化的棒喝與拳打腳踢,正出自不必說卻又不得不說這個兩難處境。語言文字難以表達絕對本體,但絕對本體又必須得到表達。這種情景可以被表述為必達難達的絕對本體之境(簡稱必達難達之境)。而棒喝與拳打腳踢,可以被視為必達難達之境的極簡形式。正是禪宗的必達難達之境伙同現代漢語的自我意志,催生了王君的另一個極其重要的詩學理念:必達難達之態。
必達難達之態的意思是:和古詩操作相對簡單、相對容易實現其目標的情景交融比起來,以現代漢語為媒介的新詩擔負著發明新現實、新世界的重任,但這種發明往往極難命中它的靶向目標,十環自不必說更是難上加難。雖然利希滕伯格(G.C.Lichtenberg)曾在某處嘲諷過:“對人類來說,天堂也許是最容易的發明。”雖然博爾赫斯一位寫小說的朋友非常輕松地說:“從吃過午飯開始整整一下午,我已經創立了一打宗教。”但新詩意欲發明的,絕不是最容易發明的天堂,它也決不會組建輕易就能組建起來的宗教。對于必達難達之態,魯迅有過非常清楚,但也似乎是十分艱難的表達:“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仿佛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它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對于詩人而非作為文體的新詩來說,發明新現實意在教育唯一存在的那個現實世界。但這得仰仗新詩的特殊內涵,這個內涵被認為是這樣的:詩人有自我意志,作為文體的新詩也有自我意志,兩者必須協商、談判和互相妥協,方可生產出一個被兩者同時接受、共同認可的抒情主人公。抒情主人公說話,詩人則像同聲傳譯一樣,充當抒情主人公的書記員。書記員記錄在案的,就是被一眾讀者閱讀的詩篇。因此,詩人而非作為文體的新詩面對的難題是:詩人站在現實世界上,卻必須伙同作為文體的新詩發明新世界,因為這是新詩的自我訴求;詩人被現實世界的巨大引力所牽制,不能像發明天堂和宗教那樣隨意驅遣新詩以制造新現實,這也是新詩鮮明的自我意志導致的結果。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前所未見的文體,新詩可以以自身為目的,可以無視現實世界,詩人卻不得不認真對待他寄身其間的那個時空體,畢竟詩人無法揪著自己的頭發飛離地球。但攻克這種險境,卻是作為文體的新詩和詩人共同承擔的任務。必達難達之態不僅是新詩現代性的重要指標之一,也是詩人和作為文體的新詩為自己認領的光榮任務。與僅僅聽從現代漢語的召喚就建立起這種詩學理念的詩人們比起來,王君還意外地獲得了佛學的加持。其間,大有可能經過了一番驚心動魄的內心體驗和內心搏斗,但這搏斗、這體驗、這驚心動魄是值得的,因為它為困難重重的新詩寫作輸入了新元素,豐富了現代詩學貧瘠的庫存。
四
自胡適以來到而今,新詩的自我意志往往被辜負;操持新詩的絕大多數人,堪稱新詩的負心郎。更多的詩人傾向于表達之易,但或許他們也只能屈服于表達之易。從表面上看,王君在不少時刻也有類似之舉,但讀者不難看出,它頂多是李澤厚所說的“故意用概念語言的尖銳矛盾和直接沖突來打破”各種執著。但王君伙同作為文體的新詩之所以有這等做法,卻不是為了參禪,不是像王維那樣寫作禪意盎然的詩篇,不是有如王士禛那般追逐詩的神韻,也不是為了追求瞬刻即永恒的無上境界,而是為了克服必達難達之境以便艱難地發明新現實、新世界。《獻詩》中另有兩行詩,非常清楚地把這個意念給擺明了,算得上最好的內證:“詞語‘哦’的月光吐出一地銀色的稱贊,/照見了詞語‘花萼’寂靜處的臉。”語詞——比如“哦”——在此自動創世,距離不立文字或棒喝也許不到十毫米;詞與詞以照見對方——比如“花萼”——為方式,互相觀看對方的秘密,彼此催促對方的生長,最終催生出一個新世界,發明出一個新現實。與此同時,作為語詞的“花萼”在寂靜處的那張臉像接近沸點的水那樣,含笑卻未笑,但到處都是笑的影子。而作為一個杰出的嘆詞,“哦”就像呂叔湘稱贊的那樣:“我們感情激動時,感嘆之聲先脫口而出,以后才繼以說明的語句。后面所說的語句或為上文所說的感嘆句,或為其他句式,但后者用在此處必然帶有濃郁的情感。”這就是語詞自動創世的語言學秘密;而對必達難達之態的成功克服,注定會將所有的語詞更新為嘆詞。但語詞自動創世并非沒有條件,它至少應該得到現實世界中某種辯證法的加持。這個辯證法是:“死過了一萬次的死并不能復活死。”很顯然,這是一種充滿禪意的辯證法,跡近于瞬刻即永恒之境。
自語言學轉向之后,數千年來視語言為工具的西方人終于意識到:語言具有態度鮮明的自我。就文學而言,舉凡象征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未來主義,甚至荒誕派,無不以此為基礎。T.S.艾略特的著名觀點——逃避自我,至少從無意識處觸及到了這一點(這也許正是他的天才之處)。中國人拿視覺性的拉丁語改造味覺性的古代漢語以成就現代漢語之時,正好是視覺性的西方人拿味覺性的中國古詩改造西方詩歌之際。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深受中國佛禪思想的影響,他也以佛禪為根基,成為英語世界公認的大詩人。斯奈德有詩曰:
松樹的樹冠
藍色的夜
有霜霧,天空中
明月朗照。
松樹的樹冠
彎成霜一般藍,淡淡地
沒入天空,霜,星光。
靴子的吱嘎聲。
兔的足跡,鹿的足跡
我們知道什么。
(加里·斯奈德:《松樹的樹冠》,楊子譯)
即使是透過漢語翻譯,會心者也能夠立刻讀出王維的味道:“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如此等等。與王君及其中國同路人的施力方向剛好相反,加里·斯奈德非常自覺地利用佛禪思維,恰到好處地降低了——而不是強化了——現代英語過于濃烈的自我意識。英語傾向于將外部世界看作被它征服的對象,充滿了侵略性和進攻性,在大多數時刻顯得很極端。當現代英語因為佛禪思維得到軟化后,便能較為溫柔地對待和看待現實世界,并對這個世界充滿了期待,讓生活于這個世界的人得以詩意地棲居。王君的詩學表達的是另一種謙虛:它強調現代漢語的尊嚴,尊重現代漢語的個性。
時間向山下流去:
刺骨的寒冷燙到了手。
從來不存在2 月16 日的梅花,但梅花,次第開放在獅子洞。
(王君:《梅花次第開在獅子洞》)
在佛禪的加持下,王君伙同現代漢語發明的諸多新世界、新現實組成的詩歌世界是善好的世界,這個世界也許比斯奈德制造的詩學世界更值得棲居。但善好并不意味著這個被發明出來的新世界上沒有丑惡、災難、暴力和屈辱,而是說作為文體的新詩本身是美好的、幸福的、向善的。在突破了必達難達之境這個堅硬的詩學難題后,詩歌世界呈現出澄明、頓悟之境。但頓悟、澄明并不是禪意的,它是從傳統中走出的現代,就像從死中走出生,但更像生在其咽喉部位竟然忍住了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