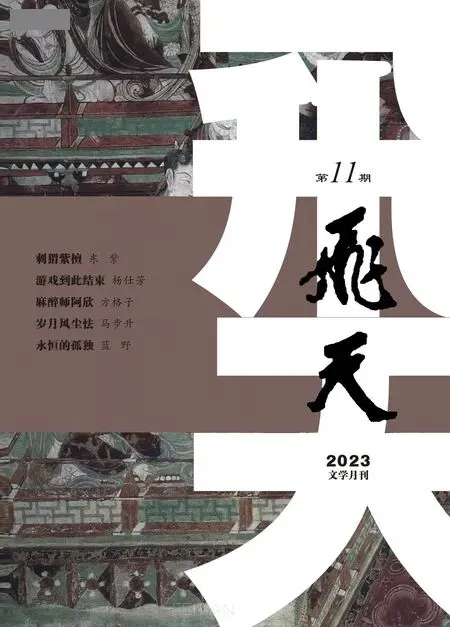秘境中的昌馬
?王新軍
一
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南北夾擊之下,悄然隆起的祁連山昂首向西,如天馬浴河般奔騰而去,形成了河西走廊這一人類文明通道的南部屏障。
無論是自駕還是乘車,翻越烏鞘嶺之后,一路西行,都會有這種奇妙的感覺。
在祁連山綿延數千里的群峰之間,分布著為數眾多的高山谷地,它們為冰川河流的發育創造了條件,進而繁衍出河西走廊燦若星辰的片片綠洲。
這其中,有一些寬谷盆地,不僅自然風光雋秀神秘,更蘊含了豐富的人文信息,地處祁連山西北部的昌馬盆地就是如此。
前些年我在玉門文聯工作期間,曾組織文藝工作者,進行過多次以尋訪歷史古跡和人文探險為主題的采風創作活動,昌馬就是在這一時期通過大量攝影作品的傳播,漸漸為外界所矚目。
昌馬地處祁連山西部,是一個四面環山的小盆地。
疏勒河從這片面積近兩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南至北穿過,其間又有眾多水流匯入,在這里形成了一幅河汊縱橫,泉眼密布,碧波蕩漾,水豐草茂的盛大景象。
相傳唐代名將樊梨花率大軍西征時路過此地,一眼就看中了這片地方,遂將這里設為西征唐軍的軍馬場。“昌馬”之名便由來于此,寓意此為軍馬隆昌之地。
打開高精度的衛星地圖俯瞰,祁連山這群奔跑的石頭,億萬年來似乎一直沒有停歇過。點綴在其褐色衣袂間的彈丸之地昌馬,卻能在乍然間凸顯出獨有的秀麗,吸引眾人的眼眸。
二
在行政區劃上,昌馬隸屬于玉門市,是一個以農牧業為主的鄉鎮。對于生活在小城玉門的人們來說,夏天去昌馬避暑散心,幾乎是抬腳就走的事。
出玉門新市區向南,沿玉昌公路前行,一路上滿眼都是令人心胸開闊的景致。迎面是飛馬揚鬃的祁連山,公路兩側,綿延的風力發電機組排列成巨大的風車森林,戈壁的遼遠在天地之間鋪開,眼前不斷擴展的蒼茫,使人瞬間涌起某種基于坦蕩的遐想。歲月悠悠,天地玄黃,人不過世間渺小一物爾,倏忽之間,便化為一抹飛塵。
沿疏勒河溯流而上,穿過八十里風車叢林,在疏勒河出山口下方拐頭向西,不多遠便進入一道山口。早年間這段進出山鄉的險路,已在幾度鄉村振興的風潮中,變成了等級的柏油通途。
在兩側大山的護持下,翻過一處險峻達坂,前方的綠洲已赫然映入眼簾。
此時極目遠眺,照壁山虎踞于北,東、南、西三面蒼山環繞,層巒疊嶂之上,長風起舞,密云飛度,古老的綠洲宛如一方碧玉,鑲嵌在群峰雄宏的環抱之中,透過時間的輕嵐,默默守護著人類繁衍的些許遺存,傳遞著生生不息的文明輝光。
目力所及之處,無垠的壯闊與空靈開始在天地間回響。
站在車路溝達坂上看去,疏勒河像一條銀色的鏈子,從綠洲的東南角垂掛下來,由南向北漸次鋪開,在照壁山前形成一處長條形的湖面。
盆地中央,無數溪流縈繞著農田,綠樹掩映之下,村莊星羅棋布。
更遠處,高山牧場與近處的濕地草甸相互映襯,將這里構造成一個別有洞天的世界。
這,就是昌馬。
三
翻過達坂,在昌馬的入口處——水峽村西面緊靠農田的地方,有一處南北走向的山崖,崖高三五十米,長約六七百米。公元423年前后,這里作為佛教東漸的必經之路,一位沒有留下法號的僧人云游至此。
他在溪水邊掬水凈面之后,乍一抬頭,便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
西邊高聳的石壁之上,驀地迸射出萬道金光,團團紫霧自崖頂徐徐而下,漂浮游移。崖下牧野之上,清風回環,崆峒有聲,狀如千佛吟誦。遠處,更有鐘鼓之聲隱約相聞。他不禁感嘆,這云山霧罩之下,好一處祥瑞之地啊!
于是,在一個清晨,伴隨著第一聲鳥鳴,石壁上下,叮咚聲次第響起。
若干年后,懸梯回廊連接起大小不一數十個洞窟,崖下殿起,佛事漸濃,香火綿延,千年不絕。
這就是昌馬石窟的前世,它隱藏在時間的長河之中,等待著有人去打撈。
在佛教東漸的過程中,許多著名的寺廟道場,都是鑿壁開窟,依崖而建。這種現象在河西走廊比比皆是,即使放大到整個絲綢之路,也是如此。昌馬石窟,自然不會例外。
如果將這條線上分布的大小石窟稍加連綴,便會恍然一悟,河西走廊還應該有另外一個名字——石窟走廊。
廟宇塑像,在整個河西農村,幾乎鄉鄉皆有,佛窟神龕,更是隨處可見。如今為人稱奇的石窟彩塑,早些年卻是我們本地人的生活日常。
盛夏時節,崖壁下綠色的麥田左右鋪開,正在灌漿的麥穗株株堅挺,如同向上張開的壯碩手指。來到崖前,駐足凝視,眼前一架數丈高的懸梯自崖底向上,通往崖壁上的走廊。隔著護欄,幾個洞窟悄然靜立,崖頂灰鴿翱翔,崖下風動鳥鳴,俗世當中的許多煩心之事,早已一掃而光了。
事實上,每踏上懸梯的一級臺階,心中都會生出一份跨越往事的感想。站在石窟前的廊道上眺望,腳下阡陌縱橫,前方碧野千傾。這哪里是印象中的河西之地,分明已經身處高原春城。
在石窟學界,一般認為敦煌石窟群包括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東千佛洞和昌馬石窟。昌馬石窟是敦煌石窟群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姊妹窟。昌馬石窟開鑿于北涼時期,后世宋、元、明都有續鑿和修復。
民國22 年冬,昌馬盆地發生了一次強烈地震,洞窟被震塌,石窟中的壁畫、彩塑等文物大多被損毀,只有四座洞窟幸存下來。近年來,經當地文物和文旅部門專業團隊保護性修繕,昌馬石窟又生發出昔日的光彩。
從洞窟開鑿形式上看,昌馬石窟與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及新疆的大多石窟寺相似之處甚多;從藝術價值上說,其彩繪和彩塑手法新穎,形象逼真,色彩驚艷;從洞窟的壁畫和雕塑內容看,主要反映了各時代的生產和生活狀況,其中滲透著濃厚的佛教思想。其藝術表現手法,與敦煌及新疆等古絲綢之路上的多個石窟極其一致,有些已經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價值。
正因為如此,早在1981 年,昌馬石窟就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四
昌馬鎮的行政中心,就在盆地的中央。村莊幾乎就是以鎮街為圓心,向周邊散射狀分散開去的。
寬敞的鎮街兩旁,除了醫院學校之類的公立機構,剩下的就是各種商鋪,再往外延伸,便是一棟棟農家的小康住宅了。家家戶戶窗明瓦亮,白色的墻面配上紅色的屋頂,點綴在漫延開去的綠野當中,充滿了詩情畫意。
前幾年,書法家潘國剛在昌馬當鎮長時,主導推進了昌馬的文化旅游融合發展,以昌馬盆地周邊的自然資源為依托,建成了民俗展演廣場、藝術品展覽館,打造了以康養體驗、民俗體驗、登山探險、山鄉民宿等為內容的國際藝術駐留村,定期舉辦內容豐富的國際藝術駐留節,每年吸引全國各地的數百名藝術家來昌馬采風創作,多所大學的藝術學院也在昌馬設立了創作基地。
經過數年努力,“文化賦能鄉村振興”這一舉措已經使昌馬的整體形象大為提升,更擁有了難得的知名度。
當地人不僅感受到了人居環境改善后的舒適生活,還從逐年增長的“三產”發展中,獲得了直接的收益——有機農產品不出家門就有了銷路,昌馬產的牛羊肉,更成了遠近聞名的緊俏貨。
昌馬漸漸進入外界的視野之后,便常常有鄰近的文朋詩友慕名而來,尤其是盛夏時節,昌馬的確是不可多得的清涼之地。
朋友來了,如果時間允許,一般我都會陪同前往。如果趕巧有事,我也會根據對方的時間和需求,為他們推薦最佳的參訪路線。
但無論這條線怎樣設計,都繞不開疏勒河。
五
疏勒河是昌馬的母親河,它的源頭在祁連山中段雄偉的大雪山下,那里是一片晶瑩的冰雪世界,每一滴水都如同大地的乳汁,擁有純凈的靈魂。它們越過遙遠的冰封期,在時間的縫隙中一滴滴匯集起來,飽含著生命的張力,在崇山峻嶺間舞動。
它穿越無數個季節,看盡了萬年輪回,記錄著大地流變的歷史與滄桑。帶著與生俱來的堅韌和靈動,向著未知的遠方奔流。
疏勒河是一條需要認真梳理的河流,它一路穿越冰川、溝壑,接納了大小無數條溪流,像一位慈祥的母親,用自己甘甜的乳汁,最先哺育出昌馬這塊豐饒的高山谷地。
疏勒河進入昌馬之后,匯小昌馬河,北出峽口一瀉而下,成就了河西走廊西部由游牧到農耕的梯次文明——在東起玉門,西至羅布泊的千里闊野之上,綠洲連片,村鎮成串,多民族聚居的形態早在漢代業已形成,這其中,敦煌文化便是多種文明交相輝映的結晶。
在進入昌馬盆地的那一段,疏勒河劈石聚力,將地面切成又窄又深的峽谷,又將巖層鑿為上小下大的空穴,形成數里地下通道。水流在最窄處噴薄迸發,如群馬歡騰,如山林虎嘯。水豐時節,其摧枯拉朽之勢,酷似黃河壺口。
最窄處更有大石橫跨深谷,形成一座天然橋梁,這就是當地人常說的天生橋,也是疏勒河進入昌馬盆地造就的第一個奇觀。很長一個時期,天生橋都是從東南方向進出昌馬的重要通道。
1907 年7 月3 日,瑞典人斯坦因帶著駝隊,從萬佛峽向東進發,一路探察了石包城、大龔岔之后,于12 日到達昌馬。沿途的一座座雪峰和豐饒的昌馬綠洲,給這個圖謀不軌的家伙留下了深刻印象。
當夜在昌馬堡子領受了一番玉門兵士的款待之后,次日便租用昌馬駝工和駱駝,從天生橋穿過疏勒河,沿山腳向東,一路經過水渠口、石門子、青草灣、白楊河,五日后出嘉峪關東去。昌馬最早的幾張人文地理照片,就出現在斯坦因此次玉門探險所拍攝的照片當中。
天生橋一段峽谷幽深,水流湍急,咆哮聲遠播數里,奇、險都可稱絕,我奇怪斯坦因為什么沒有在此處端起相機,按一下快門。是因為不值得他浪費一張膠片么?
不,或許這樣的自然景觀,本就引不起他探險的興趣。斯坦因所謂的探險,本意就是非得挖出點兒什么,然后裝箱帶走的。
到了后來,為了方便兩岸交通,人們又在天然石橋上面修了鐵橋。但習慣上,人們還把這里稱作天生橋。
河水沖向照壁山進入一道峽谷的時候,對峙的兩山之間,被一道人工大壩攔住了,蕩漾的水面從山峽之中外溢出來,與農田和草灘連接,形成數十里的闊大水面。這片水域,被今天的人們稱為昌馬湖。
昌馬湖是疏勒河上最大的人工湖泊,水面靜如碧玉,映照著天上的云彩。
從春到秋,湖邊草木搖曳,水鳥啁啾,在一派自然的律動中,盡顯無限的堅韌與活力。
昌馬盆地是疏勒河重要的轉折點,出昌馬以前為其上游,水豐流急,出昌馬大峽至走廊平地為其中游,至瓜州雙塔堡水庫以下為其下游。
在中國版圖上,疏勒河是一條少有的自東向西流淌的內陸河,千百年來,正是它催生了橫貫古今的絲綢之路,孕育了輝煌燦爛的敦煌文化,潤澤了河西走廊西部的多個綠洲。
2017 年,由國家水利部牽頭,組織了首屆尋找“全國最美家鄉河”大型主題活動,疏勒河作為敦煌文化的母親河、河西走廊的生態河、戈壁綠洲的發展河和潤澤故土的民生河,經過多個環節的激烈比拼和競爭,深深打動了廣大公眾和評委,最終獲得首屆“全國最美家鄉河”稱號。
六
昌馬盆地西側,有一片不起眼的土黃色山丘,當地人叫它土雜山。上世紀八十年代,轟動當時地質學界的“玉門甘肅鳥”化石,就發現于此。
1982 年,地質工作者在昌馬沈家灣土雜山勘探期間,發現了一件完整的鳥類化石,它是當時陸相地層中發現的最早鳥類。這種鳥類的趾節較長,很短的爪子上有尖銳的屈肌結節。它生活在距今約1.1 億年前的白堊紀時代,是一種已經滅絕的鳥類。
1984 年,經古鳥類學家、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方面多位專家研究,將其定名為“玉門甘肅鳥”。在首批《國家重點保護古生物化石名錄》中,被列為一級重點保護。
玉門甘肅鳥是我國發現的第一種中生代鳥類,也是已知最早的現代鳥類之一。剛被發現的時候,它是當世所知的、僅次于德國“始祖鳥”的第二古老鳥類。
當后來最新的研究證明德國“始祖鳥”不屬于鳥類時,玉門甘肅鳥在“世界鳥譜”中的輩分,升至頂峰。
玉門甘肅鳥是一種水陸“兩棲”鳥類,大小與鴿子相仿,體型適宜潛水,以魚類和水生昆蟲為食。現代自然界中的鸕鶿和潛鳥,就是一億多年前玉門甘肅鳥的復本。玉門甘肅鳥的科學研究價值巨大,它的發現不僅引起了世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還激起了科研人員研究的極大興趣,從而揭開了我國中生代鳥類研究的序幕。
目前我國古鳥類科學研究水平位于世界前列,玉門甘肅鳥的發現和研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如今,一塊塊玉門甘肅鳥的化石安靜地擺放在多家博物館的展廳里,儼然一件件鎮館之寶。
七
沿小昌馬河向西南方,沿一道寬闊的峽谷挺進,在峽谷最窄處登上一道高大的山脊,眼前會出現一條常年被冰雪覆蓋的巨大峽谷,這就是祁連山最大的山谷冰川——老虎溝12 號冰川,人們也叫它透明夢柯冰川。它長10 公里,最深處厚度達120 米。
幾年前我曾登上過這座冰川,那種冰河萬里,連風都晶瑩剔透的盛大景象,至今依然駭人心魄。
事實上早在舊石器時代,昌馬盆地就已經有人類活動,20 世紀末,在這里發現了多處舊石器時代遺存。除了這些遺存之外,昌馬盆地周邊的野牛溝、鹿子溝等高山牧場上,還保存著大量的古代巖畫。
昌馬地處祁連山西端,曾經是青藏高原通向蒙古高原的一條古老通道,從石器時代開始,就不斷有人類因各種原因,從這里南下北上,在昌馬留下了巖畫、窯址、石窟、城障、烽燧、墓群等豐富的歷史信息。或許這里的大山當中,還隱藏著很多不為人知的人文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