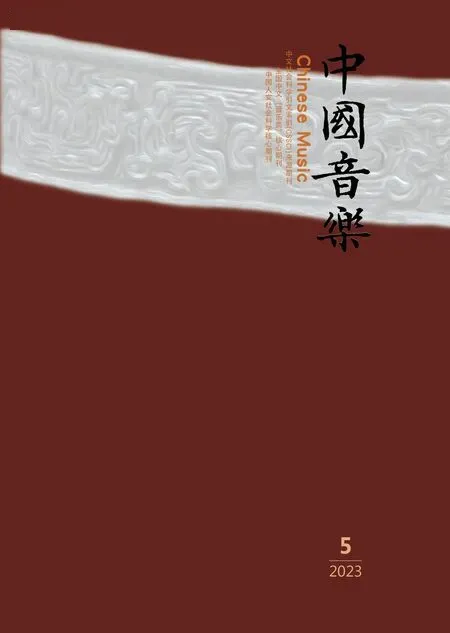論后現代人類學語境下的當代民族音樂學學術轉型路徑
○ 楊民康
源自西方的Ethnomusicology(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學術觀念在中國的輸入,若從王光祈的傳播比較音樂學算起,迄今已有近百年歷史了,其間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一樣,經歷了一個由現代性到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研究觀念轉換的過程。以梅里亞姆、賴斯等人為代表的現代民族音樂學,先后采納了學術上有較深承繼關系的博厄斯人類學多元文化觀和后現代建設論音樂觀,在以較寬容、理性的態度來處理和面對各種音樂文化危機現象的同時,還一定程度削弱、化解了由徹底、極端的后現代懷疑論所帶來的某些尖銳矛盾問題。中國民族音樂學學者在對之進行反思、批評的同時,也在有效地學習、研究和借鑒,以挖掘、開拓自己的后現代學術發展道路。本文將結合國內外的相關研究資料,對之展開如下評述。
一、反本質主義:現代民族音樂學轉型的標志性特征
在中國音樂學界,迄今所見的對于后現代主義音樂或學術觀念的介紹和引進,要多于批判性分析和評論。在后者中,又大部分是集中于后現代音樂思潮,尤其是對音樂創作觀念和表演實踐的分析和評論。也有一部分是關于后現代音樂理論,尤其是針對民族音樂學理論所包含的后現代因素。就此可再分為兩種基本傾向:一種是站在后現代音樂人類學的立場,對當下音樂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展開批判性的評論和分析。①楊沐:《后現代理論與音樂研究》(上)(下),《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第3-14頁;第2期,第41-50頁。楊沐:《跨進21世紀的音樂人類學:國際潮流與中國實踐》,《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第1-19頁。管建華:《后現代人類學與音樂人類學》,《中國音樂》,2004年,第4期,第6-10、20頁。湯亞汀:《后現代語境與中國聲音景觀斷想——兼及“新格羅夫”條目“音樂人類學:當代問題”》,《音樂藝術》,第2009期,第1頁,第114-126頁。另一種是以后現代音樂哲學、美學為立足點,對后現代音樂人類學在當今音樂文化研究中具有的理論貢獻和實踐意義進行跨學科性質的討論。②宋瑾:《后現代思想與音樂人類學》(上)(下),《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11年,第2期,第2-8頁;第3期,第8-16、35頁。當前國內有關現代性與后現代音樂理論的一種重要討論途徑,是從哲學、美學的角度,展開對于本質主義及反本質主義的討論,其討論的對象主要是“音樂的本質”是藝術性的還是具有其他多樣性、多義性(例如文化)的可解釋途徑。③楊沐:《后現代理論與音樂研究》(上)(下),《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第3-14頁;第2期,第41-50頁。同注②。而在涉及后現代民族音樂學的理論觀點中,最常見的也是對當下音樂學界存在的“本質主義”音樂文化觀的批評,并在該學術領域形成一種“反本質主義”的學術趨向。可以說,這是區分音樂學領域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學術論爭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對于此方面的研究狀況,拙文《由反本質主義到臧否表象:民族音樂學后現代轉型之路——兼論當代音樂民族志的語境研究觀》曾經做過評述,在此不贅。④楊民康:《由反本質主義到臧否表象:民族音樂學后現代轉型之路——兼論當代音樂民族志的語境研究觀》,《音樂探索》,2014年,第1期,第18-25頁。
這里,擬借半個世紀以前在北美學界開始的有關“音樂/文化”何為的研究主旨之辯,重新討論一下民族音樂學界這一同“臧否表象”有關,并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問題。20世紀50年代,正是現代主義思潮最強盛,卻也是最接近強弩之末的年代,同時,又是后現代主義思潮初現鋒芒,開始為人所知的時代。這一時期,作為兩種思潮正面交鋒的產物,也是現代民族音樂學得以確立的一個重要標志性成果,該學科學者通過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學科定義,從思維和觀念層面上,確立了以多元音樂觀作為基礎和準則的學科理論格局。當時,學者們提出并獲得普遍響應的一個學術觀念,集中體現于胡德(M.Hood)提出的學術定義:“民族音樂學是對一切音樂(any music)進行研究的一種方法,它不僅研究音樂本身,而且也研究這種音樂周圍的文化脈絡(cultural context)。”⑤Hood,M."Ethnomusicology," in Apel,Willi.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2d ed.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p.298.這個定義從學術思想或思維的層面,承續了當時為北美民族音樂學學術共同體所共有的一種代表性學術范式。而以梅里亞姆(Alan P.Merriam)為代表的一批民族音樂學學者對原有的學科思維和方法論進行反思,試圖用人類學的思維方法來解釋和研究北美及非歐國家的多民族音樂文化和亞文化現象。梅里亞姆在博厄斯(Boas,Franz)人類學方法基礎上,相繼將民族音樂學學科定義為“有關文化中音樂的研究”⑥Merriam,Alan P.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Evanston,Ill.: 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p.7.和“音樂作為文化的研究”⑦Merriam,Alan P."Definitions of 'Comparative Musicology'and 'Ethnomusicology': An Historical-Theoretical Perspective."Ethnomusicology 1977,Vol.21,pp.189-204.,以至在當時的北美民族音樂學界內部形成了“人類學派”和“音樂學派”兩大陣營。
可以說,上述兩派爭論所涉及的一個焦點問題,即同雙方對于“音樂”究竟是等同于“藝術性”這個相對固定、統一的概念,還是應該改用“文化”來表達其多元、多義的模糊性狀態有關。由此看,“音樂”等同于“藝術性”的觀點涉及所謂現代理性的問題。在后現代主義者眼中:“現代理性假定了普遍主義,統一的整合體,以及同樣的規則到處適用的觀點。合乎理性的主張被假定是在國與國、文化與文化、不同歷史階段之間基本上相同的主張。與此相反,后現代主義認為每一種情況都是不相同的,它倡導對具體情況作出特殊的理解。”⑧〔美〕波林·羅斯諾:《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1992)》,張國清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第190頁。當我們把這具有普世性特點的“音樂”概念與其同時擁有的多元、多義的模糊性“文化”狀態對置起來考慮,并想對之加以取舍時,或有必要再引入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理論所共同關注的一個重要關鍵詞“表象”,以為參照。
表象(representation),指的是客觀對象不在主體面前呈現時,在觀念中所保持的客觀對象的形象和客體形象在觀念中復現的過程。在此,表象似乎顯露出較多動詞的含義。后現代主義者相信,表象鼓勵概括,在概括活動中它又注重同一,因而忽視了差異的重要性。表象接納“在兩個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并將之歸屬于“全等,而否認差異”。由于表象“強調原型和被表象者的相同性,假定了同一性,而那種同一性蘊含著等價和等值”,⑨同注⑧,第144;144;118頁。因此,它的現代性的基本性質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基于對表象的認識和認同與否,后現代主義者大體分為懷疑論(否定論)者和肯定論(建設論)者兩派。其中,懷疑論者提出,不要關注可概括之物、統一之物、現代世界的平常之物,而要關注差異所暗含的一切,關注決不能被充分地表象的東西。這需要一個非表象的方法論。否則,將一事無成。⑩同注⑧,第144;144;118頁。關于肯定論者的觀點,有學者認為:
和懷疑論者一樣,肯定論者也傾向于擯棄普遍性真理,并且摒棄了真理是“在那里存在著的”、有待于人們去發現的觀點。但是他們中有許多人確實接受了特指局部的、主觀的、團體的真理形式的可能性。與懷疑論者相比,肯定論者不會輕易地說所有的真理觀都是相等的。不過,他們中保留了真理的那些人把真理相對化了,并且取消了它的特定的或普遍的內容。他們要么說真理等同于“自我理解”,要么主張真理因地點和歷史背景的變化而變化。他們聲稱相互沖突的真理不是問題,因為每個真理在一個不同的世界里都可以是真的(Goodman 1984:30-35)。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主張(Ferry and Renaut 1985:287)。最后,他們逐步將某種反理論的真理觀發展成給予日常生活和局部敘述以某種實質性關注的理論。?同注⑧,第144;144;118頁。
無疑,從藝術學科角度提出的“音樂”一詞,既是通過表象將不同對象和事物加以概括、歸納的結果,同時也被表象假定為在其原型和被表象者之間存在著同一性和同等價值。因而,無論在后現代的懷疑論者還是肯定論者看來,這種藝術表象都具備“本質主義”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但是,鑒于上述兩類學者對于“語境”有著相異的認識尺度和認同程度,他們分別采取了不同的應對策略。有必要指出的是,就筆者研究分析的結果而言,我們在此所說的這兩類學者或兩種應對策略,主要是體現在20世紀末與新世紀之交的兩種不同學術發展趨向上。而在此前的20世紀中后期,即所謂的人類學派與音樂學派展開論爭時,這兩種應對策略僅是初露端倪,似乎還處在某種模棱兩可的狀態之中。
在當代民族音樂學學科領域,有關本質論、表象論的討論涉及學科的基礎理論和主要性質層面。對此,筆者擬提出以下兩個必須予以進一步澄清的問題:其一,從一般意義上看,有關本質論與表象論的論爭與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理論的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其二,在民族音樂學接受后現代理論的過程中,由于受到人類學思維和方法的影響,其表現過程從時空關系上體現出某些與上述哲學、美學觀念不同的發展途徑。下文將繼續對此展開討論。
二、中國民族音樂學面臨的“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的復雜文化語境
作為非西方國家,中國音樂學界面臨的后現代“當地問題”及應對策略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在他們的(“他者”的)“后現代學術語境”中,必須面對雜糅中外風格的專業創作、流行音樂、本土傳統民間音樂等不同社會文化類型的并存,以及“前現代—現代—后現代”諸文化因素模糊不分的復雜局面。另一方面,在學術思維與方法論層面,面對前述不同研究對象,一部分學者持音樂文化哲學或美學的學術眼光,較多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后現代藝術思潮;另一部分學者則在漢族和少數民族音樂研究范圍內,把目光推及將上述學術領域與后現代人類學相結合的范疇。綜合這兩方面(類型與時間差別)的情況來看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的現狀,可以說我們在此時把民族音樂學中的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問題提出來討論,既晚于國內外音樂創作領域,也晚于國外的民族音樂學領域。但是,鑒于在我們自己的音樂文化中存在著因長期封閉的地理文化環境而存留的大量“前現代”音樂文化現象與因社會環境的驟然開放而產生的更為復雜的后現代音樂文化現象之間的矛盾,以及在音樂理論界存在的諸多從理論上對于“音樂”和“文化”研究比重的各執一端,從而,在書寫和分析的實踐上有“兩張皮”的矛盾現象。這些問題的矛頭都直指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以及“表象論”與“非表象論”的關系問題。同時,也正是因為理論和實踐發展滯后的原因,上述國內音樂文化實踐和理論界發生的事情頗像是對北美或歐洲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同類事件的重演。
上述現實造成了我們這一代中國音樂學者頗為尷尬的身份和位置:雙腳同時橫跨在現代性與后現代兩個門檻之間;在觀念和方法上也必須在兩個時期之間徘徊。由于北美民族音樂學已經走過了這段路程,從而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吸取、借鑒的教訓和經驗。這無疑也為我們不斷地重提那段幾乎已為美國學者所遺忘的學術性歷史提供了必要的依據。記得我曾經同一位華裔美國教授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我向她提起我本人對當年的胡德與梅里亞姆之間的那場“音樂學派”與“人類學派”的爭論仍有探究的興趣時,她說,在我們的課堂教學中,當然不會回避這段歷史,但一般只會花上20分鐘去講解,而不會在上面花太多精力,因為它離我們已經很遠。我回答,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我自己寫文章,還是教學生,都會花不少筆墨和時間去討論它。對我們來說,這樣做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就憑此事在美國發生后,在民族音樂學理論方法異地傳播的過程中,同樣事件仍在不斷重演這一點,就足以引起我們對它進行探究的興趣。對于美國本土學者來說,既想不到,也不愿關心,但對于事件發生地國家的學者來說,卻應該出于自身學術上的需要,對之重新解讀、審視和評價。因此,我們此時重提現代民族音樂學的早期發展歷史,既符合中國當代民族音樂學理論建設的需求,也是立足于非歐學者的學術和文化立場,對整個民族音樂學方法和歷程進行檢討、反思的必要之舉。
另外,在同這位教授的交談中,我也發現了一些中美學者因分屬“局外—局內”而存在于觀念和日常體驗中的細微差別。比如,當我們繼續討論有關胡德、梅里亞姆的學派之爭時,她認為鑒于胡德對美國民族音樂學學科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當代美國學者對于這些貢獻的認同和情感,要超過并掩蓋了對他學術觀念進行討論的興趣。這時,我又從中感受到了中美學者之間存在的一點不同之處:在我們非歐民族音樂學學者眼中,胡德主要是因為在自己的學術著作中闡釋了他對于音樂學研究的堅定信念及其學科方法論?例如后文將要述及的,他于20世紀60—80年代在諸多論著中闡述的帶有民族音樂學“音樂學派”觀點色彩的重要主張,以及提倡在田野考察中采用參與觀察手段以來獲得并運用“雙重音樂能力”(bi-musicality)的研究方法。而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我們的研究工作也給予了重要啟發。可是盡管他有關學科建設的理念早已在其幾次中國音樂學術之旅中留下了痕跡,但其中一些重要而正確的主張,卻似乎至今都未真正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換言之,對于局內的西方學者來說,學科觀念是隱藏于實踐行為之中的,認識和接受過程是潛移默化的。相較之下,對于居于局外的中國、日本等地學者來說,學科理論的傳播首先是思想和觀念的傳播,即對于學科基本概念、思維方式和文化觀等,在其理論研究及理論與實踐之間關系的討論中就會占有更為顯著的位置。由此可見,中國學界對于源自西方的民族音樂學的討論至今存在一些關于學科基本概念的模糊性認識和分歧觀念。看似僅涉及了淺顯而表皮的層面,然而,我卻認為:由于其中包含了某些外在的環境條件的差異——中西之間學科理論傳播的“時—空”差異,兩地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以及局內—局外觀的差異,而使我們不能不就該類問題中蘊含的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關系展開較深入的討論。
三、本質論、表象論學術論爭的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文化語境
(一)從“他者”和歷時性角度看本質論、表象論與現代—后現代理論的一般關系
在對“他者”——源自西方學術傳統的學術共同體及其學術話語系統和“我者”——以非西方藝術音樂為主的音樂文化研究對象系統進行理論上的區分和界定之后,可以肯定地說,迄今民族音樂學領域里有關本質論、表象論的討論,都是在“他者”的學術視野中,圍繞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歷時性交替和激烈論爭、交鋒中誕生的。當今的學術界對于“現代性”和“后現代主義”有著不同的解釋,其中的主要論點,是將現代性理解為貫穿在現代社會生活過程中的某種內在精神或反映這種精神的社會思潮。從這種角度來加以理解的“現代性”,往往成為“現代主義”或“現代精神”的同義詞。例如臺灣學者葉啟政認為:“現代性這個概念基本上是‘歷史的’,也是‘文化的’,其所呈現與反映的是歐洲人自某一特定歷史階段起的一種認知和期待心理、價值、信仰、態度與行動基調。”?葉啟政:《再論傳統和現代的斗爭游戲》,《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6期,第82頁。后現代主義者則認為,現代性(或現代理性)是啟蒙運動、現代科學和西方社會的產物。作為這種產物,理性在把啟蒙運動、現代科學和西方社會性的所有缺陷加以聯合方面,是有過錯的。理性,就像現代科學一樣,被理解成專制的、強迫的和極權主義的東西。由于假定了某個“最佳答案”和“某個唯一的解決方案”,它排斥了異端和寬容。?同注⑧,第191頁。這里涉及了對啟蒙運動之后出現在歐洲的“現代人”及“現代化”起到牽引和激勵作用的一種思想觀念、文化模式及行動準則。
除此而外,我們還有必要在此從歷時性,亦即方法論隱喻的代際變遷角度予以分析。
從歷時性視角看,有一種較溫和、中立的觀點,如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的:“后現代主義并不像它的名稱所暗示的以及流行的看法的誤解的那樣,是一種‘反現代’的思潮。應當說,它的基本內容是在20世紀上半期作為科學和藝術的主要宗旨便已經存在,只不過當初它們大多數停留在一種主張、宣言或構想之上,或僅僅是某一領域的特殊現象,而今天它已開始全面而深入地成為我們的生活現實。”?轉引自〔美〕羅蘭·羅伯森:《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梁光嚴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1頁。有關表象的后現代批判,尤其是懷疑論的后現代主義者的批判,在歷史上和哲學上受到了尼采、維特根施坦、海德格爾、巴爾特和福柯的啟示。福柯認為,在1650年到1800年之間(經典時期),表象是清晰、可靠而直截了當的,“表象是一個普遍、中性、自覺而‘客觀的’思維樣式”(1982)。但是當人們作為主體出現于18世紀末的時候,表象便逐漸地變得“昏暗不清”起來(1970)。因為人是他(她)自己知識的主體和客體,表象便變得復雜起來。它成了次要的和派生的東西,盡管沒有人認識到這一點(1970)。福柯得出結論:當表象的客體和主體緊密相關而非獨立自主的時候,單純、自然的表象便是不可能的了(1970)。因此,后現代的世界是一個不具有真正表象的世界。?轉引自〔美〕波林·羅斯諾:《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1992)》,張國清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第138頁。由此可見,關于現代性表象與后現代批判的順承關系,學者們從單一文化(西方文化)內部的歷時性角度劃出了一個較為清晰的時間表:經典時期,表象是清晰、可靠而直截了當的,此后則逐漸“昏暗不清”起來。另有學者指出:一般認為西方后現代主義時期開始于50年代末,這正好跟西方波普音樂的出現同時。?楊沐:《后現代理論與音樂研究》(下),《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第42頁。這就為民族音樂學中產生出以梅里亞姆觀點為代表的(準)后現代音樂人類學意識給出了必要的時限。同時,也為我們恰當地應用當代民族音樂理論提供了一個包括了理論與實踐、時間與空間要素的參照系。
由此來看現代民族音樂學學科里,從梅里亞姆、恩克蒂亞(J.H.Kwabena Nketia)到他們的后繼者賴斯(Timothy Rice)、西格(Anthony A.Seeger)等,其方法論及解釋體系中,不僅存在著現代性到后現代性之間方法論隱喻的歷時性變遷,而且在具有后現代性思維傾向的框架之下,同時兼顧并實踐著“非表象的方法論”與“認同表象的方法論”,在兩者之間尋找相互平衡的發展道路。他們與哲學社會科學學者一樣,循著與18世紀末以來“表象便逐漸地變得‘昏暗不清’”(福柯語)相反的路子,經歷了一個由簡略到復雜,由模糊到清晰的發展過程。由此可見,在梅里亞姆時代,一方面他在音樂文化觀層面較為籠統地提出民族音樂學即“音樂作為文化的研究”和“音樂即文化”等觀點,用來實現自己“非表象化的方法論”主張;另一方面則在學科方法論層面,提出并兼納使用“概念、行為、音聲”與“研究文化中的音樂”這一對看似相互矛盾、實際上卻彼此包含互補、呼應關系的研究范式,再通過微觀個案研究的實踐過程,用以應對和處理其非西方音樂文化研究對象中顯現的“前現代—現代—后現代性”曖昧、模糊的復雜狀況。
(二)從多學科、多文化及“我者”角度看本質論、表象論與現代—后現代理論的時空關系
從多學科交叉的角度看,中國民族音樂學學者所面對的不同后現代學術研究觀大致可分兩種:一種是較為徹底、極端的后現代懷疑論(如解構派)。該派源自歐洲的現代哲學、人類學和語言學等學科領域,以現代—后現代文化的交織更替為主要關注對象,尤以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及文學藝術領域的現代性思潮(如結構主義)為主要的批判和反思焦點。如同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后現代主義是眾多不同的、經常處于沖突之中的傾向的混合,它挪用、改造和超越了法國結構主義、浪漫主義、現象學、虛無主義、平民主義、存在主義、解釋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和無政府主義。”?同注⑧,第15頁。另一種是相對寬容、中性的后現代建設論(如闡釋人類學)。該派學術思潮主要形成于北美,以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諸階段的不同文化類型為關注對象,兼納產生自不同時期、來自不同地域的現代性—后現代性觀念和學術思想,在學科屬性上更傾向于文化人類學,更具有面向全球范圍和不同文化階層的特點。從歷時性角度看,上述兩者之間包含著某種顯在的歷史繼承性因素。這種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互相交替的現象,在當代則在不同文化之間,以共時性方式體現出來,并對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語境”研究觀念產生了明顯的影響。以人類學為例,有學者指出:從后現代人類學的發展過程來看,“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與美國人類學相比,英國人類學存在著較多的研究范式和規范;而且,也用似乎是較為精確的概念,這些概念在異文化的民族志描述和分析時十分有效。英國人類學享有崇高的威望并給美國人類學以巨大的影響……今天,這種影響的方向發生了反轉:美國文化人類學的產品廣泛而深入地影響著英國人類學研究努力的方向。同時,占據優勢支配地位的美國人類學傳統正受到現代人類學的三個主要傳統,即法國人類學傳統的強有力的影響”?同注?,第8-9;144;118頁。。也有學者以另一種角度思考,認為:“后現代轉折并非土生土長于北美;相反,它是一個歐洲大陸的養子,以德法血統為主。就像某位重要的法國知識分子沾沾自喜地指出的那樣,后現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就像博若萊新釀葡萄酒那樣也在北美的思想市場上銷售。”?同注?,第8-9;144;118頁。然而,我們一方面要看到后現代主義之風源自歐洲;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在北美人類學中,長久以來,一直都存在適合這類學術觀念在此生存的文化土壤——理論和實踐基因——博厄斯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文化生態學等基本學術思想。就此,筆者注意到,著名審美人類學家、荷蘭萊頓大學教授范丹姆(Wilfried Van Damme)曾說,當他20世紀90年代“回到了審美普遍性的觀念,嘗試運用達爾文主義的視角解釋這些普遍性”時,讓他“感到震驚的是,絕大多數人類學家對人類的整個普遍主義觀念持有敵對態度,這部分由于當時流行的后現代主義的深刻影響,它強調激進的文化相對主義,這種強調本身是基于大量人類學的調查,尤其是美國博厄斯學派的調查。很多人類學家拒絕任何意義上的普遍主義,對美學同樣如此”?〔荷蘭〕范丹姆、李修建:《審美人類學:經驗主義、語境主義和跨文化比較——范丹姆教授訪談錄》,《民族藝術》,2013年,第2期,第39頁。。換言之,包括梅氏在內的北美現代文化人類學家所持有的文化相對主義、微觀個案調查等基本學術觀念,確實同此后數十年間在北美發生的一系列較為激進、執著的后現代主義思潮有著諸多共同因素,但他們只是較多地繼承了本土的人類學遺產,而不盡然是吸取來自歐洲的后現代文化思潮,亦即在其人類學方法中,本來就包含了某些與后現代主義相符的理論和方法論元素。此后,于20世紀后半葉從西歐引入北美的后現代文化觀念,一開始較多是同藝術創作領域的后現代批評和解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等相關。相較而言,博厄斯雖然被劃歸現代人類學家之列,但他所提倡的文化相對主義、文化生態學等主張,從一開始就是與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分道揚鑣的,這是他與列維·斯特勞斯等歐洲現代人類學家不同的地方。那些帶有美國本土色彩的后現代觀念和主張,諸如后殖民主義、闡釋人類學等理論觀點,則是在對博厄斯上述學術思維予以繼承、反思的基礎上產生的。此外,北美人類學所進行的大量個案調查方法上的田野實踐,則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實踐行為內容和數據材料依據。
四、當代中外民族音樂學學者采用后現代研究思維和路徑的幾點表現
21世紀以來,一些西方民族音樂學學者帶有后現代主義風格的研究思維和方法,由于其研究對象與中國音樂文化有相似之處,或者就是以中國音樂為研究對象,從而為中國民族音樂學者所了解,并予以參考和借鑒。其中的一個例子是對以往民族音樂學研究中明顯帶有本質化、重表征的研究思維和方法進行揚棄,并且帶上符號化、隱喻化的思維,從后結構主義的研究路徑入手展開研究。從研究思維上看,他們“也傾向于摒棄普遍性真理,并且摒棄了真理是‘在那里存在著的’、有待于人們去發現的觀點。但是他們中有許多人確實接受了特指局部的、主觀的、團體的真理形式的可能性”?同注?,第8-9;144;118頁。。在此情況下,他們堅持結構主義重視探討“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以及“模式與模式變體”的分析方法,同時摒棄了早期結構主義分析遠離“歷時”和“語境”,在宏觀層面追求“宏大敘事”,在微觀層面僅注重采用文本化、形式主義的形態分析手段等做法。換言之,在他們眼中,對于他們的結構主義分析來說,那些“局部的、主觀的、團體的真理形式”不僅是有效的,而且是必須的。這些思維和方法后來被發展成為了民族音樂學分析中同局部文化和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實質性分析手段。在中外學者的此類研究中,為中國學者所熟知的西方學者的成果有如下兩例:一例是賴斯在《音樂體驗和民族志中的時間、場域和隱喻》一文中,在時空關系概念框架之外,選取了隱喻(而非明喻)作為自己對音樂研究對象進行區分和分析的平臺和入口。要知道,在文學修辭手法里,與明喻“將具有某種共同特征兩種不同事物連接起來看待”相比,隱喻是“用一種事物暗喻另一種事物”。當我們面對與文學相關或相異的不同研究對象時,通常可以采用某些現代或后現代人文社科理論和比較具體的形態分析手段展開研究。比如,在分類和描寫及其表達方式上,既可以采用明喻(或轉喻)的方法——一種現代性時期較典型的“本質化”表達方式,也可以采用隱喻(或暗喻)——一種帶有后現代色彩的“去本質化”表達方式。而在形態描寫方式上,前者(明喻)只能在符號自身(或能指)內部進行顯性、橫向的組合關系劃分;后者(隱喻)則在有必要持續關注音樂符號自身的模式系統狀況的同時,還必須進入符號的意義(或含義、所指)層面,對模式(橫組合關系)與變體(縱聚合關系)的兩軸對應和互補關系進行分析。賴斯在選擇了隱喻表達方式的同時,還舉例說明在特定社會里,音樂隨著時間和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在不同的情況下,音樂可以分別作為藝術、治療、娛樂、文字符號、社會行為、商品而存在。?Timothy Rice."Time,Place,and Metaphor in Musical Experience and Ethnography".Ethnomusicology,2003,Vol.47,No.2,pp.151-179.在這種帶有符號學與結構主義特點的分析和表述方式里,音樂及其不同的功能作為模式項和模式變體單元,其中的變體部分具有隱喻性或相互關聯性,是可以用縱聚合排列方式來表示的。倘若換一種明喻的方式,那么這些功能都可能是同時并置和互不關聯的,僅用普通的(不具有橫組合排列意義的)橫列表示即可。在上述賴斯的論文和相關專著里,不僅較好地應用了前一類藝術與文化形態分析的思維和方法,而且通過前述音樂文化意義與功能的隱喻性、模式性比較,將之與他在保加利亞田野工作中感受到的“短時段”歷史文化分期的語境予以聯系和對應,較為貼切地闡釋了他所提出來的“分析范式→形成過程→音樂學目的→人文社科目的”的“四級目標范式”?Timothy Rice."Toward the Remodeling of Ethnomusicology".Ethnomusicology 1987,Vol.313,pp.469-488.,從而較好地完成了一項音樂民族志個案課題的研究。另一個例子是英國民族音樂學家施祥生(Jonathan P.J.Stock)在《20世紀中國的音樂創作:阿炳、阿炳音樂及其意義變遷》(Musical Creativity in Twentiety-Century China:Abing,His Music,and Its Changing Meenings)一書里,采用如今西方音樂分析理論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之一——申克圖表分析法,對中國民間音樂家阿炳的二胡曲做了以音樂形態為主的模式與變體分析。?Stock,Jonathan.1996.Musical Creativity in Twentiety-Century China: Abing,His Music,and Its Changing Meenings.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在該案例里,作者一方面根據結構主義分析方法的縱聚合原則,將阿炳二胡曲中帶有相同樂思和形態特點的旋律片段的基本音上下對應,像樂隊演奏總譜那樣縱向排列起來,構成基于前景——樂曲全貌之上的模式(基本的旋律進行模態)與變體(基本模態的不同呈現方式)系統,同時采用申克分析法特有的前景、中景、背景的分析路徑,對之進行了歸納性的簡化還原分析,并且在此基礎上展開了進一步的語義和文化研討。可以說,這是一個西方民族音樂學學者采用后結構主義音樂分析思維和方法對中國傳統音樂進行藝術形態與文化語境研究的范例。值得討論的是,若避開申克及其分析理論的誕生年代——20世紀30年代前后的現代性背景來看,該分析理論在今天與后現代后結構主義有著緊密的嵌合關系并且得到廣泛應用。正應了美國學者羅蘭·羅伯森(R.Robertson)的那句話:“后現代主義被視為可以使傳統與現代的混合物合法化。”?〔美〕羅蘭·羅伯森:《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梁光嚴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9頁。由此看來,在“后現代”這個概念里,其實容納了“傳統”“現代”乃至“后現代”等不同元素。由此可以說明,在今天的西方民族音樂學領域,北美和西歐的民族音樂學都比較強調結合人類學思維和方法,對不同研究對象展開兼有音樂學和人文社科意圖的課題研究。但是緣于他們各自的學術傳統不同而對人文社科和音樂學兩個層面研究意圖各有偏重。就此,如果說能夠在同樣帶有后現代、后結構主義思維的不同民族音樂學分析方法之間做比較的話,上述賴斯和施祥生的兩個案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美民族音樂學和西歐民族音樂學的兩種不同學術研究傾向。
近幾十年來,中國學者也針對自己特有的研究對象,在民族音樂學后現代研究領域做了一定的探索和努力。除了本文提及的與后現代主義音樂思潮相關的理論性探討外,筆者僅從自身較為熟悉的少數民族和漢族傳統音樂研究課題來看,近年來比較突出的有如下幾種課題類型或研究傾向:
其一,帶有后現代、后結構主義分析方法特點的音樂隱喻與文化模式研究,分為音樂形態分析與超音樂形態分析(或文化分析)兩類。前者如一些具有后結構主義分析特征和鮮明中國特色思維的具體音樂分析方法。研究成果如周勤如?周勤如:《負陰而抱陽的兩儀五度相生陽變九音階——西北民歌新論之二》,《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第38-53頁。、蒲亨強?蒲亨強:《論民歌的基礎結構——核腔》,《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7年,第2期,第42-46頁。、楊民康?楊民康:《“減幅—增幅”與“模式—變體”——再論中國語境下的音樂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上、下),《中國音樂學》,2012年,第3期,第5-16頁;第4期,第87-99頁。等近年來發表的學術論著。這類成果將申克分析法、模式與變體結構分析法(如橫組合、縱聚合“雙軸”分析法)等原本單一(專注形態分析)、缺位(脫離語境)的音樂(或文化)結構與模式分析方法納入具體的歷史和文化語境,以圖構建“兩儀五度相生自然十二律音體系”“核腔分析法”“音樂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等新的音樂分析思維和方法。其中,有的(如周文)期望達到一種同時消解現代話語霸權、納入文化語境和重構宏觀樂論的全息性學術目的;有的(如蒲文)想要建立有關中國傳統音樂的新型形態分析方法;有的(如楊文)則意欲建立一種包含主客位“雙視角”、兼納簡化還原、轉換生成雙向路徑的音樂模式與變體分析方法。后者(如一些像賴斯那樣)意圖通過音樂作為表征的隱喻性研究來探求文化深層結構的闡釋性分析。比如楊民康在《由音樂符號線索追蹤到“隱喻—象征”文化闡釋——兼論音樂民族志書寫中的“共時—歷時”視角轉換》?楊民康:《由音樂符號線索追蹤到“隱喻—象征”文化闡釋——兼論音樂民族志書寫中的“共時—歷時”視角轉換》,《中國音樂》,2017年,第4期,第26-34+40頁。一文中,應用“時間、場域、隱喻”主體音樂民族志理論方法對云南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的孔雀舞音樂進行的研究;楊紅在《當代社會變遷中的二人臺研究》一書中,采用上述理論對內蒙古二人臺劇團及其音樂進行的研究。此外,近年來出現的有關音樂與節慶儀式的同型同構、異質同構分析等也可以歸入此類。
其二,有關音樂文化變遷、融適的專題性研究。有鑒于該類研究方法中包含了超越本質主義、文化中心主義的“解構、建構、重構”文化分析意圖,故在目前國內具備后現代音樂文化危機意識的學者中已經產生了較大影響。成果如楊民康等在《傳統與變遷:侗族大歌再研究》一書里,借鑒后現代主義研究思維和視角,結合“傳承、建構、創新”諸文化層面,對以侗族大歌為代表的侗族傳統音樂與現代經濟、旅游文化及現代教育相遇后發生的文化變遷,以及主、客位互動、交錯關系等進行了整體性、多側面研究。
其三,音樂與文化身份認同研究。2014年以后,魏琳琳在其博士導師楊民康的倡導、支持和鼓勵下,陸續翻譯了發表在《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上與“音樂與認同”相關的論文,并進行發表,呼吁民族音樂學家和人類學家就“音樂與認同”主題進行跨學科對話。2015年至2018年,楊曦帆的《音樂的文化身份——以“藏彝走廊”為例的民族音樂學探索》(2015)、趙書峰的《族群邊界與音樂認同——冀北豐寧滿族“吵子會”音樂的人類學闡釋》(2017)和魏琳琳主編的《音樂與認同》(2018)三部著作先后出版。其中第三本書是2017年民族音樂學和人類學兩個專業方向學者在內蒙古藝術學院聯合召開學術研討會和圓桌論壇的學術論文集,包括了不同學科彼此間富有啟發性的對話。這是目前國內音樂學界在跨學科對話語境中產生的較為重要的學術成果,且由此開啟了中國傳統音樂與文化認同研究領域以學術共同體身份一同撰寫和發布學術專著的先例。在論文發表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該學術共同體在楊民康主持下,由楊民康、楊曦帆、趙書峰、魏琳琳、胡曉東、張林、李延紅、李緯霖、董宸、苗金海、路菊芳分別撰文,先后在本學科的三個核心刊物上發表了三個相關的學術專題:其一是在《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刊發的“‘音樂與認同’語境下的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研討專題,一共7篇。該組論文結合海內外文獻,回顧了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民族音樂學屆開始關注“音樂與認同”的關系問題的歷史,以及90年代中國學者亦開始借鑒人類學的同類研究方法及成果,對中國漢族傳統音樂及少數民族音樂與文化認同的關系問題展開的一系列討論和研究。這些論文首次由中國學者對文化認同與音樂認同的關系作出明確的理論界定,集中體現了該學術領域在中國學界的最新進展,為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提供了新的學術思路和方法。其二是在《音樂研究》2019年第1期發表的“音樂文化與身份認同”研究專題,一共6篇。該組論文從“跨界族群音樂”“宏觀與微觀”“傳統的發明”“傳統的建構與認同”“樂器、身體與文化認同”等角度展開話題。其三是在《中國音樂》2020年第1期和第6期發表的“中國少數民族節慶儀式音樂的建構與認同”,一共11篇。主要聚焦中國民族音樂話語體系研究的“兩頭熱,中間冷”現象,提出少數民族當代節慶與儀式音樂活動涉及文化身份塑造與建構過程,學界和學者有必要在繼續展開“非遺”音樂傳承與保護研究的同時,以少數民族傳統節慶儀式活動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和載體,重點關注少數民族主體、地方政府與國家三者之間的多維互動關系,以及以傳統節慶儀式音樂活動為代表的社會音樂文化實踐活動在文化認同多層級(階序)構建方面發揮的重要意義與功能作用。
此外,與中國傳統音樂、跨界族群音樂相關的后現代主義研究思維和方法,還有用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內部東方主義等研究觀念去考察少數民族流行音樂、旅游音樂和“海上、南方”絲綢之路離散族群音樂等諸多課題,今后或以專文再做進一步研究分析,在此恕不一一枚舉。
結語
若給上述中國民族音樂學領域發生的后現代主義研究思維和方法一個簡略的結論,目前的學科研究對象還主要局限于傳統音樂,旁涉城市音樂和流行音樂等,再加上其他種種原因的限制,我們的此方面研究的范圍還更多局限在一些偏重藝術性和人文性的內容方面,研究思維和觀念上也還明顯偏向于較溫和的“建設派”特點。今后還有待更多富含思想性、哲學性和學術前沿性的研究觀念和方法出現。
當今世界已經進入后現代時期,身為非歐地區的中國民族音樂學學者,我們的思維、方法無疑也與那些西方學者一樣,從總體上看,具有這一基本的階段性特征。但是,若從具體的研究對象及其應對策略看,我們所面對的則是與西方后現代文化學者不盡相同的,更為混融、復雜的學術局面。因此,采納、吸取什么樣的后現代學術研究觀,是我們這一代中國民族音樂學學者正在面臨的一個很大的難題。
從相同的一面看,我們彼此所面對的研究對象里,都雜糅了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諸種因素。由于研究對象的復雜性,我們的研究思維、觀念和方法中,也同樣包含了諸多主要來自文化哲學、人類學和語言學等現代學科,跨越了上述三個階段時空關系的學術因素。而從相異的一面看,在以西方現代文化為對象的后現代語境里,以相對龐然、穩固的現代性為中心,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諸要素之間涇渭分明,學者們也依此劃分為具有不同主攻方向的學術陣營;而在我們的非西方文化學術語境中,現代性的因素明顯偏弱,很多時候,前述三個階段還具有前后貫通,無法以現代性加以完全分隔的特點。就此筆者認為,我們在對待西方后現代主義研究方法時,應該采取與西方文化陣營有所區別的對策和方法。同時,在如何認識我們自己學科的歷史和學術傳統時,也應該持有一定的相異態度。比如,在持徹底、極端的后現代懷疑論(如解構派)與較寬容、中性的后現代建設論(如闡釋人類學)兩派之間,盡管二者對于“本質”和“表象”具有的不確定性都持有認同的態度,但同樣也由于彼此對于“上下文語境”所起的限定作用存在著認識差別,使他們在批判和運用的尺度上表現出無條件與有條件之分,并因此導致了雙方在音樂民族志研究觀及考察實踐方式上產生了明顯的差異。
從“我者”的角度看,非西方國家(音樂)人類學者的學術態度和發展意愿,很大程度取決于解決本土文化生存與發展的現實需求,具有較明顯的后發性和即時性等特點。有學者認為:“在現時代,對全球相互依賴性的認識和覺悟,沖擊著學術研究的民族傳統分立的觀點。雖然我們不能否認學術研究的民族傳統仍然有其微妙的重要性,但是民族傳統已不再是交流和互動的障礙。在巴西、印度、以色列、日本和墨西哥以及其他一些國家,新的人類學者是在受到當地問題以及西方社會理論的傳統問題兩者的綜合影響下崛起的。”?〔美〕馬爾庫斯、費徹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王銘銘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9頁。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應該說,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兩類學術觀念并存于各國音樂理論界的共時性特征已經延續了很久,至今還存在于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同地區,并且還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延續下去。在中國這樣的民族音樂學理論的晚至區域,該學科真正進入不過二三十年,像西方社會那樣由現代性向后現代性轉型的過程,在中國遲到了更不止這些時間。鑒于目前中國音樂研究領域在此方面的研究還異常薄弱,很多對于具有較成熟的后現代理論學術思維的西方學者看似屬于“小兒科”“不值一顧”,顯得“陳舊”的常識,或許正是在這一時期讓東方青年學子充滿困惑,要想弄明白的問題,同時,這也是在自己的學習、求知道路上繞不開的環節。因此,我們既有必要從現代民族音樂學的發端時期開始“補課”,同時也應該結合自己音樂研究對象十分豐富、復雜的國情特點,盡可能發揮我們已經逐漸積累起來的較好的學術研究基礎和潛在的“后發”優勢,讓我們的后現代民族音樂學/音樂民族志研究快速崛起,逐漸走向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