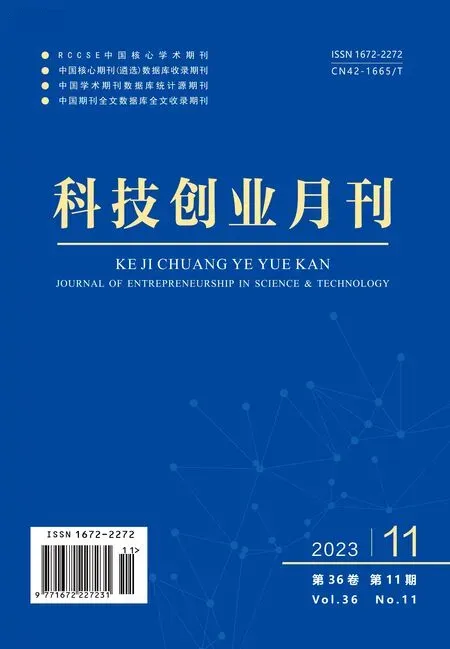網絡直播知識產權風險多元化治理研究
余立立,胡神松
(武漢理工大學 法學與人文社會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0 引言
網絡直播作為一種新型娛樂方式,2016年以來在我國呈井噴式發展。《中國網絡表演(直播與短視頻)行業發展報告(2022-2023)》顯示,2022年我國網絡表演行業市場規模達1 992.34億元,具有直播經營資質的經營性互聯網文化單位6 263家,主播賬號累計開通超1.5億個,同比增長7.1%[1]。隨著網絡直播從業者的大量增加,網絡直播行業成為知識產權風險高發地區,對網絡直播知識產權風險的多元化治理,有助于凈化網絡空間,維護權利人權益。通過中國知網數據庫(CNKI)、Web of Science(WOS)核心數據庫,對國內外關于網絡直播知識產權風險問題研究進行文獻檢索,并運用CiteSpace對所得文獻進行知識圖譜分析,得出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體育賽事直播畫面是否構成單獨作品類型及如何認定其獨創性的問題;二是網絡游戲直播行為是否構成侵權、侵犯何種權利以及網絡游戲直播畫面是否構成合理使用的問題;三是從行政監管及侵權賠償等方面提出網絡直播音樂著作權保護與救濟的相關對策;四是從法律層面提出網絡直播監管的相應路徑,如提高立法層級、設置專門機構行使專屬監管權以及完善懲戒制度等。但對于網絡直播中出現的其他知識產權客體風險問題、網絡直播知識產權風險治理困境以及從多元協同、齊抓共管、整體推進的角度實現綜合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尚不深入。新時代網絡經濟、數據經濟、知識產權經濟飛速發展,對網絡直播知識產權風險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因此需要通過健全法律法規、細化行業規范、明確平臺責任、強化技術輔助及提高主播法治素養等來完善網絡直播知識產權風險多元化治理路徑。
1 網絡直播概念界定與分類
依據《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網絡直播又稱互聯網直播,是指基于互聯網,以視頻、音頻、圖文等形式向公眾持續發布實時信息的活動[2]。按照網絡直播的內容進行分類,可將網絡直播劃分為秀場類、游戲類、泛娛樂類、專業類和電商直播類[3]。秀場類直播是指主播通過視頻錄制工具,實時向直播間觀眾表演歌曲、舞蹈等節目以期獲得一定金額打賞的表現形式[4],代表平臺有YY直播、六間房等;網絡游戲直播分為游戲主播錄制的游戲節目與大型的電子競技直播,游戲主播錄制的游戲節目是主播通過加入對游戲的操作和解讀,與觀眾進行互動的直播形式[5],代表平臺有虎牙、斗魚等;電子競技直播是以游戲競技比賽為基礎,比賽現場主持人對游戲畫面進行解說,并配以相關字幕、音樂與競技數據信息的直播形式[6];泛娛樂類涉及內容較為豐富,常包含吃播、萌寵、影視等生活化內容,代表平臺有抖音、快手等;專業類直播則涉及財經、法律、醫療等專業性較強的領域,在Bilibili較為常見;電商直播類常搭載于購物平臺,如淘寶、京東等。
2 網絡直播知識產權風險類型
2.1 著作權侵權
由于網絡直播通常呈現為“畫面+聲音”的模式,因此著作權侵權風險高發于網絡直播中。一是游戲直播著作權侵權。由于我國并未將網絡游戲單獨作為一種類型化作品予以規制,所以在司法實踐中對于網絡游戲畫面的定性問題還存在不同觀點[7],但總體上我國學者在理論上肯定了部分網絡游戲畫面只要符合獨創性就可以構成作品,受到著作權保護,只是對于獨創性的標準,目前還存在爭議。因此,在游戲畫面符合獨創性而構成作品的情形下,游戲直播將游戲畫面進行直播的行為,具有侵犯游戲開發商著作權的風險。二是音樂作品翻唱與背景音樂播放著作權侵權。網絡主播表演獨創性作品不多,往往系未經著作權人同意私自表演或者播放他人尚在著作權保護期內的作品牟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規定[8],使用這些處于著作權保護期內的作品,應當獲得作品著作權人許可并支付使用費,否則就構成對著作權人的侵權。同時,這種利用他人作品謀取金錢打賞的牟利行為并不屬于著作權法所規定的的合理使用范疇。例如,主播馮提莫在斗魚直播平臺直播時將歌曲《戀人心》作為背景音樂,詞曲作者張超以斗魚公司侵權為由提起訴訟,2018年年底,北京互聯網法院一審判決斗魚直播敗訴[9],斗魚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由于主播個人和直播機構直播時通常未對音樂曲目進行篩查,對于音樂的授權事宜也未做準備,因此網絡直播成為著作權侵權的重災區。
2.2 專利、商標侵權
我國專利包括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由于一項產品可能同時存在商標權與專利權,因此商標權、專利權侵權風險也高發于電商直播中。在電商直播中存在大量假冒注冊商標、專利產品,如上海警方偵破的廖某售賣假貨案中,廖某及其團隊于2020年3-8月在電商直播平臺以直播方式為商家營銷假冒DIOR、CHANEL、LOEWE等品牌服裝、手表等商品,銷售額近70萬元[10]。此類行為侵犯了權利人的商標專用權和專利權人的合法權益。考慮到電商直播的特殊性、直播平臺的審核能力和審核成本等,立法并未對網絡直播平臺采取嚴苛的事前審核標準,導致電商直播經營者準入門檻低、違法行為難以及時被監測等問題。即使侵權賬號被封禁,侵權者仍能通過重新申請小號進行直播,致使網絡直播專利權、商標權侵權現象屢禁不止。
2.3 其他知識產權侵權
網絡直播知識產權侵權風險還表現在商業秘密、地理標志等方面。目前已有地區發布了規范直播電商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相關文件,如廣東省印發《直播電商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指引》[11],引導MCN機構保護商業秘密和地理標志,對于涉及到技術信息、經營信息的商業秘密,建議MCN機構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比如設定訪問權限、添加商業秘密水印標識、與商業秘密有接觸的工作人員簽訂保密協議等;MCN機構方如需播出涉及地理標志的相關內容,須先行獲得地理標志權利人關于所播出地理標志的權利證明及地理標志使用人依法使用地理標志的承諾。但由于網絡直播行業仍處于新興發展階段,侵犯商業秘密、地理標志等行為仍時有發生,需進一步完善相應法律規范。
3 網絡直播知識產權風險治理困境
3.1 法律法規不健全
我國先后出臺了《網絡交易監督管理辦法》《關于加強網絡視聽節目直播服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和《網絡表演經紀機構管理辦法》[12]等文件,對網絡直播行業進行了約束,但對網絡直播中主體的法律地位、主體責任分配等還需進一步明確和細化;對網絡直播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賠償規定,如補償性賠償、懲罰性賠償或者法定賠償金的適用規定還需進一步完善。在上述廖某知識產權侵權案中,廖某場均銷售額突破7位數,年收入超過千萬元,但其最終僅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4個月,處罰金人民幣40萬元。馮提莫未經許可在直播間演唱歌曲《戀人心》并將視頻保存在斗魚直播平臺上,最終武漢斗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只被判處賠償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經濟損失2 000元及許可使用費3 200元。在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以及許可使用費難以計算時,應當將侵權人的故意程度作為確定法定賠償金數額的法定因素。現有法律法規對于侵權人的惡意并未作出具體規定,因此可以通過對侵權行為的性質、時間、后果等進行細化,判斷侵權人的主觀過錯程度,從而為網絡直播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賠償適用提供法律依據。
3.2 行業規范不夠完善
國家已經通過發布《關于加強網絡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關于進一步規范網絡直播營利行為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的意見》[13]等文件對直播行業進行規范,但行業規范中依然存在知識產權相關規定不完善、對直播平臺的指引和監管不充分等問題。首先,網絡直播行業中關于知識產權的相關管理與規定不夠明晰。在斗魚、虎牙等頭部直播平臺的直播協議中,雖然對主播方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行為作出了禁止性約定,但對何為侵犯他人知識產權并未作詳細解釋,主播方往往難以意識到侵權行為并知曉相應法律后果。其次,網絡直播行業與傳統行業相比,就業形態存在明顯區別。網絡直播行業用工較為靈活,工作時間、地點、方式等不固定,網絡主播通常不需要去專門的地點工作,只需一臺移動網絡設備就可進行直播,同一MCN機構的簽約主播可能來自全國不同地區,因此,直播公司對主播進行集中統一的知識產權培訓與考核的難度較大,加大了網絡主播侵犯知識產權的風險。最后,在電商直播領域中,由于電商機構間的競爭關系和電商平臺經營范圍的多樣性,整個行業的資源與信息難以共享,也無法定期開展行業交流會或制定行業規范,加大了網絡直播知識產權風險治理難度。
3.3 平臺監管不到位
網絡直播平臺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監管主要體現在對侵權主播的處罰、主播及電商企業資質認證以及協助權利人維權3個方面。目前,在對侵權主播的處罰方面,網絡直播平臺主要采取封禁其賬號的方式,然而封禁時間較短,且很少永久封禁,導致網絡主播的試錯成本較低。在主播及電商企業資質認證方面,網絡直播平臺對主播資質認證往往較為寬松,只需上傳身份信息即可進行直播,因此存在借用他人身份信息進行直播的亂象,導致發生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時,難以對實際侵權人進行規制;且網絡直播平臺僅在前期注冊時審核電商企業營業執照、ICP經營許可證及相關行業許可證,如食品流通許可證等,當網絡主播進行帶貨直播時,并未要求企業上傳商品質檢報告,導致部分企業出現售賣他人知識產權商品的行為。在協助權利人維權方面,由于網絡直播的隨機性特點,網絡主播對于權利人作品的使用或商品的銷售可能僅限于某一場直播,權利人很難及時對網絡主播侵權行為進行錄音和錄像,這就要求直播平臺實現便捷、有效的舉報及存證功能。以斗魚和虎牙直播平臺為例,這兩個直播平臺無論是網頁端還是移動端,都已設置舉報按鈕,且對舉報理由進行分類,如低俗色情、版權糾紛等,對于舉報結果也能通過舉報人留下的聯系方式(如QQ、電話等)及時反饋。斗魚直播平臺能自動截取舉報人點擊舉報按鈕瞬間的直播截圖,方便舉報人存證。但由于網絡直播知識產權侵權往往涉及聲音、圖像等多方面,一張截圖很難充分證明侵權事實,因此需要加大平臺監管力度,對于權利人點擊舉報按鈕前后一整段時長的直播進行錄像,協助權利人維權。
3.4 監管技術創新不夠
根據《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14],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落實主體責任,配備與服務規模相適應的專業人員,健全信息審核、信息安全管理、值班巡查、應急處置、技術保障等制度;應當建立直播內容審核平臺,根據互聯網直播的內容類別、用戶規模等實施分級分類管理,對圖文、視頻、音頻等直播內容加注或播報平臺標識信息,對互聯網新聞信息直播及其互動內容采取先審后發的管理模式。由于直播流量較大,采取純人工手段對網絡直播侵權風險進行監管往往收效甚微,因此,直播平臺一般采取以機器審核為主、人工審核為輔的監管手段,通過屏幕捕捉技術、人工智能、算法和OCR技術來識別侵權內容。然而,由于近幾年網絡直播平臺的大量出現,平臺間同質化競爭嚴重,部分直播平臺為降低成本,并未配備專業的技術人員,不能及時更新技術手段對網絡直播中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進行有效監管。另外,直播平臺的算法推送也是網絡直播侵權的一大潛在因素。算法推送是基于網絡用戶在一定時間內的歷史選擇記錄、評論以及相關輔助信息來發現其關注的內容,如果網絡用戶的選擇偏好正好涉及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時,直播平臺所推薦的內容就可能是用戶擅自上傳的未經著作權人同意的侵權作品[15],因此,直播平臺的算法推送技術亟待進一步優化。
3.5 主播法治意識不強
網絡主播素質良莠不齊,部分網絡主播并無良好的專業背景,是當下網絡直播知識產權侵權案件頻發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據2017年騰訊研究院聯合龍珠直播平臺對4 500名網絡主播的調查結果顯示,網絡主播的學歷主要集中在初、高中等中等學歷水平。其中高中學歷的網絡主播最多,占比33%,其次為大專、初中學歷,占比分別為24%和23%,本科學歷占比15%,碩士和博士學歷占比僅3%[16](圖1)。網絡主播較少接受過專業法律培訓,對知識產權概念模糊,并且部分網絡主播面對金錢打賞的誘惑或為了增加用戶關注量,極易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線,以違法犯罪的方式開展直播活動。

圖1 網絡主播學歷構成情況
4 網絡直播知識產權風險多元化治理對策
4.1 完善直播法律法規,提高懲罰賠償力度
我國當前互聯網立法仍處于探索階段,司法實踐中很多網絡直播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判決標準不一,不能有效發揮法律的預測和強制作用。因此,立法部門可以考慮制定專門針對網絡直播行業的法律法規,在專項立法中明確直播平臺、網絡主播的權利和義務,并確保相關條款的可操作性[17],為執法者和司法機關確立統一規范。首先,法律法規應將有關問題加以明確,如游戲畫面的著作權歸屬和主播使用他人作品在何種程度屬于合理使用范疇等問題。其次,由于網絡直播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以及許可使用費往往難以計算,司法機關在辦理網絡直播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時,應當根據適用比例原則確定法定賠償金,以及侵權人的惡意程度提高嚴重侵權行為人的違法成本,加強對網絡直播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處罰力度,以此激勵權利人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4.2 細化行業操作規范,建立行業協作機制
加強網絡直播行業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直播平臺、網絡主播、MCN機構和電商商家都應充分自省自查。首先,應當加強直播行業知識產權保護,在平臺協議、電商入駐協議中細化知識產權相關規定,依法建立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包括但不限于通知、移除等規則,同時在網絡主播、電商商家簽約協議中增加知識產權警示條款;其次,MCN機構與主播合同中也應加入知識產權條款,對知識產權賠償及責任承擔作相關說明;再次,直播公司應當通過定期組織線上會議、開發公眾號推送網絡直播產權知識及侵權案例等方式對簽約主播進行知識產權培訓與考核,從而提高網絡主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最后,在電商直播中,電商主播、MCN機構不僅要注意所銷售商品本身是否涉及知識產權侵權,同時還應該關注直播內容是否涉及知識產權侵權,MCN機構應按要求落實主播實名制,拒絕非實名認證主播加入直播行業,商家自身也應當提前審查銷售商品是否具有知識產權侵權風險。網絡直播從業者以及MCN機構應當帶頭建立行業協作機制,通過組建行業協會、召開行業交流會等形式,整合行業資源與信息,細化行業操作規范,將主播、MCN機構對電商產品的審查程序,以及直播公司對主播的定期知識產權培訓與考核作為行業標準加以確立,制定全行業信用體系與征信體系,營造良好的行業競爭秩序。
4.3 明確直播平臺責任,協助權利主體取證
直播平臺的盈利模式和運營模式決定了直播平臺相較于傳統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承擔更高的責任義務。直播平臺的內容來源于主播,在某些平臺與主播的合同中甚至約定主播直播產生的一切作品著作權由平臺享有。因此,根據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網絡直播平臺不僅是網絡服務的提供者,還是平臺音、視頻產品的所有者,其享有這些成果所帶來的收益。網絡直播平臺并不能依據“避風港原則”免責,即使其及時刪除了存在侵權內容的涉案視頻,其仍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平臺應當建立直播帶貨準入機制,履行對直播間運營者資質、商品等的審核義務,并制定公開直播平臺規范。同時,直播平臺應當積極協助權利人維權,健全、完善直播內容監看、審查,侵權及及時阻斷等制度,對涉及權利人投訴的網絡直播視頻強制保留直播回放,或將涉及投訴的電商直播產品強制留樣,為權利人提供高效、便捷的維權通道和存證渠道。
4.4 加強監測技術創新,引入多元監測主體
針對網絡直播知識產權侵權問題,我國網絡直播行業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經驗。英國對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的監督,由網絡商和網絡用戶共同建立一個獨立組織,由該組織負責對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SP)進行職責分工;新加坡實行嚴格的互聯網“審查制度”,由政府信息與藝術部下設的檢察署依法負責對在互聯網上傳播的信息進行審查[18];韓國政府非常重視網民監督舉報機制,將用戶對直播平臺侵權行為的監督力度發揮到最大。我國目前網絡直播依然采取技術監測為主、人工審核為輔的監管模式,因此,完善我國網絡直播監測機制,可以從技術和人工監測主體兩方面加以完善。在技術方面,可以對數據交互進行監控,對于識別出的疑似侵權的直播源頭進行截斷,在減少算法推薦侵權作品推送的同時,加大算法對侵權直播舉報的監測力度,并將多次被舉報的直播間提交到人工審核組做進一步判定。在人工監測主體方面,一是可以將政府監管部門、社會組織和用戶等多方監測主體引入網絡直播侵權監督中,針對網絡直播知識產權侵權問題,政府監管部門可以采取類似指導組進駐直播平臺的方式進行指導與整改。二是落實人工監測內部責任制,明確各分類管理員職責,避免各分類管理員互相推諉,發揮人工監測的優質過濾器作用。
4.5 實施資格準入制度,提高主播法治素養
治理網絡直播知識產權侵權風險,要從源頭規治網絡主播的侵權行為。網絡直播行業應當提高網絡主播入職門檻,對網絡直播從業人員實行職業資格準入制度。2020年,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和國家統計局等部門聯合發布了互聯網營銷師等9個新職業信息[19],其中,在“互聯網營銷師”職業下增設“直播銷售員”,意味著帶貨主播成為國家認證的新興職業。網絡直播行業應當實行職業資格準入制度,將直播銷售員證書作為網絡直播從業人員的硬性要求。在職業資格考試培訓中,應當融入知識產權法律知識,以提高網絡主播法治素養。同時,要落實網絡直播跨平臺警示名單制度,對于某一網絡直播平臺內有多次不良記錄的主播要及時進行管理和整治,并對違規主播作出跨平臺禁止直播的嚴格限制,以增強網絡主播的法律責任意識。
5 結語
針對網絡直播知識產權風險問題,在法律層面,制定專門針對網絡直播的法律法規,提高侵權人侵權成本;在行業層面,細化網絡直播行業規范,完善合同條款及加強主播知識產權培訓,加強主播行為規范;在技術層面,創新平臺監測技術,提高網絡直播平臺對直播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審查和監管水平;在主播層面,提高網絡直播從業者的法治素養和法律意識,從源頭上減少網絡直播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發生。通過網絡直播知識產權風險多元化治理,為網絡直播行業健康、有序發展提供堅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