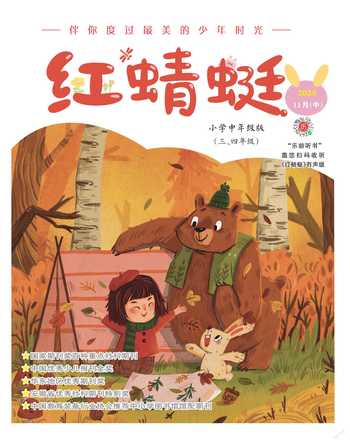不能忘卻的容顏
祝鴻霞



在合肥蜀山烈士陵園,有一張寫著我爸爸名字的照片。我的爸爸叫王亞箴,是一位革命烈士。很少有人知道,烈士陵園里那張照片上的人,其實并不是我爸爸,而是我。
我的爸爸出生在蚌埠五河縣的天井湖畔,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家鄉開展革命,組織農民運動。后來,爸爸被國民黨抓進了監獄,受盡酷刑。爺爺愛子心切,心急如焚,探監時,把“認了吧”的字條塞入饅頭中,勸他早日認“罪”出獄。爸爸看后,只回復了“此藥不能服”五個字,表達他對革命的忠誠。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合作,共御外辱。爸爸結束了五年多非人的牢獄生活,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斗爭中。在淮北抗日根據地,爸爸擔任了抗日民主政府的縣長。他所戰斗的地區,緊鄰著兩條重要的鐵路,沿線日偽據點林立,斗爭環境險惡。爸爸既要參加敵后抗日游擊戰斗,對付敵人的大規模“掃蕩”,還要組織根據地群眾為抗日隊伍籌集后勤補給。
那個時候,物資很匱乏。有一年冬天,縣里籌集到了一批棉衣,有人看爸爸身上的黑色棉袍又破又舊了,就給他送來一件新棉衣,可是爸爸堅決不接受。他的破棉袍,白天當棉衣,夜里當被子。
有一年,五河縣鬧饑荒,縣里籌到一批救濟糧。那時家里有好幾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媽媽又剛生下我,連雜糧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可是爸爸在發放救濟糧時沒有為我們家多爭取一粒糧食。婦救會得知情況后,悄悄派人送來了40斤小麥。媽媽很高興,爸爸知道后卻原封不動地把小麥給退回了。
爸爸就是這樣,用他的忠誠堅定、大公無私和以身作則,贏得了根據地軍民的擁護。大家團結一心,艱苦斗爭,終于迎來了抗戰的勝利。
正當淮北解放區軍民準備休養生息、恢復生產時,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又開始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由于解放區主力部隊已經撤走,面對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爸爸帶領地方武裝堅持游擊斗爭,他們忽攻忽停,忽進忽退,轉戰到洪澤湖地區。最后,在1946年一個雨雪初停、濃霧彌漫的早晨,在敵人重兵包圍下,爸爸的隊伍彈盡糧絕,被打散,他也倒在了洪澤湖畔。
新中國成立后,黨史部門整理爸爸的資料,怎么也找不到爸爸的照片。爸爸當過區長、縣長,應該是有機會照上一張照片的,可是他生前竟然沒有留下一張照片。
于是,大家便想根據親人和戰友的描述為爸爸畫一張遺像,但怎么畫都覺得不太像。這時,有人提出讓我和姐姐穿戴上爸爸的衣服、帽子試著拍張照片。照片一拍出來,大家都指著我的照片說:“小三子像,小三子最像!”就這樣,我的這張“女代父照”就成為爸爸的遺像,展示在了蜀山烈士陵園。
其實,爸爸犧牲的時候,我只有3歲。爸爸的樣子在我的記憶里也只是一個模糊的身影。長大以后,每當想起爸爸,我就拿起我的那張據說最像爸爸的照片,想著爸爸的故事,在腦海里一點一點還原他長著怎樣的面龐輪廓、怎樣的眉梢眼角……
在革命年代,像爸爸這樣的烈士還有很多。他們生前沒有留下過照片,甚至很多連姓名也沒能留下。今天,我們只能憑著親人的記憶去描摹他們的容貌,只能靠著模糊的線索去尋訪他們的英名。有人說,他們的模樣,就是歷史的模樣。我相信,他們的容顏已經融進了歷史,永遠不會被忘記。
- 紅蜻蜓·中年級的其它文章
- 鸚鵡百花
- 收獲
- 航天夢
- 變色的小喇叭
- 打造一支神奇的“學習箭”
-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