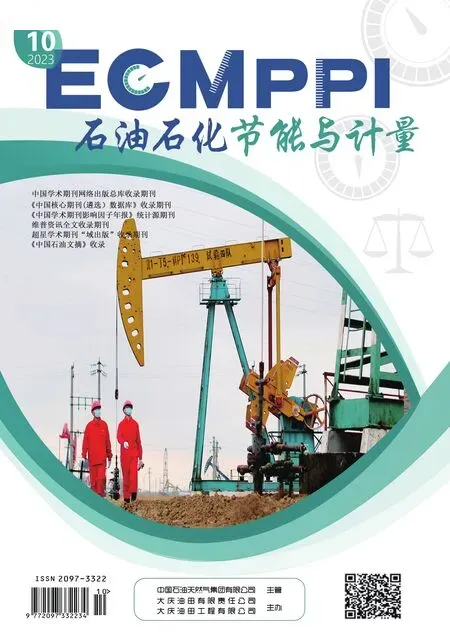“雙碳”目標下川中低碳發展的資源優勢與建議
林涵 林青 張文霞 趙鐵 陳垚 王歡 李紅彬
(1.西華大學電氣與電子信息工程學院;2.中國石油西南油氣田公司川中油氣礦)
油氣開采業是碳排放的重點行業之一,生產過程中消耗大量的天然氣、電等能源,排放CO2,特別是含硫氣田。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中石油面對世界能源格局的深度調整,肩負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對能源消費快速增長的剛性需求,助力國家實現“雙碳”目標的雙重使命[1],明確“清潔替代、戰略接替、綠色轉型”三步走總體部署[2],加快推進綠色低碳發展。2021 年5 月中國石油等七家企業聯合發起成立中國油氣企業CH4控排聯盟,致力于油氣生產、儲運、銷售全產業鏈管控CH4排放,力爭2025 年將天然氣生產過程CH4平均排放強度降到0.25%以下。川中含硫天然氣生產用能占比超過氣田用能總量的80%,CO2排放量的84%以上源于燃料天然氣燃燒。川中地區光伏、風電資源稟賦不足,但作為西南油氣田主力天然氣產區,具有天然氣管道壓力能、放空天然氣回收、低小產井天然氣發電、氣田水提鋰提溴、H2S 利用等優勢,為綠色低碳發展提供良好的資源條件。
1 碳排放情況
1.1 主要碳排放環節
試油試氣、用氣設備、天然氣凈化工藝過程直接燃燒天然氣排放CO2是油氣生產活動的主要碳排放環節,CH4排放主要源于天然氣放空及氣田水、原油等地層產出液收集儲存系統。
1.2 碳排放現狀
1.2.1 CO2排放
試油試氣(放噴測試)是油氣開采重要的碳排放環節,通過求產放噴排出井筒積液、疏通近井筒地層油氣通道,獲取準確的氣藏油氣產能、壓力、溫度等動態數據和油氣無阻流量、油氣水性質,為認識氣藏特征,編制開發方案,地面產能建設提供依據。Q/SY 01070—2020《試油(氣)試采資料錄取規范》 對常規氣層測試要求:產量大于或等于50×104m3/d 時,井口壓力和產量穩定2 h 以上;產量小于50×104m3/d 時,井口壓力和產量穩定4 h以上;產量大于或等于10×104m3/d 時,井口壓力和產量穩定8 h 以上;定產氣井放空試采時間6~15 d。某含硫氣藏2014—2020 年17 口獲產開發井,放噴排液與測試最短時長4 h,最長放噴時長超過42 h,最少放空量23.97×104m3,井均CO2排放超過1 300 t。
天然氣脫硫、脫水、脫烴環節用能設備較集中,鍋爐、加熱爐、增壓機組等以天然氣為燃料的用能設備排放CO2,也是主要的碳排放環節。2022年川中天然氣產量超過180×108m3,其中含硫天然氣占88%,脫硫凈化燃料氣直接排放CO2達36×104t。含硫天然氣中CO2平均含量0.66%~4.19%,脫除H2S時也從原料氣中脫除CO2約30×104t,以滿足GB 17820—2018《天然氣》對產品氣中CO2限值的規定。
1.2.2 CH4排放
CH4是僅次于CO2的第二大溫室氣體,近1/3 的CH4排放來源于原油和天然氣開采、集輸和配送過程[3],全產業鏈均會產生甲烷逃逸排放,包括整個系統中的生產設施檢維修、設備密封件泄漏、工藝過程排放和放空火炬燃燒。《IPCC 2006 指南》提供了3 個層級的方法核算石油和天然氣系統產生的甲烷逃逸,公式(1)使用最廣:
式中:E為甲烷逃逸總排放量,Gg;P為石油和天然氣系統各環節的活動水平數據,活動單位;SEF為甲烷排放因子,Gg/單位活動;i為石油和天然氣系統;k為石油和天然氣系統的活動類別。
試油試氣放噴排液和測試放空天然氣一般采取燃燒后排放,以確保作業安全。在未及時點燃之前直接排放采用《中國石油天然氣生產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試行)》提供的試井作業CH4排放量公式計算。
從地層產出液中逸散是CH4的主要排放方式。產出液在地層壓力環境下溶解一定量CH4,其溶解度受壓力、溫度、鹽度等因素控制。地層產出液從井口、經分離器進入儲罐,受壓力突降和外界環境溫度影響,CH4等飽和氣體會迅速釋放,形成閃蒸氣,通過儲罐敞口或呼吸管逸散到大氣中。以某含硫氣藏為例,檢測表明氣田水罐中閃蒸氣含CH4為35%~70%、H2S 為7%~29%。為保障人員健康安全,采用液相氧化還原法脫H2S 后CH4被冷排放。某集氣站閃蒸氣脫硫尾氣2 h 連續監測數據表明,CH4最大排放濃度1.27×105mg/m3。該氣藏2022 年產水近75×104m3,閃蒸氣脫硫除臭裝置生成硫泥約360 t,估算直接排放CH4為15×104m3。
油氣勘探開發全過程的CH4排放計量理論、方法、標準尚不完善。統計時采用《中國石油天然氣生產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試行)》附錄二中油氣系統不同設施CH4排放因子進行核算。礦場安裝固定式或巡檢時配置可燃氣體、H2S 檢測儀器,重要生產站場設置云臺式激光甲烷遙測儀,對工藝流程區生產介質泄漏進行監測。管道設備安裝工藝技術的提升和安全監控措施的完善,有效管控了CH4泄漏。現場CH4、VOCs 泄漏檢測數據表明,采用排放因子核算CH4排放量,數值較實際偏大。
1.2.3 揮發性有機物排放
油氣生產井和天然氣脫水脫烴站油氣儲存、裝卸有揮發性有機物(VOCs) 排放,特別在氣溫較高時VOCs 排放更明顯,有關文獻估算我國每年的油氣揮發損失超過25×106t[5-6]。川中凝析油氣田新建產能采取氣液混輸,集中脫水脫烴,集氣站VOCs 采取增壓回收或引至放空火炬焚燒,缺少油氣開采VOCs 排放水平方面的研究。老油氣田受限于油氣生產井分散,油產量低,一般為20 m3儲罐,缺乏適用的VOCs 管控技術。
2 減碳潛力分析
2.1 低碳技術應用
井下節流技術:即在井筒內一定深度安裝井下油嘴,天然氣在井筒內節流后吸收地層的熱量而避免水合物形成。井下節流替代了水套加熱爐、電伴熱裝置,減少乙二醇等水合物抑制劑加注,簡化地面流程,節約能源。井下節流器投放深度需滿足公式(2):
式中:H為入井深度,m;M0為地溫增率,m/℃;th為水合物形成溫度,℃;p1為油嘴入口壓力,MPa;p2為油嘴出口端壓力,MPa;t0為地面平均溫度,℃;k為天然氣絕熱指數。
節流器投放越深,井口溫度越高,但也會承受更高的工作環境溫度和壓力。川中須家河、沙溪廟等氣層深度一般2 000~2 500 m, 地層溫度58.73~70.87 ℃,具有良好的應用條件。2006 年以來應用超過1 000 井次,單井平均節氣10×104m3/a,節能減排效果顯著。含硫氣井受井深、溫度、腐蝕介質等因素限制,應用較少。
電能替代天然氣:近年新建項目采取電能加熱裝置替代水套加熱爐,電驅增壓機組替代燃氣驅,實現更低的碳排放。電加熱裝置單套功率40~160 kW,高頻控制器將380 V/50 Hz 交流電轉換為15~25 kHz高頻交流電,通過電磁感應毯轉換為高頻交變磁場,天然氣管道在高頻交變磁場中因電渦流而產生熱效應直接對天然氣加熱,效率更高。
低排放工藝技術,包括清管放空天然氣回收,管道帶壓碰口作業,清管放空天然氣回收,邊遠井、零散井試采放空天然氣回收等。非含硫天然氣測試放空天然氣回收或低小產井試采制CNG、LNG技術在探評價井測試中推廣,工藝流程已實現模塊化、撬裝化。針對不同壓力等級、處理工況組合加熱撬、高壓分離燃氣撬、增壓撬、高壓分子篩脫水撬、低壓分離燃氣撬、存儲撬、加氣撬等工藝流程。
建設信息化氣田。地面系統采用“多井集氣、采氣管線氣液混輸、集氣干線氣液分輸”工藝,簡化單井生產流程。生產數據自動采集傳輸,自動聯鎖、遠程控制等自動化技術的全履蓋,為站場無人值守、中心井站集中管理、電子巡井創造了條件。SCADA、DCS/SIS、視頻安防綜合管理系統、物聯網系統和氣田生產建設的深度融合,自控水平不斷提升,促進生產管理方式轉變和組織管理效率的提高[7],實現輔助生產系統低碳運行。
2.2 節能減碳潛力
川中深入推進“清潔能源貢獻者行動”和節能降碳等十大工程[8]。助力集團公司2025 年甲烷排放強度較2019 年降低50%,達到國際一流公司甲烷排放管控水平[9]目標。
節能提效。節能是實現碳達峰最直接有效的途徑,據有關規劃測算2030 年實現碳達峰,通過節能減排CO2量將達到70.1%[10]。川中近70 a 開發,區塊發展不均衡,老油氣田單井產量低,十分分散,生產設施陳舊,能效低。新建氣田產量高,自動化程度高,高效開發。調整能源消費結構,提高電能占比,降低CO2排放,如加熱爐、鍋爐、增壓機組節能提效;壓縮機組、加熱爐氣改電;高耗低效機電設備淘汰;熄滅長明火炬;老油氣田地面系統降阻改造;天然氣高低壓分輸等。四座含硫天然氣凈化廠中有一廠實際處理量不足設計能力的39%,配套的供熱、供電系統利用率不足10%;四套脫水脫烴裝置,僅一套裝置滿負荷運行,一套裝置負荷率50%,一套負荷率僅10%;四個天然氣增壓站均處于低負荷運行。地面系統節能提效,特別是含硫天然氣凈化廠的用能系統按“高位高用,低位低用,溫度對口,梯級利用”原則優化,將鍋爐負荷率提升至80%以上,可節能3 000 tce、CO2減排4 300 t。
放空天然氣回收:油氣勘探開發相關甲烷逃逸排放對區域空間CH4分布有較大影響[11],開發力度越大,區域空間CH4增長越顯著。特別在試油試氣階段,僅少量非含硫放空氣得到回收,復雜氣質和工況條件下放空氣回收有很大潛力。凝析油氣田集氣站、含硫氣凈化站采用火炬焚燒VOCs、氣田水閃蒸氣或凈化尾氣,單座火炬年用氣20×104m3以上,熄滅火炬將減少大量自用氣消耗。
2.3 綠色發展資源優勢
2.3.1 新能源
據Ember《2023 年全球電力評論》數據,我國2022 年電力需求增長的69%由風能和太陽能提供,至2040 年風能和太陽能發電將提供全球75%的新增清潔電力。川中年平均風速2.1 m/s,不具有規模利用風能條件。參照GB/T 37526—2019《太陽能資源評估方法》,區域水平面總輻照量多處于太陽能資源第四類地區,年輻射總量基本在4 000 MJ/m2左右,大部分區域內年日照時數普遍在800 h,太陽能資源穩定程度和直射比為欠穩定,但個別區域光伏仍具價值。儀隴凈化廠光伏發電項目2023 年3 月投運, 安裝光伏組件9 626.92 m2, 裝機容量1 998.54 kWp,4 月發電量近16×104kWh。油氣田可利用土地空間較多,充分利用辦公建筑屋頂、立面和廠站空置場地空間,安裝光電轉換效率高的光伏發電設施,可鋪盡鋪,結合儲能技術,依托內部電網自發自用。
2.3.2 天然氣壓力能資源
天然氣從地層至終端用戶是一個壓力連續降低的系統,通過節流降壓以滿足各級地面系統的工作壓力要求。特別在氣田開發初期和中期,氣井產量高、壓力高,有豐富的壓力能資源可以利用。天然氣節流降壓釋放的壓力能可采用公式(3)估算:
式中:ex為天然氣的比?,kJ/m3;Cp為天然氣的比定壓熱容,kJ/(m3·℃);T1、T2分別為天然氣節流前后的溫度,℃;R為氣體摩爾常數,8.314 5 J/(mol · K);M為氣體的摩爾質量,kg/mol;p1、p2分別為天然氣節流前后的壓力,MPa。
以某含硫氣田MX009-X1 為例,井口天然氣壓力24.27 MPa、 溫度105.8 ℃, 節流后壓力6.71 MPa、溫度69.15 ℃,日產天然氣145×104m3。天然氣中主要組分摩爾濃度:CH4為96.998%、CO2為1.852%、H2S 為0.379%,相對密度0.578。天然氣的比壓力?為238.933 kJ/m3, 理論壓力能9.701×104kWh/d。初期井口壓力超過65 MPa,產量超過170×104m3/d,壓力能更高。 區塊內9 口回注井年用電量203×104kWh,如該井壓力能用于發電,將超過區塊氣田水回注系統的用電需求。
2.3.3 氣田水資源
高-磨地區龍王廟組氣藏為特大型超壓碳酸鹽巖邊水氣藏,氣田水礦化度較高,富含鋰、溴等有價值元素,早期開發階段即制訂整體治水方案[13],據預測2025 年產水量將超過150×104m3/a。主產水井氣田水中鋰離子(Li+)濃度超過60 mg/L、溴離子(Br-) 平均濃度500 mg/L、硼離子平均濃度460 mg/L,含量優于DZ-T 0212.4—2020《礦產地質勘查規范鹽類第4 部分:深藏鹵水鹽類》附錄表C.2 中礦產綜合評價指標:LiCl 大于或等于150 mg/L、Br-大于或等于50~60 mg/L,現場中試已成功提取鋰鹽。該氣藏產水已逾75×104m3/a,地面輸水管網較完善,提鋰、溴和廢水深度處理后作為周邊工業園區工業用水,為氣藏綜合治水、效益開發提供新的途徑。
根據大地熱流分布與熱儲系統,四川盆地三類有利的地熱資源類型[14],高-磨區塊處于第一類區內,為兼顧震旦系-早寒武系熱儲系統、晚二疊系-中三疊系熱儲系統和斷褶熱儲系統的斷裂帶深循環地熱資源[15],地溫梯度和大地熱流較高,分別介于24~30 ℃/km、60~70 mW/m2。龍王廟組氣藏中部平均溫度140 ℃,地溫梯度平均32 ℃/km,目前單井最大產水量600 m3/d,井口溫度103 ℃,一套80 kW 的地熱源ORC 發電機組已在該井投入試驗,設計年發電40×104kWh。據估算氣藏水體儲量大致為3.486×108m3,可利用地熱資源1.70×1014kJ,但較分散。隨治水方案有序推進,氣田水中熱量用于發電、農業的價值愈顯。
2.3.4 H2S 制氫
氫是用能終端實現綠色低碳轉型的重要載體,氫能產業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重點發展方向[16]。天然氣工業通常采用Claus 法工藝將天然氣中99.98%的H2S 氧化為單質硫回收,氫氣未作為資源利用。 川中含硫天然氣中H2S 平均含量11.43~44.64 g/m3,2022 年脫除H2S 約23.68×104t,其中氫氣1.39×104t 未轉化為資源利用,H2S 制氫可實現資源利用最大化。
2.3.5 天然氣發電
天然氣是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的新型電力系統下電力安全的“穩定器”[17],發電是天然氣產業未來重要的發展方向[18]。川中邊遠、低壓、小產氣井多,除保障周邊場鎮民生用氣,天然氣就地轉化發電,不僅可降低氣井廢棄壓力,延長生產期,提高天然氣采收率,還可減少外輸能耗和降低地面系統運維成本。
2.3.6 CCS/CCUS
天然氣凈化廠排放的CO2可作為CCS/CCUS 的碳源。評價結果表明老油田有CO2封存潛力,已完成擬選封存區水文地質調查、回注層縱橫向封閉性評價、鉆井固井質量調查與評價,提出了首選區塊層系及目標井可封存量計算方法、回注井工程及工藝,封存井的井口裝置、完井管柱及材質評價建議。CO2的利用近年雖取得積極進展,CCUS 從驅油向微藻、礦化等生物、化工領域拓展,但技術水平和項目規模還不能滿足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減排需求[19]。且凈化尾氣中CO2濃度低于10%,CCS/CCUS以及DACCS 的能耗高,大規模全流程的應用技術尚不成熟,環境風險需長期跟蹤監測,配套政策、標準不完善,宜作為實現低碳、“零碳”目標的兜底水手段。
3 低碳發展建議
在2050 年左右實現近零排放的目標下,新建項目電氣化率不斷提高,持續增加油氣開發成本。《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費不納入能源消費總量控制有關工作的通知》(發改運行〔2022〕1258 號)明確:新增可再生能源電力消費量不納入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發揮資源優勢,加大研究實踐,成熟技術推廣應用,可行技術適應性轉化,新興技術跟蹤儲備,“天然氣+”業務提升電能自給率,是控制生產成本和能耗總量、強度的有效手段。
3.1 重視項目科學合理設計
川中生產設施點多面廣,用能系統和設備數量大。建設時設計規模和設備功率裕量較大,隨著氣田產量逐年遞減,裝置和壓縮機組、機泵、鍋爐等設備與設計值偏離越來越大,能效越來越低。如某脫水脫烴裝置設計處理規模100×104m3/d,投運12 a 后實際處理量不足12×104m3/d,系統性改造投入高,投資回收期長。新建項目應考慮中后期經濟運行,科學論證,根據穩產期合理選取規模和設備額定功率。一定條件下多套裝置或設備聯合運行,在中后期比一套等規模裝置或等功率的大功率設備更易于調度調節,能效更優。標準化設計宜依據國家節能減排和綠色發展的政策、標準適時修訂,體現綠色要求,固化成熟低碳技術。
3.2 強化適宜技術研究應用
3.2.1 放空天然氣回收
試油試氣或酸化壓裂等儲層改造是油氣勘探開發重要的碳排放環節,大規模和高強度的勘探開發會致空間CH4濃度明顯增加,在油氣開發全過程的碳排放貢獻率還需深入研究。近年,非含硫放空天然氣回收工藝技術研究和應用方面取得進展,但受放噴氣井點多,產能和穩定期不確定,氣量和壓力變化范圍大,氣流中攜帶砂、壓裂酸化殘液、鉆井泥漿等因素的制約,礦場上應用有限,高壓高產、含硫氣井試氣放空天然氣的回收更是難題。開展不同場景放空天然氣回收利用關鍵技術裝備的研究,對實現油氣勘探開發減碳有著重要意義。
3.2.2 天然氣壓力能利用
天然氣全流程壓力能合理利用研究方興未艾,近年積累了豐富的利用技術,尤以中低壓凈化氣壓力能發電技術較成熟,此外還用于冷庫、制冰、空調、制取干冰和LNG 等領域,現場應用上逐漸趨于采用“發電聯合制冷”的解決方案[20]。MX 天然氣凈化廠和XQMZ 集氣站天然氣壓力能發電項目進入實施階段,應用壓力低于6 MPa,壓差約1 MPa,設計天然氣流量分別為300×104m3/d、400×104m3/d,相應裝機功率為700 kW、800 kW,理論上MX 凈化廠年發電量可達419×104kWh,滿足工廠20%的用電需求;XQMZ 集氣站年發電量402×104kWh,90%電量上載氣田內網。形成系列配套技術,特別是發電裝置小微型化,及含硫、高溫、高壓等復雜場景氣井的壓力能利用[21],將成為氣田綠色發展的新引擎。
3.3 做好新興技術跟蹤轉化
3.3.1 H2S 制氫或開發含硫化學品
川渝地區天然氣資源豐富[22],60%以上為含硫天然氣,保證了H2S 制氫、開發含硫化學品的原料來源。H2S 分解直接制單質硫和氫的方法有熱分解法、電化學分解法、光催化分解法和等離子體法等[23],相關的工藝技術尚處于研究階段,高效、經濟的催化劑和反應條件溫和、轉化率高、能耗低的工藝方法是H2S 制氫研究的主要方向。電催化分解H2S 是一種溫和高效的方法,目前使用的催化劑中,貴金屬價格昂貴,過渡金屬及其氧化物易被反應介質毒化或腐蝕而失去活性,極大地限制了這項技術的發展。目前,一種新型石墨烯殼層封裝鈷鎳納米粒子的“鎧甲”催化劑已被研究人員開發出來[24],成功實現電催化高效分解H2S 制備高純氫。H2S 分解制單質硫和氫如在技術上取得突破,對天然氣凈化工藝技術的進步將產生十分深刻的影響[25],也為含硫氣田綠色發展提供新機遇。
含硫天然氣產生的高濃度H2S 提純后,可用于開發甲硫醇、叔十二碳硫醇等有機硫精細化工產品,其產值數倍甚至數十倍于硫黃[26],提高天然氣附加值。實現H2S 高效利用,也是探索含硫氣田效益開發的新路徑。
3.3.2 低壓天然氣發電
油氣田步入開發中后期后,部分油氣井因低產低效關停。邊遠、低壓、小產井發展分布式天然氣發電,可實現資源就地轉化消納,降低氣井廢棄井口壓力,增加經濟可采儲量。致密氣氣田集氣站采用增壓回收VOCs,工藝技術不成熟,現場仍采用火炬焚燒處置輕質原油和氣田水中逸出的揮發烴。加大小微型燃氣輪機發電技術的研究和實踐,改變能源生產方式,實現老油氣田經濟環保開發。據報道,國內自主設計研制的首款500 W 級輕量化可移動式微型燃氣渦輪發電機已研發成功,能量密度可達1 500 W/kg,不失為低壓閃蒸氣、VOCs 利用及老油氣田效益開發提供一種新的技術思路。
4 結論
1)國家發改委在《加快推進天然氣利用的意見》中提出,到2030 年天然氣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提升至15%。中國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2050 年世界能源展望(2020 版)》預測,到2050年我國天然氣需求將達到6 700×108m3。利用天然氣開發的優勢地位,拓展“天然氣+”業務,油氣業務與新能源融合發展,是能源革命提出的新要求。
2)老油田要做好“減法”,通過地面集輸系統適時簡化,生產制度和設備運行參數優化提效,降低資源能源消耗,減少碳排放。新建產能項目要做好“加法”,因地制宜利用太陽能、低小產井天然氣、生產系統天然氣壓力能等資源發電,資源優勢轉化為生產力。川中油氣生產年用電近2×108kWh,在全球氣候變暖、極端高溫可能成為新常態的背景下,通過“天然氣+”提高電能自給率,讓電于社會,也是對國家建設高溫適應型社會的貢獻。
3)加大試油試氣、天然氣凈化等重要碳排放環節減污降碳技術研究和低碳技術應用,形成一批適應油氣田生產特點,標準化、可復制、易推廣的配套技術體系是是實現碳“近零”排放的關鍵。
4)科技創造未來的能源。“雙碳”目標下能源科技創新進入持續高度活躍期,能源生產逐步向集中式與分散式并重轉變,系統模式由大基地大網絡為主逐步向與微電網、智能微網并行轉變。利用智能微電網技術構建新型的天然氣開發能源系統,實現傳統上游業務的創新升級,在綠色轉型道路上“彎道超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