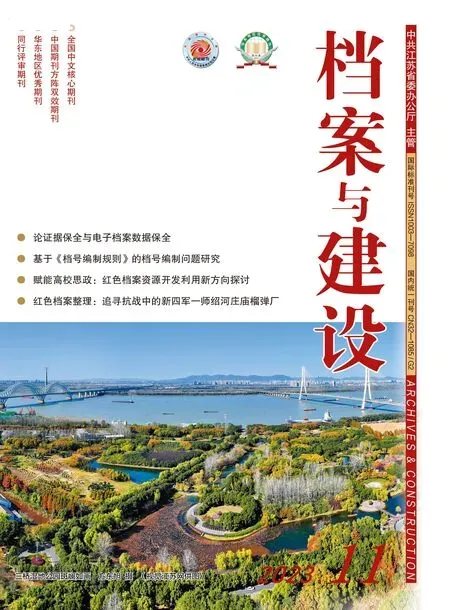1937 年南京軍民的空防斗爭
陳曉寒 經(jīng)盛鴻 李 婷 王 勇
(1.南京市博物總館,江蘇南京, 210001;2.南京師范大學(xué)歷史系,江蘇南京, 210097)
從1937 年8 月15 日起,日軍對國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南京進(jìn)行了瘋狂空襲,直至12 月13 日南京淪陷,造成南京城的嚴(yán)重破壞與軍民的重大傷亡。面對敵人的狂轟濫炸,南京軍民積極組織反擊,為保衛(wèi)祖國和民族尊嚴(yán)而戰(zhàn)斗。回顧與總結(jié)這段血與火的歷史,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xiàn)實(shí)意義。
一、日軍對南京的空襲及惡劣影響
1937 年8 月15 日,日本海軍第一聯(lián)合航空隊(duì)木更津部隊(duì)的20 架96 式陸上攻擊機(jī)自長崎大村航空基地起飛,于當(dāng)日下午2 時(shí)05 分抵達(dá)南京。在沖破中國戰(zhàn)機(jī)與地面防空火力的攔截后,強(qiáng)行沖入市區(qū)上空,對明故宮機(jī)場、大校場機(jī)場等軍事設(shè)施進(jìn)行轟炸與掃射,先后投下多枚250 千克陸用炸彈,炸毀機(jī)場的飛機(jī)庫與飛機(jī)多架[1];同時(shí)對八府塘、第一公園、大行宮、新街口等商業(yè)區(qū)與居民區(qū)進(jìn)行狂轟濫炸,造成了市民重大傷亡。南京各防空陣地奮勇反擊,空軍驅(qū)逐機(jī)起飛迎敵,與日機(jī)展開激烈的空戰(zhàn),先后擊落日機(jī)4 架,擊傷多架。[2]
此次空襲是日軍戰(zhàn)機(jī)對南京的第一次空襲。日機(jī)對南京商業(yè)區(qū)與居民區(qū)的轟炸,明顯違反了國際公法,引起世界輿論的譴責(zé)。此后,日機(jī)對南京的空襲連續(xù)不斷,并日益加劇,依仗其數(shù)量的優(yōu)勢與性能的先進(jìn),常常突破中方的防空攔截,對南京城內(nèi)外實(shí)施猖狂的轟炸與屠殺。

日機(jī)飛臨南京上空
8 月26 日,日機(jī)猛烈轟炸南京的中央大學(xué)、中大附中、革命遺族學(xué)校及志成醫(yī)院。位于南京北極閣下大石橋畔的中央大學(xué)實(shí)驗(yàn)學(xué)校被日機(jī)炸毀。中央社8 月28 日電訊《敵機(jī)擲彈毀滅我文化機(jī)關(guān)》報(bào)道了日機(jī)轟炸中央大學(xué)的慘痛景況,揭露日本當(dāng)局“毀滅我中華民族文化之有計(jì)劃的殘暴行為”。[3]日機(jī)還再次野蠻轟炸了南京城南的八府塘地區(qū)。這里是沒有任何軍事設(shè)施的城市貧苦平民居住區(qū)。南京詩人沙雁親身經(jīng)歷、目睹了八府塘地區(qū)遭受空襲的慘景。他以滿腔的悲憤,寫成敘事詩《憶八府塘血火》,刊登在武漢《大公報(bào)》上,“八府塘,就這樣遇了難,遭了殃!無數(shù)間茅屋,火燒得凄涼,百余條無辜的生命,全數(shù)在炮火中埋葬!全數(shù)在敵軍慘絕人寰的炮煙中埋葬!”[4]這首詩真實(shí)展現(xiàn)了八府塘地區(qū)遭受空襲的悲慘狀況及沙雁對敵軍殘暴行徑的憤怒。
1937年9月19日(農(nóng)歷中秋節(jié)),日機(jī)自早8時(shí)至晚6時(shí)許,輪番轟炸南京。當(dāng)時(shí)家住國府路(現(xiàn)長江路)207號的吳野,在晚年回憶了這天他家遭受的巨大災(zāi)難:“中秋節(jié)這天,國府路207號張燈結(jié)彩(為兒子辦婚事)……沒有想到,噩耗說來就來,日機(jī)在國府路扔下3枚炸彈,一枚落在罵駕橋鄧府巷吳家老宅的水塘,另一枚落在國府路207號老宅婚房,彈坑有一丈多深。罵駕橋六爺爺家26歲的正庠叔攜他的兩個(gè)女兒,正打算到國府路207號這邊吃喜酒,炸彈落下來,三人倒在血泊中。大伯母李潔卿,40歲,被土掩埋,當(dāng)場窒息,搶救無效。三爺爺家的誠駬堂兄是個(gè)10歲的小神童……這天,棋興正濃時(shí),屋頂卻塌了下來,死的時(shí)候,手心里還捏著一顆棋子。一枚炸彈,瞬間奪去了5位親人的生命。……國府路周邊不止我們一家遭難,街邊擺著一具具尸體,成了露天的停尸場。”[5]
9 月25日是日機(jī)轟炸南京最血腥的一天,自上午9 時(shí)半至下午4 時(shí)半,先后有96 架日機(jī)分5 次空襲,投炸彈500 枚,轟炸的多為文教衛(wèi)生機(jī)關(guān)與公用設(shè)施,如中央大學(xué)、中央通訊社、中央醫(yī)院、下關(guān)電廠、首都電燈公司、首都自來水公司、下關(guān)難民所等,以及江東門、三條巷、邊營、中山東路等居民住宅區(qū)。僅僅一天南京居民傷亡達(dá)600 人。[6]
日方對南京日益加劇的野蠻空襲,其目的除了摧毀南京的軍事設(shè)施外,更重要的是實(shí)施對中國軍民的恐怖威懾,摧毀中國軍民的抗戰(zhàn)意志,迫使中國政府迅速屈服。1937年9月,日本海軍第二聯(lián)合航空隊(duì)下達(dá)作戰(zhàn)命令,向執(zhí)行空襲的日軍飛行員宣布:“轟擊無須直擊目標(biāo),以使敵人恐怖為著眼點(diǎn)。”[7]為了實(shí)現(xiàn)這一卑鄙目的,日機(jī)對南京進(jìn)行了瘋狂轟炸與血腥屠殺。
1937 年11 月12 日,日軍占領(lǐng)上海以后,立即兵分?jǐn)?shù)路向南京發(fā)起包抄圍攻,并進(jìn)一步對南京進(jìn)行所謂“進(jìn)攻性轟炸”。這時(shí),中國空軍戰(zhàn)機(jī)損失嚴(yán)重,又得不到補(bǔ)充,無力制止敵機(jī)的瘋狂轟炸。日機(jī)取得了南京地區(qū)的制空權(quán),將對南京的空襲推向頂峰。南京城市與南京民眾遭到了更大的災(zāi)難。
從1937年8月15日到12月13日,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南京共遭受日機(jī)空襲118次,投彈1357枚,市民死亡430人,重傷528人,房屋全毀24所、1607間”[8]。這些數(shù)字,僅指南京城區(qū)遭受的空襲與城區(qū)傷亡的普通市民,不包括中國軍人與南京郊區(qū)的民眾,而由此造成的財(cái)產(chǎn)、房屋、文化遺產(chǎn)損失,更難以計(jì)算。
二、南京軍民在空襲期間的英勇抵抗
面對日本戰(zhàn)機(jī)的瘋狂轟炸與屠殺,南京軍民并未被恐懼所征服,而是展現(xiàn)出堅(jiān)韌不屈的空防戰(zhàn)斗精神。
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在南京加強(qiáng)對日備戰(zhàn)的工作中,大力推進(jìn)南京防空建設(shè)和國民防空知識的宣傳教育。南京市民接受了各種防空知識教育,并進(jìn)行過多次防空演習(xí)。當(dāng)面臨日軍戰(zhàn)機(jī)連續(xù)不斷的空襲時(shí),南京廣大民眾在開始階段曾一度恐慌,但很快就積累了空防經(jīng)驗(yàn),家家都利用南京傍山近水的自然地理優(yōu)勢,在屋內(nèi)屋外建造了各種防空設(shè)施,積極應(yīng)對日軍空襲,并表現(xiàn)出無畏的蔑視與英勇的斗爭精神。
被時(shí)人稱為“江南才子”的南京著名學(xué)者盧前(盧冀野)一家,住在南京中華門東側(cè)城墻下的小膺福街。在朋友幫助下,他雇請工人在自家院子里造了一座可以容20 人的“小型地下室”。他記述說:“‘竄地洞’成了我們每天必有的工作。我集了兩句古語作為地下室的門聯(lián),道:‘見機(jī)而作,入土為安。’朋友們反笑我這樣的閑情逸致。”[9]這副獨(dú)具匠心的對聯(lián),表現(xiàn)了南京人民在日機(jī)轟炸下真實(shí)而又樂觀的生活狀態(tài)與心理狀態(tài)。
1937 年8 月26 日,中央大學(xué)實(shí)驗(yàn)學(xué)校被日機(jī)炸毀。中央大學(xué)校長羅家倫指著被毀的校舍說:“敵能毀之,吾能復(fù)之!”他始終留在中央大學(xué),與師生們護(hù)校支前。詩人沙雁則在敘事詩《憶八府塘血火》的最后部分,以堅(jiān)毅的語調(diào),發(fā)出了南京人民不屈的聲音:
告訴您,
野蠻的猖狂的暴寇,
不只傷亡我大中華無辜的人民,
實(shí)在世界的和平、自由、文化,
無不遭受重大的威脅,重大的恐慌!
我全人類愛好和平、自由、文明的朋友,
快一齊起來,
起來捕捉這人類中的豺狼![10]
由著名作家張恨水創(chuàng)辦與主持的《南京人報(bào)》,克服困難,艱苦支撐,宣傳抗日。報(bào)紙沒有廣告收入,一度陷入經(jīng)濟(jì)困境。全社人員主動(dòng)提出,除飯食外,工薪全免。張恨水家住郊區(qū)上新河,他每天步行十幾里上班,敵機(jī)一來,他就趴在田坎下,或是伏在大樹下,一待警報(bào)解除,立即奔向報(bào)館,馬上著手編當(dāng)天的稿件。不到一個(gè)月,他就病倒了,但仍堅(jiān)持出報(bào)。《南京人報(bào)》一直堅(jiān)持到12月9日才停刊,距離南京淪陷只有4天。[11]
在空襲中,南京市民還不顧危險(xiǎn),支援前線淞滬會戰(zhàn)的保障工作。當(dāng)時(shí)上海戰(zhàn)場的傷兵被源源不斷地運(yùn)到南京。1937年9月,國民政府衛(wèi)生署署長劉瑞恒和中國紅十字總會秘書長龐京周決定,在南京籌設(shè)一家規(guī)模“打破世界紀(jì)錄”的傷兵醫(yī)院。1937年10月4日,中國紅十字總會在中央大學(xué)的校園內(nèi)開辦“首都醫(yī)院”,因該校早就停課,正在組織西遷,遂把學(xué)校的大禮堂、科學(xué)館、體育館、圖書館、教學(xué)樓、學(xué)生宿舍等,全部改成病房與手術(shù)室等。從全國各地趕來的醫(yī)護(hù)人員有300多人,從事各項(xiàng)雜役工作的人員有400多人,設(shè)置病床5200張,手術(shù)室“同時(shí)可供行使十余人手術(shù)之用”,“每日平均大小手術(shù)在二三十次左右”,被譽(yù)為“傷兵醫(yī)院之冠”。南京市民為該醫(yī)院捐贈(zèng)了大量物資,許多人踴躍來到這里義務(wù)擔(dān)任救護(hù)工作。該醫(yī)院一直工作到11月中旬才奉命撤出南京,在這1個(gè)多月的時(shí)間里,共救治了3000多名傷員,還收治了兩名日本戰(zhàn)俘。中央大學(xué)建筑系教授許道謙在1938年初回憶這段歷史時(shí),寫道:“這里,多少中華男兒,多少熱血青年。負(fù)傷的南京中央大學(xué)在發(fā)出安慰的微笑。”[12]
為了保衛(wèi)南京,中國年輕的空軍飛行員不畏強(qiáng)敵,在戰(zhàn)機(jī)的數(shù)量、性能、航速等方面都不如日機(jī)的情況下,以滿腔的保家衛(wèi)國熱情,與日機(jī)展開殊死搏斗,涌現(xiàn)了高志航、劉粹剛等空軍英雄。樂以琴等數(shù)十名飛行員血灑南京長空,壯烈犧牲。1937 年9 月19 日,40 多架日機(jī)空襲南京。被稱為“空軍勇士”的21 歲鎮(zhèn)江籍飛行員陳懷民駕機(jī)迎戰(zhàn),重傷一架敵機(jī),后被4架敵機(jī)包圍,他以一敵四,左沖右突,擊落一架日機(jī),但他自己戰(zhàn)機(jī)的油箱被敵機(jī)打中起火,從空中急速下降。他為了保全戰(zhàn)機(jī),在離地面只有百余米時(shí),才停掉螺旋槳,進(jìn)行滑翔,迫降在南京江北江浦縣一片小樹林中的空地上。戰(zhàn)機(jī)撞到一棵大樹,陳懷民被彈出座艙,夾在一棵大樹的樹杈上,巨大的沖擊力將他的鼻梁骨折斷,胸部、肩部血肉模糊,昏迷過去。當(dāng)?shù)剜l(xiāng)民紛紛趕來解救,先把他送往江浦縣醫(yī)院,后轉(zhuǎn)送南京中央醫(yī)院,數(shù)萬民眾夾道歡送。陳懷民傷愈后立即重返藍(lán)天。
1937年11月2日上海失守,日軍兵分三路向南京包抄進(jìn)攻。從1937年11月16日開始,南京的各機(jī)關(guān)、工廠、學(xué)校以及大量市民,在日機(jī)的轟炸下組織了悲壯的大撤退、大遷徙。南京是個(gè)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不僅有大量黨政軍機(jī)構(gòu),而且有許多工商企業(yè)與學(xué)校,設(shè)備、圖書、資料等如山如海,在日機(jī)空襲下組織與實(shí)施內(nèi)遷,其困難可想而知。但在南京軍民的努力下,不僅各機(jī)關(guān)都及時(shí)遷往目的地,重新開展工作,而且許多工廠、學(xué)校也多安全撤出南京,保存了設(shè)備與人才,為大后方的持久抗戰(zhàn)作出了重大貢獻(xiàn)。如著名的金陵兵工廠,在接到西遷的命令后,廠長李承干指揮全廠員工,進(jìn)行緊張有序的拆卸、裝箱、運(yùn)輸和轉(zhuǎn)運(yùn)工作,僅用16天的時(shí)間就將4300余噸的設(shè)備、機(jī)器、材料裝船完畢,分批沿長江運(yùn)往重慶。1938年初,他們在重慶的指定地點(diǎn)搭棚安身,在“開工第一,出貨第一”口號的感召下,艱苦奮斗,于1938年3月1日正式復(fù)工。[13]再如著名的中央大學(xué),7個(gè)學(xué)院的1500多名學(xué)生、1000多名教職工及其家屬,總共約4000多人,攜帶學(xué)校的圖書、資料、儀器、設(shè)備共1900余箱,其中包括航空機(jī)械系用于教學(xué)的3架飛機(jī)與醫(yī)學(xué)院用于教學(xué)解剖用的24具尸體,以及農(nóng)學(xué)院的部分教學(xué)用動(dòng)物,分批登上民生公司的輪船,“雞犬圖書共一船”,沿長江西上,于11月中旬撤至重慶,1937年11月22日復(fù)校復(fù)課,成為全國內(nèi)遷最好、損失最小、復(fù)課最早的高校。[14]
三、結(jié)語
日軍對南京罪惡空襲給南京城市和居民帶來了嚴(yán)重的災(zāi)難,是南京大屠殺的預(yù)演。面對日軍轟炸學(xué)校、居民區(qū)等違反人道主義原則和國際法的殘暴行徑,南京軍民并沒有被恐懼所征服,而是積極開展防空、救援、撤退和遷徙工作,昂揚(yáng)不屈,眾志成城。在日軍的罪惡空襲中,中國人民的奮起抗?fàn)帲日蔑@了偉大的抗戰(zhàn)精神,也為結(jié)束戰(zhàn)爭、孕育和平奠定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