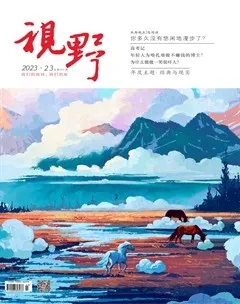我在南大讀天文
方和斐

入學的時候,我對天文學所知不多。高中教學樓廢置的圓頂實驗室,磨毛了邊的《天文學新概論》《通俗天文學》,撐起了此前我對星空的全部想象。
懵懂且巧合,我被全中國最好的天文學類專業學校錄取了。
我一直覺得,夏末是南京最美的時節。日光溫柔,晚風習習,校園中滿地荷葉青如碧璽。但更鮮艷的,是開學時無數為迎新搭建的帳篷與展板上鋪天蓋地的“南大紫”。
方肇周體育館幾千人的開學典禮上,校領導、學者和企業家們輪番演講。清癯儒雅的方成院士一出場,便引起同學們一陣騷動。
那時我對“中國天文學會理事長”“世界知名太陽物理學家”等榮譽沒多少概念,只是那頭銀絲,莫名讓我對這個行業的職業頂點產生了一些不一樣的期待。
用校領導致辭的話來說:“虛懷若谷,唯真是求,唯美力修。有偉大的成就,也可以做最平凡的勞動者。”
院里大一開課不多,不過是數學、英語、計算機這幾門課程。但單單是一科微積分,就讓乍入“高等”大門的我冷汗漣漣。幾百人的大教室座無虛席,稍晚到一點兒,連過道里都坐滿了人。數學系的黃老師編撰過教材課本,功底深厚,上課拈一支粉筆,從頭寫到尾。仿佛一有風吹草動,講臺下幾十支筆桿子也隨之唰唰地搖動;無數數學符號像北大樓上密密麻麻的藤蔓,瞬間爬滿整個教室。
數學老師耐心慈祥,教大學物理的肖教授“肖因斯坦”則嚴厲得多。第一節課剛開始,他下軍令似的訓道:“你們現在是大學生了,學的是大學物理,大學課程不能用腦子里過電影那樣的學法。”
大學課程應該怎么學?我一時半會兒領悟不到。唯知道肖老師講課天馬行空,前一句剛講到滑塊小車,后一句就掉進宇宙和暗物質的深淵。一節課上,他縱馬馳騁,經典物理、理論數學、現代前沿,殺個七進七出,大放異彩。我跟在后面,棄甲曳兵,氣喘吁吁。
我曾以為高考是神燈,擦亮它后就能擁有魔力,實現一切夢想。但神話破滅以后,很多人還盼望著在別的洞窟里抓到新的精靈。尋之不得,便日日被惶恐煎熬著。
變美、瘋玩、談戀愛——往昔對大學的期待猶在腦海;出國、拿獎、高績點——各種“校園神話”充斥于社交平臺。
當一頭插滿花鏢的牛面對紅布,它還能做什么?于是,我們一邊懷著脫靶的恐懼,一邊閉著眼睛猛沖向前。
并不是所有人都對這種生活有所準備。那年冬天,我們到盱眙縣去看雙子座流星雨。寒冷夜空下聊起了填志愿時的趣事,一位同學說,當時以為天文學是文科;另一位同學說,以為學天文能當宇航員。
學院在拓展學生認知上煞費苦心。有一門課專門請中國最有名的天文學家輪番舉辦講座,學期末還組織了一次到上海天文臺訪問的活動。講座內容今日已不記得,但猶記得那天畬山陽光明媚,天文臺食堂里的醬排骨格外好吃。
最震撼的時刻當屬目睹射電望遠鏡。65米口徑的天馬射電望遠鏡屹立在曠野上,頂天立地,雄姿英發。機房里的機箱隆隆作響,指示燈像科幻電影里的場景一樣閃個不停。這就是我們將要經歷的科研生活嗎?回程的大巴車上,每個人都激動不已。
在南大,對文學素養的培育,不只局限于文學相關專業。有一學期我選修了董曉教授的俄羅斯文學課,他上課從不帶講義,每次三節課連堂,從作家生卒年到作品原文倒背如流。他講到普希金詩歌的音樂美,言不盡意,干脆用俄語高聲吟誦數首。
在他口中,托爾斯泰一改悲天憫人的面容,契訶夫摘掉了小丑逗樂的面具,屠格涅夫牽起了魯迅和郁達夫的手。
文學自有其真實的脈絡,而學者口述的“親歷感”,是看多少有關文學的節目都無法比擬的。
比起悶頭苦讀,學術理念的傳承更為珍貴。教近代史的劉握宇教授溫文儒雅、風度翩翩。他說:“我要講的是普通人的歷史,是母親、農民、小演員、作家等人的歷史。”他上課從不用課本,考試只設問答題,且答案不論對錯。我猶記得他出的第一道題目:“歷史有無規律可循?”
老師們嘗試著幫我們建立一種與歷史、人類、社會的深層聯系。就像科學史老師說的:“唯有肩負社會責任的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我們也是頭一次聽到有人說:“你們要從‘自處到‘共處,從‘知道到‘懂得。”
這是天文教育的一部分嗎?不算是,至少不是學院有意的安排。但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相輔相成,二者如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大三暑假,同學們紛紛飛去不同的大洲實習,我來到北京天文臺興隆觀測站。河北群山之間,郭守敬望遠鏡劍指蒼穹。通向焦點室的樓梯上,一幅題字赫然在目:“探索宇宙奧秘,造福人類社會。”
與更廣泛天文界的這種接觸,對職業意識的形成至關重要。南大天文系屬于國家“珠峰計劃”的培養基地,入選計劃的學生有專門的差旅津貼。大四秋天,我受資助去青海德令哈參加中國天文學年會,那里有中國唯一的毫米波望遠鏡。全國的天文學家濟濟一堂,我第一次目睹如此多樣的研究方向。
南大天文系建系70周年時,中國國家天文臺報請國際天文聯合會,將宇宙中一顆小行星命名為“南大天文學子星”。但是微信朋友圈里,沒有人因為這條消息而太過激動。
在我的記憶中,畢業前留下的最后一個畫面是我和室友們登上天文臺拍合影。九鄉河亮晶晶地盤旋在遠方,那是青春的粼粼閃光,比任何星星的名字都更為珍貴。
(天天摘自“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