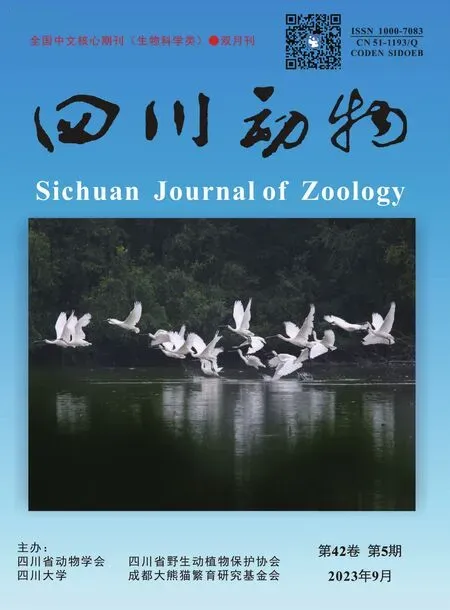大熊貓國家公園清退設施價值利用的路徑思考
許萍 ,樊星, ,劉洋, ,余楊麗娜, ,張志和,李青,
(1. 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成都 610081;2. 大熊貓國家公園成都管理分局,成都 610095;3. 成都市植物園(成都市公園城市植物科學研究院),成都 610083;4. 成都市文化公園,成都 610072;5. 成都市公園城市園林綠化管護中心,成都 610081)
國家公園屬于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中生態價值與保護強度最高的類型,實行嚴格限制人為活動的分區管控制度,其中,核心保護區原則上禁止人為活動,一般控制區禁止開發性、生產性建設活動(國家林業和草原局,2022)。在嚴格管控制度背景下,國家公園內開展了對園內小水電、礦業權、旅游設施等人類干擾活動相關設施的清退工作(母金榮,趙龍,2021;孫繼瓊等,2021)。隨著國家公園建設工作的深入,清退設施的處置愈發迫切地需要管理者做出科學抉擇。
國家公園堅持全民共享,鼓勵公眾參與,開展自然環境教育,為公眾提供親近自然、體驗自然、了解自然的游憩機會(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17)。科普基礎設施是提供自然環境教育、生態體驗、自然游憩等公眾服務的重要基礎。國家公園需夯實公共服務基礎、開展豐富多樣的科普教育活動,踐行“全民共享”的國家公園理念(蔚東英等,2021)。
清退設施改建為科普基礎設施,不僅是清退設施本身價值的延續,也是國家公園建設成效提升的需要。大熊貓國家公園作為人類干擾活動非常頻繁的國家公園(李悅等,2022),平衡“保護與發展”關系較其他國家公園更迫切。大熊貓國家公園成都片區位于常住人口2 126.8 萬人(成都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成都調查隊,2023)的超大城市一隅,清退設施處置問題也更繁雜,城市及周邊社區居民對科普宣教等公共服務需求也更強烈。因此,本文通過分析大熊貓國家公園成都片區清退設施現狀,探討其改建為科普基礎設施的工作路徑,以期摸索更具代表性和實用性的國家公園建設發展策略。
1 大熊貓國家公園成都片區清退設施現狀
自大熊貓國家公園試點以來,成都片區開展了包括有序遷出原住民52 人,分類退出31 宗礦業權、36 座小水電等減少人為干擾活動的工作(王琳黎,2021)。由此,成都片區面臨著清退基礎設施“拆”與“留”的處置問題。
1.1 清退設施的處置現狀
清退設施處置方式有全部拆除后生態修復、部分拆除部分保留、全部保留等,具體處置方式根據生態影響評價、建筑安全水平、使用現狀、退出政策等,評估制定清退設施的“一事一策”處置方案。成都片區各類清退設施占地面積共約100 000 m2,建筑面積約60 000 m2。其中,保留的清退設施占地面積約30 000 m2,建筑面積約18 000 m2,其余清退設施均已完成拆除、并由原業主單位恢復林業生產條件以及植被栽植等處置工作。
1.2 保留的清退設施概況
保留的清退設施包括小水電的大壩、廠房和管理用房:大壩因防洪、灌溉、供水等民生需求而保留;廠房和管理用房主要作為保護管理用房而保留,用于開展森林防火、防汛、野生動物救護、自然教育等工作的辦公、值守、物資存放和活動開展場所等。70%左右的小水電設施用地不超過3 000 m2,建筑面積不超過500 m2,房屋結構為磚木或磚混,多為大開間的廠房(約30間),配套部分小開間、單層的辦公和生活用房(近200 間),建成時間多為20世紀80、90年代。
2 清退設施改建為科普基礎設施的必要性
保留的清退設施均已在編制處置方案時確定用途,除直接改建為科普基礎設施外,在其他用途中仍有兼容科普宣傳功能的需要,比如科考站、管護站、森林防火器材庫、野生動物救護收容站等,均有必要向公眾科普國家公園的各項保護工作內容和保護設施。可在后期正式啟動改建時將科普宣教功能一并納入改建方案。因此,從使用的角度看,保留的清退設施均可視為科普基礎設施的改建。
2.1 契合“生態保護第一”理念
國家公園內清退設施再利用的做法符合國家公園要求的“充分利用原有設施”“遵循綠色營建理念”“采取必要措施消減對自然、人文資源和生態系統的不利影響”等(國家林業和草原局,2022)。清退設施的再利用意味著原計劃拆除的設施將被再次改建利用,也意味著這種方式將節約國土資源、減少建筑材料浪費、延長建筑使用壽命、節約投資與縮短工期等(呂西林,2001),必然會降低碳排放、減小生態影響,這完全契合堅持生態保護第一的國家公園理念。
2.2 完善國家公園科普宣教功能
科研、教育、游憩等是國家公園除生態保護外的重要綜合功能(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17),這也是國家公園體現全民公益性、提供公眾服務產品的主要方式。科普基礎設施作為科研、教育、游憩等綜合功能的重要載體和重要平臺(李朝暉,2019;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2022),具有鮮明的公益性特征(劉婭等,2021),是國家公園體現國家代表性和生態價值的重要窗口,是聯結國家公園和公眾的重要橋梁。國家公園大部分區域因區位、社會經濟等因素,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發展較為滯后,特別是公眾服務方面的基礎設施。大熊貓國家公園成都片區在體制試點之初,僅有1 處較為完善的宣教中心和一些較零星的科普基礎設施。因此,進一步完善國家公園科普基礎設施是國家公園建設的重點工作,將清退設施改建成科普基礎設施為開展這項工作提供了寶貴基礎(邵煒等,2021)。
2.3 激活國家公園稀缺資源利用
國家公園整體位于我國生態保護紅線范圍內,這意味著國家公園內的建設用地將會以縮減為主。經過評估保留下來的清退設施數量不多,并且其所在用地的建設用地屬性對于國家公園來說更為稀缺。比如大熊貓國家公園成都片區各類建設用地占總用地面積約0.23%,清退設施用地占建設用地約2.5%、占總用地約0.007%,保留的清退設施用地占比更少。同時,據錢江源國家公園2015—2019 年的土地利用類型變化統計,其建設用地面積呈下降趨勢(孫德順等,2021)。保留清退設施的稀缺屬性,意味著用好這份資源的現實意義重大。
3 清退設施改建為科普基礎設施的路徑
3.1 改建形式
改建是指在原基礎上根據需求改造建設,包括改變外形、特點、性質或作用等(李玉榮,2016)。結合國家公園管控要求,國家公園內的改建一般僅針對在一般控制區內各種類型設施的整體或局部改造,改造內容包括但不限于功能、流線、平面、形體造型、結構、設備等,不包括加建、擴建等類型的改造。科普基礎設施主要包括科技類博物館、基層科普設施、科普傳媒設施、科普教育基地等5 大類(李朝暉,2019),除科普傳媒設施不完全需要實體設施支持外,其余設施均需要。因此,國家公園內清退的各類設施均可改建為各類型的科普基礎設施,具體的改建形式則可靈活地根據清退設施實際和科普展示需要進行選擇。
結合成都片區現狀,除極個別單體建筑較大的清退設施可改建為科技類博物館,極個別整體占地較大的清退設施可改建為科普教育基地(營地)外,其余大部分清退設施可改建為體量較小、使用靈活的基層科普場館(設施),如自然教育展廳、科普活動中心、科普室外裝置等。整體上,以基層科普場館(設施)為主,其他類型為輔,多層次構建國家公園內的科普基礎設施體系。
3.2 改建路徑
國家公園管理機構在清退設施改建科普基礎設施的過程中,可從管理程序、策劃設計、建設施工、后期運營等方面著手,探索其改建路徑。
3.2.1 提前籌備謀劃,優化管理程序國家公園管理機構在開展清退、搬遷的同時,應將其價值利用計劃納入其中,盡量保留可再利用的設施,做好登記造冊,并結合國家公園發展規劃,制定好價值利用計劃。需特別注意提前做好清退設施的產權、使用權等物權的轉移。現暫未有正式發布的專門針對國家公園內建設活動的管理程序,建設活動在符合國家公園管控要求的前提下,大致需開展立項審批、方案編制、生態影響評價、備案審查等管理程序,不同建設活動按不同類型項目進行分類管理。希望未來能正式出臺相關制度文件,簡化管理程序,縮短前期籌備周期,鼓勵此類型項目開展。
3.2.2 創新策劃設計,突出文化特色參考眾多國內外案例(李亦哲,2014;許揚帆,王冬,2018;胡小華,2019),在以工業設施為主的改建策劃設計中,需關注和挖掘工業設施的歷史文化價值,強調對設施自身和所處區域的文脈呼應與延續,為改建項目賦予獨特而深厚的場域精神價值。結合成都片區實際,應挖掘清退設施在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的價值貢獻,展示當前“綠色發展”背景下清退工作的必要性,建立“發展與保護”的歷史對話,深化國家公園科普基礎設施的文化內涵與保護意義。此外,策劃設計還需兼顧生態保護需要、環境融合需要、科學知識傳播功能、公共產品屬性等多種因素,充分融合不同需求,突出清退設施改建為科普基礎設施的獨特魅力。
3.2.3 堅持綠色營建,降低環境影響改建工程建設需遵循綠色營建理念,采用最有利于環境保護、最小工程量和最小干擾的施工作業方法,最大限度考量全周期、全壽命、全過程的生態環境保護(呂雪蕾等,2021)。在設計方面,注重保留設施的原真性與鄉土性,積極將科普基礎設施融入在地環境;同時,建設路線輕量化,合理控制規模與數量。在材料選擇和施工工藝方面,加大再生、天然、環保、節能等材料的應用,合理就地取材,減少非必要施工措施,選用傳統生態工法,最大程度降低改建過程的環境影響。
3.2.4 重視運營管理,聯動各方資源國家公園的區位條件和人為干擾控制要求意味著園內科普基礎設施不適宜服務大流量訪客,因此,科普基礎設施除控制建設規模外,也需要加強運營管理,提升設施利用率(張婧文,郭美廷,2021)。科學合理的運營管理將有效平抑訪客峰值,提升國家公園科普效率,而運營管理的基礎是人才隊伍。科普基礎設施的運營隊伍組建應多渠道合作,豐富隊伍人員構成,互相協助補位(譚超,張天慧,2021)。運營隊伍宜以國家公園管理人員為基礎,協調科普、科研、巡護、監測多崗位人員參與運營管理,開展科普基礎設施的日常管理;以周邊社區居民為補充,通過科普工作培訓,引導社區居民參與科普講解、科普活動帶領等工作,豐富社區居民參與國家公園建設的渠道;以專業機構為提升,探索特許經營等方式,引入專業科普機構,借助機構運營力量,組織科普體驗活動,研發相關課程與文創,豐富科普展示形式。
4 結論
當前,國家公園發展建設面臨著清退設施“拆”與“留”的處置問題,又面臨著科普基礎設施“怎么建”與“建什么”的發展問題,協同處置這2個問題,尋求協同解決的優化方案,是“清退設施改建為科普基礎設施”這一探索的現實基礎。本文通過分析與探討這2 個問題,提出了“清退設施改建為科普基礎設施”的價值利用思路,并提出管理程序、設計規劃、營建策略、運營管理等方面的路徑實施建議,以期這一價值利用舉措早日得以實踐,在實踐中獲得更科學合理的發展策略,為我國國家公園體系建設提供有益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