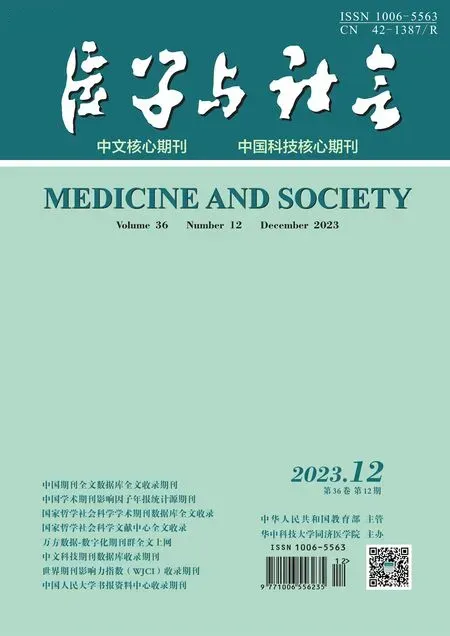國內外過度診斷相關研究的現狀及熱點分析
嚴俊濤,魏 艷,楊 毅,劉世蒙,陳英耀
1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上海,200032;2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衛生技術評估重點實驗室(復旦大學),上海,200032
隨著醫學診療技術的不斷更新以及疾病定義的日益擴大,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過度診療正逐漸損害人群的健康,包括過度用藥、過度治療和過度診斷等行為[1]。其中,“過度診斷”是現代醫療保健過程中危害較大、耗費資源較多的問題之一,現已成為一項全球公共衛生問題[2]。“過度診斷”指無癥狀的人被診斷出原本不會繼續發展為癥狀或導致死亡的疾病[2]。雖然學術界尚未對過度診斷的概念定義達成普遍共識,但總體而言,過度診斷的發生應包含一個事實和兩個先決條件,即:存在一個相對巨大的潛在患病群體;疾病的發病率與篩查的普及度呈正相關;確診后的疾病可不急于治療處理而是選擇采取必要的隨訪觀察即可[3]。
目前,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過度診斷易出現在癌癥篩查以及部分慢性病中,如哮喘病、注意缺陷多動障礙、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甲狀腺癌、慢性腎臟疾病、高血壓、高膽固醇血癥、骨質疏松癥、肺栓塞等[1,2,4-14]。以甲狀腺癌為例,《美國醫學會雜志》(JAMA)期刊已將甲狀腺癌的過度診斷作為2018年度十大過度醫療行為之一[15];在許多高收入國家中甲狀腺癌的過度診斷案例都有所增加,將近90%的韓國患者以及70%-80%的美國患者有過度診斷的經歷,并接受了非必要的手術和抗癌治療[16],而在我國同樣存在甲狀腺癌過度診斷問題[17]。在全球多數國家和地區中,甲狀腺癌的發病率高但死亡率普遍較低的流行病學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研究者歸因于過度診斷效應[18]。國外研究對過度診斷的定義及影響因素均有涉及,且針對重點病種都有一定探索,也有研究從生物學視角論述癌癥篩查的過度診斷成因[19]。而我國現有研究則主要涉及過度診斷內涵的界定和在不同疾病領域中可能存在過度診斷的定性討論[20-26],起步相對較晚。總體上,近年國內外“過度診斷”主題的研究較多,有必要了解相關研究的現狀及趨勢,指導未來的研究開展。文獻計量分析采用數學和統計學等計量方法分析文獻信息,有助于了解某一學科領域的研究熱點與前沿[27]。目前尚未檢索到過度診斷相關的文獻計量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CiteSpace對已發表的中英文過度診斷相關研究進行計量分析,識別過度診斷的研究現狀、發文趨勢及熱點,以期為后續研究提供參考。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檢索策略
在中國知網(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中文數據庫中以“過度診斷”為檢索詞進行文獻檢索,選擇“篇名”“關鍵詞”“摘要”作為檢索字段,語言限定為中文。以overdiagnosis, overtreatment, screening, diagnosis等作為檢索詞在核心合集(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WOSCC)英文數據庫中進行檢索,檢索字段限定為“主題”,語言限定為英文。檢索時間均設定為建庫至2023年5月31日。納排標準:納入有關過度診斷的所有已發表研究文獻,排除重復文獻、學位論文、會議摘要、報紙文章、動物試驗、缺少分析所需字段的文獻(如:篇名不詳、作者信息不全、發表年份不清等)、經驗交流。針對存疑的文獻,通過課題組研究人員共同討論加以明確。
1.2 研究方法
目前,CiteSpace已被廣泛用于探索相應的研究熱點、前沿及趨勢[28]。本研究結合標準化提取表收集和錄入文獻信息,而后分別對國家、機構、作者、關鍵詞及文獻共被引情況等開展可視化分析。具體采用CiteSpace 6.2.R4進行計量分析,時間分區設置為1975-2023年,主要分析發表文章數量、研究機構及其所在國家分布、研究熱點與發展趨勢等內容,并對相關數據進行循證可視化分析。
2 結果
2.1 英文文獻分析結果
2.1.1 研究概況。英文數據庫中,截至2023年5月31日,排除不相關文獻后,最終共納入2513條文獻題錄。結合圖1可以看出,全球近50年來過度診斷相關的英文文章發表量保持持續增長態勢,而在2010年之前總體發文量處于相對較低水平;自2010年Welch等人對于過度診斷的數篇研究發表后,逐漸引發社會對過度診斷問題的廣泛關注,研究發文量開始急劇增加;在2012年后,相關研究的發文量在每年均能超過100篇。

圖1 過度診斷領域英文文獻發文量年度變化趨勢(截至2023年5月31日)
過度診斷相關研究的英文文章數量相對較多,相關研究文獻發文量最多的期刊見表1。

表1 過度診斷主題發文量前10的英文期刊
2.1.2 核心發文機構和合作強度。結合已有的英文文章發文機構視角來看,美國的國家癌癥研究所、華盛頓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密歇根大學、福瑞德·哈金森癌癥研究中心、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斯坦福大學、杜克大學、哈佛大學與妙佑醫療國際,荷蘭的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醫學院和拉德堡德奈梅亨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瑞典的卡羅琳斯卡醫學院以及丹麥的哥本哈根大學等科研機構或醫院的發文量最多,可看出高校與部分癌癥研究中心為過度診斷相關研究的主力軍,且各機構間節點連線較為緊密,網絡密度為0.008。
結合國家合作網絡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當下開展過度診斷研究相對較多的主要是美國、英國、荷蘭、德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西班牙、瑞典和日本等高收入發達國家,各國間的節點連線相對緊密,網絡密度高達0.144,說明各國在過度診斷相關研究中的合作強度相對較高。
2.1.3 研究熱點。基于關鍵詞聚類知識圖譜,得到目前已形成中心度較高的9個關鍵詞聚類,包括diagnosis(診斷),mammography(乳腺X光檢查),prostate cancer(前列腺癌),thyroid cancer(甲狀腺癌),lung cancer(肺癌),cardiomyopathy(心肌病),neuroblastoma(神經母細胞瘤),disease(疾病)和adenoid cystic carcinoma(腺樣囊性癌)等聚類標簽。而在過度診斷相關研究中,已發表的文章也較多關注哮喘、疾病隨訪、死亡率、生存期和早期篩查等方面的研究。見圖2。

圖2 英文文獻關鍵詞聚類知識圖譜
2.1.4 研究趨勢。通過文獻計量分析得到25個關鍵突現詞,分別代表了各時期中英文相關研究前沿熱點,1991-1997年,過度診斷相關研究的突現詞相對多元,或處于對過度診斷定義、影響因素與形成機制的探索階段,關注不同的疾病領域;1997-2017年,過度診斷的相關研究開始重點聚焦于腫瘤領域,研究熱點逐漸涉及前列腺癌、肺癌、甲狀腺癌等具體癌種,并逐漸涵蓋癌癥檢查診斷技術和不同的篩查項目;而自2017年開始,研究開始關注特定疾病的生物學標記物、流行病學現狀及其變化趨勢,同時開始涉及成本-效果研究,反映出目前病理學、流行病學和衛生經濟學與過度診斷研究的結合已逐步成為一個前沿的研究熱點。
2.2 中文文獻分析結果
2.2.1 研究概況。在中國知網中文學術數據庫中進行文獻檢索,排除不相關研究后,最終納入52篇期刊文章。國內近25年來過度診斷相關研究的文章數量相對較低,但總體上呈現出一個緩慢增長的趨勢;2013年以后,中文文獻發文量開始顯著增加,而2016-2017年發表的中文文章數量最多。見圖3。

圖3 過度診斷相關中文研究年度發文量變化趨勢(截至2023年5月31日)
過度診斷相關研究的中文文章數量較少,發文量最多的期刊見表2。僅有少數的科研機構與醫院嘗試探索過度診斷的相關問題,國內研究機構合作圖譜的網絡密度為0.000,提示在相關的研究中我國各機構間缺乏合作。

表2 過度診斷主題發文量最多的中文期刊
2.2.2 研究熱點。基于關鍵詞聚類知識圖譜,得到的聚類關鍵詞包括過度治療、早診早治和甲狀腺癌等標簽。其中,發表的文獻主要針對由過度診斷導致的過度治療、疾病篩查和甲狀腺癌診療等領域,且不同聚類的研究間幾乎不存在連線,顯示出關聯程度較弱。見圖4。

圖4 中文文獻聚類知識圖譜
2.2.3 研究趨勢。過度診斷的中文研究領域網絡模塊化評價指標(Q值)為0.770,具有顯著的網絡結構;而聚類輪廓指數(S值)為0.930。結果顯示,1994年,我國該領域的研究開始提出了過度診斷的概念;2008-2023年國內對于過度診斷的研究數量持續增加。2015年前后,國內研究開始涉及包括腫瘤篩查、檢測結果、過度治療、過度診斷的現狀分析等領域,逐漸聚焦于惰性癌和惰性病變及其醫學干預與癌癥的早診早治,并關注肺栓塞、甲狀腺癌和前列腺癌等病種的過度診斷。
3 討論
3.1 目前國內外過度診斷相關研究的發文量整體呈上升趨勢
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以及早期篩查項目的實施,過度診斷問題逐漸突顯,鑒于其潛在危害巨大,學界對相關領域的關注日益增加[29]。國外研究者對于“過度診斷”的研究起步較早,對于易發的特定疾病均有相應探索。全球近50年來過度診斷相關的英文文章發表量保持持續增長態勢,并自Welch等人的《過度診斷:追求健康卻使人患病(Overdiagnosed: Making People Sick in the Pursuit of Health)》書籍出版起,社會對過度診斷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2],隨后的年均發文量都能維持在高位。
目前已有的英文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3個方面。①過度診斷程度與水平的測定[6-9,16-17]。國外研究者應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對特定癌種開展過度診斷的評估與測量,而測量方式基本為長時間的隊列研究及估算預測。②過度診斷發生機理與形成機制的研究[2,13-14]。國外過度診斷的研究主要是對影響因素的探討,雖聚焦關注某個研究視角,但對醫患群體行為驅動因素的解析研究不足,總體上缺乏對過度診斷影響因素的系統識別和作用機制的分析與歸納。③過度診斷的健康及社會經濟影響研究[1,15]。國外研究當前主要通過定性評述或綜述等方式,對過度診斷所導致的健康及社會經濟影響進行分析,但對于因活動受限及疾病標簽效應產生的間接經濟負擔測算研究較為缺失。
我國對過度診斷及其引發的過度治療問題同樣開展了研究,但相較國外更為薄弱。針對過度診斷的驅動因素、健康及社會經濟影響以及應對策略等關鍵內容,國內已有初步的探索與討論,但內容略顯碎片化。①過度診斷的相關驅動因素[24,26]。多數的國內研究僅對過度診斷某單一視角下的原因進行探討。②過度診斷的健康及社會經濟影響。有研究分析了甲狀腺癌過度診斷及治療可能造成的健康損害及關鍵因素[23-24],有學者嘗試總結歸納了測定過度診斷的定量方法[30]。③過度診斷的應對策略。總體研究相對分散,涉及分級診療對于過度診斷的潛在遏制能力[26],美國臨床腫瘤學會的推薦建議中可借鑒的部分[31],以及甲狀腺癌過度診斷情境下可采取的應對策略等內容[32]。由于“過度診斷”概念的復雜性和廣泛性,較難予以直接測量和定量評價[33-34],已發表的國內外文獻多為現況分析,定量研究較少,研究視角多聚焦在宏觀視域下對過度診斷的評述討論。而厘清過度診斷的概念,并對特定條件下和特定疾病的過度診斷進行精準定義和標準制定,將有助于明晰與其相關概念間的關聯,助力后續研究開展[35]。
3.2 國內外過度診斷相關研究的熱點存在差異,國內相關研究機構間缺乏合作交流
在過度診斷相關的研究中,已發表的英文文章數量較多,并主要集中發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BMJ Open, PLoS One以及腫瘤與放射學等領域的學術期刊雜志上,表明此類期刊在該領域具有較強學術影響力,或更關注過度診斷這一主題。而國內中文研究發文量則相對較少,多發表于《醫學與哲學》《臨床誤診誤治》《中國誤診學雜志》和《中國腫瘤》等期刊。
研究熱點與趨勢方面,由于關鍵詞是對文獻內容的提煉,能反映文獻的核心要點,通過對關鍵詞的梳理和計量分析可確定某一學科領域的熱點問題[36]。結果顯示,過度診斷相關的英文研究初期側重內涵定義、影響因素和機制探索,隨著醫療技術水平的提升研究逐漸深入,開始重點關注腫瘤領域,并聚焦各具體癌種和篩查項目的探索,相關主題的病理學、流行病學、衛生經濟學研究也開始成為過度診斷相關研究的前沿熱點,表明目前在該研究領域已取得了一定突破。而我國直到21世紀初才開始關注過度診斷并嘗試研究探索,中文研究多集中在肺栓塞、前列腺癌和甲狀腺癌等容易發生過度診斷的具體病種及其“早診早治”領域,總體上仍處于起步階段。國內外研究熱點和趨勢的差異,可能是由于我國和其他國家具有不同的疾病譜、社會經濟發展情況、醫學技術水平、就醫文化以及對過度診斷重視程度等因素所致[29,37],未來或可參考國外研究熱點并結合我國實際,針對性地擴展過度診斷相關研究內容和方向。此外,在過度診斷相關的英文研究中,各國與各機構間的交流合作較為充分,形成了顯著的合作網絡。但國內各機構和核心學者的研究側重點不同、主題分散且幾乎沒有聯系,表明發文機構和學者間缺乏交流合作,或不利于我國相關的成果轉化與產出。因而,有待加強和鼓勵開展跨領域、多學科、多團隊的合作交流,從而提升我國相關領域的整體科研能力和水平。
3.3 過度診斷相關的研究有待進一步開展
過度診斷對于個體健康及社會經濟將產生多層次的影響。或可導致因給低風險人群貼上非必要的疾病標簽所引發的副反應,因非必要的檢查和治療造成的健康損害,由其引發后續過度治療及誤工的經濟負擔,以及造成的衛生資源浪費等問題[30,38],這都將對我國的衛生服務公平性與衛生系統健康可持續發展提出嚴峻挑戰,是一個潛在的嚴重問題[19]。因而,過度診斷的研究有著較強的現實意義;同時,正確識別和辨析過度診斷的概念內涵、驅動因素及其影響,并系統分析過度診斷的發生機理與形成機制,對于設計和實施預防與監管策略而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當前,過度診斷的確切定義在學界尚未達成共識,原因在于其驅動因素較多、形成機制復雜。雖然學界對其量化評價、發生機理與形成機制的系統性分析和研究有一定探索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多數研究是針對過度診斷的內涵、影響因素及其產生的影響進行定性評述,缺乏有關發生機理與形成機制的深入剖析,現有的研究存在整合性不足、內容分散等問題,尚未形成體系,且我國的相關研究較為缺乏,不利于衛生決策者系統把握過度診斷問題,針對性制定合理的應對策略與監管措施。因而,我國對于過度診斷的重視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積極推進過度診斷相關的各項研究,可為我國衛生決策者提供科學充分的循證依據,助力政府部門適時采取合適的應對措施和監管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