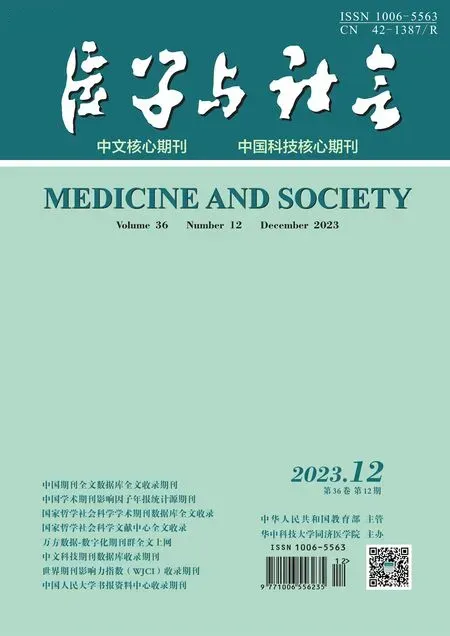老年癌癥患者治療決策質(zhì)性研究的系統(tǒng)評價(jià)
馮雨佳,蘇明珠,劉彥秀,張錦欣,童西洋,孫曉杰
1山東大學(xué)齊魯醫(yī)學(xué)院公共衛(wèi)生學(xué)院衛(wèi)生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山東濟(jì)南,250012;2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員會衛(wèi)生經(jīng)濟(jì)與政策研究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山東大學(xué)),山東濟(jì)南,250012
全球癌癥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顯示,2020年全球新發(fā)癌癥患者數(shù)量達(dá)到1929萬例[1],預(yù)計(jì)2040年新發(fā)癌癥病例將到達(dá)2840萬例[2],癌癥已成為當(dāng)代社會重大公共衛(wèi)生問題之一,而年齡是罹患癌癥的主要危險(xiǎn)因素之一[3-4]。由于合并癥的影響,隨年齡增長,老年人更有可能產(chǎn)生超出其癌癥疾病范圍的健康和照護(hù)問題[5]。因此,其治療方案的制定通常涉及多方主體參與,不同利益主體間的觀念與經(jīng)驗(yàn)沖突加劇了決策的復(fù)雜性。
隨著現(xiàn)代循證醫(yī)學(xué)和精準(zhǔn)醫(yī)學(xué)的發(fā)展,患者不再作為單純的“病人”角色被動(dòng)參與決策之中[6]。在此背景下,治療決策是指在公共政策和社會環(huán)境影響下,醫(yī)患雙方基于相關(guān)信息的分析和權(quán)衡,共同制定的符合患者生活目標(biāo)的醫(yī)療方案[7]。從本質(zhì)上來說,治療決策是一個(gè)信息集成的過程,因此患者在這一過程中勢必會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信息需求。信息需求是指個(gè)體及時(shí)獲取問題解決所需要的完整可靠的信息的要求[8]。由于現(xiàn)代醫(yī)學(xué)所固有的專業(yè)性與復(fù)雜性,患者被迫成為信息不對稱問題中的劣勢方,不得不尋求路徑來獲取更為完整可靠的信息,以實(shí)現(xiàn)制定最優(yōu)治療決策的目的。
當(dāng)前,老年癌癥患者的治療決策已引起眾多國內(nèi)外學(xué)者的關(guān)注,大多數(shù)學(xué)者普遍認(rèn)為,高齡會使得癌癥患者面臨更高的化療或放療不耐受、術(shù)后并發(fā)癥等風(fēng)險(xiǎn),其群體異質(zhì)性表現(xiàn)較為明顯[9],在治療中多處于被動(dòng)地位[10]。而聚焦于老年癌癥患者關(guān)注的核心要素,吳珺瑋等研究發(fā)現(xiàn)部分老年患者把生理功能狀態(tài)、認(rèn)知能力和生活質(zhì)量放在更優(yōu)先位置[11]。Angarita等同樣認(rèn)為老年癌癥患者在治療決策中會更優(yōu)先考慮功能獨(dú)立性[12]。Karuturi等則指出老年患者的決策策略是由其知識水平、價(jià)值觀和他人的經(jīng)驗(yàn)所決定的[13]。此外,老年癌癥患者信息需求的相關(guān)研究已經(jīng)證實(shí)了絕大多數(shù)患者都會接收治療決策信息[14],這能夠?yàn)榛颊咛峁?yīng)對癌癥的知識以及情感支持[15]。但Bol等研究則指出部分老年患者事實(shí)上并不期待過多的治療決策信息[16]。同時(shí),老年癌癥患者的信息來源[17]、偏好的信息類型等細(xì)分領(lǐng)域研究也正得到不斷充實(shí)[18]。這些研究結(jié)果為優(yōu)化老年癌癥患者的治療決策與信息需求提供了一定的科學(xué)依據(jù),但也揭示了當(dāng)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第一,部分研究僅針對單性別、單病種的老年癌癥患者[12-13],可能會限制其研究結(jié)論的外推性。第二,由于單一研究所聚焦的維度有限[15-16],當(dāng)前研究對決策中所采用的策略分析仍較為片面。第三,當(dāng)前該主題研究幾乎都為原始研究[12-14],對其進(jìn)行整合與歸納的二次研究仍較為缺乏。同時(shí),考慮到相較于量性研究,質(zhì)性研究能夠更全面觀察患者的觀點(diǎn)和行為,剖析其復(fù)雜決策背后的本質(zhì)。因此,本研究采用Meta整合方法探究老年癌癥患者的治療決策,全面分析老年癌癥患者的決策策略,為增強(qiáng)醫(yī)療方案的患者導(dǎo)向性提供循證支持。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文獻(xiàn)納入和排除標(biāo)準(zhǔn)
1.1.1 納入標(biāo)準(zhǔn)。①研究對象:年齡≥60歲,且被明確診斷為癌癥的患者。②感興趣的現(xiàn)象:老年癌癥患者的治療決策制定。③研究設(shè)計(jì):質(zhì)性研究、混合型研究。④研究主題:老年癌癥患者的治療決策偏好、影響因素及信息需求。⑤研究類型:描述性質(zhì)性研究等質(zhì)性研究方法。
1.1.2 排除標(biāo)準(zhǔn)。①重復(fù)發(fā)表。②非中文、英文文獻(xiàn)。③結(jié)果僅來自混合型研究中的量性研究。
1.2 文獻(xiàn)檢索策略
檢索PubMed,Web of Science,Elsevier ScienceDirect,Cochrane Library,CINAH和中國知網(wǎng)、萬方、維普、中國生物醫(yī)學(xué)文獻(xiàn)數(shù)據(jù)庫,檢索時(shí)限為建庫至2022年12月31日。英文檢索詞包括:“old*/elder*/aged/senior citizen”“cancer/carcino*/tumor”“decision/decide*/treatment”“qualitative/mixed/interview/phenomenology/grounded theory”。中文檢索詞包括:“老年”“癌/腫瘤”“決策/治療/策略”“質(zhì)性/定性/混合/訪談/現(xiàn)象學(xué)/扎根理論”,并對納入文獻(xiàn)的參考文獻(xiàn)進(jìn)行追溯。
1.3 文獻(xiàn)篩選和資料提取
篩除重復(fù)文獻(xiàn)后,通過閱讀標(biāo)題與摘要進(jìn)行初篩,隨后通過閱讀全文進(jìn)行復(fù)篩。資料提取內(nèi)容包括作者、國家、分析方法、樣本量、研究對象、感興趣的現(xiàn)象和主要結(jié)果。所有程序皆由2名經(jīng)過質(zhì)性研究培訓(xùn)的研究者獨(dú)立進(jìn)行,當(dāng)存在分歧時(shí)由第3名研究者參與討論并決斷。
1.4 文獻(xiàn)質(zhì)量評價(jià)
采用2016版澳大利亞喬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oanna Briggs Institute,JBI)循證衛(wèi)生保健中心質(zhì)性研究質(zhì)量評價(jià)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評價(jià)[19]。該評價(jià)標(biāo)準(zhǔn)共包含10項(xiàng)具體指標(biāo),每項(xiàng)均以“是”“否”“不清楚”作為評價(jià)結(jié)果。若文獻(xiàn)滿足全部評價(jià)指標(biāo)即為A級,發(fā)生偏倚的可能性較小;若文獻(xiàn)滿足部分評價(jià)指標(biāo)即為B級,發(fā)生偏倚的可能性為中等;若文獻(xiàn)完全不滿足評價(jià)指標(biāo)即為C級,發(fā)生偏倚的可能性較高。本研究納入質(zhì)量等級為A、B級的文獻(xiàn),篩除等級為C級的文獻(xiàn)。
1.5 資料分析方法
采用匯集性整合方法[20],由研究者重新對研究結(jié)果進(jìn)行歸納、整合,并最終形成新的解釋。該系統(tǒng)評價(jià)實(shí)施方案已在PROSPERO平臺注冊(ID為 CRD42023430961)。
2 結(jié)果
2.1 文獻(xiàn)檢索結(jié)果與方法學(xué)質(zhì)量評價(jià)
剔除重復(fù)文獻(xiàn)后,本研究共檢索出1651篇文獻(xiàn),納入13篇文獻(xiàn)。見圖1。根據(jù)JBI評價(jià)標(biāo)準(zhǔn),除Sattar等人和Tsuboi等人的質(zhì)量評價(jià)為A級[21-22],其余皆為B級。

圖1 文獻(xiàn)檢索及篩選結(jié)果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如表1所示,納入的研究較多采用主題分析(4篇)、框架分析(3篇)、扎根理論(3篇)的分析方法。在研究對象方面,乳腺癌被廣泛關(guān)注,但不同研究對癌癥階段、確診時(shí)間、治療狀態(tài)各有側(cè)重。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2.3 Meta整合結(jié)果
對納入的13篇文獻(xiàn)進(jìn)行Meta整合后,共提煉出67個(gè)研究結(jié)果,歸納為10個(gè)類別,并匯總成3個(gè)新主題:患者對決策主體的偏好、治療決策的影響因素和患者的決策信息需求。
2.3.1 患者對決策主體的偏好。第1類患者偏好由患者本人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認(rèn)為自己有足夠的能力主導(dǎo)決策過程,因而堅(jiān)持在治療決策中保有自主和獨(dú)立意識,他人的觀點(diǎn)和建議在決策過程中不起決定作用(3篇)[12,21,23]。第2類患者偏好由醫(yī)護(hù)人員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這類患者主要選擇以醫(yī)護(hù)人員為中心討論制定的治療決策,通常嚴(yán)重依賴于醫(yī)護(hù)人員的意見和建議(3篇)[22,24-25]。第3類患者偏好由家庭成員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主張治療決策需要首先在家庭內(nèi)部達(dá)成一致,而患者本人也更傾向于向家庭決策妥協(xié)(1篇)[26]。第4類患者偏好由多主體共享決策,并不希望由患者或醫(yī)護(hù)人員任一方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而是期望由多主體在溝通協(xié)商的基礎(chǔ)上制定最終決策(2篇)[27-28]。
2.3.2 治療決策的影響因素。在患者特征層面,一些患者認(rèn)為高齡會促使其避開風(fēng)險(xiǎn)更高的治療方案(3篇)[12,23,25],經(jīng)濟(jì)和社會支持狀況也會限制其選擇(2篇)[23,28]。此外,患者還會考慮自診斷以來所承受的精神痛苦(3篇)[22,28-29]。在醫(yī)療供給層面主要存在兩方面因素。一方面,醫(yī)護(hù)人員的職業(yè)素養(yǎng)和醫(yī)療機(jī)構(gòu)的硬件能力與條件是患者考慮的重要因素(5篇)[12,27,29-31]。另一方面,患者看重治療方式對軀體功能獨(dú)立性和生活質(zhì)量的影響,因此治療副作用、恢復(fù)時(shí)間等因素都被納入考慮范圍(4篇)[12-13,28-29]。在家庭及親友層面,許多患者強(qiáng)調(diào)家庭成員或朋友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意見和觀點(diǎn)對治療決策具有重要影響,但有時(shí)也會讓患者感到被限制(3篇)[12,27-28]。
2.3.3 患者的決策信息需求。老年癌癥患者對信息尋求的態(tài)度存在較大差異。一些患者對決策信息持較為積極的態(tài)度,希望能夠獲取更多相關(guān)信息(2篇)[27,31]。但由于個(gè)體治療細(xì)節(jié)信息的缺失和信息過載現(xiàn)象的存在,部分患者對決策信息持消極態(tài)度,害怕了解疾病真實(shí)狀況(2篇)[22,27]。在決策信息的來源方面,部分老年癌癥患者通過網(wǎng)絡(luò)資源、紙質(zhì)書籍等途徑自行收集治療決策信息(2篇)[21,27]。此外,還有許多患者通過向臨床醫(yī)生、朋友和家人、有類似醫(yī)療經(jīng)歷的人尋求幫助的方式獲取信息(2篇)[13,23]。當(dāng)前老年癌癥患者尋求的信息類型主要包括關(guān)于治療方案和并發(fā)癥如何影響生活的實(shí)用信息、預(yù)后和復(fù)發(fā)方面的概率信息、醫(yī)生的專業(yè)信息等(2篇)[13,31]。
3 討論
3.1 老年癌癥患者的治療決策根植于其社會文化背景
當(dāng)前老年癌癥患者治療的決策模式主要包括患者主導(dǎo)[12,21,23]、醫(yī)護(hù)人員主導(dǎo)[22,24-25]、家庭成員主導(dǎo)和多主體共享4類[26-28]。社會認(rèn)知理論中的三元交互決定論認(rèn)為,人類功能是個(gè)人、行為和環(huán)境因素三者互為影響的因果關(guān)系[32],引申至健康領(lǐng)域則是強(qiáng)調(diào)社會環(huán)境對健康相關(guān)行為具有重要作用[33]。因此,進(jìn)一步聚焦于研究對象所在地區(qū)不難發(fā)現(xiàn),在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的影響下,英國、美國等國家的患者更傾向于獨(dú)立做出治療決策[34]。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等東亞國家受傳統(tǒng)儒家文化的深遠(yuǎn)影響,將個(gè)人決策與家庭決策相勾連,認(rèn)為生存時(shí)長比生活質(zhì)量更重要[35]。正如王樂研究所言,中國家庭通常會代替患者成為實(shí)施自主權(quán)的主體[36],這也意味著家庭資源的傾斜和個(gè)人權(quán)利的讓渡。因此,患者在面臨決策過程中的分歧時(shí),有較大可能性服從于家庭決策[26]。但這種決策極易形成對患者利益與自主權(quán)的侵蝕[37],甚至引發(fā)患者的焦慮情緒[27]。未來應(yīng)從醫(yī)學(xué)倫理的角度進(jìn)一步明晰家庭與個(gè)人自主權(quán)的邊界問題,在充分尊重患者個(gè)人意愿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家庭決策的討論與協(xié)商,確保治療決策真正維護(hù)患者權(quán)益。
3.2 功能獨(dú)立性和生活質(zhì)量等因素對老年癌癥患者的治療決策有影響
老年癌癥患者的治療決策實(shí)質(zhì)上是年齡[12,23,25]、經(jīng)濟(jì)與社會支持[12,23,28]、精神狀態(tài)[22-23]、醫(yī)療服務(wù)質(zhì)量[27,29,31]、親友建議等諸多因素的持續(xù)博弈[13,26,28]。Bridges等人研究證實(shí),高齡使得老年癌癥患者更容易產(chǎn)生超出其疾病范圍的健康和照護(hù)問題[5]。因此,患者的功能獨(dú)立性和生活質(zhì)量往往被其視為決策的核心要素[12-13,22,28-29]。即使罹患癌癥,患者也并不希望自己徹底失去軀體獨(dú)立性,甚至完全成為他人的負(fù)擔(dān)[22],這會使他們不得不面臨更為沉重的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與精神壓力。一方面,當(dāng)老年癌癥患者喪失行動(dòng)能力與自我照護(hù)能力時(shí),其個(gè)人和家庭需承擔(dān)包括人力成本、交通成本和醫(yī)療成本等在內(nèi)的額外護(hù)理成本;另一方面,作為原本社會鏈接中的一環(huán),老年癌癥患者因病被迫遠(yuǎn)離社會關(guān)系,所有自主行為都不得不依賴于他人幫助進(jìn)行,這無疑會讓其感到無助與恐慌,甚至進(jìn)一步加劇其抑郁等負(fù)面情緒。基于此,患者更希望治療決策能最大程度保障生活質(zhì)量,降低對實(shí)現(xiàn)個(gè)人目標(biāo)和優(yōu)先事項(xiàng)能力的影響[13]。在治療決策制定的過程中,醫(yī)護(hù)人員需要關(guān)注老年患者的生活質(zhì)量需求,尊重其對于自身軀體獨(dú)立性的要求與期望,通過著力發(fā)展高質(zhì)量醫(yī)療提升老年癌癥患者的生命質(zhì)量。
3.3 高質(zhì)量決策信息是滿足患者信息需求的前提
信息不對稱理論認(rèn)為,信息占有相對量的差別導(dǎo)致了交易者信息地位的不同[38]。聚焦于本研究,醫(yī)患雙方在醫(yī)療信息方面存在著嚴(yán)重的信息不對稱,而不具備專業(yè)知識的患者通常處于劣勢地位。因此,為了跨越知識鴻溝,患者的信息來源通常包括醫(yī)護(hù)人員、家人、書籍、網(wǎng)絡(luò)等多方面[21,23,27]。來源多樣、細(xì)致全面的決策信息能夠幫助患者建立對于自身病情的準(zhǔn)確認(rèn)知,進(jìn)而為其決策制定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撐。2021年,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發(fā)布的新版《醫(yī)療衛(wèi)生機(jī)構(gòu)信息公開管理辦法》也著力于縮小醫(yī)患之間的信息差,為患者信息需求提供支撐。但隨著當(dāng)前社會信息交流速率與方式的迅猛發(fā)展,信息資源逐漸變得冗雜且碎片化[27]。而大部分患者并不具備專業(yè)能力來辨識各類信息的真實(shí)性、科學(xué)性、適當(dāng)性[21]。大量重復(fù)、虛假的劣質(zhì)信息充斥在醫(yī)療信息市場,極易對患者造成迷惑效果。因此,醫(yī)護(hù)人員在實(shí)際決策過程中面向患者提供明確、適量、符合患者個(gè)性化需求、來源可靠的信息至關(guān)重要[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