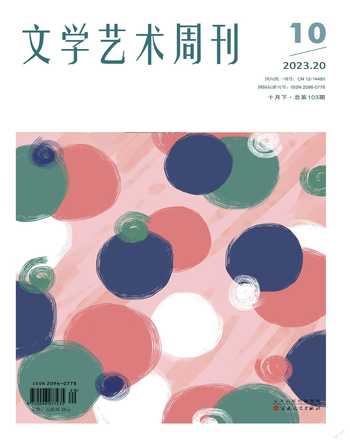探析《詩經》中的女性
《詩經》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也是最為重要的作品。綜覽《詩經》的相關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幾乎是一個必被提及的角度,各類研究也相應地關注到女性在詩歌內容中的特殊地位,關注到《詩經》中女性所表現出的突出的個人意識。本文概括了《詩經》中三種在當下也有表現的女性意識,并聯系當時社會背景進行分析。
一、自由平等追求愛情的意識
《詩經》中的許多詩句都呈現出了女性的本真生命力,對個體喜怒哀樂的表達也極為到位,形象且生動, 彰顯著女性在精神上的自由、人格上的獨立。特別是在愛情中認為自身與男性平等的意識。
對愛情的向往以及渴求是《詩經》中女性心理活動的突出表現, 如《鄭風·子矜》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 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顯然詩中所寫之“子”乃是少女心中所想的人,然而這位少女依然有些矜持,只是在心里揣摩或是思念,從“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仿佛可以看到女子又愛又恨的嗔怨表情。雖然男子對她有些冷落,可她依然還是在等待,“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清晰生動地表現了女子內心的想念。
不僅是對于愛情本身,在對生命本能的自然情欲的追求上, 《詩經》中的女子也表現得十分勇敢。《召南·野有死麕》中, “作者”用第三人稱向我們展現了男女相遇并相互吸引? 歡愛的場景:“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懷春意指春心萌動,吉士玉女在野外相遇,相互愛慕,吉士以白茅包死鹿作為定情信物,俘獲女子芳心。末句十分形象地描寫了少女與吉士親密之時羞澀矜持卻又激動欣喜的? 內心活動,表現了男女對自然情欲的天性渴望。
遇見心之相悅的男子固然令女子歡心,可也有不遂人愿之時。《齊風·南山》中寫道:“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可見那時候男女的自由戀愛常常受阻于禮儀的約束。但也正是在這樣的要求和約束下,反倒激發了女子對愛情的勇敢追求和堅貞的態度。如《鄘風·柏舟》,詩中女子愛上一個少年,然而母親強迫她接受已安排的婚事,可她寧死 不愿。在綱常和愛情之間, 她毅然選擇了后者,堅守自己的信念,表達了對禮制的抗衡和對愛 情無比堅貞的態度。由此可見,《詩經》中的 女性都有著人性自然的光輝,其對于愛情有著 共性的向往與追求,在愛情中有鮮明的自由與 平等意識,而且對于本能情欲的大膽渴望追求 和表達也是令后世女子震驚的。雖禮制規范已成型,可也正是由于其束縛,更顯《詩經》中 女子對愛情的勇敢與堅貞, 這些女子構成了《詩 經》獨有的光芒。
二、對完整婚姻模式的渴望意識
在《詩經》現存的三百零五篇詩歌中,愛情詩占了大量的篇幅。相識相知、兩情相悅、別后相思、思而不得、遭棄悲思等主題的詩歌比比皆是。綜觀此類詩歌主題,不難總結出,除了對愛情的向往外,其他基本可以歸納為對完整婚姻模式的渴望,即從待嫁狀態的懷春思嫁,到婚后為人妻、為人母、成為賢妻的完整婚姻內容。
思嫁意識。不論是在古代抑或現代,談婚論嫁都是男女一生中重要的大事。而在古時,婚事嫁娶又有季節的要求,錯過嫁娶的季節或者超過嫁娶的年齡都被稱為“失時”。在周朝,女子的適婚年齡為十五歲至二十歲,二十歲而未嫁是為過時,顯然適齡期限較短。同時由于季節的限制,可以說女子只有五個季節的適齡,加之當時諸侯戰事頻繁,男子因參與戰事故而死亡率高于女子,因此女子失時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對于還未定婚事的女子,其內心深處都潛藏著對失時的焦慮,對于愛情婚姻的希望在嫁娶時節尤為強烈。
賢妻意識。未出門的女子思嫁擔心失時,時刻為出嫁準備著, 準備著婚后成為賢妻。《詩經》中有大量的詩篇表達了對女子婚后成為賢 妻良母的期盼。著名的《周南·桃夭》里就提 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這里就是從客觀層面表達對女子出嫁后“宜其 室家”的希望。而“之子于歸”之后,所賴以宜室宜家的,無非是有花有實有葉而且能茂盛 這幾種條件罷了。中國古來女子,不作興有主 張,亦無主觀的道德和人格。所謂三從,就是 未嫁從父,既嫁從夫, 夫死從子。在既嫁之后,要想稱得上賢妻,那就要完全依從丈夫的主張,設法討丈夫歡喜。在這樣的傳統意識主導下,不管是出嫁前還是出嫁后的女子都會有意識地 向賢妻的方向努力。
生育意識。在古代,女子無后是家庭極為? 敏感的事,古代女子出嫁前努力學習人妻所需要掌握的家務技能,出嫁后則必須將生育看作大事。《詩經》中也用了大量詩篇或是意象來表達對女子生育的期望,例如《周南·桃夭》中的“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 家室”,希望新娘能夠多生多育。《周南·螽斯》也反用蝗蟲多子來比人之多子,表示對多子者的祝福。在這種希望的潛移默化之下,生育意識也成為《詩經》中女性極其重視的意識。《詩經》中的棄婦詩也較多因為無后而產生。
思嫁、成為母親、成為賢妻,是《詩經》中女子普遍都擁有的意識,她們的經歷和訴說構成了《詩經》的豐富內容,也讓后世看到了古代女子的賢良和純真的性靈。
三、心系家國的參政意識
這一種女性意識在《詩經》中是較少出現的,但也是典型的。之所以提到此類意識是因為在 現代社會女子參政不再像古代那般被完全禁止,因此在當時的父系社會,對政治對國家做出重 要貢獻的女子與她所作的詩篇同樣值得現代人 的欽佩與尊敬,這個人就是許穆夫人。許穆夫人是衛戴公、衛文公的妹妹,雖在深閨成長,? 她卻清楚天下的形勢,并心系國家的興衰榮辱。衛國被狄人破滅后,遺民在宋國幫助下被安置? 漕邑。許穆夫人聽到衛亡的消息,立刻奔到漕邑吊唁,并提出連齊抗狄的主張,得到齊桓公的支持而復國于楚丘。《鄘風·載馳》便是她當時抵達漕邑時所作的詩篇: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許穆夫人心憂國家,一心思考良策為宗國解難, 她認為“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女子也有為國分憂、為國出力的責任。事實證明她做到了,并且做得很成功。許穆夫人表現出來的政治意識與能力已遠遠勝過膽小怕事的衛國大夫。雖然像許穆夫人這樣的女子在《詩經》中確是少數,但也因此其更加綻放獨特的光輝。放之現代社會,其巾幗英氣也十分值得稱贊。
四、結語
《詩經》中,女性是不可忽視的主體,而女性所表現出來的追求自由平等抑或對婚姻的渴望,實際上都反映出當時父系社會男尊女卑的社會文化對女性的壓迫,正是社會禮制強調 女子應服從父權、夫權、君權,女子才會渴望婚姻、渴望依賴男子,也才會不甘受制而產生反抗和自由平等的女性意識。因此分析這類意識產生的原因,便是分析父系社會的產生原因及其影響。
《詩經》的創作年代在先秦時期,正處于歷史上重要的生產力變革期。人們從石器時代轉入鐵器時代,發生了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社會生產力向縱深發展,畜牧業和農業從狩獵和 采集業中分化出來,男子從漁獵轉向農業和手工業。女子在傳統行業中所占的優勢地位逐步讓位于擅長放牧和種植的男子,加上體力較男子弱且有生育之累,女子便只從事紡織、炊事和養育子女等家務勞作。夏至周朝,宗法制逐
步形成并確立,男子成為國家領導者。男子娶妻,女子出嫁跟隨男子,且為了生子的要求,男子 多廣納妻妾,女人的社會地位下降,由此形成 夫權至上的社會,男子除了擁有離婚的特權外,也成為社會的主導者,形成“男外女內”的社 會形態,男尊女卑的觀念于是形成。因此,從《詩 經》及相關史料中可以看到,女性從被奉為各 開國先祖之母到逐漸失去地位,淪為父權、夫 權的奴隸在這一時期有鮮明的脈絡可循。一個 時代的作品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變遷, 于是《詩 經》中自然也少不了記載這一重要社會階級變 化的作品。
另外,在《詩經》產生的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前后約五百年間,大小諸侯國為了領土而發生戰爭,戰爭帶來徭役,男子成為戰爭主力。戰爭給各國帶來了人口損失,造成男女比例失衡,于是便有了女子擔心失時的思嫁意識出現,或是因丈夫參戰而遲遲無法擁有生育機會,甚至是因為丈夫戰死沙場而成為守寡之人,造成婚姻不完整。這都是《詩經》中普遍的女性意識產生的原因。
總的來說,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其中關于女性的描寫也多種多樣、多姿多彩,這些優秀詩篇所反映出的女性意識不僅是展現當時女性風貌的重要載體,也是我們了解古代女性及女性意識產生的重要途徑。本文所概括的自由平等、思嫁、賢妻等典型的女性意識,不僅展現了《詩經》本身豐富多彩的內容,也對現代社會女權主義、男女平等的重視或倡導有一定啟發和研究意義。當然,本文所提及與分析的內容還不盡詳細與透徹,借以此文,發現《詩經》不可或缺的研究價值,旨在對今后的涉獵或研究做一引導。
[作者簡介]李佳軒,女,漢族,河南鄭州人,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實習員,碩士,研究方向為文藝學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