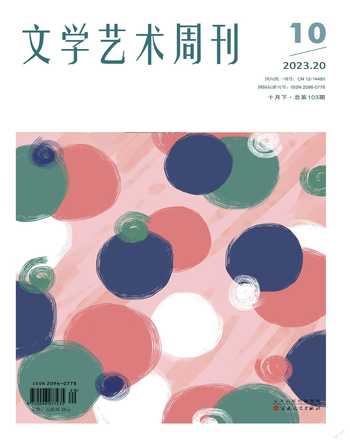《紅線》中的物敘事
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Jose, 1952—)根據沈復的《浮生六記》創作了《紅線》。他讓人物經歷“輪回轉世”,將沈復、蕓娘和憨園的愛情故事改寫到了現代上海。小說以細膩的筆法描寫了跨越種族的愛情故事。尼古拉斯·周思將《浮生六記》和《紅線》有機結合,《浮生六記》成為情節發展的重要推手。小說中關于文物的描寫細致入微,這些文物和《浮生六記》原稿在小說敘事中發揮重要作用。它們既是中國文化的見證者和象征,也發揮了主體性,影響了小說中人物的命運,同時具有超越語言與文字的價值,發揮了其本體性。然而小說中的物敘事卻傳達出了作家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誤讀。
一、文化符號
物具有文化屬性。1996年,布朗提出了“物質無意識”的概念,強調學者應關注文學作品中展現的物質文化。這一觀念很快被應用于物與人的關系研究之中,成為文學批評領域“物轉向”的敲門磚。布朗主張從物入手,反向研究文學作品,肯定了物的文化屬性, “文化是
物質的媒介,反之,物質也是文化的媒介”。
小說中的物具有文化隱喻功能,但其文化屬性下暗藏著西方中心主義的政治話語。小說開頭,沈是中國文化的弘揚者, 而在后半部分,沈因尋找遺失的原稿喪失了思考能力,以高價買到了假的書稿,沈前后的反差暗含著作家對于中國人形象的誤解。這種誤解還體現在其他人物對這本原稿的態度上。小說中描寫的中國人對西方文明過度崇尚。琳達對沈撤出這本原 稿拍賣的不滿來自沈的行為讓她在副市長面前丟人。她并不理解原稿背后的文化內涵,關注的僅僅是其商業價值。琳達是美籍華人,卻不理解認同中國文化,反而崇尚西方文明,唯利是圖。作家筆下的司徒貪婪奸詐,他將自己國家的文化遺產當作斂財的工具。而西方人魯絲卻身負傳承中國文化的使命。作家將西方人置于主體地位,彰顯了西方人的重要性,而東方人對于自身文化傳承卻態度消極。
此外,文物本應該收藏在博物館之中,承 擔著傳承歷史的重要作用。而小說中,這些文 物出現在了拍賣會上,其價值被物化成了金錢,這就使得文物成為被金錢物化的具體商品。同時,小說第二章中,沈用明代的杯子給魯絲倒酒,他忽視了古董的文化價值,將其當作愉悅他人的工具。
小說中的古籍和古董沒有彰顯其文化歷史傳承功能,不斷被物化和商品化,傳遞的是尼古拉斯·周思對于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形象的誤讀,小說中沈沒有完成傳承自身文化的責任, 反而是魯絲成為文化傳承的重要推動者。
二、主體性
物具有明顯的主體性。在小說中“物件居于某種因果關系中,從而決定人物的命運”。物并不僅僅是人物活動的背景工具,它具有自己的獨特性。簡·本妮特認為物具有施事能力,可以促進或者阻礙人物的活動,這就是她歸納的“物的力量”。因此,研究者應該突破物的文化表征,正視物在敘事進程中起到的獨特作用和展現出的力量。
《紅線》中,物的力量表現為原稿對于小說中人物命運的影響。書稿貫穿整個故事的發展,居主宰地位的是作為物的原稿,而不是小說中的男主人公沈。作家賦予了這本原稿神秘的力量。原稿在小說情節的發展中彰顯了物的積極和消極力量。
物的積極力量促成了小說主人公的結緣。小說開頭,老翁拿著原稿進行售賣時,沈與這本原稿結下了不解之緣。沈在閱讀原稿過程中,被小說的發展吸引,因此做出了在拍賣會上臨時撤銷原稿拍賣的決定。這本書不僅對他的工作產生了影響,也促成了他和魯絲的愛情。沈與魯絲的初次見面是在拍賣原稿時,之后他們的甜蜜時光也都與這本原稿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可以說, 《紅線》的前半部分主人公的命 運與原稿中人物的命運緊緊相連。此時作為物的原稿彰顯著其獨特的積極力量,推動著小說情節的發展。
物的消極力量主要體現在遺失的兩卷原稿對于小說人物命運的影響。小說的后半部分, 原稿的故事戛然而止。在確定原稿與沈、魯絲、韓三人的命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之后,他們 將原稿當作是他們命運的指南。此時,物的消極力量開始展現。小說不斷提及這本原稿對于 三人的重要性, 這就造成了一種閱讀效果:《紅 線》中的物處于一種神秘隱退的狀態。21世紀 物轉向興起, “面向物的本體論”進入研究者 的視野。“面向物的本體論是將思辨哲學的視 角轉向‘物,探討物的本體存在方式。”在《紅線》中,尼古拉斯·周思將原文穿插在小說之中,試圖給讀者呈現小說與《浮生六記》之間的特 殊關系。然而,尼古拉斯·周思插入的這些原 文,帶給讀者的都是外在的感受,使得讀者忽 略了這本書所代表的物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傳統的理論思潮都是將人放在主體的地位,而 哲學研究領域的物轉向,就是將物置于主體地 位,強調物對于人的影響。在《紅線》中, 《浮生六記》發揮了主體性作用,顛覆了傳統的物 人關系。小說中,沈的結局、魯絲的病、韓的 歸宿都是在按照《浮生六記》的走向發展的。作為物隱匿起來的《浮生六記》處于了主體地 位,它獨立于人物而存在,以一種上帝視角審 視著三人的未來走向。而在小說的最后,物幾 乎完全控制了沈和魯絲,在與物接觸的過程中,兩人成為失敗的一方,因此他們在物的控制下,為物服務,并徹底淪為了物的奴隸。
三、本體性
物具有“獨立于人類理性的本體性”。布朗認為物具有獨立于語言和文化的“物性”。唐偉勝教授也指出作者應該“運籌物與其語言文化表征之間的空隙來突顯物的真相以及人與物的關系”。
博古斯特強調“本體之物”具有無限隱退的特征且互不相關,提出了羅列是物本體書寫的最佳形式。小說《紅線》中,尼古拉斯·周思羅列了大量的文物,在這些看似毫無聯系的事物羅列背后,實際上蘊含著一個彼此獨立又相互影響的有機整體。這些文物敘說了自己的故事,展現了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基礎上尼古拉斯·周思所傳遞的以利益為根本的資本主義思想。小說中的文物都獨具特色,大都與故事的主題情節發展關系不大,但是這種看似毫無因果關系的羅列,讓物擺脫了作為符號或者敘事工具的地位。在書中,這些文物不具有實用性,也不是背景或者參照物,而是獨立的本體,展現出其生機與活力,吸引讀者關注這些文物本身。它們看似毫不相干,其實都是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尼古拉斯·周思沒有對其進行詳細描寫,盡管其背后的歷史含義和審美含義被金錢化和數字化,這些文物卻帶給了中國讀者文化認同以及外國讀者了解中國文化的機會,此時文物不再是單一的被作家控制的物,而是有機的具有本體性的整體。
《紅線》中, 《浮生六記》原稿同樣具有 獨立于人之外的物性,彰顯了其實在性,首先 表現在其超越歷史的文化功能之上。不同于物 的文化功能,這里的文化功能超越語言和文字。尼古拉斯·周思將《浮生六記》設定在現代, 使得這本書具有了超越時代的文化性。尼古拉 斯·周思大量引用《浮生六記》原文,使得這 本書在小說的情節發展中具有了相對的獨立性,看似這一原文是小說情節的真實寫照,實則是 在推動小說故事情節的發展,其超越文字的主 體性得以展現,其故事具有超越時間、種族、性別的文化意義。
實在性還體現在心物感應。小說中沈、魯 絲、韓三位主人公與《浮生六記》原稿融為一體,達到了“以物觀我”的狀態。沈與魯絲在閱讀《浮生六記》時,將自己當成了書中的主人公沈復 和蕓娘,形成了心物感應,將自己的命運與書 中主人公的命運等同,感受到物對于人物命運的影響。物我融合的狀態使得物的本體性得到有效發揮,人與物之間的界限被進一步消解。
小說中,物的本體性得到了有效發揮,然 而被消解的是中國人與物之間的界限,而以魯 絲為代表的西方人則是沖破了這一界限,重新 控制物。在小說的結尾,魯絲不辭而別,開始 過一種與蕓娘截然不同的生活,她雖然首先被 物所誘惑,但她也最先沖破原稿對其命運束縛。“故事還沒有完結。相互之間的愛讓我們又一次得以重生。憨園虔誠奉獻中蘊涵的勃勃生機 又讓我們回到塵世,成為一對凡夫俗子、癡男怨女。而我們仍為情所困,為什么?”魯絲理 解了輪回重生的意義,因此原稿不再控制她,她沖破了其本體性,重新成為物的統治者。而 韓的命運雖然也得到了改變,但是是她的丈夫 幫助她改變了命運, 因此韓并沒有完全沖破《浮生六記》。而男主人公沈, 仍然是和物融為一體,沒有沖破物與人之間的界限。因此,尼古拉斯·周 思的文字傳遞出一種西方的優越感,雖然故事 的地點人物都是來自中國,但是中國人仍然沒 有控制物,反而是西方人在不屬于自己的領地 重新支配了物。
四、結語
物的敘事功能在《紅線》中得到彰顯。這些物是中國文化的符號,然而在小說中其文化功能被弱化,并被物化成了商品。其主體性和本體性雖然得到了發揮,但是被物控制的是東方人,西方人始終具有沖破物的力量,以理性的視角冷眼旁觀中國人成為物的奴隸。小說中對物的描寫很精彩,但作家字里行間彰顯著西方的優越,因此,中國人應以文化傳承為己任,改變西方人的這種看法。
[作者簡介]崔璨,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