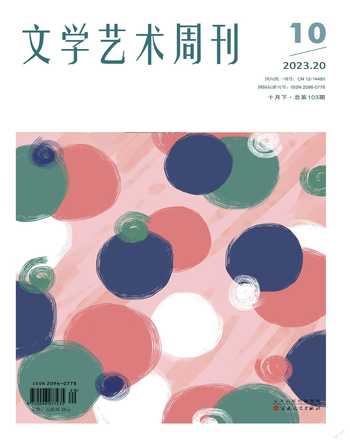論小說《采集螢火蟲》中個人和家族之根的追尋
美國赫蒙(Hmong)藝術家、作家麥超(MaiChao)在2015年出版了小說《采集螢火蟲》(GatheringFirefies),她希望通過這部作品來喚醒生活在美國的赫蒙人對過去的記憶,并緬懷那些為了后世子孫的幸福生活而甘于奉獻的先輩。該書真實地反映了赫蒙人多年的流散歷程與內心世界,再現了他們對故土的思念以及對尋根的渴望。小說的主人公卡夏(Kashia)是一個混血兒,他的母親帕英是赫蒙人,而父 親則是一個美國人。十三歲的卡夏因為一次契機訪談了自己的外祖父母吉魯和麥娘,逐漸對祖輩曾經生活過的故土產生了濃烈的好奇心與求知欲,了解到了戰爭時期家族的痛苦遭遇, 在人滿為患的難民營的潦倒生活,以及移民美國后為了生存而做出的艱苦努力。麥超在作品中采用了詩韻體小說的創作手法,使得整部作品既有小說攝人心魄的故事情節,又有詩歌婉轉柔和的優美旋律。作家對筆下人物追尋自我“身份”之根的過程主要通過人物的回憶進行
傳達。小說中的四個主要人物,即卡夏、帕英、麥娘和吉魯,交替述說著自己的故事,用不同的聲音給讀者呈現了他們各自的尋根之旅。這部虛構性的小說以卡夏對其家族的追根溯源為起點,將整個文本置于真實的歷史背景之中,以虛構的方式來探尋宏大家族和民族之根。
一、執著尋根的卡夏
作為一個混血兒,卡夏同時擁有著父母雙方的相貌和體格特征,從未對自己的血緣產生 過任何疑問,對他的祖先和民族更是一無所知。然而,這些都在“全國歷史日”那天發生了逆轉,一心只惦記著籃球比賽的卡夏必須按照老師的 要求完成一項意義非凡的課題。正在他一籌莫 展的時候,卡夏的母親提醒他可以對外祖父母 做一次訪談,她認為這對于年紀尚輕的卡夏來 說是一次很好的機會,他可以借此接觸并加深 自己對族群歷史和文化的了解。在母親帕英的指引下,卡夏踏上了一條尋根之路。而他身體里流淌著的赫蒙人血液也喚醒了他潛意識里對自我和家族之根的追尋。
卡夏從訪談一開始就時常夜不能寐,他不僅對自己從哪里來產生了好奇,還對祖輩進行了一系列的追問,而這一系列的追問在卡夏那里凝結成對自己家族淵源的追根溯源。卡夏的夢里總是填滿了外祖父母口中的各種故事。他時而腳踏泥土,同外祖母一起奔走在田間地頭忙于生計;時而手握槍支,同外祖父一起穿梭于崇山峻嶺并肩戰斗。卡夏在外祖父母的故事里聽到了很多以前從未經歷過的事情,并由此看到了赫蒙人的堅強與勇敢,以及他們在失去一切后為新生活做出的掙扎。卡夏想要為族人發聲,他希望所有本族先輩的故事在官方的歷史書上不被涂抹和遺忘。
卡夏一開始對族群的歷史是陌生和無知的,但在訪談結束后, 他最終醒悟而變得成熟。作為美國赫蒙人第二代移民的典型,卡夏對于族群歷史的發現和認識建立起了他們對于族群文化的自信。因此,卡夏對外祖父母的訪談與其說是他的一項課題,不如說是他努力尋找家族之根的一次精神之旅,借此得以全面地認識自己的族群,最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自我。
二、勇敢追夢的帕英
卡夏的母親帕英出生在難民營,并在幼年時期跟隨父母遷居美國,她尚在孩童時就認識到,父母是她生命中最為重要的人,他們給她幼小的心靈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帕英的父母打小就教導她要對人誠實、關愛和體貼,更重要的是,他們要求她永遠銘記自己身為赫蒙人的事實。雖然他們在她面前并不愿過多地提及往事,但帕英卻清楚地知道父母和祖輩們一直都在努力地回憶,回憶族群那段發源于中國的歷史。
帕英的第一個家就在難民營,她生命中的 前十年都是在那里度過的,而難民營也承載著 她童年時期最美好的回憶。這個占地約0.27平 方千米,為 12000名難民所建造的營地,最多 的時候容納了將近42000人。在那里,赫蒙人 難民是一群沒有身份、被連根拔起的人,官方 給每一戶難民家庭提供了一連串編號,而他們 也只能憑借這個編號來領取食物和援助。所以,營地里的每一個成年人都清楚地記得這個七位 數的編號,但人們根本就沒有選擇的余地。即便如此,帕英還是把難民營當作是自己的家園般懷念,因為這里的生活簡單而又寧靜。她每 天都會和母親還有女伴們坐在一起刺繡。盡管 長時間低頭彎腰的姿勢讓帕英的身體僵硬疼痛,但她依然樂意與母親坐在一起勞作。即便已經 過去了很多年,她依然清晰地記得自己當時刺 繡時的情景。
帕英和難民營中的苗族婦女通過本族傳統的技藝追憶曾經輝煌的民族文化,正體現了她們對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這不僅是她緬懷自己家族與民族的方式,同時也體現了她對自我之根的認同與肯定。
帕英來到美國后,開始接受美國主流文化,自我意識也逐漸萌芽。帕英是家中的長女,父母對她寄予了厚望,他們期待她能夠成為一名律師或是醫生,這樣才能在美國站穩腳跟,幫助整個家族擺脫貧困。帕英雖然同情并理解飽受主流文化歧視的移民父母,但她卻不愿被傳統的角色定義所束縛,不愿像母親或是其他本族婦女那樣茍且度日,在她看來,這些女人們是沒有自由和夢想的,也沒有任何機會去感悟和體驗這個世界。帕英熱愛藝術并渴望做一名畫家,她整天埋頭于書本,而不像其他苗族女孩一樣年紀輕輕就談婚論嫁。不僅如此,她還 愛上了一個美國人。帕英不愿意再做一個單純的赫蒙人,她要成為一個美國赫蒙人。面對帕英的一系列蛻變,她的父母心懷焦慮,而帕英的內心卻一如既往地堅定,她不會忘記自己身體里面流淌著的赫蒙人血液。她想要告訴父母,她并沒有瘋狂,而是心中懷揣著更大的理想和抱負。
帕英對自我之根的追尋體現了她對兩種文化的兼容,并汲取兩種文化的力量。正是通過帕英這樣一個善于進行跨文化對話的敘述者,卡夏才得以發現消隱在美國主流文化中赫蒙人先輩的“歷史記憶”。
三、父權制下的麥娘
赫蒙人女性,特別是母親,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關系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她們以自己堅忍的意志、博愛的母性情懷和吃苦耐勞的品質支撐起整個家庭甚至整個族群。她們不僅是生命的孕育者,更重要的還是生活的強者。卡夏的外祖母麥娘正是這樣一位赫蒙人傳統女性的代表。麥娘出生在老撾,她的故鄉坐落在老撾中北部的川壙省。在與卡夏的交談中,故土并非只是一個純粹的具體地理位置,而是由高山、河流、洞穴、村寨、樹木、森林等構成的文化符號,也是她寄托精神情感的地方。對于那片深藏著童年記憶和成長經驗的土地,麥娘的情感是真實而飽滿的,她始終想要回到那片生養她的土地。
麥娘在嫁給卡夏的外祖父之前是家中唯一的女兒,母親和幾個哥哥把她視作掌上明珠。童年時期的麥娘整天生活在無憂無慮之中,她對于未來的想法是天真和純粹的,父母希望她成年后要做一個賢妻良母,這些要求構成了她理想的全部。麥娘在對卡夏的講述中對親情的回憶與渴求也是她找尋自我之根的一種方式。麥娘遇到了自己的心上人,可她的美貌也被眾多苗族男子所覬覦,其中就包括卡夏的外祖父吉魯。慶典過后,麥娘被吉魯搶婚。
當她被帶到一位親戚家時才發現,他們早已為她準備好了婚禮。麥娘就這樣在自己年僅十三歲時被迫成了一個陌生男子的妻子。即便如此,麥娘也不能抗婚,因為她的出逃會令父母顏面掃地,他們將無法忍受周遭的譴責;她的名聲也會因此被毀掉,沒有任何男子會娶她為妻。所以,盡管麥娘需要父母的幫助,盡管這一切并非她的過錯,盡管她一直不停地哭泣、哀求和申述,她的父母都不可能帶她回家。
麥娘的婚后生活一開始并不幸福,她的公婆不喜歡她,把她當作外人對待。父母在她嫁人之后便不再喚她兒時的小名“麥娘”,而是稱呼她為“吉魯的老婆”。麥娘羨慕家里那些男孩們,他們不管身在何處,永遠都是父母的兒子。而像她一樣的女孩,總有一天會嫁作人婦而離開父母。婚后的麥娘變得沉默寡言,仿佛總有一堵隱形的墻將她和真正的親人分隔開來。她時常失聲痛哭,陷入深深的悲傷當中。對她來說,做女人是不幸的,原本應該相互體諒和包容的女性卻在彼此傾軋與詆毀對方。
無論是忍受著婚后丈夫家人的冷眼和排擠,還是在丈夫被迫加入戰爭后獨自支撐生活,忍 受婚姻的不幸,麥娘總在泰然接受人生的苦痛 和孤寂。她對自己的處境并非混沌無知,而是 主動選擇了堅守和包容。
這些都是她身上赫蒙人女性特有的性格特征,她們承受著苦難和寂寞,承受著一切,并包容了一切,她們可以為家族心甘情愿地奉獻自己的一生。
四、消極反抗的吉魯
在《采集螢火蟲》中,卡夏的外祖父吉魯是赫蒙人父輩移民的縮影,他們苦苦掙扎于美國的主流社會之中,且備受種族主義的歧視。小說中的吉魯來自山高林密的老撾叢林,那里的赫蒙人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是與世隔絕的,只有在一些比較特殊的場合,他們才會走到低地去購買食鹽或是和老撾人做生意。叢林的生 活是原始和艱苦的,然而,故土卻有著和諧的環境、靜謐的生活和純樸的族人。
老撾險惡的山水和艱苦的環境決定了赫蒙人特有的生存方式,而吉魯對種種舊有的生活 習慣的回憶也印證了他對“根”的追尋。然而,吉魯在對故土的回憶中也摻雜著痛苦的記憶。戰爭摧毀了他們原本安定的生活,吉魯被迫加入戰斗,并指揮著一支由十四名赫蒙人士兵組成的隊伍。險峻惡劣的自然環境磨煉了他堅韌的生存意志,也塑造了他剛強的性格。他們雖然平凡而卑微,但依然堅強地面對生活,帶領著家人躲過了空軍的轟炸和敵軍的種族清洗,跨過了波濤洶涌的湄公河,最終逃到了泰國的難民營。吉魯的骨子里有一種身為赫蒙人的驕傲,所以他的這段回憶中充滿了對赫蒙人勇敢正直的贊美,通過敘述赫蒙人的這些優良品行,來尋找令他驕傲的自我之根。
在難民營里,吉魯與朋友開了一家首飾作 坊,靠著制作銀飾來養活家人。他精湛的手藝 不僅讓他有了穩定的收入,還讓他得到了眾多 苗族女人的青睞,她們有時委身于他僅僅為了獲得一對免費的耳環或是手鐲。吉魯沉醉在這 樣的感覺之中,以至于他一度反對麥娘想要舉 家遷居美國的想法。移民美國后,吉魯開始面 對美國主流文化對于自己的沖擊,他的心態發 生了變化。在美國,吉魯一方面為了生計而不 得不從事美國勞動者所不愿意從事的低賤工作,另一方面還承受著種族歧視和語言障礙的巨大 壓力。
無論是在社會生活中還是個人的精神世界里,吉魯都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在家庭中的傳統地位也遭到了威脅, 曾經的“一家之主”和“最高權威”,現在連自己的長女帕英也“質疑和挑釁我(他)代表的一切”。所以,“家園”的缺失成為以吉魯為代表的赫蒙人父輩移民的集體記憶,他們也試圖通過回憶來擺脫孤獨感和漂浮感,為自己漂泊的靈魂和精神尋找最后的歸宿,實現精神上的溯源和回歸。
五、結語
小說《采集螢火蟲》以卡夏一家的家庭生活和家庭經歷為題材,描寫了發生在外祖父吉魯、外祖母麥娘、母親帕英和兒子卡夏三代人身上富有傳奇色彩的家族故事。作家麥超以四個人的不同視角講述了三代人各自的尋根之旅。作為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赫蒙人后裔,卡夏因為自己身上的另外一半美國血統而從未對自己的身份產生過疑問,直至在母親的引導下,他開始思索“我是誰”,并借著訪談外祖父母的機會倒溯了三代赫蒙人的身世。生命深處的文化基因賦予了卡夏某種方向感,激發了他想要了解外祖父母和母親所代表的族裔歷史和文化的渴望。于是,卡夏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母系文化——赫蒙人文化,并最終在外祖父母和母親的講述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園,找到了自己家族的歷史,更是血脈的歷史,用“講述是為了保存記憶”的方式深深地打動了讀者。
[作者簡介]王薇,女,漢族,江蘇揚州人,貴州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與文學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