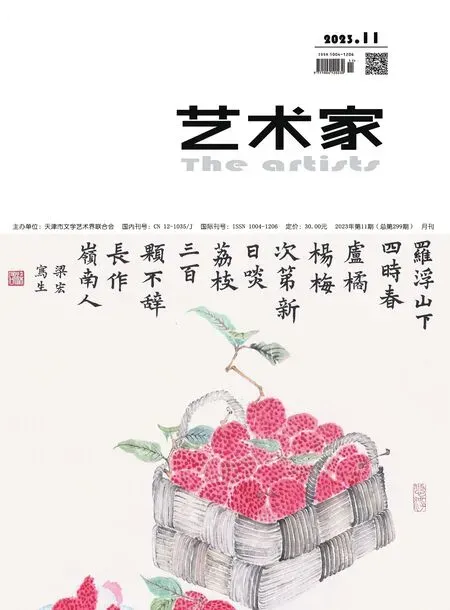回溯與重構:當代語境下的新山水影像創作
□王 歡 劉安經
山水,往往作為自然的代稱。“孔子在山水之中,有言:逝者如斯夫;老子在山水之中,有言:天長地久;莊子在山水之中,有言:無極之外復無極。”山水詩、山水游記、山水畫等正是他們“性好山水”的佐證。攝影藝術誕生之后,受繪畫的影響,一批藝術家從形式和內容上模仿繪畫,形成了“畫意攝影”“高藝術攝影”等流派。在中國,以郎靜山為代表的攝影師把攝影和山水畫進行拼貼、合成,形成山水畫意攝影。近年來,一批攝影藝術家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回溯,創作了一批具有中國特色的山水攝影作品,“新山水影像”也由此成為當代影像的一種現象。
一、新山水影像含義及特點
自20 世紀初至今,關于“新山水攝影”“新山水影像”的概念不斷被提及,但目前學界并沒有統一的定義。其中林蔭認為,所謂的“新山水”是利用數碼攝影等技術手段對中國傳統山水畫進行再創作的藝術表現形式。這種新山水影像是對山水的全新解讀,但他對新山水影像的分析主要局限在平面攝影領域。蘇海音認為,新山水攝影與錄像藝術是中國當代藝術“對話傳統”的一種方式,通過創作符合中國山水畫審美觀念的作品,以表達他們關注社會問題和個人主張的觀點。中國美術學院高世強教授認為,山水影像由廣義和狹義兩方面構成,廣義是指基于山水所產生的所有圖像作品,既包括上古巖畫、中西方各類山水和風景畫,也包括近代、當代的各類山水相關的攝影作品。狹義層面則特指由中國美術學院于2017 年所發起的近年來持續進行的山水活動影像和山水影像裝置創作實踐。他認為,山水精神、山水影像與山水行動是一個整體,山水精神是由山水文化所生發,卻是支持山水藝術創作這一文化實踐的發生土壤和內在驅動力。山水影像作品是在山水精神感召之下所形成的“文化產品”。而山水影像的具體創作過程、展演傳播和理論梳理與發表等,則構成了山水行動的部分。
綜上,筆者認為,新山水影像是指運用攝影與錄像技術對中國傳統山水文化進行的影像再創作,以表達他們關注當下社會問題和個人的藝術主張,從而建構中國山水影像審美的當代藝術作品。基于此,新山水影像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以山水文化為創作內容,而不僅僅局限于山水繪畫,新山水影像包括了山水詩歌、游記、繪畫、攝影等諸多形式。第二,新山水影像一般是兩種以上媒介的有機融合,其媒介形式主要有文字、圖片、繪畫、動態影像、聲音、裝置藝術等。第三,結合新技術進行創作,使用3D 成像技術、虛擬現實技術、人工技能技術等。第四,新山水影像的創作表達了攝影藝術家們對當下社會問題的關注、個人的獨特主張與生命體驗。
二、當代語境下的新山水影像實踐
(一)城市山水:虛擬景觀下的當代表達
中央美術學院姚璐教授的作品《新山水》系列,遠觀,青山綠水,云霧繚繞,猶如中國古代山水畫,但仔細觀看,可以看出畫面中的“山水”是由覆蓋著綠色防塵布的工地現場構成的。
作者通過圖片掃描、下載圖片、現場拍攝等方法收集素材,形成了古畫、防塵布等資料庫,并將它們重新組合。姚璐運用數字技術按照古代山水畫的樣式(扇面、卷軸和圓框等)將素材進行拼貼合成,形成一幅幅具有中國傳統范式的山水畫(如圖1)。姚璐自述:“我的作品是運用傳統繪畫的形式表現當代中國的面貌,中國在不斷的建設發展過程中,那些‘防塵布’覆蓋的土堆和垃圾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我希望我所做的一切都使世界形成良性轉變。我們必須保護環境……”姚璐的作品在帶有中國畫“外表”下蘊含著強烈的環保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圖1 姚璐 《新山水系列——富春山居圖》
藝術家邵文歡的作品一直在探索影像語言中的多樣性,在《浮玉》系列利用3D 及虛擬技術制作構建了一個“山水世界”。作品靈感來自文人筆下理想的世界,這些山石、水波、云霧等意象似乎原本只存在于中國傳統古畫中,作者采用了一種對照古畫寫生的方式完成了一種“無中生有”式的創作,試圖打破現實與虛幻、真實與虛假之間的模糊界限。藝術家在解讀“古畫”和再造“現實”中搭建了橋梁,將傳統山水畫元素運用當下技術進行轉譯,帶我們進入一個虛擬影像世界。后來邵文歡在此基礎上延伸出了名為《浮玉·早春圖》的動態作品,打破靜態效果,云霧繚繞、層層疊疊在山巒水面間迭出,不斷打破攝影影像的媒介桎梏,探索影像生成技術與觀念表達的互涉關系。
(二)景觀山水:人造景觀的異化呈現
曾翰的《酷山水》系列試圖以中國傳統山水畫加攝影的觀察和思考方式,來觀看和描繪當下中國的“山水”。“酷”字為英語COOL 的音譯,有時髦、新潮的意思,而漢語中,“酷”字又有殘酷之意。曾翰用《酷山水》系列來形容正在變化中的中國,通過對“山水”的重新審視,促使我們思考傳統東方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的結合究竟會出現怎樣的一種結果。他指出,自然的殘酷性是超出人類的預料的,在地震、海嘯、洪水、雪災、颶風等自然災害面前,人類的力量是渺小的。他的《三峽大壩2006》《貴州破山2006》《汶川震后2009》《滇池藍藻2007》《南嶺斷樹圖2008》系列作品既有著發展背后的反思,也有著對中國古人“天人合一”的至高理想被異化后的憂思。

圖2 火炎 《新桂林山水》
火炎《新桂林山水》(如圖2)以挑戰傳統桂林山水攝影的方式,為我們展示了異化后的桂林山水。山水中的主體,不是奇特的喀斯特地貌連綿的曲線和清澈的水,而是那些插入自然風景中的M 形拱門、雕塑、煙囪、纜車等黑白影像。他的畫面多采取平角度進行拍攝,使傳統中成為風景主體的山水成了這些異物的前景或背景。火炎的桂林山水攝影以耐心的踏勘,搜羅、捕捉了當地因各種人為因素而形成的“新”景觀。“這種‘新’的、也是‘奇’的變化,有著其符合當代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自身邏輯。基于發展至上的邏輯,出于自私的利益考量,人們對于自然景觀的頤指氣使的生硬、粗暴的干擾,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見怪不怪。”
除了曾翰、火炎外,關注實體山水景觀的還有張克純、王巖、趙智等,張克純從最初的《北流活活》到《山水之間》,再到《中國風景》,關注點已從黃河逐漸擴展到全中國的河流,在創作上也從單一靜態影像走向靜動態相結合,其單頻道錄像《跌水》記錄了河南武修云臺山落差達314 米的亞洲最高瀑布在枯水期依靠人工抽水來維持運轉的過程。張克純的山水影像,重新審視當下的山水景觀,并以此介入關注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
(三)記憶山水:虛實之間的情感獨白
盧彥鵬早年間學習傳統繪畫,他的代表作品《石頭的記憶》是他送給妻子和當時還未出生的寶寶的禮物。該作品由《破裂》《撞擊》《拖著石頭的嬰孩》三組作品構成,靈感源于妻子的一卷47cm×3000cm 的鉛筆素描紙本《石頭的記憶》。這是一次攝影與繪畫作品兩種媒介融合的影像實驗,創作這組作品時正值妻子懷孕,兩人作品的結合就像他們愛情的結晶一樣,結合后的作品似畫非畫,呈現出粗糲虛渺、若隱若現、煙霧繚繞、亦真亦幻的質感。作品以中國傳統山水影像為基底,是一種記憶與情感的寫作,在氤氳的云霧中進行現代和傳統的碰撞與融合,充斥著詩意的敘事,這種“詩意的顯影”正如他的情感自述:“和石頭一般,無聲無息。”
韓磊的《山水》,與盧彥鵬屬同一類別,以圓形加邊沿暗圈的形式,通過自己回憶起的老照片來構建私人記憶中的風景,作品充滿夢幻和懷舊感。楊怡以《沒·故里》(如圖3)為大家所熟知,他在創作系列作品時說:“2009 年,作為三峽工程最后一個移民的縣城。我的故鄉重慶開縣,有著1 800年歷史的老城,將永久沉入江水之下!36 年前,我出生在此地。”他的作品以水來反映空間改變和記憶的關系。這些超現實主義風格的照片展現了居民在被淹沒的小城里繼續著每天的生活,打牌、理發、聊天等,只是人物都帶著潛水面具,“水下之城”也成了攝影家的記憶與深藏于心田的眷戀。

圖3 楊怡 《沒·故里》
(四)跨媒介山水:綜合媒介的跨界表達
黃巖從1994 年開始在人臉上、身體上、畫布上繪制傳統宋代和元代的山水景觀。他為圖像轉移到人體畫布上的想象空間感到震撼。從此之后,人體山水畫成為現代語境中引發觀眾對古代文化與日常生活之關系的不斷思考和反省。將身體作為畫布承載山水,在黃色皮膚上畫下傳統山水影像,有種肉體和精神融合的意味。《人體山水》系列作品可以說是融合表演、行為、影像的實踐。
楊福東的《竹林七賢》(2003—2007)五部曲是新山水影像的重要電影代表作品,“竹林七賢”原指三國魏正始年間(240—249),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因常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焦作修武縣,可能為現今云臺山一帶)竹林之下喝酒、縱歌,肆意酣暢,世謂“七賢”,后與地名竹林合稱。楊福東的作品選擇以七個青年“隱居式”的生活來表述當代青年的迷茫和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在作品里,我們能看到他受到元代畫家趙雍《澄江寒月圖》的影響,將山石、樹木等主體放置在畫面的左下角,整個畫面布局帶有鮮明的中國傳統文人畫的特征(如圖4)。

圖4 楊福東 《竹林七賢之一》 單屏電影35mm黑白電影膠片轉DVD 2003年
“山水”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標志之一,為藝術家們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對傳統文化的回溯能讓我們尋找到根,因此,當代語境下的新山水影像創作,也被藝術家們賦予了新的形式與內容。在當代語境下,山水作為中國的一個文化符號,與西方的攝影術結合,更成為一個復雜的文化議題,在全球互通時代,它也成為西方了解中國文化精神和當代藝術的一個窗口。而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當代語境下的新山水影像必然會以新的形式出現,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再次回溯完成藝術家的精神構建和審美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