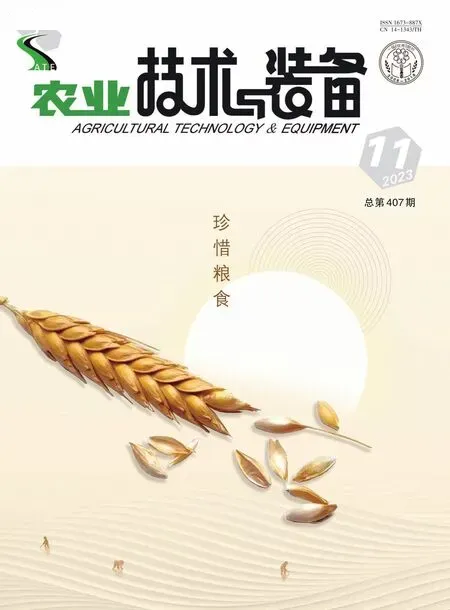麻城市耕地拋荒現狀的調查研究
肖齊圣,董曉麗,劉蘭軍,鄧宏林,王為峰,戴傳武
(麻城市農業農村局,湖北 麻城 438300)
1 麻城市耕地拋荒的基本情況
1.1 麻城市人口與耕地情況
麻城市位于湖北省東北部,大別山中段南麓,境內丘陵山區較多。2021 年末戶籍總人口113.96×104人,按性別分,男性人口60.61×104人,女性人口53.35×104人;年末常住人口87.35×104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9.82%,比2020 年提高1.13 個百分點[1]。全市版圖面積374 7 km2,耕地總面積52 386.667 hm2,人均耕地面積0.047 hm2,低于國際公認的人均耕地0.053 hm2警戒線,麻城具有版圖面積較大、人均耕地偏少的特點。
1.2 麻城市耕地拋荒基本情況
耕地拋荒指原有的耕地由于生產成本增加等原因而處于閑置狀態[2]。麻城耕地拋荒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3.7%,其中水田拋荒面積占水田總面積的2.7%,旱地拋荒面積占旱地總面積的5.6%,全市共有拋荒耕地1 963 hm2,具體情況見表1。從區域看,麻城山區、丘陵地域的拋荒較多,平原地域的拋荒較少,如杏花村(15.4%)、胡家樓子村(9.6%)等丘陵山區村的拋荒率明顯高于硯池村(0.4%)、鄢河村(1.3%)等平原村的拋荒率。總體看,麻城市耕地拋荒比例較高,且旱地拋荒率是水田拋荒率的1倍多。

表1 勞動力結構及耕地拋荒1 a以上情況表Tab.1 The structure of labor force and the situation of arable land abandoned more than 1a
2 麻城市耕地拋荒的原因
2.1 農業勞動力結構失衡導致拋荒
據調查,全市農業勞動力占農業人口的58.42%(見表1),常住農業人口為43.83×104人,實際農業勞動力為25.61×104人,勞力人均種植耕地面積為0.207 3 hm2,是人均耕地0.046 5 hm2的4.46倍。從務農勞力性別、年齡結構看,女性占比45.5%;50 歲以上的占比高達67.6%,40~50 歲的占比26.75%,40 歲以下的占比僅5.65%,具體情況見表2。這說明麻城勞力人均種植耕地面積較大,居家務農勞力的占比偏低且以女性和老年為主,青壯年勞力占比極低。失衡的勞動力結構導致了耕地拋荒。

表2 居家務農勞力年齡、性別情況表Tab.2 Age and sex of domestic farm labor
2.2 落后的農業基礎設施加重拋荒
2.1.1 “飛地”“插花地”、偏遠地等拋荒較多
因歷史歸屬、人口遷移等原因,部分農民的承包耕地不在居住地周邊。農戶承包“飛地”“插花地”、偏遠耕地的現象較多。有的農民住宅與承包耕地相隔極遠,有的農民承包地在偏遠難行的山區,有的農民的耕地交錯插花,或成為“飛地”。住宅與耕地在地理空間上的錯位現象,增加了耕種過程中行走、搬運、管理的時間,降低了農業生產效率,逼迫農民放棄類似耕地的種植,造成了偏遠、插花耕地和“飛地”的拋荒。
2.1.2 耕地灌溉設施的損毀造成了拋荒
丘陵山區地勢起伏較大,耕地及其配套的池塘、溝渠抗擊暴雨沖擊的能力極差,灌溉設施極易損毀。池塘泥沙淤積而庫容縮小,堤壩垮塌而喪失蓄水功能,水溝損毀而失去灌溉排洪功能等原因,導致耕地防洪抗旱功能減弱,收成不穩而拋荒。
2.1.3 農業機械化條件的缺乏擴大了拋荒
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責任制以來,依耕地優劣按面積平均分配,導致大田分小,耕地的零碎化、插花化加大,加上農民各自種植的作物類型和收獲季節不同又形成時空阻隔,導致特定耕地的機械作業受阻,耕地的零碎小塊化加大了機械的作業難度,降低了耕種效率;二是機耕道路建設落后,許多鄉村不具備修建機耕道路的經濟條件,例如丘陵山區耕地普遍起伏較大,里岸、外岸普遍較高,農機下田作業難度較大;三是適合丘陵山區使用的農業機械種類不多,少數農機的作業效果差,農村普遍缺乏技術熟練的年輕農機操作人員。
2.3 年輕人對土地感情的淡化加大了拋荒
目前農村的青壯年勞力大多常年在外務工,不愿意也不會耕種,不懂也不屑于務農,不再依附于土地,不再把務農當成謀生的手段,不像祖輩那樣對土地懷有深厚的情感,普遍不知道自家的承包地在哪里,總是極力勸告父母“少勞動、少耕種”“累壞了身體無人照顧,累病了住院治療的花費遠大于耕種的收益”。農村青年對土地情感的日益淡化加大了拋荒面積。
2.4 農業資金使用不均導致拋荒
近年來國家重視各類新型經營主體參與項目建設,而傳統小農戶則鮮有項目資金的支持。麻城市2023 年新型經營主體流轉耕地面積約8 000 hm2,占總耕面積的15.08%,卻享受了全市90%以上的種植業項目資金扶持。落實項目資金時的“愛富賺貧”,導致耕種面積占84.92%的傳統農戶種植條件變得越來越差而失去耕種積極性,而新型經營主體因有大量項目資金的支撐,反而滋生了縮小種植規模的欲望,最終導致傳統農戶越種越窮而放棄耕種。
2.5 種植效益偏低加速了拋荒
麻城市主要種植水稻、花生、油菜、棉花等農作物,農作物種植效益普遍較低。2022年,不計土地流轉費(見表3),農作物純收入最高的是中稻289.7 元/667 m2,其次為棉花196.2元/667 m2、第三為油菜177.6元/667 m2,最低的是花生僅83.2元/667 m2。麻城市城區砌匠的日工資為300 元,雜工的日工資為200元,兩項比較,種植667 m2水稻的純收低于砌匠的日工資,種植667 hm2棉花、油菜的純收低于雜工的日工資,種植花生667 m2的純收不足百元。農作物種植效益偏低的現實,迫使大量青壯年農民為了養家糊口只能外出務工,留下老人、婦女為主的勞力居家務農,種田虧本加速了耕地拋荒。

表3 麻城市2022年主要農作物種植效益情況表Tab.3 Planting benefits of major crops in Macheng City in 2022單位:元/667 m2
2.6 缺乏管理耕地拋荒的法律手段而放任拋荒
我國實行農業土地集體所有制,村民與村委會簽訂土地承包合同后,享有法律賦予30年不變的承包期限。《土地承包法》第5 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和非法限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承包土地的權利”。第14條規定:“尊重承包方的經營自主權,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進行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保護了承包者的經營自主權。農民種什么、種多少,村委會無權干涉。但《土地承包法》等法規卻沒有具體的法律條文規定由哪級基層組織負責對耕地拋荒進行管理和制止,沒有賦予基層組織管理耕地拋荒的法律手段。面對拋荒情況,基層組織既無權制止,不能收回,只能放任拋荒。
3 耕地拋荒產生的危害
3.1 減少農作物耕種面積,影響農產品供給安全
拋荒最直接的危害是減少了農作物種植面積和產量,影響農產品供給安全。麻城市有3.7%的耕地拋荒,就有1 963 hm2耕地不能種植農作物,形成17 289 t 稻谷、4 478 t 油菜籽的生產缺口,這將嚴重地危害全市糧油等農產品的供給安全,影響全市國民經濟發展和經濟社會穩定。
3.2 破壞了耕地土壤結構,加大了復耕種植難度
耕地拋荒后,短期內雜草叢生,長期后雜樹瘋長。樹木和雜草的根系對土壤耕作層的穿透破壞,會導致水田喪失保水功能而漏水,加大復耕時開墾、修復難度。據麻城市熊崗種養殖專業合作社開荒復耕的統計,拋荒1~2 a 雜草叢生的耕地,開荒復種要增加成本200 元/667 m2,拋荒2 a 后長出了小樹苗的耕地,開荒復種要增加成本400元/667 m2,拋荒多年樹木成林的耕地,開荒復種要增加成本900 元/667 m2。足見開荒復耕成本高,難度大。
3.3 影響周邊農戶種植意愿,造成“跟風”拋荒
一個地方出現拋荒而沒有及時采取措施,就會影響周邊農戶的種植積極性,當農戶看到他人拋荒未受到道德的譴責和法律的約束時,就在心中默認了拋荒的合理,任由自己的承包地荒蕪,影響更多的農戶放棄耕種而拋荒。
3.4 改變了毗鄰耕地農業生態環境,不利于農業可持續發展
從生態的角度講,耕地拋荒后難免雜草叢生,樹木成林,遮擋周邊田地的光照,輕則影響周邊耕地農作物生長,重則導致周邊耕地無法耕種。拋荒耕地植被的改變還會加重病蟲草害的發生,破壞耕作區農業生態平衡,降低周邊耕地農作物產量,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4 減少耕地拋荒的方法
4.1 優化農業勞動力結構
政府部門要制定政策優化農村勞動力結構,讓農業成為讓人羨慕的行業。一是要宣傳年青人返鄉創業務農光榮的思想,讓他們樹立扎根農村,振興鄉村的理想;二是要加大對年輕人農業技能的培訓力度,提高農民勞動素質和科技水平[3]。對青年人進行免費的農業實用技術培訓,使他們成為適應新時代的新型農民;三是要建立覆蓋全體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讓農民年老后能享受基本的養老福利待遇;四是要加強對老年農民的務農扶持,鼓勵他們既要向年青人傳授種植經驗技術,也要提高自身學習農業新技術的思想能力;五是要加大美麗鄉村建設力度,筑巢引鳳,讓農村有留住年輕人的魅力。只要農村保有適量的年輕人,農業勞動力結構就能得到優化,耕地拋荒就會受到遏制。
4.2 加大投入改進農業基礎設施
減少拋荒應該從3 個方面改善農業基礎設施:一是加強耕地道路建設,以方便農業機械進入田地作業和農民往返田園從事農事活動。二是提高耕地平整質量。主要是科學降低坡度,提高平整度,將小塊的零碎耕地拼成連片的大塊耕地。三是加強耕地的排灌系統、供電設施建設,確保農事用電方便優惠,促進耕種旱澇保收。四是做好“飛地”“插花地”、偏遠耕地的調換工作。更新相鄰村組、農戶的思想觀念,按便利、自愿、等值的原則調換其耕地所有權、承包權,實現耕種管理方便、勞動生產高效、拋荒面積減少的目標。
4.3 多措并舉提高農民的種植效益
第一,設定合理的種植效益期望。俗話說“十年難富莊稼漢”,說明種田不可能一夜暴富。要廣泛宣傳農業的戰略地位不可動搖,要讓農民明白農業效益不高、風險系數較大、戰略地位重要的道理。第二,創新土地集約化經營模式。強化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規模種植效益。第三,擴大農業保險的覆蓋面,增加農戶抵御農業風險的能力。要規范好雙方當事人權益,確保在農作物遭受自然災害時,保險公司賠付方便、及時、足額。第四,加強對農業生產資料銷售價格的管理,減輕農民的投資負擔。建立農產品價格保護機制,確保農民種植收入穩定增長。第五,建立高效專業的農機服務體系,擴大對傳統種植農戶的機械化服務范圍。促進體系收費公平,服務及時,擴大耕種面積,提高種植效益。
4.4 調整思路促進項目資金均衡使用
在設計農業項目實施方案時,要兼顧好各方利益,主管部門既要看到新型經營主體在規模種植上的閃光點,也要發揮傳統小農戶在減少耕地拋荒、擴大種植面積上的積極性。在丘陵山區,傳統小農戶依然是農業生產的主體,他們一直在默默為糧食安全作貢獻,他們用傳統的、落后的勞動支撐著山區農業的脊梁。均衡地使用項目資金有助于各方擴大耕種面積,減少拋荒。
4.5 完善法規賦予基層組織管理拋荒的權力
村委會只是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沒有管理耕地拋荒的法律依據和手段,基層組織既無法干預拋荒,也沒有從事復耕的義務,只能任由耕地拋荒存在。因此,要適應變化了的勞力結構、生產方式等實際情況,修改《土地承包法》有關條款,創新耕地資源連片承包、流轉方式,在保護農民土地承包權和經營自主權的同時,賦予村委會管理耕地,限制承包者惡意拋荒的權力,為減少拋荒,促進耕地種滿種足提供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