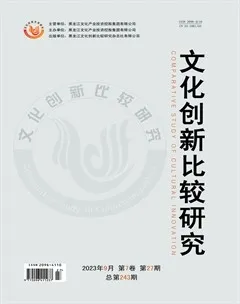甲骨文構造的概念隱喻理據研究
焦麗
(安陽工學院 外國語學院,河南安陽 455000)
中華文化的賡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字這一載體,漢字也是人類文明史上唯一沒有間斷的文字,自甲骨文時代至今已有3 000多年的歷史,為中華文化的歷史更替、推陳出新貢獻了巨大的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文化自信對國家發展和民族自強自立的重要性,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我們要堅定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動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因此,深入挖掘甲骨文背后的思維模式和文化因素有助于對中國文化的追根溯源,也是實現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徑。
甲骨文作為漢字最早期的形態,是華夏先民智慧的體現,與當時的歷史和文化因素息息相關,是人們與外部世界互動的產物。通過對甲骨文構字的分析可以窺見華夏先民的思維模式、社會文化特征,在此基礎上可以更好地推動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
概念隱喻是認知語言學的基本理論之一,探究人類思維方式和語言本體的關系,透過語言現象揭示外部現實,探討人類心智和語言的互動。概念隱喻理論與甲骨文的構造機制相契合,正如《說文解字》中所描述的漢字創造過程:華夏先民俯仰天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依類象形”而后“形聲相益”[1],因此,幾乎所有甲骨文字都有“據形索義”的特征[2]。由此可見,從概念隱喻角度來研究甲骨文的內在生成機制有助于深入理解文字背后的思維和文化因素,深化人們對甲骨文的認識。
1 概念隱喻理論
概念隱喻區別于傳統的隱喻,不是語言的修辭方式,而是人們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概念隱喻是認知語言學的重要理論,該學科是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一種語言研究范式,是認知學科和語言研究結合的產物,致力于對語言本質的探索和揭示,其研究對象是語言與人類認知的關系,Lakoff和Johnson的著作 《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標志著該學科的成立。經過30多年的發展,認知語言學已經形成“理論多元、方法多元和研究范圍廣闊的綜合研究范式”[3]。作為經典理論的概念隱喻也被廣泛應用于文字構造分析,通過共時與歷時研究來解釋語言的成因和發展規律。
文字的創造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如何用有限的符號來傳達無限的意義是必須面對的問題,即語言要具有一定的經濟性。概念隱喻是文字和語言形成的重要理據,通過概念隱喻,有限的語言符號可以表達無限的概念系統,同時語言符號也可以隨著歷史的變遷進行意義的增減。
概念隱喻指人們通過具體的、熟悉的、簡單的事物來認識抽象的、陌生的、復雜的概念。其認知機制是源域和目標域之間的映射,即已知或熟悉的概念向未知或不熟悉概念的映射,在這個過程中認知主體需要將源域和目標域進行并置和比較,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有時候還需要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從而加深對概念結構的認識[4]。在人類與外部世界互動過程中,人類的認知活動逐漸深入,推動了語言形式的創新和語言系統的完善,逐漸從簡單、具體、有限的語言形式發展到復雜、抽象、多樣的語言系統。
目前,概念隱喻的分類標準比較多樣,其中最經典的是Lakoff和Johnson的分類,即根據源域與目標域映射關系的不同,概念隱喻包括方位隱喻、結構隱喻、本體隱喻[5]。方位隱喻又稱作空間隱喻,指將空間位置映射到非空間概念上的隱喻范式,從而賦予后者一個空間方位。例如:“近幾年失業率上升了”中,上升的基本意思是物體空間從下向上的位置變化,但是通過向概念域“失業率”的隱喻映射,延伸出抽象的意義。人類的情感也可以通過具象的方位變化來表達,如“情緒高漲”“情緒低落”“心情處于低谷”等。結構隱喻是通過一個界限清晰、結構分明的概念去建構一個界限模糊或內部結構不完全的概念。例如:旅行和婚姻之間具有相似性,因此,兩個概念域之間的映射關系在語言中非常常見,“婚姻觸礁”“婚姻走到盡頭”等都是基于這一隱喻模式形成的。類似的表達還有“生活陷入泥潭”“生活失去方向”等,抽象的概念像是行駛的車輛或船只,而兩個概念域的部分結構則實現了關聯。本體隱喻也叫作實體隱喻,該類隱喻使人們可以把抽象的事件、活動和情感等視作有形的實體和物質。例如:在句子“謝謝您抽出寶貴時間接待我們”中,抽象的時間概念具有了實體界限和外形,類似于具有重要價值的產品。漢語詞匯中和語言相關的“話匣子”“畫外音”“言外之意”等都是將語言看作有界限之物,從而有里外之分。
基于概念隱喻這一認知機制,詞匯意義得以擴展,語法和篇章結構得以豐富。漢語中多義字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概念隱喻機制。例如:漢字“頭”是人體的一個重要部位,但是通過隱喻映射,延伸出豐富的內涵,包括物體的頂端(山頭、筆頭)、首領(頭目、頭領)、事情的起點(頭緒)、時間的前端(頭三天)、排序的前列(頭等、頭條)等。正是因為人類思維普遍的隱喻性,語言表達才能呈現豐富多樣的色彩,人類的思維和體驗成果才能夠有效地表達出來。隱喻思維使語言符號能夠承載更多的信息和情感,人們之間的交流更加準確、流暢。
2 甲骨文的概念隱喻特征
西方現代語言學體系主要以英語為研究對象,但是認知語言學仍然可以為漢字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因為其理論基礎和漢字的造字過程具有高度相似性[6]。該理論將語言看作語言社團與外部世界互動的結果,反映了語言社團對自身和萬物的認識。將認知語言學理論應用于研究甲骨文的形意關系有助于揭示其背后的認知機制。
概念隱喻是漢字構造的重要理據,正如Northrop Frye所言,漢字的解讀需要“隱喻性思維飛躍”[7]。目前,盡管以漢語為語料的相關研究并不多,隱喻在漢字構造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因為隱喻在生活中廣泛存在,“我們賴以思維和行動的一般概念系統從根本上講是隱喻式的”[8],語言也不例外。作為表意文字的甲骨文是基于相似性創造出來的,人們通過對客觀事物的臨摹來以此達彼,這符合概念隱喻的思維。例如:甲骨文“”(永)的字形似流動的河流,其常用義項為“永久”,即以空間中具體的、有形的、容易識別的概念河流來隱喻抽象的、無形的、難以表述的時間概念,意指時間具有河流的特征,奔流不息、永無止境。
甲骨文字形結構和字義之間存在對應關系,即象似性是其文字創造的重要依據,其中的單一結構字基本上都是象形文字,即對現實世界的臨摹,組合文字雖然含有較明顯的會意特征,但也是和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經驗密不可分的。甲骨文字“”的意思是木,很明顯是對客觀世界中樹木形象的臨摹,盡管該字形和實際的樹木不是完全對等的,進行了一定的抽象化,但在結構上仍然存在高度相似性,該字的結構具有典型的隱喻思維特征。
與上述案例相似的文字還有很多,尤其是一些與日常生活相關的詞匯,如 “”(火)、“”(水)、“”(山)、“”(小)、“”(戈)、“”(干)等。前 3 個字為自然現象,以簡單的線條來比擬自然存在事物的形態特征。“”字由一些微小的點組成,突出事物體積上的特征。“”為一種兵器,是對該兵器實際模樣的簡化。“”為一種工具,也是參照實際物體的形狀創造出來的。這些字體和現實世界是照應的,是對現實事物的隱喻。
指事字的字形和字義之間也具有典型的隱喻關系,例如:“ ”(一)、“”(二)等表示數量的文字通過簡單的筆畫描述了抽象的含義,用橫線的數量歸納了事物的本質屬性,隱喻所描述實體的數量。同樣,表示方位關系的空間詞匯“”(上)、“”(下)等通過對兩個實體相對位置的描述,反映物體的空間方位關系。
甲骨文的隱喻理據反映了華夏先民對客觀世界的體驗和認知成果,是基于當時的社會現實創造出來的。例如,甲骨文的“(買)”字由上部網狀結構和下部貝組合而成,其字面義為用網捕貝,意義延伸為買賣。在字形中缺少交易相關的場景或線索的前提下,人們通過隱喻映射也可以推斷出含義。因為貝是古代常用交易貨幣之一,撒網捕貝等捕魚相關的概念域映射到人類社會的商品交易中,通過具象的動作來指向抽象的概念,撒網捕貝的過程就像通過商品交易來獲得利潤,“網貝”即是“網利”,該字通過隱喻機制將具體的動作和抽象的概念聯系到一起。
3 甲骨文形意關系的隱喻類型和特征
甲骨文形意關系中的概念隱喻包括哪些類型?各個類型具有什么特征?本文以《甲骨文字典》等辭書為依據,參考Lakoff和Johnson對隱喻的分類,對甲骨文背后的隱喻機制進行分析和比較。
3.1 甲骨文字的隱喻類型
3.1.1 甲骨文中的方位隱喻
方位隱喻或空間隱喻和空間方位相關,較為容易理解和識別,賦予抽象事物或概念一個空間方位,繼而能夠根據方位變化來描述抽象意義。
3.1.2 甲骨文中的結構隱喻
結構隱喻是甲骨文構字的隱喻類型之一,用界限和結構清晰的概念來描述界限和結構模糊的抽象概念。甲骨文的“生”字為“”,其上半部分象征樹木,下半部分象征大地,意指樹木破土而出,象征生命力。該字的構造具有明顯的隱喻特征,人或動物的成長和樹木的生長過程類似,從幼小到粗壯再到衰老,因此兩個概念在結構上相似,通過樹木的生長過程可以隱喻人或動物的成長,故該字指生長過程或活著的狀態。
3.1.3 甲骨文中的本體隱喻
3.2 甲骨文字隱喻理據的特征
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出,甲骨文字構造涵蓋了隱喻的基本類型,很多字形不能用單一的隱喻思維模式來解釋,往往需要借助轉喻或者其他隱喻類型,例如,結構隱喻和本體隱喻,兩者具有重合的特征,很多時候相互交織、共同作用。
目前,甲骨文已經識別出的文字很多語義不詳,缺少確切的考證,很多字體用于地名或人名,通過隱喻得以延伸的語義比較有限。因此,從獨體字的構造上看,毋庸置疑,甲骨文是華夏先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加工成果,文字和現實具有高度的象似性,即“漢字的創造就是先民將心中的意象符號化的過程”[10]。但是,甲骨文通過隱喻映射向更加抽象概念域的意義延伸是相對有限的,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釋。一方面,甲骨文最初創造的目的是用于人類和超自然力量的溝通,即占卜,而普通百姓接觸和使用的機會不多,這也限制了文字的傳播和意義的創新;另一方面,文字是基于人的體驗而形成的,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決定了人們首先要實現的是簡單的意義表達和思想溝通,隨著華夏先民體驗的豐富和活動領域的拓展,語言和文字也得以不斷創新和豐富。
從隱喻類型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時間和空間概念域之間的映射在甲骨文字的隱喻機制中比較常見,抽象的時間概念可以通過空間方位和距離的變化來表達,如“”(永)、“”(翌或昱)等。由此可見,華夏先民對于抽象的時間概念已經形成較為成熟的表達系統。
4 結束語
目前,已有的甲骨文研究側重于字義的注釋,但是很少有文字根源的探索,在文字和文化的追根溯源上還有很大的空間。從甲骨文構字隱喻機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甲骨文的創造和隱喻思維息息相關,根據源域和目標域之間的映射關系可以更好地窺見文字背后的思維模式。通過甲骨文隱喻理據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其背后的思維和文化因素,并將這些理據融入詞典編纂、語料庫建設、文化研究等多個領域,以推動甲骨文的傳承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