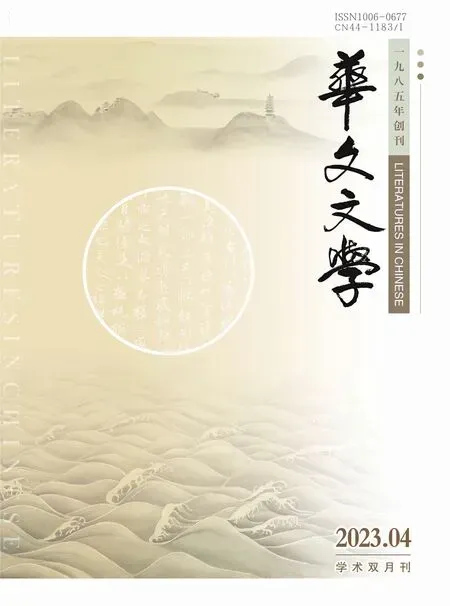“島上社”以外的1930 年代香港新文學
——以《新命》《晨光》為例
劉月悅
以1924 年的《小說星期刊》為前驅,香港開始出現新文學萌芽。而后相繼出現的大報副刊,如《大光報·大光文藝》《循環日報·燈塔》《大同日報·大同世界》《南強日報·華岳》《南華日報·南華文藝》《天南日報·明燈》等,標志著香港新文學的滋長。及至1928 年,呂倫、張吻冰創辦新文學期刊《伴侶》,1929 年1 月,《伴侶》停刊后,其主要作者創辦了“島上社”。1929 年9 月,“島上”成員之一的張吻冰主編了同人性質的刊物《鐵馬》,只出一期即停刊,而后,島上社諸人又于1930 年4 月1 日創辦《島上》,共發行兩期(第二期實際出版于1931 年10 月)。無論是從創作者的數量、刊物的生存境況還是接受者來看,1938 年之前,新文學在香港實在是小眾而邊緣的。但是,在這為數不多的“鼓吹新文學”的“趨新者”中,以今日可見資料來看,“島上社”同仁以及相關人士已經算是這“邊緣”中的“主流”,與“島上”諸人沒有太多瓜葛的新文學創作者們,則更是邊緣中的邊緣,《新命》《晨光》同仁便可看作是他們的代表。
一、《新命》《晨光》的創刊
《新命》創刊于1932 年1 月,現僅存創刊號,全刊共69 頁(含封面、封底及廣告),督印人廖亞子,編輯張輝,由新命雜志社發行,永信印務公司承印,每冊定價大洋一角,原定五星期出版一次。
在《新命》創刊的1932 年前后,新文學在香港的生存環境已多有論者論及。陳學然在《五四在香港》一書中援引許多時人時論,說明“在英中二國舊士的舊勢力相互結合下,導致新文化不能興起的局面,縱有趨新者鼓吹新文學,又或者是有個別人士有文學覺醒,但始終難以引起社會回響”,“盡管時人在1929 年已呼喊新文學,但直至胡適南來的一段時間里,香港的文學仍然是死水一潭,進展不大”①。
對于創刊的動機,《新命》在《卷頭語》中有所表述:
“雞既鳴矣,東方始白”,響了五下的晨鐘,似告訴我們的黑夜已過,晨早來臨了。有意無意的白璧無瑕底太陽,似給眾生們長進的開始機會呦!
趁著這如氈似錦的陽光,在出世第一天的——新命——啼聲,如波紋式似的聲浪,掀動到社會里去。此薄如紙而且無色彩的一片,能撼動觀眾們的耳鼓和眼睛,留點印象的,或者得到同情和效力。我們惟有絞盡腦汁,以求貫徹主張,而酬報閱者與本刊相見的雅意。
我們感覺到痛苦,是在惡劣環境底下支配著的,我們所以不斷地拼命,不是想在惡環境里茍延殘喘的,仍望出惡環境外死灰復燃,為人生爭回點志氣!不論環境怎樣,我們惟有秉著萬劫不復的精神,和熱情的勇氣,沖出重圍。從事整理陣容,站在創作之鄉,求到做人和解決人生的觀念!這點熱望和志愿,是與讀者互相砥礪的。②
從《卷頭語》看,《新命》的創刊與《鐵馬》《島上》有相類似的動機,即在香港比較貧瘠的新文學土壤上,力爭開出花來。這大約是當時香港新文學倡導者和創作者們的共識。《鐵馬》在《Adieu——并說幾句關于本刊的話》中寫道:“在香港,慢些說及文藝罷,真沒有東西可以說是適合我們這一群的脾胃的,有許多應該是很藝術的地方都統統的給流俗化了……香港有了算盤是因為做生意,香港有了筆墨也是因了做生意的!……然而我們試看看,香港的文壇現在是什么情狀的呢?如果香港還有那所謂文壇的話。我們不得不自尋我們的出路了!”③創刊于1931 年的新文學刊物《激流》在《卷頭語》中寫道:“沙漠在這里!沒有花,沒有詩,沒有光,沒有熱,沒有藝術……任它是平沙無垠的大戈壁,我們都要發一個最微的小愿,在這沙漠中培植一朵鮮艷的薇薔!……水會把海變成陸地,當然亦會把沙漠變了平原。”④
不過,與“島上社”相比,《新命》的“撼動觀眾們的耳鼓和眼睛”,似乎更有啟迪民智的愿望和野心。這一點,可與《晨光》相互印證。《晨光》出版于1932 年8 月,編輯與《新命》同為張輝,也由永信印務公司出版,同樣計劃每五周出一期,督印人為伍蕘,現僅存創刊號,共12 頁。《晨光》創刊號共發文9 篇,其中5 篇與《新命》的撰稿人重合,兩幅插畫中,也有一副與《新命》畫師同為黃璧林,兩本刊物的關系密切可見一斑。
《晨光》在其《前奏曲》中寫道“太陽在沉沒中就把大地一切的……都感受黑暗的籠罩著了!而社會上一般人的環境處處都感受黑暗的痛苦!但經過相當時期的沉寂和黑暗后,到底那個美滿的陽光產生出來,給我們在黑暗途中的掙扎者得到光明;同時在被窩發夢囈的人們,可以打破他們的迷夢!受晨光的庇蔭,努力地向前途掙扎去。呵晨光,晨光,美麗底晨光喲!你驚醒了社會一切的迷夢者,和幫助一切的黑暗中掙扎者啊!”⑤可以看到,“晨光”的“驚醒”,與“新命”的“啼聲”,同樣代表了作者穿透黑暗與寂靜、“求到做人和解決人生的觀念”的啟蒙的熱望。
二、《新命》《晨光》同仁對新文學的認識
《新命》《晨光》同仁與“島上社”的這一區別,或許與他們對大陸新文學的不同認識有關。有論者提及,“由《鐵馬》的整體風貌看來,香港文藝青年并不直接言及‘革命’,更接近早期創造社的主張:承認主體憑直覺追求‘生存’和‘唯美’的合理性。”⑥而《新命》對大陸新文學的認識,則體現在刊物緊隨卷頭語之后的《中國新文學的鳥瞰》一文中,作者是張輝。這篇“鳥瞰”,意在介紹大陸新文學的整體面貌,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介紹了新文化運動及新文學的開端,“為了時的代(原文如此,疑為錯排,應為時代的)進化,語言和文字都同時改造刷新起來;胡適等提倡的國語文學,就是對語言和文字改進的著想。而思想方面亦隨著這新文化運動而另開一個新的途徑,于是新文學的旗幟便展開了,昔日鴛鴦蝴蝶派的文學便消滅了;這不能不算是新文學在目前已占了一個相當的位置”。⑦第二部分簡略記述了新文學的發展歷程,不但涉及了一些重要作家、社團、刊物,還涉及了幾場重要的筆墨官司,如錢杏邨等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對魯迅、茅盾等人的批評;左翼文藝與民族主義文藝的斗爭等,也提及了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作家方面,他重點介紹的有魯迅和郭沫若,他稱魯迅“只要一提及五四的時代文學,大概誰也不會把魯迅忘掉吧。我們首先憶及的就應該是這一位英勇的、不斷和當時封建勢力作戰的魯迅”。他稱贊郭沫若:“郭沫若的《女神》《橄欖》等,更為一般青年所愛讀;他的小說是很富有詩意,描寫個人生活,迸出人生的火花!他的漂流卻可憐,而他的作品的成功也在這點表現出來了!”除此之外,還對幾位重要的新文學作家各有一句“考語”:“葉紹鈞有《隔膜》《火災》《稻香人》,而《倪煥之》描寫教育界的情況,也是很好不過的。葉靈鳳的小品文很不錯。汪敬之的《耶穌的吩咐》確是難得之作。其他如張資平,郁達夫,都是一時杰出的人物。老舍(即舒慶春)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的三本東西,用諷刺的文筆去描寫,自成一個風格,這一位是可算近日新文壇的怪杰,鄭振鐸自發表《且漫談所謂國學》一文,但不久他又拿起筆桿和國學算賬了。他對于國學的研究是很不錯(按:許多人說他濫談國學,往往錯誤,這也許是的。但他對于中西文學的探討精神,在目前中國文壇上也不失為一位勇敢而有貢獻的。)但他的創作手腕卻不見得怎樣的好了。女作家如冰心,丁玲,廬隱,及新進的陳學昭,在文壇上也有相當的貢獻。”社團流派方面,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等是他介紹的重點。
從這一部分來看,作者對大陸的新文學的大致脈絡還是比較熟悉的,但是對于具體的作家、社團,似乎認識就比較籠統而一知半解,甚至不乏不甚了了之處。比如他說,“能站在文壇上兀立不動的,還是彼一般文藝家目為‘布爾喬亞派文學’的小說月報的一流人物吧!”眾所周知,《小說月報》與文學研究會關系密切,自1920 年沈雁冰接任《小說月報》主編開始,它的主編始終是由文學研究會的重要成員擔任。改革之后的第十二、十三卷由沈雁冰主編,之后由鄭振鐸任主編,1927 年6 月至1928 年底鄭振鐸旅歐期間,第十八卷第六期至第十九卷第十二期,由葉紹鈞代編。1930 年底葉圣陶和鄭振鐸脫離商務印書館,改由原來的助編徐調孚(也是文學研究會成員)繼編,直至1932 年第二十三卷第一期終刊。而且《小說月報》從第十三卷第一期便開始連續刊登了“本刊文稿擔任者”的名單,有周作人、魯迅、瞿世英、葉紹鈞、耿濟之、蔣百里、郭夢良、許地山、郭紹虞、冰心、孫伏園、鄭振鐸、明心(沈雁冰化名)、廬隱、王統照等17 人。除魯迅外,皆是文學研究會的中堅作家。作者將“小說月報一流人物”稱為“布爾喬亞派文學”且稱其“兀立不動”,但是卻同時稱文學研究會“鴉雀無聲”,理解上似乎有點誤差。再如作者對創造社的介紹,他寫道:“創造社在當時已得了一般青年熱烈的歡迎,他的革命思想有與社會國家共同一條路跑,聲勢烜赫!”顯然,作者在這里指的是后期創造社發生轉變以后的文學主張,而對創造社前期“為藝術而藝術”,重視文學的美感作用的文學主張,他似乎并不清楚。此外,他提到“自國民革命軍到長江的時候,他們竟拋了筆桿而從事實際的革命工作,一時如火如荼的新文壇,又沉寂下去了”。這里所說的“國民革命軍到長江的時候”,應當是指北伐。北伐前后,恰恰是創造社由前期的“唯美”“純文學”轉向后期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到無產階級文藝運動之中的時期,而他所提到的“拋了筆桿而從事實際的革命工作”,意指郭沫若、成仿吾等創造社主要成員在廣東直接、間接地參加了國民革命運動。但是,這不但并非如張輝所說,從此讓創造社乃至新文學沉寂下去,反而恰恰是創造社由前期轉向后期主張的重要契機。香港與大陸山水阻隔,作者似乎并沒有搞清楚創造社前后期的轉變與“五四”退潮以后的社會文化氛圍帶來的作家的無可作為的焦灼、失卻路標的苦悶和理想幻滅的痛楚、創造社核心成員參加北伐這幾件事情之間的關系,因而做出了“文壇現在的確是暮氣沉沉了”的悲觀判斷。
最后一部分,作者對翻譯作品的情況做了一個簡單的概述,談及魯迅和梁實秋的“硬譯”之爭,并感嘆說:“照現在的情形看來,譯品倒比創作銷路得多,如《西線無戰事》《屠場》《波士頓》等也是近人所喜看的,這不能不令我們中國新文壇的作家叫苦!”
總體來看,作者對大陸新文學的了解并不十分深入,但以當時香港的文化界狀況來看,也不好求全責備。另外,整篇文章作者盡力保持了盡量公允的介紹式的語氣,但還是可以看出一些傾向,作者對(他所理解的)創造社更加富有感情,更認同后期創造社“與社會國家共同一條路跑”的創作觀念,也更欣賞創造社的作家作品,這尤其體現在全文的最后一句話中。他總結道:“現在的創作能有效力而令青年們愛讀的,是郭沫若、魯迅、張資平、蔣光慈(已死)、葉靈鳳這幾位”。在他所開出的這份名單里,除魯迅外,全部是創造社的作家。而對于作品,他更偏好能如《倪煥之》《二馬》等能直接反應現實生活、直面問題的作品,這樣的傾向,也多少影響了《新命》《晨光》的面貌。
三、《新命》《晨光》的內容與創作
《新命》不分欄目,但按內容和體裁實際上可以分為四個板塊,楊國雄在其《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中將之分為論著、小說、新詩、雜文四個部分。⑧論著部分實際就是比較長的議論性質的文章,包括張輝的《中國新文學的鳥瞰》、帆風的《小說的索隱》、丈八的《學生應怎樣去修養》和廖亞子的《是愛的問題——是性欲與愛的較量》。小說有帆風的《逃走》和旅寒的《是失戀者的悲哀》,連載有黃飛然的《癡戀的姑娘》和志輝的《月明之夜(上)》。新詩有旅寒的《給新命刊諸朋友》、潔冰的《倘使我是一位詩人》、黃定球的《給我的親愛的青年戰士》和《給劉姑娘》及阿堅的《回憶》。
雜文每篇大約有300—800 字,包括秋水伊人的《戀愛與義務》《戀愛新話》和《嗚呼西裝》,漢遜的《談“肉感”》,真我的《萬物之靈》和《莫名其妙的“妙”》,阿銘的《學問與職業》,怪客的《摩登青年與璇宮艷史》和《心血來潮》,慕儂的《兩種野外生活》,巷伯的《政治家的離合》,狂濤的《談摩登》和《飯后隨筆》,薔薇的《全盤召頂》,麗娜的《關于Talkie》,及弱柳的《百年內之獸世界》。插圖部份有黃璧林的《少女美》和《黃粱夢甜》。
從總體面貌上看,這些作品并沒有體現出特別明確的風格特征,但是大體上有一個總體的傾向,就是關注具體的社會人生的問題。如張輝的詩歌《我們的新命》所言,“我們為著新時代的追求,新人生的吶喊,完成我們的新生命。”⑨
長篇論文中,《中國新文學的鳥瞰》《小說的索引》談的是文學以內的問題以外,《青年應該怎樣去修養》談的是青年怎樣成長為能夠承擔社會重任的人才,并給出了養成高尚的人格、愛惜光陰、養成強健的體魄、戒除不良的嗜好、戒除虛榮心、打破消極態度、團結精神七條具體的建議。《是愛的問題——是性欲與愛的較量》,以相當長的篇幅,探討性與愛的關系,最后得出結論“肉欲不是愛是性的問題,是任情之結果!愛不僅是有條件的結合,同時要愛的出于誠,要愛的在時間性的配合,而彼此理解得到最后的幸福。”⑩
雜文則針對性更強且更富于批判性,《百年內的獸世界》《嗚呼西裝》《談摩登》《摩登青年與璇宮密史》針對的是青年對西方新鮮事物的態度問題;《談肉感》《戀愛與義務》《戀愛新話》,討論的是戀愛的話題,大半與歐風之下新的戀愛觀有關,從這兩個主題來看,刊物對于西方事物和觀念的態度比較偏于保守;《關于Talkie》表達了對普羅大眾的同情;《全盤昭頂》《兩種野外生活》討論的是抵抗日本經濟侵略的問題,《政治家的離合》批判當局;《學問與職業》批判自滿自足的國民性,同情無法接受教育的民眾;《萬物之靈》則批判人的統治欲。
小說共有四篇,《癡戀的姑娘》標明是長篇小說,從小說的開頭來看,尚看不出故事的走向。《失戀者的悲哀》講的是一位“失戀”了的姑娘,全篇在寫姑娘“失戀”后的心情,以及周圍人的反應,到結尾處作者才講明,姑娘并不是遇上了負心漢,而是他的心上人做了革命軍而在戰場上犧牲了。《月明之夜》和《逃走》是現實問題的指向性非常明確的兩篇作品,《月明之夜》以一對新婚燕爾的夫婦的睡前聊天為背景,討論了民族進取精神的問題,《逃走》討論的是女仆的婚嫁自由問題。
《晨光》只有12 頁,刊發雜文5 篇,計有張輝的《關于內戰的消息》、嘉勉的《關于日本的新聞報業》、薔薇的《婦女日常生活之一頁》和《屁的功用和價值》、王壺冰的《由漢奸聯想到兒童教育》、弱柳的《失敗以后》、真我的《三只角子兩條鼻子》;詩歌三首,《死與生》《死神》《父親的死》,作者均為確靈;小說一篇,為海外逃叟的《回顧》。與《新命》相比,《晨光》最顯著的特點在于更有時代感,出現了抗日相關的內容,在《關于內戰的消息》《關于日本的新聞報業》《從漢奸聯想到兒童教育》都有所涉及。
《新命》《晨光》的這一群作者,對于香港新文學來說十分“眼生”,除了在這兩本刊物以外,在其它地方幾乎未見發表,從創作水平來看,更是差強人意。鄭樹森等人曾評論20 年代末、30年代的香港新文學作品,散文是“模擬五四階段”的作品,“這時期香港的散文在文字、文體技巧上的摸索,較為乏善可陳。”“小說似乎比散文更墮后,連五四時直面社會的作品都及不上。”[11]即便在總體水平如此的香港新文學創作中,《新命》《晨光》的作品也明顯地更為不成熟,與《島上》《鐵馬》等刊物發表的作品尚有差距。
以小說為例。《逃走》是《新命》刊載篇幅最長的一篇小說,應當是本期《新命》中的“重頭戲”。小說的背景設定在一個小家庭,男主人名叫蕭仲平,小說中介紹他是一名商人,結婚剛兩年,跟女主人飛鳳感情很好。飛鳳的陪嫁女仆秋花已年滿18,有些“恨嫁”,總是跟飛鳳吵嘴。因為要嫁人,秋花某天夜里從家中逃走,男仆阿四發現后告訴蕭仲平夫婦,二人急忙尋找,卻不料秋花為此去法庭狀告了蕭仲平。《逃走》看起來講述的是五四小說中常見的反封建的故事,但是整個小說卻存在著許多含糊不清之處。首先蕭仲平夫婦二人,并未見苛待仆人,對秋花和阿四,態度都頗為和藹,在發現秋花“恨嫁”之后,二人也并未阻撓,而確實在商量,就在這籌備期間,秋花逃走了,到了法庭上,審判官的態度也模棱兩可:
(審判官):你控告蕭仲平做甚?
(秋花):我告他不嫁我!
(審判官):為什么你要嫁?
(秋花):因為我無人依靠,男婚女嫁,理所當然!
(審判官):仲平有苛待你沒有?
(秋花):沒有。
(審判官):她(原文如此)夫人呢?
(秋花):沒有。
(審判官):現在你控告他是因為他不嫁你,是么?
(秋花):是!是!
……
那審判官只問了這兩句,于是又對著秋花說:“你控告你主人是不應該的;他一定會嫁你,你以后別要這樣干。”
秋花連忙點點頭。
判官又向仲平說:“你須知男大思婚,女大思嫁的嗎,你不能阻礙她,然而這些是家庭小事,不必弄到上警署來。你底侍婢想嫁了,就快些嫁了她,現在這種小事情,不成案子,快帶她回去。可是你不可苛待她。”
仲平便帶著秋花回家去了。
不但審判官的態度令人生疑,秋花在庭上的表現也全然不像跟主人家有多大矛盾,只是諾諾應聲。而仲平領秋花回家之后,叫來了秋花的母親陳大嬸,仲平、飛鳳、陳大嬸三人的對話則更讓人疑惑。這篇小說明顯有模仿五四初期“問題小說”的痕跡,但作者的立場卻十分曖昧,似乎是同情以秋花為代表的女仆,沒有人身自由,法律不為其主張,父母也不為他們做主,但是在人物塑造上,卻又把仲平夫婦塑造的十分和善甚至有點軟弱可欺。整個故事的起承轉合都顯得比較生硬,小說的結尾也很突兀。
《月明之夜》和刊載于《晨光》的《回顧》也是類似的情況。《月明之夜》寫一對新婚夫妻的閨房談話,從一起賞月的你儂我儂,忽而轉向對社會、民族的大問題的探討,轉折十分突然,不過因為標明了是“上”,不知道后面的故事會如何發展。《晨光》刊載的唯一一篇小說《回顧》寫一對革命者戀人,但人物形象的塑造頗為模糊,主旨不甚明確。總而言之,以小說創作而言,可以感到《新命》的作者還是比較生澀的,他們著力在模仿五四時期小說直面現實人生的寫作態度,和“問題小說”的寫作方法,但因為技法的不熟練,或者本身自己觀點也并不十分鮮明,致使小說呈現出比較生硬、模糊的面貌。
前面提到過,香港新文學在當時的香港,處境頗為艱難,這批作家,又并非新文學作者中的佼佼者,創作不夠成熟,原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相比于小說的創作,雜文因為短小精悍,情況則要好得多,無論是語言還是行文的邏輯,也許談不上如何精彩,但也稱得上觀點鮮明,又因為其中的不少篇目針對的是當時的某種風氣和現象,亦可作時代的記錄和觀察。
四、生存處境與刊物地位
新文學刊物在香港的生存處境是十分艱難的。與《鐵馬》等新文學刊物相比,《新命》的有趣之處是他有不少廣告,內頁廣告有8 頁共10 則,包括香煙、藥物、鞋靴等,還有一則封二廣告,為國民商業儲蓄銀行有限公司所刊。但即便如此,《新命》也只存在了一期。對于此,《新命》諸人也很有自覺,他們自稱“慘淡經營”,在《晨光》的《編后》一文中則說得更為清楚:“真慚愧,這會編成這樣一本東西且又是五星期刊,在香江的出版界情形以往及現在都是曇花一現,尤其是新文化的刊物;環境這樣的惡劣,想來大眾也起了同情之感啦!朋友!辦刊物去賺錢比較登天堂還難些吧!”[12]確實,同時期的香港新文學刊物,只出版或者只留存了一二期的不在少數,除《新命》《晨光》以及前面提到的《鐵馬》《島上》外,還有《激流》《白貓現代文集》《小齒輪》《春雷半月刊》等。
在彼時香港的新文學刊物中,《新命》不是如何出挑或有特色的,論者論及時,往往也是一筆帶過。《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中寫道:“一九三二年一月計有《新命》,八月又有《晨光》,都是由張輝主編,內容都包括小說、詩歌、散文及論文四種,是差不多的風格,差不多的作者,這些作者,名字都是陌生的,可見有更多的青年,已嘗試加入新文學的行列”[13]。楊建民在一篇論文中提到“盡管文學刊物相繼停刊,但文學青年的活動并沒有停止,他們千方百計創辦新的刊物,為新文學搖旗吶喊。從1931 年至1937 年之間,又有《激流》《春雷》《今日詩歌》《新命》《晨光》《時代風景》《時代筆語》《文藝漫話》《南風》等刊物在香港問世。”[14]雖然創作未見得多么優秀成熟,但對于“釘子之多,不勝枚舉”[15],“缺少了容許他們生存的社會環境”[16]的香港新文學而言,每一份刊物的創辦,都是“荷著鋤,肩著劍,建筑未來的花園”[17]的努力和勇氣。
①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與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 年版,第191 頁。
②亞子:《卷頭語》,《新命》,1932 年1 月。
③編者:《Adieu 告別之辭:并說幾句關于本刊的話》,《鐵馬》,1929 年9 月。
④魯蓀:《卷頭語》,《激流》,1931 年6 月。
⑤蕘:《前奏曲》,《晨光》,1936 年8 月。
⑥王芳:《并非只有“時差”的香港新文學:〈鐵馬〉綜論》,《華文文學》2022 年第3 期。
⑦張輝:《中國新文學的鳥瞰》,《新命》。
⑧楊國雄:《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 年版,第271 頁。
⑨[17]張輝:《我們的新命》,《新命》。
⑩廖亞子:《是愛的問題,是性欲與愛的較量》,《新命》。
[11]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1927-1941)》,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 年版,第14、15 頁。
[12]張輝:《編后》,《晨光》。
[13]黃康顯:《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香港:秋海棠出版社1996 年版,第30 頁。
[14]楊建民:《香港文學的起點和新文學的興起》,《文學評論》1997 年第4 期。
[15]侶倫:《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5 年版,第33 頁。
[16]魯迅:《致章延謙》,《魯迅書信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 年版,第129-13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