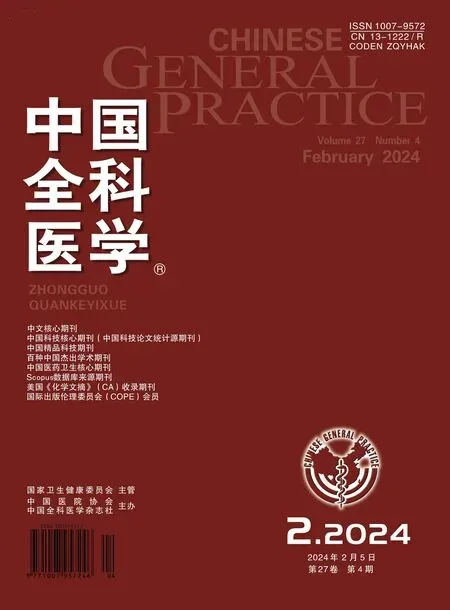醫學中的全科醫學
——從《柳葉刀》200 年歷史看現代醫學中的全科醫學發展(三):哈特論醫學本科教育對基本醫療的影響
楊輝,澳大利亞 Monash 大學
朱利安·哈特醫生(Julian Tudor Hart,1927—2018 年)是一名研究者、高血壓專家、流行病學家、科學家、作家、政治評論員和社會倡導者,但在其內心深處,其始終是一名全科執業醫師。哈特醫生在英國南威爾士的一個煤礦村的全科診所工作,為大約2 100 人提供全科服務30 年,哈特醫生的研究和反思都是基于在這家診所的實踐開展的。哈特醫生將其與患者的關系描述為:最初是面對面,最終是肩并肩。
哈特醫生是“醫學社會主義者”,其是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和社會主義的積極倡導者,提出的“反向服務定律”(inverse care law)于1971 年在《柳葉刀》發表[HART J T.The inverse care law[J].Lancet,1971,1(7696):405-412.DOI:10.1016/S0140-6736(71)92410-X.],該文被很多學者反復引用,使哈特醫生成為健康公平和初級保健最有名的倡導者。哈特醫生以全科醫生的睿智和溝通技巧詮釋了“反向服務定律”:光腳的人,顯然是最需要鞋的人。哈特醫生認為,追求利潤可能會阻礙醫學的理性進步,其著作《衛生服務的政治經濟學:臨床的視角》根據NHS 實施以來的臨床經驗描繪了NHS 從19 世紀起源于工人互助協會的發展和演進歷程,探索如何將NHS 重組為面向所有人的人道服務,而不是為少數人提供“有利可圖”的服務,并推動醫學發展、影響整個社會文明。哈特醫生抨擊了醫療服務商業化,根據自身對醫療保健經濟的實際經驗提出了對NHS 的經濟分析[HART J 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care:a clinical perspective[M].Bristol:The Policy Press,2006.]。
哈特醫生的診所是英國第一個研究型全科診所,該診所承接過很多醫學委員會的研究項目。哈特醫生與Richard Doll(英國知名流行病學專家,第一個證明吸煙與肺癌和心血管疾病發生風險存在關系的專家之一)、Archie Cochrane(現代臨床流行病學和循證醫學之父)一起參與了很多流行病學研究。
哈特醫生是第一位給所有患者測量和記錄血壓的醫生,其為所有患者提供無條件和個性化的連續性服務,并發表了連續觀察25 年的研究結果,證實了測量血壓可以將過早死亡的風險降低30%[HART J T.Huypertensioncommunity control of high blood pressure[M].3rd ed.Florida:CRC Press,1993.]。
哈特醫生做過全科審計,是自己的“驗尸官”,其從診所保存了20 多年的1 800 份患者醫療記錄中找出500 份死亡病歷,發現45%的死亡包括了可避免的死因,其中59%歸因于患者、20%歸因于全科醫生、9%歸因于醫院、17%歸因于其他[HART J T,HUMPHREYS C.Be your own coroner:an audit of 500 consecutive deaths in a general practice[J].Br Med J(Clin Res Ed),1987,294(6576):871-874.DOI:10.1136/bmj.294.6576.871.]。哈特醫生認為,由全科醫生對社區人群的疾病和死亡進行評判性分析,有助于識別出醫療服務組織和團隊需要改進的地方,以及社區人群需要改變的生活行為方式。哈特醫生以犀利的筆觸評判社會、醫學界及全科領域,同時也毫不猶豫地評判自己,其是一位敢于發表自己所在診所500 份死亡病歷的醫生。哈特醫生對全科醫學的思想和研究處于前沿,并且篤信全科團隊和全科審計是改善全科醫療相關健康結果的關鍵。
哈特醫生是位高產的研究者和思想者,發表過350 多篇同行評議文章和多本著作,僅在《柳葉刀》就發表了20 篇文章。下面選讀的是其針對醫學本科教育與全科醫學發展的討論性文章[HART J T.Relation of primary care to undergraduate education[J].Lancet,1973,302(7832):778-781.DOI:10.1016/S0140-6736(73)91049-0.]。受限于篇幅,譯文有刪節。
幾乎每位到醫院接受專科服務的患者,在來醫院前都經過了全科醫生的先期梳理和管理,全科醫生通常只把4%~10%的患者轉介給醫院。從這個意義來看,初級保健是國家衛生服務的基礎。顯然,醫學本科生教學應該包括初級保健。如果情況并非如此,就應該去尋找發生這種異象的原因。
◆過去
1950 年,柯林斯在英國NHS 實施后6 個月,對初級保健服務的真實和丑陋狀況做了描述,其描繪了覆蓋人口最多的基本醫療服務最糟糕的方面:“在工業區開業的全科醫生的工作環境非常糟糕,以至于醫生的個人能力顯得微乎其微,對工業區全科醫生最基本的資質要求是具備快速處理患者的能力。質量最差的全科醫學服務,存在于最大量和最迫切需要高質量醫療服務的地方……全科診所條件的糟糕程度,足以在瞬間把一位好醫生變成壞醫生。”
教學醫院本可以為扭轉這種局面做出重大貢獻。巴伯代表當時其他進步的全科醫生發聲,認為“學生要認識到大學所教的與實際所見之間的差異,樹立起與劣質醫學斗爭的態度,準備好為踐行好的醫學而去做出改變”。這是(或應該是)每一所醫學院的首要職能:讓新一代醫生做好準備,與服務中的不公正和劣行做斗爭,支持醫生在批評中無所畏懼、準確無誤、契合實際,并通過為醫生提供比以往更好的技術培訓來減少無理的醫學行為。醫學生們肯定接受了很不錯的醫學技能培訓,不過除了那些知名的省級或蘇格蘭的醫學院外,學生們還沒有嘗試過這項任務,更別說要完成任務了。
醫學院并沒有刻意地傳授那些自鳴得意的、功利主義的、與患者利益無關的價值觀,其只是自然流露。現實中,醫生的個人抱負和職業滿足感與患者需要存在交叉,但兩者并不重疊。只不過大多數醫學院假設醫生的取向就是患者的需要。要想讓好的初級保健得以生存,需要明確定義其任務,發展其畢業后教育,提高其研究水平,而這些不能指望倫敦那些高級的醫學院去實現。醫學院的態度是:醫學教育是徹頭徹尾地提供當代最好的醫學臨床知識和技術,讓學生畢業后在真實世界里盡可能地使用這些先進知識和技能。
大多數能力較強的畢業生會尋找那些可以獲取、發揮和保留這些先進知識和技能的臨床領域。在這些領域里,遵從權威比熱衷改革更重要。學生們要去高級的醫院,而不是去縣醫院、集鎮的貧民救濟醫院、如同居民家的全科診所,也不是去工業區里的醫療室。
在發展完善的卓越中心里制造技術創新是一種慣常做法,而且也不那么費力,然而這些創新通常不意味著能推動社會變革。而在一個貧困的、人力資源不足的、設備陳舊不堪的工業區周邊建立起基本的醫療服務,那才意味著真正的挑戰。面臨這種挑戰的是在工業區里的全科醫生,然而可惜的是,這些醫生通常是醫院多重選拔后裁減下來的。每次醫院的人才選拔,都會把更有能力和更雄心勃勃的醫生輸送到更有名望的、更可能順利發展的醫學專業中去。
這就是“反向服務定律”的主要原因:高質量醫療服務的可得性,通常與所服務人群的醫療需要呈反比(最需要的人反而得到的最少)。
莫蘭勛爵在1958 年表示:“所有杰出者(極少數除外)的目標都是成為人上人。這里只有一個梯子,有些人從梯子上掉下來。你認為爬到梯子頂端的人與掉下來的人是一樣的嗎?”科文于1963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在75 名隨機抽取的執業全科醫師中,19 名一直以全科醫學為目標,39 名曾嘗試成為顧問醫生但未能成功,于是轉到全科,17 名在沒有任何明確目標的情況下漂流到或被迫進入全科領域。但對70 名顧問醫生的調查發現,有61 名醫生在學生時期或剛獲得行醫資格后就瞄準了自己的專科方向。
教學醫院顧問醫生教授的內容是其所知曉的知識,與其擅長的執業技能一致。顧問醫生的大多數學生后來也自然成為該領域的專家。然而大多數全科醫學/基本醫療醫生是這個選擇過程的“副產品”,全科醫生的招募過程向任何有行醫注冊的醫生開放,無須專門的畢業后培訓。在現在的教師們看來,全科醫生往好了說是“殘余行醫者”,往壞了說是“不良行醫者”。有什么可能的理由讓老師來傳授殘留或不良的醫學呢?
◆理想與現實
托德的報告顯示,23.5%的畢業生對全科醫學有偏好。對1 971 名曼徹斯特和謝菲爾德醫學院畢業生的調查結果顯示,32.2%的畢業生有全科偏好。
期望全科職業培訓學員的質量是比較高的,不應該是“被挑剩下的”醫生。英國全科醫生學會(RCGP)的理想是:初級保健是一個獨立的重要專業,是在各種衛生技術人員支持下的集體醫學實踐,是在專門建造的醫療場所中工作的醫學專業。過去10 年對全科醫學的研究結果令人印象深刻:RCGP 圖書館1960—1970年的出版物清單長達181 頁,其中還不包括治療試驗和大量的小型操作研究。隨著越來越多的學生承諾要承擔社會責任,招募更多、更好的醫生進入全科領域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
不過,這種對初級保健的新意識形態,遠遠超出了許多其他倡導者的社會理解。真正的社會變革不是靠優秀文章帶來的,也不是靠建立大量小型卓越中心帶來的,即便是在最需要基本醫療的工業區建立優秀的示范點。真正的社會變革取決于是否喚起了從變革中受益的社會群體。當然,任何變革都會遭到那些將受到損失的社會群體的反對。出版物及英雄式的個人榜樣產生的影響,完全取決于在多大程度上協助了對社會群體的動員。從目前初級保健的現實及社會支持力量的來源、方向和規模來看,情況是不樂觀的。
歐文和杰弗里斯于1969 年對全科診所進行的抽樣研究表明,90%沒有心電圖機,32%沒有窺陰器,65%沒有血紅蛋白檢測儀,22%沒有小型手術設備,15%沒有尿液分析設備,16%沒有秘書室,31%沒有打字機,62%沒有錄音機,29%沒有供患者使用的衛生間。
在81%的合伙式全科診所中,全科醫生接診的是預約列表中的所有患者,而非優先接診選擇自己看診的患者,也沒有診所內轉診,這意味著全科診所存在缺乏服務個性化和連續性的問題。僅22%的合伙式全科診所每周召開一次會議來討論案例或問題,30%的診所在財務上存在不平等。10%的醫生沒有或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獲得醫院診斷服務。這些質量問題顯示出南北梯度:英國中部和南部的年輕醫生會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全科醫學資源最差的地區與健康問題最嚴重的地區是一致的。可滿足未來全科教學需要(有完善組織和足夠空間)的診所是很少的。年輕全科醫生想去現代化的、有足夠診療工具和衛生人力的診所工作。某些全科診所已經做了明顯的改進,如果要滿足年輕醫生的職業期望,必須把這種改進迅速擴展到其他診所。
1968—1971 年,英國增加的全科醫生中,有83%出生在英國境外。工業區的醫院和全科診所的人員配備更依賴來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年輕醫生。愛爾蘭和蘇格蘭也曾是這樣的情況。這些“輸入醫生”原本的職業目標是醫院專科,其中大多數人有外科經驗,但這并不適合初級保健。“輸入醫生”中很少有人延長畢業后培訓時間去接受全科醫學的學徒式職業培訓。因此,總是難以找到兩全的服務方案。
全科醫學“新人”們一直在糾結中,即面對現實是否要改變自己的醫學初心。當然,醫院專家也會遇到類似的糾結。然而,最大的需要及最好的創新機會仍是在初級保健層面。
◆醫學本科教育的機會
明顯而迫切的變革需求,以及已制定但未應用的初級保健意識形態,使醫學本科中的全科醫學教學變得如此重要。這不是把初級保健當成一個專業進行“碎片化”教學,不是在無菌條件下給學生注射一點安全劑量的全科醫學,也不是通過宣傳全科形象來改善大學招生狀況,這是一個利用獨特機會向所有專業、所有學生拓展全科醫學教育的問題。
從認識和糾正錯誤中學到的東西,與從成功中學到的東西一樣多(甚至更多)。醫學教育不僅是對卓越和先進的觀察和模仿;醫學生要學到的,是在未來復雜的工作和真實世界中去使用處理復雜問題的技能。這是初級保健在教學情境中的普遍價值。其中有三項具體任務,在大學本科階段要比任何醫院都教得更好。
第一個任務是糾正社會無知。目前只有很小部分醫學生對未來所服務患者的個人和工作生活特點有切實了解。很多學生不能理智地反對社會不公正,即便是有些感悟,也僅是剛剛開始。如果要讓學生堅持“以患者為導向”的動機,而非“以疾病為導向”的動機,學生們就必須學會用復雜、具體、詳細的方式識別出那些粗俗、刻板的印象。對患者的人道承諾和理想,必須轉化為對現實生活中的人的有效關心。目前的醫學專業等級制度將基本醫學、老年醫學和精神病學置于底層,這表明醫學教育很難嘗試這種轉變,更不用說實現了。然而只有經過本科階段的社會再教育,才能進行部分的和可控的改變,這對于當好醫生來說是絕對必要的。初級保健教師可以給學生傳授以往不曾共享的共同社會經驗;學習真正尊重患者,而非形式上的禮貌;在很多方面,醫生必須服從患者;患者必須成為醫療服務的主體,而非客體。醫學的這一部分必須重建,而最好的重建者是權威程度較低的醫生,其與患者密切接觸,具有最低限度的技術和社會裝甲。
第二個任務是應對不確定性。全科醫生與醫院共同分擔責任和技術復雜性,能幫助全科醫學避免大多數醫療服務中真正的不精確性和不確定性。當代醫學生很少接觸從未見過的病例,大多數病例至少見過2 次,通常是10 次或12 次。醫學生把自己見到的問題歸納整理成可以用醫學術語理解的疾病,這些臨床材料是醫院教學過程中最原始的數據,實際上是初級保健提出問題的10%的精華,是所有癥狀的三分之一。顧問醫生在醫院里接診患者的時候,絕大部分有一定程度的“事后諸葛亮”行為,顧問醫生很少意識到這些患者的癥狀已經被整理過,除非有一天到全科診所來觀察,否則其不能理解患者去醫院之前的癥狀的混亂程度。重要的是,學生不僅應該了解每位醫生都有局限性,還應該知道整個醫學知識存在局限性,存在大量不精確的領域,存在因信息貧乏而做的臨床猜測。醫學生還必須學會保持頭腦清醒,堅持建立適合其工作水平的完整而精確的數據庫。處理醫學的不精確性和不確定性是一項日益復雜和負責任的技能,應該在整個本科期間以有組織的方式在真實情況下進行教授。這不應該像過去那樣通過個人反復嘗試而習得,也不應該以患者為代價來學習。初級保健并不是傳授應對不確定性策略的唯一層次,如果要培養出對自己工作有更平衡和現實看法的醫生,學習解決不確定性必須成為本科生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個任務是改變世界。學習初級保健最好的一點,是要告訴學生:不僅要學會解釋醫學服務這個世界,而且要能去改變這個世界。新建的全科醫學部門的任務,不僅是為已經很優秀的醫療團隊輸入新的年輕伙伴,更是向最需要基本醫療服務的地方輸送新的和更好的醫療服務開拓者。在那些最需要的地方工作的人,可能是莫蘭勛爵所說的從“爭高”的梯子上掉下來的人,在醫學階層中疲憊不堪的人、對踏上新臺階缺乏信心的人。新建的全科醫學系應該培養學生的“有紀律的憤怒”(有理的、克制的、真誠的)。這種憤怒不是針對某個人,而是針對阻礙向患者提供有效醫學服務的態度和情況。如果年輕醫生沒有這種“有紀律的憤怒”,那么其只能在仁慈的醫學中順從地成長。當然,沒有紀律的憤怒只是咒罵而已,是不可取的。
◆不久的未來
未來幾年很難樂觀。大多數現有的全科醫學部門似乎忙于證明自己的臨床信譽,無暇在培養真正的新型醫生上進行冒險,盡管從長遠來看,更大膽的方法可能會讓其他專業勉強接受全科醫學。
還有一個風險,某些全科醫學部門的場所、人員和設備配備并不適合全科醫學教育,所營造出來的教學情境如同“高級醫學”那樣的不真實,不能反映出全科醫學的患者特征和診治過程。當然,建立卓越中心(即樣板教學和優秀服務)的理念是必要的,在工業區繁忙和陳舊、簡陋的診所不可能進行全科教學。另外,不能因為工業區診所的問題太多,就認為“這里不能培養出好醫生”,而放棄把這里作為教學場所。
堅決反對初級保健教學的時代已成為過去。隨著時間的推移,即便是倫敦的知名大學也會設立全科醫學部或社區醫學部,姑且把基于人群的流行病學研究或操作層面研究算作全科或社區醫學。現在的挑戰,并非大學是否設立了全科醫學部,而是其如何看待教育目標。杰弗里·維克斯爵士將公共衛生史描述為“不斷重新定義不可接受事物的記錄”。醫學教育也應該重新定義不可接受的事物,幫助新一代拒絕這一代所傾向的事物,并以偉大和簡潔的方式表達新一代的拒絕。全科醫學系可成為這種新型醫學教育的創新者。
感悟——
我在哈特醫生文章的字里行間都看到了“公平”二字。哈特醫生于1971 年在《柳葉刀》發表了長篇文章《反向服務定律》,兩年后發表了上述文章。首先感受到的是哈特醫生對當時醫學教育模式的憂慮,其認為醫學院不應僅向學生傳授醫學知識和技能,更要讓其準備好去促進和踐行醫學的改革和進步。哈特認為醫生的取向不一定就是患者的需要,醫學階層對權威的追求遠大于對改革的渴望。迎接醫學改革的通常是弱勢社區的全科醫生,但其大多是醫生中的弱勢群體,是爬梯過程中“掉下來”的醫生,這也是“反向服務定律”的重要成因之一。哈特醫生認為,發展全科研究和設立全科示范診所是不夠的,真正的社會變革取決于是否喚起了從變革中受益的利益相關者,全科醫學“新人”們一直糾結的是面對現實是否要改變自己的醫學初心。
哈特醫生提出本科教育在推動全科發展上可做具有獨特優勢的三件事情。第一,應在鞏固社會良知的基礎上糾正社會無知;理解社會、理解患者;把醫學理想轉化為對患者的有效關懷;必須讓患者成為醫療服務的主體,而非客體。第二,學會應對醫學的不精確性和不確定性,從醫院專家與全科醫生的分擔服務著手,在認識各學科和整個醫學知識局限性的基礎上,對復雜和不確定性共擔責任。第三,教會學生不僅能解釋醫學世界,而且要有能力改變醫學世界。哈特醫生提到的“有紀律的憤怒”是建設性的評判和思辨,醫學進步是把不可接受的事情變成可能的過程。
哈特醫生所描述的情形距離現在的英國基本醫療服務和醫學教育已經很遠,然而其所期望的全科醫學教育的理想仍沒有完全實現。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到哈特醫生的批判精神,同時也可以看到其對問題的解決方案。在評判和揭示問題的同時,也給出下一步有針對性和可行性的做法和建議,這是負責的學者風范。
哈特的文字是鋒利的。不過在筆者看來,哈特醫生是最有情懷的全科醫生,是理想主義者,熱衷于推動全科醫學發展和社會進步。哈特醫生對大學的期望,是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培養學生評判和擔責的能力,這對于促進全科醫學學科發展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大學是培養學生評判思維能力的地方,評判思維是一項核心學術技能,是質疑和反思自己獲得的知識和信息,這對于學生完成學業、研究者開展研究、醫生進行臨床實踐都是一項非常寶貴的技能。醫生隨著年資的增長會成為教育者,那么,從哈特的文字中一定會得到有益的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