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與“非虛構”的爭鋒
——關于“中國非虛構詩學”研究的思考
□ 邱 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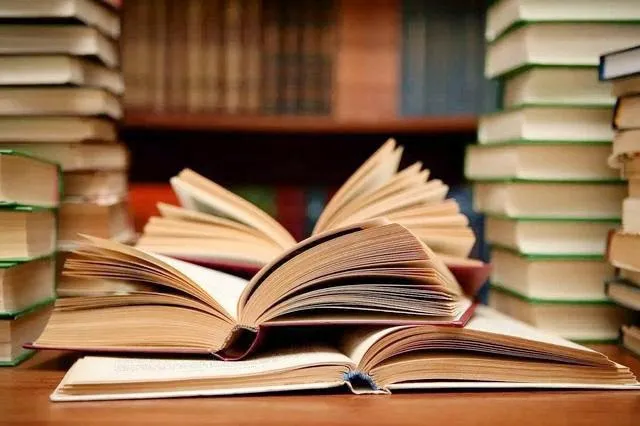
“中國非虛構詩學”研究是當今中國比較詩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從“中國非虛構詩學”的研究中可以延伸出另一維度的問題:當下,要怎樣合理地進行中西詩學的對話?要如何保持中國詩學的主體地位?中國比較詩學應如何更好地發展?本文從比較詩學角度出發,對“中國非虛構詩學”的相關漢學家及其詩學思想進行簡要介紹,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中國非虛構詩學”這個提法的積極意義和局限性,進而進行一些對中國比較詩學的發展走向和中西跨文化對話等話題的思考。
中國詩學的“非虛構”傳統是以宇文所安、余寶琳、吉川幸次郎等為代表的海外漢學家所推崇的一種理論假設,他們認為中國古代詩歌和西方詩歌的區別主要體現為:西方詩歌擅長用隱喻、模仿和虛構;中國詩歌則擅長寫實,在詩歌中真實地表現作者的內心世界和他們所處的外部世界,即在中國傳統詩歌中,不存在西方詩歌中的“模仿”和“隱喻”。
一方面,“中國非虛構詩學”的提法為中西比較詩學研究拓寬了發展空間,這個概念并非起源于中國本土,也不是中國本土化的理論成果,而是由漢學家提出并在海外逐漸興起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國文化及文學受到了更多海外學者的關注,使中國文化和文學在世界舞臺上大放異彩。同時,海外漢學家從西方角度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和思考,也為中國本土學者提供了一種新的可供參考的研究視域。但從另一方面講,“中國非虛構詩學”這個概念畢竟是一批受到正統的西方文化影響的漢學家提出的,或多或少地都會受到西方學術話語的影響,所以在對中國詩學進行分析時,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文化、文學的誤讀或者“強制闡釋”現象。
一、“中國非虛構詩學”的源頭與流變
“中國非虛構詩學”是二十世紀產生于海外漢學界的一種理論假設,其代表學者大多有著中西雙重文化學術背景,在對中國古代詩歌進行研究時,受到了西方“虛構詩學”話語體系的闡發,提出了“中國非虛構詩學”的理論主張。為了對這一重要理論進行更深入的分析,首先需要對“中國非虛構詩學”的源頭與流變情況加以闡述。

吉川幸次郎作品封面
“中國非虛構詩學”這一特殊提法較早由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提出,他曾于二十世紀上半葉前往北京大學留學,在中國文化和文學研究方面有著頗高的學術造詣。在吉川幸次郎的著作《中國詩史》(1986)中,他鮮明地指出了中國傳統文學缺乏“虛構性”的特點:“以特異人物的特異生活為素材、從而必須從事虛構的敘事詩的傳統在這個國家里是缺乏的。”①吉川幸次郎還認為,中國文學的表現形式是“遠離日常”的,其素材并不總是來源于日常生活經歷,即文學語言是“遠離日常”的特殊語言,他認為直到文學革命時期,中國文學才完全由口語寫作。經由此,吉川幸次郎提出了中國文學史的兩大特征:重視非虛構素材和語言表現技巧。他認為這種重視日常生活的原則同中國哲學高度關注現實世界有著密切的關聯:“正如中國人被稱為現實的國民那樣,他們認為,感知到的現實是客觀實在的,只有在現實世界中,而不是在空想中,才有陶冶人情操的美好事物。這種哲學決定了將平凡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現的事作為素材的文學,并以此作為其文學傳統。”②其次,吉川幸次郎認為這種傳統還和文學家的非職業化有關,因為中國古代并不存在專門以文學創作為職業的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往往集文學、政治、哲學于一身,因此,“跟其他地域的任何文學相比,(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恐都更加細心周到地凝視著并非由于虛構的、人間的事實,更加精細地挖掘著日常事實所含有的意義”。③吉川幸次郎還肯定了中國文學的“非虛構”傾向:“像中國這種只注目于現實世界,只注目于人而抑制對神的關心的文學,在其他文明領域確實是無與倫比的。”④吉川幸次郎作為早期“中國非虛構詩學”命題的開拓者之一,雖然對這個理論并未展開多角度、深度的論述,但是他對“中國非虛構詩學”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對中國古代文學的觀照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后來“中國非虛構詩學”命題的建構,并對其他海外漢學家的后續研究產生了啟發。
宇文所安是將“中國非虛構詩學”理論發揚光大的學者。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宇文所安出版了《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征象》(1985),這是一部細致研究中國詩學的著作,在對中國和西方詩歌的比較研究中,他為更加全面地討論中國文學提供了五條建議,第一條建議便圍繞中國傳統詩歌的“非虛構”性質展開:“在中國文學傳統中,詩歌通常被假定為非虛構;它的表述被當作絕對真實。意義不是通過文本詞語指向另一種事物的隱喻活動來揭示。相反,經驗世界呈現意義給詩人,詩使這一過程顯明。”⑤宇文所安對中國古代詩歌的“非虛構”傳統的這一獨到理解影響了一大批海外漢學界的學者,他們對中國古代文學和文論進行深度研究,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中國古代詩歌最大限度地記錄了詩人的真實感受和生活,而不是詩人異想天開進行虛構的結果,中國古代詩歌區別于西方詩歌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中國詩歌不存在西方文學中的所謂虛構和隱喻的因素。
將中國詩人杜甫的《旅夜書懷》和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在西敏寺橋上》進行比較后,宇文所安認為杜甫的這首詩中雖然沒有出現具體的時間和地點,但卻是“非虛構”的,因為整首詩中有好幾句都是在寫景,但是對景的描寫表現出了詩人當時的心境,詩人并不意圖表現現實世界之外的虛構的世界;反之,華茲華斯的這首詩雖然清晰地展現了詩人寫作的時間和地點,即1802 年9月3 日黎明,地點是倫敦的教堂、劇院等各種場所,但是華茲華斯的詩并不是為了再現彼時彼刻倫敦西敏寺橋上的真實場景,而是指向了現實之外的另一個維度。“華茲華斯無論是看到、依稀記得,還是通過想象構造出這一景色,均是無關要旨的。詩歌所指向的并非是對歷史上倫敦的細致描繪,而是將人們引向別的,引向某種意蘊,與其中泰晤士河上的船只數是完全不相干的。”⑥宇文所安所指的“非虛構”主要體現在:在西方詩歌傳統中,詩人本人并不是抒情的主體,而是另外的抒情主人公“我”,借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所以在西方詩歌中,抒情主體并不是詩人本人,而是虛構出來的。但是在中國傳統詩歌中,詩人本身就是作為抒情主體而存在的。詩人借詩歌表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懷才不遇、思鄉懷親、愛人別離、年老多病等各種真實的遭遇和境況,不需要借助本人之外的抒情主人公來抒發感情。
此外,宇文所安認為中國傳統的“非虛構”還體現在詩人和自然景物之間的呼應關系,用中國傳統觀念來概括就是“天人合一”。“中國詩歌最終顯現的世界之道與詩歌內容是無法分離的,因為這種道本身就體現在詩人描述的情景之中,體現在詩人的情感當中。詩歌所表現的道是現世之道,只能在對自然和人事的描述體驗中去尋求顯現。”⑦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宇文所安所提的“虛構”更多的還是偏向西方哲學層面的虛構,基于此,他給中國傳統詩歌下了“非虛構”的結論。
余寶琳也是從事“中國非虛構詩學”這一理論研究的著名學者,她也認為中國古代詩歌中不存在西方詩歌中隱喻的傳統,但值得一提的是,她鮮明地指出中國古代詩歌中的比、興是和西方隱喻相對照的模式。余寶琳并不試圖總是用西方理論術語來對中國文學進行分析,她對中西比較詩學的發展有著獨特的理解和鮮明的預見性,她指出當下的研究必須分清中西有著不同的文化語境,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點。“余寶琳深知混淆甚至忽視中西不同的文化語境而去進行文學比較是沒有出路的。只有在承認二者社會歷史文化差異的基礎上對產生這一差異的深層次原因,也就是中國不同于西方的哲學背景、詩歌傳統和文化慣例進行深層次的研究,才能在中西比較文學中做出些有價值的東西。”⑧在中國詩學研究方面,余寶琳認為造成中國非虛構詩學和西方虛構詩學這兩個傳統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奉行的是一元論哲學,而西方奉行二元論哲學,即在中國傳統哲學觀中,認為現實世界是一元的,而西方奉行的是自古希臘以來的哲學體系,認為現實世界是對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詩歌等藝術形式是對現實世界的模仿。余寶琳還對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意象”概念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在《中國詩歌傳統中意象的讀法》一書中分析了中西詩歌傳統中對“意象”的不同解讀。余寶琳對于中西詩學的研究是從多角度切入的,在《中國詩論和象征主義詩學》一書中,余寶琳比較了中國形而上批評家與西方象征主義、后象征主義批評家的異同。通過對中西詩論不同層面的一系列比較研究,余寶琳得出了重要結論,認為中國詩歌和西方源自古希臘“模仿說”不同,它是一種非虛構文學,更注重寫實。
“中國非虛構詩學”這一提法自誕生以來,就在不斷地更新和發展,除了上述外,還有許多致力于這一研究范疇的學者,他們的觀點各有異同,但幾乎都指向了一個相似的結論:中國傳統詩歌中是不存在和西方“隱喻”“模仿”類似成分的,是“非虛構”的。
二、“中國非虛構詩學”理論的不足和局限性
在宇文所安、余寶琳、吉川幸次郎等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國非虛構詩學”的理論已經被越來越多的海外漢學家和學者所推崇,并逐漸被眾多國內學者所接納,對國內學者的詩學研究產生了進一步的啟發。但是,對于這樣一種來源于西方文化語境的理論成果,我們必須加以辯證看待,在明確其局限性后,可取其精華,“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融會貫通中西詩學理論中的精華,促進中國詩論更好地發展。
比如,從事中西文學及跨文化研究的著名學者張隆溪就對“非虛構詩學”的理論假設提出了質疑。張隆溪認為這一提法未免牽強附會,有刻意尋求中西文化差異進而得出“文化差異性”論點的嫌疑,“基于自然與文化、獨特性與普遍性、具體與抽象諸如此類的基本差異上加以臆斷”⑨他以劉勰的《文心雕龍·神思》為例,指出中國古人在創作過程中存在“想象”的因素,對持“中國非虛構詩學”理論設想的學者所推崇的寫實與虛構二元對立的研究模式,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所謂中國傳統詩歌是對詩人的內心世界和所處的現實世界純粹的記錄的觀點是不成立的,因為中國文學中蘊含夸張的表達法的詩句比比皆是,“非虛構”的假設不攻自破。
四川大學的學者王曉路同樣也對“中國非虛構詩學”這一提法持懷疑態度。他認為將中西詩學用“虛構”“非虛構”這種純粹二元對立模式來劃分的做法值得進一步商榷,因為在中國古代詩歌的創作過程中,虛與實是很難完全分開、獨立討論的。“顯然,采納這種‘一元——自然——非虛構’的模式而不從中國歷史語境和文化傳統的實際出發對中國文學及文論加以總括并非合適的。”⑩
史冬冬是國內目前對宇文所安的詩學理論研究較為透徹的學者之一,他在對宇文所安的論著進行研讀時,也發現了宇文所安的“中國非虛構詩學”理論假設的局限性。“不可否認的是,面對中國古典詩歌中大量運用夸張等虛構性修辭手法的詩歌,非虛構的閱讀方法確實不能把握其中的真正意蘊。”?從史冬冬的角度來看,李白的詩和《詩經·國風》中有許多夸張、想象的景物描寫,其實是隨著作者內心的情感變化而變化的,如果執意用現實描寫來對其進行解讀,其中的意蘊將蕩然無存。這樣就不能對中國古代詩歌作出準確、貼合實際的解讀,內容、主題和思想情感的“誤讀”現象便出現了。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首先,可以認為“中國非虛構詩學”這一提法畢竟是從接受者的角度出發而談的,這樣就很容易忽略作者的主體地位,而在中國古代詩歌中,詩人即作者就是詩歌所記錄的情景最直接、現實的敘述者,并不存在西方詩歌中那種專門被創造出來的抒情主人公。如果忽略作者的主體地位,而一味從接受者角度進行考察,那么我們就不能更真實地體會作者的表情達意,對詩的理解也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偏差。其次,“中國非虛構詩學”這一提法的不足還體現在容易單方面地從西方固有的思想觀念和現有的理論模式出發,無法準確地結合中國本土文化歷史語境,因此對中國詩學思想難以避免地出現了“誤讀”。以宇文所安為例,他在對“中國非虛構詩學”這一理論進行命名時,就體現出這一傾向。宇文所安所謂的“虛構”是從西方理論中擇取出來的,在前面加上一個否定前綴“非”,便對中國詩學思想的特征進行了界定,但結合其理論主張和中國詩學的現實情況來看,這一命名就顯得非常牽強。除此之外,這種命名無論對中國接受者還是西方接受者來說,都容易引起一些問題,“使得中國接受者在理解這一概念時,首先面臨的是命名上的疏離感;而西方接受者則容易跌入東方主義的泥沼,仿佛中國的詩學概念天然就是拿來應對西方文學傳統危機的,抑或只是一種‘非’的異國想象。”?這種命名其實是不利于中西文學和文化長期平等、友好發展的。
“中國非虛構詩學”的理論雖然有著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但畢竟這一理論尚在發展初期,未來還會有更多的觀點為其注入新鮮血液,不能因為它產生于海外,就認為其對中國詩學研究得不夠深刻,這種否定本身就是一種偏見,國內學界要用更加開放、包容的態度對待這類非本土理論思想。廣大學者應秉持理性態度正視西方理論,合理汲取西方理論的精華加以利用,用更加平等、友好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學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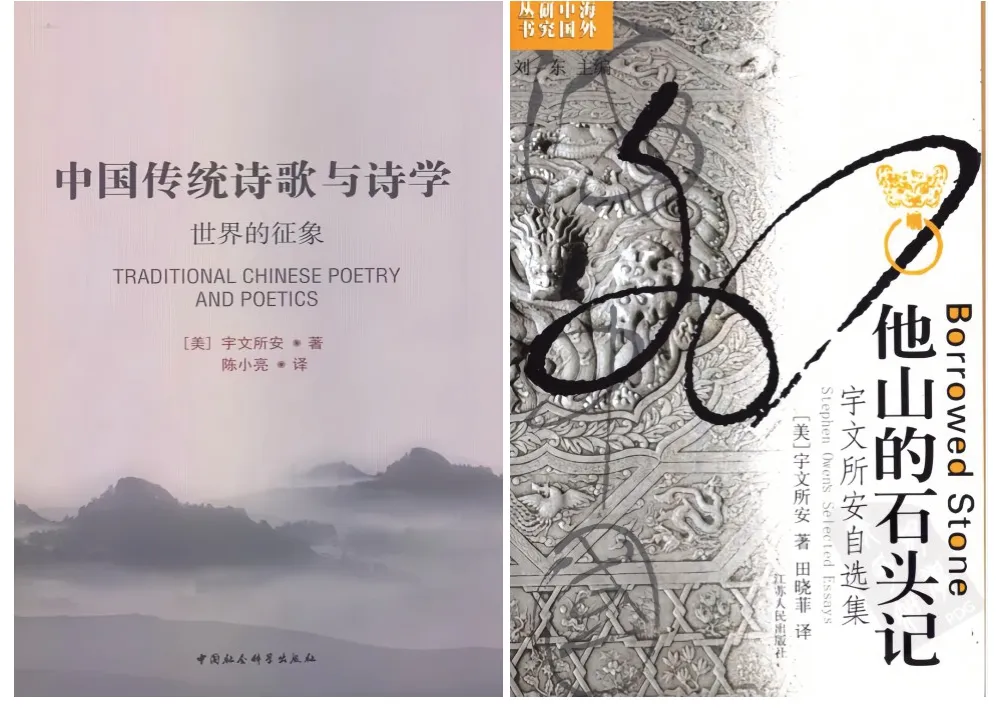
宇文所安作品封面
三、由“中國非虛構詩學”引發的問題及思考
通過對“中國非虛構詩學”的主要觀點進行分析,可以認為其作為一種中西文化雙重作用下的“混血兒”,既有著自身的話語優勢,也有著不足和局限性。在對“中國非虛構詩學”這一理論研究的過程中,筆者也產生了另一維度的思考:當下,應該怎樣合理地進行中西詩學的對話?要如何保持中國詩學的主體地位?中國比較詩學未來如何更好地發展?首先是怎樣合理地進行中西詩學對話的問題。當下,隨著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世界文學”已不再是一種構想,得益于一代代秉持開放、包容態度的學者,中西對話才能呈現出如今的嶄新局面。由于閉關鎖國政策,中國古代很難與外界進行對話,而鴉片戰爭以來,國人的對話意識普遍開始覺醒,但此后很長一段時間,中國與西方在文學方面的對話地位都是不平等的,經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奉行“拿來主義”,將西方理論奉為圭臬,并把這種拿來的東西不假思索地植入中國本土文學中,有人甚至還提出要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學的提議。這種對話模式顯然是畸形的、病態的,中國在中西對話中喪失了主體性,成了被動的接受者。而當下,隨著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不斷上升,中國學界也需要用更加自信、平等的姿態與西方進行對話。要做到中西詩學的友好對話,首先要對中國古代的文學經典進行更加深度的研讀,不斷發掘其重要內涵,如果能從中找到與西方相類似的觀點,再用中國自身的術語對文學作品或者文學現象進行闡釋,便能更好地保持中國詩學自身的獨立性和主體性。當然,在進行中西對話時,也必須先對西方的文化和文學有深入的了解與認識,中國古話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此,中國學界便能更加積極主動地吸取西方文化和文學中的有益成分。而對于中西詩學之間存在的矛盾,也能更好地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加以解決。此外,還要加強區域文化合作,用平等、友好的態度與周邊國家進行交流和溝通。長期以來,中國文學的影響力總是輻射到周邊國家,對周邊文學及詩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就得用高人一等的眼光看待周邊國家的文學和詩學成果,某種詩學理論即使最初產生于中國,也可能于日本、韓國、越南、馬來西亞等其他國家的文化語境中成長出另一種結果,這種理論便具有了該國的特色,理論的內部體系也獲得了新的填充,反過來對中國原始的詩學理論進行著新的解讀和補充。因此,中國學界應適當接受周邊國家文學和詩學理論的“回流”,以此不斷完善出穩固的、系統的東方詩學體系。
其次,關于如何堅持中國詩學的主體地位,在筆者看來,在實踐方面,對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理論體系進行研究和考察時,必須首先從中國傳統詩學理論中汲取營養,而不是下意識地從西方詩學理論中獲得幫助。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土生土長,并深深根植于中國,有著自己一套獨立的話語體系,如果不回到中國傳統中考察,不回歸中國本身的語言環境和文學傳統,而僅僅依賴于西方現代的理論,那將會造成“驢唇不對馬嘴”的情景,難免患上“強制闡釋”的弊病,這對維護中國詩學的主體地位是非常不利的。王曉路認為:“在這種雜語共生、多元文化并行的時代,在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文化趨同潮流中,本土的傳統意識與非本土借鑒意識往往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復雜、微妙的文化現象。文化互融性與文化獨特性由此形成了某種張力。對于經濟相對落后的文化區域來說,一方面它必須面對強勢文化即對西方文化中值得借鑒的東西,加以認真的透視、篩選和理性的思考,而另一方面它又必須依據本土經驗,在充分展示自身、發展自身的同時對西方以及自身傳統中的阻礙因素予以雙重梳理和清除,從而實現批判性超越”。?這段論述非常客觀地理清了中國詩學目前面對的現實情況,同時也為“如何堅持中國詩學的主體地位”這一問題提出了方法論。中國古人曾說:“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中國有著幾千年的詩學思想積淀,學界要深入挖掘中國文學的寶庫,從中國詩學的源頭入手,進一步更新完善自己的理論體系,從而維護中國比較詩學的主體地位。
最后,關于中國比較詩學未來如何更好地發展,筆者認為,中國比較詩學作為一種現代提法,需要兩種或多種不同的文化傳統進行深度的、平等的溝通和聯系。“中國比較詩學”里的“比較”并不是一般方法論意義上的簡單比較,而是從縱向和橫向多個維度挖掘其中的內涵,是詩學關系的研究。“中國比較詩學”這一理論體系絕不是通過“比較”最終達成一種非此即彼的、某一共識結果的學科,不是A 文化一定要同化甚至侵蝕B 文化,而是從平等的立場出發,希望通過“比較”達到求同存異的效果,在“比較”的過程中,認識到中國傳統詩學自身的優勢,并從別的詩學理論中汲取營養,最終促進中國詩學更好的發展。需要注意的是,在進行“中國比較詩學”研究時,不能一味地追求“趨同”,也不能只做到“求異”,這兩種傾向都不能引導中國詩學朝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在“中國比較詩學”發展初期,海外漢學家為了減少中西文化的隔閡,便于西方讀者理解中國傳統詩學,曾經出現過刻意“趨同”的現象,也就是用西方文化中已有的概念來闡釋中國傳統詩歌,這樣做對準確解讀中國詩學思想是極其不利的,“在中西詩學傳統中尋找對應物的做法,往往會流于簡單化與表面化……無視文化背景的盲目搬用,一方面,夸大了不同文化間的同質性存在,可能將西方的文學理論作為權威標準,以此來裁剪中國詩學,此為一弊;另一方面,此種對應往往只是表面上的相似,貼標簽式的研究方式只會掩蓋漢詩的特性,此為另一弊病。”?在意識到一味地“趨同”會把中國比較詩學研究引向“死胡同”時,葉維廉和英國漢學家葛瑞漢等學者開始關照異質文化間的差異性,這種研究方法使中西詩學理論間的差異被放大,使得中國傳統詩學的“獨特性”脫穎而出,但是如果僅僅進行“求異”的比較,就會把中國比較詩學引向另一個“死胡同”。“承認差異的存在,認識到每一種文化體系都有自己的特點,這是西方思想的進步;但若是將中西文化差異過于放大、推至極端,將中國視為絕對的“他者”,也會遮蔽中西文學思想的互通。”?通過漢學家和中國本土學者的嘗試,能夠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未來,中國比較詩學想要更好地發展,必須正視中西文化的地位和關系,平等、友好地進行對話,中國學界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只有在求同存異的過程中,中國比較詩學才能不斷地獲得能量和營養,不斷地擴大國際影響力。
結語
“中國非虛構詩學”作為海外漢學家對中國傳統詩學進行深度研究和解讀后所提出的一種理論假設,一方面,使得中國傳統詩學逐漸走出了國門,并在西方的文化語境中衍生出了新的變體,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傳統詩學注入了新鮮血液,使其煥發出新的生機,同時還擴大了中國傳統詩學的國際影響力,為中國本土學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另一方面,這一理論受到了根深蒂固的西方思想觀念和文化語境影響,很難單純從中國文學和哲學視角出發對傳統詩學進行貼切的理解,難免會出現誤讀、“強制闡釋”和“創造性叛逆”。總的來說,“中國非虛構詩學”這一命題促進了中國學界更好地審視“他者”與“自我”的關系,并促進了其與中國本土思想的自洽。“中國非虛構詩學”歷史生成與當代傳承的研究,是兩種異質文化間相互聆聽、友好對話的過程,相信在海外漢學家和中國本土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國非虛構詩學”能夠克服自身不足,發揚自身優勢,促進中國比較詩學更好地發展。
注釋:
①(日)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章培恒等譯,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 年版,第1 頁。
②(日)吉川幸次郎:《中國文學史》,陳順智、徐少舟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7 頁。
③(日)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章培恒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版,第5 頁。
④(日)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學記》,錢婉約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 年版,第178 頁。
⑤Stephen Owen,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p.34.
⑥Stephen Owen,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p.14.
⑦史冬冬:《辯詩:論宇文所安中國詩學研究之非虛構觀》,《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4期,第450 頁。
⑧孫莉莉:《吉川幸次郎和余寶琳中國詩歌“非虛構”傳統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浙江大學,2012 年,第20 頁。
⑨張隆溪:《文為何物,且如此怪異?》,《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 年第3 期,第85 頁。
⑩王曉路:《中西詩學對話——英語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巴蜀書社2000 年版,第94-95 頁。
?史冬冬:《辯詩:論宇文所安中國詩學研究之非虛構觀》,《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4期,第452 頁。
?李鳳亮、周飛:《空泛與錯位的“非虛構詩學傳統”——評宇文所安〈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征象〉》,《文藝研究》2019 年第4 期,第155 頁。
?王曉路:《中西詩學對話——英語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巴蜀書社2000 年版,第3 頁。
?任增強:《“非虛構”與“無我”:海外漢學視域中的中國詩性》,《國際漢學》2015 年第4 期,第130 頁。
?任增強:《“非虛構”與“無我”:海外漢學視域中的中國詩性》,《國際漢學》2015 年第4 期,第13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