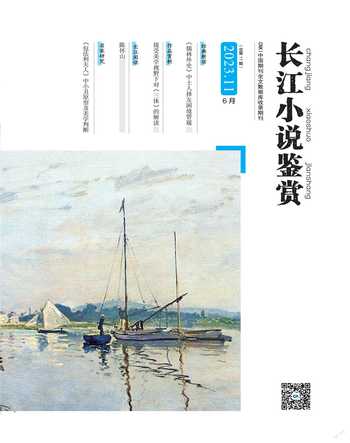晚清小說中的西方女豪杰形象
[摘? 要] 晚清知識分子為應對民族危機,呼吁女性擔負救國責任,在小說創作中引入了西方女豪杰形象,以此啟蒙中國女性,號召她們效仿西方女豪杰,積極參與家國事務。中國知識分子在引入西方女豪杰形象的同時,都對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寫。晚清小說《東歐女豪杰》《黃繡球》中的西方女豪杰被塑造成了中國化的美女、神圣化的啟蒙者,她們在這兩部小說中的政治立場也受到了作者改良立場的影響,西方女豪杰形象在中國的重新建構反映了晚清男性知識分子的復雜心態。這兩部小說中的西方女豪杰形象塑造具有符號化、套路化、國族化的特點。晚清小說的女豪杰形象塑造雖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然對中國女豪杰的生成產生了積極影響,促進了中國女性的覺醒,構筑起了晚清甚至民國時期關于新女性的期待與想象。
[關鍵詞] 晚清小說? 西學東漸? 女豪杰? 形象建構? 國族話語
[中圖分類號] I207.4?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11-0080-05
一、西方女豪杰的引入背景
因國家動蕩,內外交困,晚清知識分子為挽救民族危機,提出了各種救國主張。其中,女性問題得到了晚清知識分子的高度關注,知識分子將女性問題同國族問題連接在一起,丁初我就曾提出“欲造國,先造家;欲生國民,先生女子”的觀點[1]。金一也在《女子世界》發刊詞里提出:“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2]與此同時,西方女權思想被譯介到中國,如馬軍武就將斯賓塞和彌勒的女權理論譯介到中國,他們“男女同權”的觀點在中國引起了極大的輿論反響。由此,晚清知識分子在中國女性身上寄予了新的想象與期待,希望女性能夠成為富有智識、關注國族命運、與男性同擔國民責任的“女國民”。困守于閨閣繡樓中的傳統女性則在此語境之下被視為坐食者、分利者,不符合晚清知識分子的新女性想象,被其排斥到輿論場邊緣。此時,蘇菲亞、羅蘭夫人、若安、批茶等西方女豪杰就作為中國傳統女性的對立面和這種新女性想象的具象呈現,被晚清知識分子引入中國,這些西方女豪杰的相關傳記、彈詞、詩歌直接促進了其女性形象在中國的傳播,其中尤以梁啟超的《羅蘭夫人傳》影響最大。晚清知識分子希望以西方女豪杰作為女性模范,建構、塑造、規訓中國女性,使其成為統攝在國族話語之下的“女國民”。在此背景下,知識分子也將這些西方女豪杰形象直接或間接地放置在其寄托了“群治”理想的新小說中,以期擴大西方女豪杰在中國的影響力,號召中國女性走出閨閣,進入社會,參與到救國運動中。蘇菲亞、羅蘭夫人這兩位在當時中國頗具影響力的西方女豪杰就直接作為小說人物分別出現在《東歐女豪杰》《黃繡球》這兩部晚清小說中。
二、西方女豪杰在晚清小說中的形象建構
1.中國化的美女
《東歐女豪杰》和《黃繡球》這兩部晚清小說分別對蘇菲亞和羅蘭夫人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外貌描寫,蘇菲亞和羅蘭夫人在這兩部小說中被塑造成帶有濃厚中國色彩的美女。《東歐女豪杰》中,蘇菲亞一出場,作者便著意強調其美貌:
青春十六,正長得不豐不瘦,不短不長,紅顏奪花,素手欺玉,腰纖纖而若折,眼炯炯而多情,舉止則鳳舞鸞翔,談笑則蘭芬蕙馥。[3]
作者在這里顯然運用了古典小說描寫美女的傳統筆法對蘇菲亞的外貌進行刻畫,蘇菲亞的外貌在作者筆下并沒有顯露出明顯的異域風情,其外貌的塑造始終沒有脫離中國舊式文人的審美范式。
在小說《黃繡球》中,來自西方的羅蘭夫人更是直接一身中國古代美人的裝扮:
牌坊頂上站著一位女子,身上穿的衣服像戲上扮的楊貴妃,一派古裝,卻純是雪白雪白的,裙子拖得甚長,臉也不像本地人,且又不像如今世上的人。[4]
《黃繡球》的作者在此處將羅蘭夫人同楊貴妃聯系起來,使羅蘭夫人以一身中國化的裝束亮相讀者面前。氣質、神韻的古典化、東方化以及裝束的中國化、本土化都極大削減了蘇菲亞和羅蘭夫人的異域性,促使讀者按照傳統中國美人的外在形象來想象、建構這兩位西方女豪杰。這種外在形象的建構策略不是一種簡單的書寫慣性,其背后所蘊含的心理機制尤為復雜。
當時,在輿論場極力貶抑中國傳統女性身體陰柔特質的晚清知識分子不在少數,他們主張健美的女性審美標準,但在當時一些男性啟蒙者的實際創作中,對于女性的外貌書寫又不乏“腰纖纖而若折”之語,陷落在古典文學敘寫傳統美人的陳舊話語格套里。這一方面顯露出晚清新小說作者在女性書寫上的話語匱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晚清的男性啟蒙者在女性審美標準方面的主張與具體創作實踐上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不豐不瘦”與“腰纖纖而若折”這兩處矛盾之語本身就已經將晚清男性啟蒙者隱藏于背后的糾結與反復展露出來。梁啟超在議論女性之美時,就將“剛健”與“婀娜”這看似矛盾的兩重標準并舉,認為“最妙者是剛健之中處處含婀娜”[5]。 晚清男性啟蒙者一方面期待剛健的女性身體的出現,一方面又留戀于舊式文人偏好女性柔美身體的審美意趣,這種處于新舊交織之際的內在心理矛盾恰好體現在作者對西方女豪杰的外貌書寫中。這表明即使作為啟蒙者的作者對西方女豪杰多有推崇,但這些女豪杰依舊被其不自覺放置在了被觀看、被凝視的客體位置。不能否認的是,西方女豪杰外表的中國化可以減少讀者對于她們形象的陌生感,而對她們的美女化描寫則增添了這些西方女豪杰的傳奇性,使其事跡更具浪漫色彩。這種方式使讀者更容易想象、認同西方女豪杰,從而促進了西方女豪杰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與接受,魯迅就認為蘇菲亞的美貌對其影響力的擴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6]而這種美女豪杰的敘事策略是否會使小說的讀者僅僅迷戀于西方女豪杰的美麗風韻,是否會在讀者接受過程中對女豪杰的革命精神與救世情懷造成新的遮蔽,這是值得進一步省思的。
2.神圣化的啟蒙者
《東歐女豪杰》中的蘇菲亞和《黃繡球》中的羅蘭夫人都在小說中承擔著啟蒙者的角色,致力于使被啟蒙者擺脫蒙昧的狀態。蘇菲亞在《東歐女豪杰》中通過演說,對俄國貧富分化、社會不公的狀況進行深入分析;向烏拉山的礦工灌輸人人平等的理念;鼓勵平民大眾聯合起來,組織新政府,造就人人平等的新世界。顯然在小說中,蘇菲亞自覺承擔了啟蒙大眾的任務,主動向大眾輸出先進的價值理念和她認為行之有效的斗爭手段。在小說《黃繡球》中,羅蘭夫人入夢黃繡球,在其夢中先質疑男強女弱的傳統性別定位,向黃繡球傳遞“男女同權”的觀念,進而促進其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而后她又授《英雄傳》和地理書籍于黃繡球,賦予其解放自我、改良社會的思想支撐和知識武器。羅蘭夫人成為黃繡球走出閨閣、進入公共領域的引路人,是促使其獲得主體性的啟蒙者。
同時,蘇菲亞和羅蘭夫人在這兩部小說中的啟蒙者形象又被作者神圣化。蘇菲亞出生時有“白鶴舞庭,幽香滿室”[3]的異象,直接使其形象被蒙上一層明顯的神秘主義色彩。而羅蘭夫人的出場、退場與啟蒙過程同樣被神化,羅蘭夫人于黃繡球夢境中以一襲白衣出場,又在其夢境中倏忽消失于云端,黃繡球在夢中“忽見那女子拖著一條白裙,遠遠的像在云端里去了,須臾連牌坊都不見”[4]。這段退場描寫明顯借鑒了志怪小說中神仙退場的敘事手法,使羅蘭夫人的形象如夢似幻。而羅蘭夫人夢中授書的啟蒙過程設置同樣受到了志怪小說中神授天書情節的影響,夢醒之后黃繡球“把那夢中女子所講的書開了思路,得著頭緒,真如經過神佛點化似的,豁然貫通”[4]。這段描寫直接點明這種神圣化、速成化的啟蒙其實更近似于古代戲劇、小說中的“神仙點化”。這些借鑒于志怪小說中的敘事策略都誘引著讀者以女神的形象來想象、建構這兩位女豪杰。從被啟蒙者的接受心理維度來看,蘇菲亞和羅蘭夫人的啟蒙者形象與佛教中的觀音菩薩形象重合,蘇菲亞被工人視為渡化他們的菩薩:
蘇姑娘回去了,我們正大家議論,都說蘇姑娘是個救苦救難的菩薩,特來普度我們的,我們人人家里都崇拜他才是的話。[3]
黃繡球則猜測羅蘭夫人為點化她的觀音:
心中又想道難道是:“只難道是白衣觀音嗎?我向來也不曾相信菩薩,奉個觀音齋,怎么他回來點化我?不去管他,我取了幾本書快點回去吧。”[4]
將西方女豪杰的啟蒙者形象神圣化實際上是對西方女豪杰形象的賦魅。一方面,這可能是作者希望借助神仙形象在普羅大眾中的深遠影響力和強大感召力,來增強蘇菲亞和羅蘭夫人形象的權威性、她們所秉持的啟蒙觀點的說服力及其在讀者心中的可信度,以此促進小說啟蒙思想的傳播,達到開啟民智的“群治”效果;另一方面,將西方女豪杰置換成神仙,也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想象的偏狹和對古典文學資源的依賴,他們可能由于現實經驗的缺乏和文化差異,難以把握準確塑造女性啟蒙者形象的方式,于是只能從古典文學的形象譜系中來尋找對應物,并以此建構女豪杰形象,而作者對于啟蒙者啟迪民眾的認識和理解也沒有脫離“神仙救世”的傳統邏輯。作者將啟蒙的敘事嵌套在“神仙救世”的舊有模式里,使承擔啟蒙者角色的西方女豪杰需要借助神仙的外殼來傳播啟蒙思想,這可能既是作者在面對啟蒙的現實困境時所做出的權宜之計,也是啟蒙者借用宗教信仰建構新話語權威的有意之舉。從而以救亡圖存為最終目標的晚清啟蒙運動與反宗教神權的西方啟蒙運動的本質差異亦由此處得以被窺見。與此同時,當啟蒙者在小說中作為一種超驗性存在指引被啟蒙對象時,啟蒙者的啟蒙實踐就在作者的建構下走向了理想化,而與之相對的是啟蒙理想落實在現實境遇中的艱難性。在虛構文學中被簡化甚至被神化的啟蒙過程與現實實踐中的啟蒙困境相互映照,這兩者在無形之中形成了一種互動的張力。
3.服務于改良主義的政治立場
《東歐女豪杰》中的蘇菲亞和《黃繡球》中的羅蘭夫人雖然在小說中都是爭取男女平等、追求自由獨立、具有崇高理想和救世精神的女豪杰,但這兩部小說對她們二人政治主張與政治立場的書寫出現了明顯的分野。
蘇菲亞在俄國歷史上以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而著名,她所在的虛無黨主張推翻專制制度,認為應該廢除一切國家和政府,追求個人的絕對自由,虛無黨常以暗殺手段對抗政府,因此該黨在一段時間曾被中國的革命黨人大力推崇。而《東歐女豪杰》中的蘇菲亞卻被作者塑造成一個與歷史形象截然不同的溫和改良派人物,蘇菲亞否定了激進者直接沒收貴族土地的主張,提倡進行政權的和平過渡,認為普羅大眾應組建新的“大公局”,聯合購買貴族土地,以溫和平穩的手段實現土地的人民共有。蘇菲亞在小說中的政治傾向與其事實上所持的政治理念之間顯然存在著巨大的裂隙,作者改良主義的政治立場使得蘇菲亞的政治主張在小說中被改換,蘇菲亞在小說中被改寫為“一位遵奉國家主義的改革者”[7]。
在法國歷史上,羅蘭夫人是革命黨溫和派吉倫特派的一員,并非屬于革命黨中另一支更為激進的派系——雅各賓派。吉倫特派雖主張共和,要求廢除君主制,但反對處決國王與暴力革命,維新派的代表康有為稱吉倫特派“平和義熱”[8]。即便如此,當時同樣持改良主張的梁啟超在《羅蘭夫人傳》的撰寫中仍然流露出對羅蘭夫人的復雜態度,他一方面贊頌了羅蘭夫人的愛國情懷,另一方面也對羅蘭夫人“放出革命之猛獸”[9]的行為頗有微詞。與梁啟超的態度相呼應的是小說《黃繡球》中的虛構人物對羅蘭夫人的評價。《黃繡球》中,雖然羅蘭夫人所授的“宗旨學問”被黃繡球的丈夫黃理通大加肯定,但其所做之事仍舊被黃理通認定為“激烈”,黃理通直言黃繡球“不必處那羅蘭夫人的處境,不必學那夫人的激烈”[4],這直接顯示了《黃繡球》作者溫和改良的政治取向。而后羅蘭夫人所啟蒙的中國女性黃繡球在黃村所采取的興辦新式教育、以彈詞教化大眾等溫和改良措施正印證了作者頤瑣的政治立場。
《東歐女豪杰》對蘇菲亞政治主張的改寫和《黃繡球》對于羅蘭夫人政治立場的判定,都表明了兩部小說作者作為溫和改良派的政治立場,展露了這兩部小說創作的政治意圖——宣揚改良主義,為其召喚更多的追隨者。蘇菲亞和羅蘭夫人在晚清小說中的形象建構很大程度上服務于作者的政治理念,從屬于作者現代性的家國想象。這些西方女豪杰形象在中國有嚴重國族危機的背景下被引入中國,其文學形象最終亦無可避免地受到政治話語和國族話語的統攝。同時,晚清小說中西方女豪杰政治形象的重新建構也揭露了當時改良與革命兩種政治力量激烈交鋒的一隅。
三、晚清小說中西方女豪杰形象塑造的特點
1.符號化、概念化
蘇菲亞和羅蘭夫人在《東歐女豪杰》和《黃繡球》這兩部小說中更像是凝結了豐富意韻的符號人物[10],成為表達作者改良政治主張、彰顯其救世愛國情懷的工具。她們二人在小說里被設置為昭示女子獨立的女性模范,是指引普羅大眾的先知性人物,高揚愛國精神、承擔救國責任的國民典范。她們同樣是改良政治話語、啟蒙神話的載體,是知識分子為表達現代性國族想象而建構起的借鑒對象。蘇菲亞在《東歐女豪杰》中被塑造成出身不凡、外表姝麗、救世為民的完美女性典范;羅蘭夫人在《黃繡球》中本身就是一個功能性人物,僅作為啟蒙黃繡球的引路人存在。兩位西方女豪杰在小說中性格模糊,缺少層次變化,內心情感缺失,形象扁平,缺乏人物的內在張力和個性呈現,其人物書寫缺乏細節真實,完全服務于情節發展和作者的政治意圖。這一方面是晚清政治小說常見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晚清新小說作者關于新女性想象的匱乏。除此之外,西方女豪杰形象引入中國的政治目的也一定程度上催發了符號化、概念化的女豪杰形象的產生,但符號化、概念化的西方女豪杰形象是否能夠產生梁啟超所期望新小說發揮的“熏”“浸”“刺”“提”四力?是否能夠達到號召、感化普羅大眾的原始目的?是否能夠使讀者將西方女豪杰形象上集合的概念內化到現實實踐中?這是有待商榷的。
2.模式化、套路化
蘇菲亞和羅蘭夫人在兩部小說中的形象塑造都流于模式化、套路化。兩本小說的作者主要依靠對這兩人的行動書寫來呈現二者的女豪杰形象。蘇菲亞和羅蘭夫人在小說中都沒有出現復雜的人物行動。蘇菲亞僅僅出現了離家求學、成立盟會、大會演說、下獄被捕、等待被救這五個主要行動,其中,離家求學、成立盟會、大會演說、下獄被捕都是晚清小說中豪杰人物同質化的經典行動范式。這種同質化的行動范式既可以說是對多個女豪杰事跡的機械借鑒與模仿,也可以說是作者政治理念的套路化呈現:離家求學是為了說明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大會演說是豪杰精神與啟蒙主張的現實實踐;下獄被捕則是舍身為國情懷的顯像呈現。羅蘭夫人作為《黃繡球》中的功能性人物,其行動相比《東歐女豪杰》中的蘇菲亞更為簡單化,入夢授書這一行動模式則直接套用了志怪小說的程式化情節設置。蘇菲亞和羅蘭夫人女豪杰形象的模式化、套路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二人在小說中行動的模式化、套路化所造成的。西方女豪杰的套路化演繹一方面是由作者女豪杰想象的單一化所導致,另一方面亦是人物形象概念化的后果顯現,人物行動都屈從于一定的政治框架,為展現政治觀念服務,而這些政治觀念都有與之對應的固化的人物行動模板。值得一提的是,行動的模式化造成了二人行動的簡單化,小說中呈現出二人改進社會、啟蒙他人的方式較為單一,大會演說成為《東歐女豪杰》中的蘇菲亞參與公共政治生活、踐行政治主張的主要途徑;羅蘭夫人在《黃繡球》只憑借入夢授書這一個簡單動作便完成啟蒙者的角色任務,這都展現出作者對于女性啟蒙者形象塑造的陌生,女性啟蒙大眾的敘事在這兩本小說中只能以簡單化、套路化的模式呈現出來。
3.國族化
蘇菲亞和羅蘭夫人在小說中的形象塑造很明顯由國族話語主導,統攝于國族敘事話語之下。《東歐女豪杰》的作者重點表現蘇菲亞的國民責任感,蘇菲亞在公共領域的演說帶有強烈的國民意識,她組建新政府、和平實現土地共有的號召顯然是其以國民身份為出發點建構起來的國族想象,小說開頭的引子所提出的女性事業最終直接指向了救國濟民的國民重任。在小說《黃繡球》中,羅蘭夫人向黃繡球展開“雌雄之辯”、傳遞男女平等觀念的最終目的是賦予女性“國民”的身份,讓黃繡球這樣的閨閣女性與男子一樣同擔救亡濟世的責任,羅蘭夫人對男女平權的倡導以國家主義為依歸,促使女性主動進入國族敘事的話語之中。小說《黃繡球》的這樣一處描寫頗耐人尋味:當黃繡球向羅蘭夫人尋求改良黃村的建議時,羅蘭夫人則直接對黃繡球言道:“這是你黃姓村上的事,自然你姓黃的人關心切己,與我白家無涉,你黃家果然做得出點兒事,豈不叫我白家減色?”[4]這里表明,對于作者來說,羅蘭夫人的國族身份仍舊蓋過其性別身份,相互之間的國族競存壓力在此時越過性別困境所引起的同性相惜。小說中由這些女豪杰引出的女權話語明顯具有濃厚的國家主義色彩。
四、結語
雖然晚清小說中的西方女豪杰形象具有某種局限性;但不能否認的是,這些女豪杰形象對于呼喚女性的主體意識、肯定女性的主體價值、促進女性掙脫舊的思想藩籬和激發女性愛國熱情具有正向影響,小說中的西方女豪杰形象為當時的中國女性提供了某種可供借鑒與學習的范本,具有明顯的典范作用。這些西方女豪杰形象不僅催生出了華明卿、黃繡球、貞娘等中國女豪杰形象,同時也推動了現實中中國女豪杰的出現,以秋瑾為代表的晚清革命女性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女豪杰形象的感召,她們作為西方女豪杰的精神追隨者,突破傳統女性的角色定位,走出閨閣,積極參與到救國運動中。從西方到中國,從虛構小說到歷史現實,這些女豪杰形象共同促進了中國女性的覺醒與抗爭,共同構筑起了晚清甚至民國時期關于新女性的期待與想象。
參考文獻
[1]? ?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說[J].女子世界,1904(4).
[2]? ? 金一.社說:《女子世界》發刊詞[J] . 女子世界,1904(1).
[3]? ?嶺南羽衣女士,震旦女士自由花,軒轅正裔,等.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東歐女豪杰、自由結婚、瓜分慘禍預言記等[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1.
[4]? ? ?頤瑣.黃繡球[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5]? ?梁啟超.梁啟超文選(下)[M].夏曉虹,編.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2.
[6]? ? ?魯迅.魯迅全集 4[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7]? ? 張新璐.羅普《東歐女豪杰》的女性設計與政治想象[J].婦女研究論叢,2017(3).
[8]? ?康有為.康南海政史文選[M].沈茂駿,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9]? ?梁啟超.梁啟超文選(上)[M].夏曉虹,編.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
[10]?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特約編輯 劉夢瑤)
作者簡介:龔雪蓮,武漢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