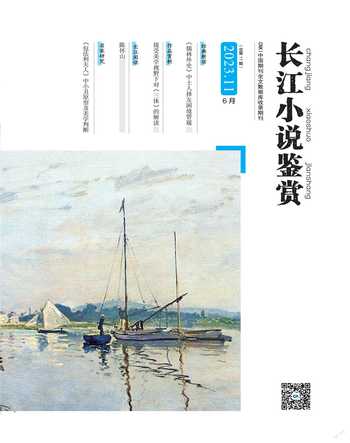論非虛構文學的跨文體特征
[摘? 要] 作為一個開放的文學性概念,學界對非虛構文學的內(nèi)涵和外延雖未達成統(tǒng)一的規(guī)定,但對其跨文體性的認識似乎已達成共識。蕭相風創(chuàng)作的詞典體小說《詞典:南方工業(yè)生活》從結構布局、語言、內(nèi)容三個方面體現(xiàn)了其作為非虛構文學的跨文體特征:詞典體小說兼具詞典的框架特征和小說的敘事功能,滿足非虛構文學展現(xiàn)真實生活的需要;散文體、詩歌體的滲入打破了語言的諸多限制;小說超出敘述故事,呈現(xiàn)出學術探討的基本面貌,展現(xiàn)出學術化趨勢。《詞典:南方工業(yè)生活》作為非虛構文學,打破了文體界限,勇于對傳統(tǒng)文類進行實驗性的探索和嘗試,其文體的多樣化表達使文本成為意義豐富的復合符號空間,打開了文學發(fā)展的新視野,同時為文學的發(fā)展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
[關鍵詞] 非虛構文學? 跨文體? 《詞典:南方工業(yè)生活》
[中圖分類號] I207.4?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11-0085-04
一、研究背景
2010年之后,《人民文學》《鐘山》等國內(nèi)多家重要文學刊物對非虛構文學的提倡引發(fā)了一股討論與創(chuàng)作非虛構文學的熱潮。非虛構文學是滿足人們對真實感、在場感的渴求而產(chǎn)生的一種打破原有文體界限的新文學,它提倡達到最大限度的真實的寫作,重視作者“在場”的姿態(tài),力圖摒除文學中浮夸、虛假的一面。“非虛構”的概念之辯一直是學界熱議的命題,有學者認為它是一個大的文學類型的集合,如王暉在《“非虛構”的內(nèi)涵和意義》和《現(xiàn)實與歷史:非虛構文學的獨特敘述》中認為非虛構文學“更多的是指一個大的文學類型的集合”[1],而“田野調查、新聞真實、文獻價值、跨文體呈現(xiàn)應該成為構建非虛構文學的基本內(nèi)核”[2];丁曉原認為,“‘非虛構顯然是一個包含了報告文學在內(nèi),但比報告文學內(nèi)涵更多、外延更大的文類概念”[3]。另一些學者認為非虛構文學已然構成一種新的獨立的文學類型,如張文東認為“非虛構寫作的理想和現(xiàn)實的可能性都在于:在盡可能模糊的文體界限中營造一種特殊的敘事策略,以某種‘中間性的創(chuàng)新模式打破傳統(tǒng)文學(小說)敘事的存在樣態(tài),使歷史或事實在被最大限度還原的基礎上成為一種新的文學景觀”[4];李云雷則認為非虛構文學是“新興的文體和新的文學現(xiàn)象”[5],其以個人的體驗為核心來表現(xiàn)世界。盡管學界尚未對“非虛構”的概念達成統(tǒng)一的認識,非虛構文學的邊界不明確、含義含混也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但人們也可以從上述討論中獲得一個共性的認識,即“非虛構文學”確實具有跨文體性。
文體是文本構成的規(guī)格和模式,是構成文學作品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所謂跨文體性,即指作家在創(chuàng)作某一作品時打破了單一的文體限制,滲透、共存了多種文體的特質,使文本變得更豐富多樣,增強了文本的張力。需注意的是,跨文體不是不同文體的簡單疊加拼湊,而是要融各種文體之長,以達到協(xié)調的效果。童慶炳在《文體與文體的創(chuàng)造》一書中認為文體“指一定的話語秩序所形成的文本體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評家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其他社會歷史、文化精神”[6]。面向更紛繁復雜的現(xiàn)實世界,非虛構文學的跨文體性正是其質疑和挑戰(zhàn)傳統(tǒng)文類秩序的表征,也正因如此,作為一個開放的文學性概念,它的生長和發(fā)展獲得了更充分的自由和空間,也得以展現(xiàn)出更豐富多彩的面貌。正如《人民文學》專設“非虛構”欄目,打出旗幟將其引入文壇主流視野時解讀道:“我們其實不能肯定地為‘非虛構概念劃出界線,今天的文學不能局限于那個傳統(tǒng)的文類秩序,文學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學本身也應容納多姿多彩的書寫活動,這其中潛藏著巨大的、新的可能性。”[7]非虛構文學跨越文體的規(guī)范和邊界,其呈現(xiàn)出的各種文體互滲和共存的現(xiàn)象值得關注。本文將以蕭相風的詞典體非虛構小說《詞典:南方工業(yè)生活》為例,分析非虛構文學的跨文體性。
二、《詞典:南方工業(yè)生活》的跨文體特征
《詞典:南方工業(yè)生活》(后簡稱為《詞典》)最初發(fā)表于《人民文學》2010年第10期,后以單行本出版。作者蕭相風于2000年南下廣東開啟“南漂”生活,輾轉在不同的工廠做過多份工作。他以詞典為敘事結構,有意整理出與工廠生活密切相關的四十幾個關鍵詞,按照字母順序排列,融入多年來的親身經(jīng)歷和所見所聞,以夾敘夾議的方式解釋和說明,形成一本“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的還原之美”的非虛構詞典體小說,因“從無可置疑的個人體驗出發(fā)對這個時代工業(yè)生活做出了大規(guī)模表現(xiàn)和思考”而獲得2010年度人民文學獎非虛構作品獎。《詞典》中,非虛構文學的跨文體特征在結構布局、語言、內(nèi)容三個層面上有所展現(xiàn)。
1.結構布局:介于詞典和小說之間
蕭相風以詞典的體式建構《詞典》的外部框架。《詞典》的內(nèi)容核心是圍繞工業(yè)生活而挑選出來的44個關鍵詞。作為同一個場域下的要素,這些關鍵詞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作者并未根據(jù)含義和相關性對其進行分類和歸納,而是嚴格按照詞典的結構特點,將其按照二十六字母表A-Z的順序組織。同時,作者使用“詳見‘××詞條”的方式,將各章節(jié)提及的內(nèi)容索引到其他章節(jié)詞條,通過這種指向性的提示將各關鍵詞重新鏈接成網(wǎng)絡,彌補按字母表排序所造成的零散的不足,強化了詞典在繪制工業(yè)生活縮影上的實操性。這也為讀者在閱讀時提供了可供選擇的便利多樣的閱讀方式和路徑。書中的各章節(jié)以關鍵詞為標題,正文則圍繞其展開闡釋,正如一般詞典對詞語的釋義。當然,《詞典》并非只是一本詞典,其內(nèi)部對章節(jié)詞條的闡釋保留了其作為小說的實質內(nèi)容,即敘事。各章節(jié)詞條中,作者圍繞各章的關鍵詞展開故事的敘述,盡管情節(jié)并不采用線性的敘事,人物和情節(jié)的發(fā)展也有斷裂的情況,但各章內(nèi)部都具備相對完整的故事內(nèi)容,基本符合小說敘事的特質。
作者蕭相風在跋文中寫道:“假若我將現(xiàn)實作為目的地,那么從詞語這個入口進入,就會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的還原之美。假若我將詞語作為目的地,從現(xiàn)實的入口進入詞語,同樣令人大為驚奇,歷史與現(xiàn)在、現(xiàn)實與美學的距離仿佛裂開的彼岸,同時也讓我意外地找到了距離產(chǎn)生之后的參照物……為了找到真理最小巧的人口,我選擇了個人詞典,用心存敬畏的態(tài)度,試圖與大家的記憶找到相似的姿勢。”[8]其主要使用了兩個策略:其一是將現(xiàn)實的生活體驗解構為詞語,以詞語作為故事的中心和主題,在敘事中重新建構并逐步還原接近真實的現(xiàn)實,實現(xiàn)小說“非虛構”的功能;其二是結合現(xiàn)實,觀照作為符號的詞語,透視詞語所凝結的內(nèi)涵及其歷史變遷,在保持一定的審美距離下重新觀照現(xiàn)實,獲得詞典對現(xiàn)實的注解和解說意義,進一步深入認識現(xiàn)實。詞典體小說兼具詞典百科全書式的嚴謹和小說閑談式的個人化體驗,既符合非虛構文學最大限度展現(xiàn)真實生活的訴求,同時也蘊含作者介入生活的思考和個人化的體驗,展現(xiàn)了非虛構文學不同于傳統(tǒng)虛構小說、社會百科全書的別樣意義。
2.語言:散文體、詩歌體的滲入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如何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文學的風格和質量。在傳統(tǒng)的文體規(guī)范認知中,一個特定文體的語言風格和特點應該符合該文體的性質并一以貫之,不能旁逸斜出。小說的主要功能為敘事,盡管不同作者的語言有其個性化的特征,但總體而言,小說的語言通常應該是簡明形象、雅俗共賞的。非虛構文學打破了文體的界限,也打破了語言方面的諸多限制和壁壘,使文本的語言選擇變得自由而豐富多樣,展現(xiàn)了價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狀態(tài)。
蕭相風對《詞典》有著明確的定位——這是一部個人詞典:“我筆下的南方是一個小小的切片,是堅實具體的南方和情感虛擬的南方?jīng)_突構建下的個人詞典。我反對它僅僅是社會史、血淚史或統(tǒng)計數(shù)據(jù)。”[8]因此,在《詞典》中,他運用了個性化的語言,在常規(guī)的小說敘事語言之外,展現(xiàn)了散文體、詩歌體滲入和共存的獨特風格。
散文的語言風格通常靈動而自然,運用在小說中更能展現(xiàn)出形象的生活情態(tài)和細膩豐富的情感。在《詞典》中,蕭相風常采用散文化的語言,茶余飯后式的閑談,向讀者闡釋各個關鍵詞。同時,他也充分發(fā)揮了散文化語言優(yōu)美細膩的風格,比如“電子廠”一章中有這樣一段描寫:“熒光燈掛在低矮的流水線上,在夕照或月夜之時,遠望那些熒光燈,它們是新的夕陽或明月,懸在那工業(yè)的屋檐下嚶嚶地叫著,哼著。黃昏時的蝙蝠從瓦片下飛起,也是輕輕地打開聲音相似的電波。”[8]這句話運用了比喻、擬人、聯(lián)想等修辭手法,作者將流水線的燈比喻成浪漫的夕陽、明月,并感知到電燈發(fā)出的微弱的聲音,將其描述為纏綿的嚶嚶聲,將電波聲聯(lián)想成蝙蝠飛起的振翅聲。這句話融入了作者的親身體驗和個人情感,將電子廠流水線的工作場景描繪得溫柔寧靜,顛覆了讀者心中認為電子廠流水線工作枯燥無味的刻板印象,表露出作者細膩的心靈和生活化、感性的語言風格。再比如“老鄉(xiāng)”一章中的描述:“老鄉(xiāng)作為宗族文化的產(chǎn)物,它是從與血緣相連到與土地結盟的候鳥。在長途跋涉的遷徙里,可以相互呼喚,相互結伴并指引方向。從農(nóng)村到城市,老鄉(xiāng)是一個過渡的木船。”[8]作者將老鄉(xiāng)比喻成候鳥和木船,在從農(nóng)村到城市的過程中相互陪伴,幫助彼此適應新的環(huán)境,形象地表達出城市底層中老鄉(xiāng)關系的人情味。讀者能從文字中感受到蕭相風對生活細致入微的觀察力、輕盈浪漫的想象力和溫柔細膩的情感感知力。
蕭相風對詩歌也頗有興趣,著有《中國現(xiàn)代詩歌普及十講》,對詩歌的寫作手法、表達方式等頗為熟悉。在《詞典》中,他引入了自創(chuàng)的四首詩,用詩歌表達了對南方工業(yè)生活的切身感受,充滿真摯的生活體驗和蓬勃的生命氣息。在“沖涼”一章中,他引入了自己作的詩作闡釋:“記得兩千年到東莞/第一個落腳點是黃江/老鄉(xiāng)說,沖涼!/后來我才明白是洗澡//這個鳥地方/洗澡就洗澡/咋叫作沖涼//也對/一腔熱血壯志,很快/就被徹底地沖涼//”[8]詩歌簡明的語言不僅解釋了“沖涼”在生活中的常見含義,還借“沖涼”的多義表達了在南方工業(yè)生活中屢遭挫折的無奈之情,抒發(fā)自身情感,豐富了敘事和抒情的語言表達形式,增強了文本的張力,讀罷令人回味無窮。
3.內(nèi)容:超出“故事”的學術化趨勢
人們通常認為,小說最基本的功能是講好一個故事,但非虛構文學與生俱來的對真實“現(xiàn)場”的關注、對作者“在場”深入思考的期待、對社會功用的重視預示了它不僅僅滿足于講好一個故事。非虛構文學展現(xiàn)出向學術化發(fā)展的趨勢,故事似乎已不再是它的核心,非虛構文學的目光轉向關注,甚至是討論社會熱點話題,其切入點專業(yè)而深入,在展開講述時注重措辭的準確和符合事實,盡可能避免夸大或遮蔽。
《詞典》呈現(xiàn)出明顯的學術化趨勢。首先體現(xiàn)在小說故事線的弱化和人物的模糊化上。《詞典》的關鍵詞按照字母表排序,切斷了不同關鍵詞之間語義上的關聯(lián),削弱了文本中敘事的連貫性和銜接性,故事零散分布在文本的各個角落,呈現(xiàn)出片段化的特點,只為闡釋關鍵詞服務,成為詞語的注解。傳統(tǒng)小說常以人物塑造為核心,而《詞典》并非如此,其故事中的人物常沒有具體的姓名,僅以小Q等化名或甚至以簡單的“老鄉(xiāng)”代稱,人物面目模糊,缺乏立體的形象和鮮明的特征,只擔當演繹故事橋段、注解詞條的功能,在需要的時候草率登場,講解完詞條所需的故事內(nèi)容后便匆匆離場。其次還體現(xiàn)在討論話題的全面性和專業(yè)化上。《詞典》作者從自身多年工廠工作經(jīng)驗出發(fā),列舉了44個關鍵詞,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和工廠生產(chǎn)秩序直接相關的,如“ISO”(國際標準化組織)、“QC”(品控)等;一類是和打工日常生活相關的,如“集體宿舍”“食堂”等;一類是和整體社會生活相關的,如“流動人口證”“暫住證”等,較全面地涵蓋了打工群體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其對詞語的闡釋十分專業(yè)和嚴謹,比如在“流水拉”一章中,作者詳細介紹了“流水拉”的構造和使用方式,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拉長、助拉、物料員等崗位,近乎一本專業(yè)指導手冊。此外,在“打工詩人”一章,作者對打工詩歌的藝術特征、命名及其面臨的詩歌內(nèi)部話語權糾紛等問題進行了冷靜的審視和討論,批評了打工詩歌中對苦難直白、毫不克制的宣泄,以及在詩歌藝術上的自我限制和滿足,并表達出對打工詩歌中存在的“詩歌為個人私利打工”現(xiàn)象,即對某些詩人以打工詩歌揚名和自我包裝行為的批判,這些有深度的獨特思考也呈現(xiàn)出學術探討的基本面貌。
實際上,古代的“小說”本為瑣屑淺薄的言論與小道理之意,與論說、議論并不互斥。直到近代,中國小說吸納了西方文學理論,才將議論和小說截然分開。非虛構文學的學術化傾向似乎可以說是一種對中國小說傳統(tǒng)的復歸。余岱宗認為:“‘百科辭典式創(chuàng)作意識以及多種學科話語對現(xiàn)代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讓現(xiàn)代小說的文體呈現(xiàn)出多角度多方位地吸納各種學科知識的態(tài)勢。現(xiàn)代小說文體不再以單一的敘事路徑貫徹文本始終,而是不斷延伸出種種話題,讓小說創(chuàng)作的‘故事成為吸納多學科話語的載體,而不是讓多學科話語成為‘故事的附庸。”[9]非虛構文學的學術化傾向正好印證了這一觀點,不滿足于講故事的野心以及作者身份的多重性使它的文本獲得了豐富的含義和意義。
三、結語
選擇跨文體進行創(chuàng)作意味著要打破傳統(tǒng)文類秩序,勇于對傳統(tǒng)文類進行實驗性的探索和嘗試,這對創(chuàng)作者而言是考驗和挑戰(zhàn)。蕭相風從個人的感受出發(fā),自覺地進行跨文體創(chuàng)作,他的《詞典》是應對這場挑戰(zhàn)的一次有效嘗試。《詞典》體現(xiàn)出的跨文體特征印證了杜魯門·卡波特所說的“非虛構作品是一種既通俗有趣又不失規(guī)范的形式,它允許使用文學所有的手段”[10]。這種跨文體特征分別體現(xiàn)在結構布局、語言以及內(nèi)容上:詞典體小說的跨文體體式既能分門別類地展現(xiàn)真實生活,又能包含作者介入文學現(xiàn)場的思考;散文體、詩歌體的滲入在小說中增強了文本的抒情功能,豐富了文本的個性化色彩;小說超出“故事”的學術化趨勢則使文本成為吸納多學科話語的載體,賦予文本更豐富的價值和意義。文體的多樣化表達使小說成為意義豐富的復合符號空間,打開了文學發(fā)展的新視野,同時也帶來創(chuàng)作手法的革新,為文學的發(fā)展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
參考文獻
[1]? ?王暉.現(xiàn)實與歷史:非虛構文學的獨特敘述[J].當代作家評論,2017(1).
[2]? ? 王暉.“非虛構”的內(nèi)涵和意義[J].杉鄉(xiāng)文學,2011(6).
[3]? ? 丁曉原.報告文學,回到現(xiàn)實大地的行走——《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二〇一〇年紀實文學》序[J].當代作家評論,2011(1).
[4]? ? 張文東.“非虛構”寫作:新的文學可能性?——從《人民文學》的“非虛構”說起[J].文藝爭鳴,2011(3).
[5]? ?李云雷.我們能否理解這個世界?——“非虛構”與文學的可能性[J].文藝爭鳴,2011(3).
[6]? ?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chuàng)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7]? ? ?留言[J].人民文學,2010(2).
[8]? ? 蕭相風.詞典:南方工業(yè)生活[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1.
[9]? ?余岱宗.百科辭典式的創(chuàng)作意識與現(xiàn)代小說的文體變革[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6).
[10]? 霍洛韋爾.非虛構小說的寫作[M].仲大軍,周友皋,譯.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
(責任編輯 陸曉璇)
作者簡介:劉雅芳,武漢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