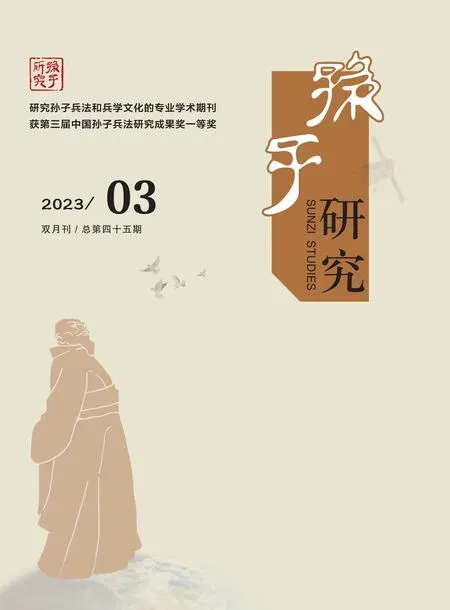周、鄭葛之戰析論
張賀森
東周初年,鄭國同晉國一起輔佐周平王東遷,在周邊諸侯國尚未崛起時,走向周王朝的權力中心,成為周王所依憑的重要諸侯國。鄭國國君武公、莊公先后擔任周王室執政卿,在實現鄭國東遷、穩定內政后,實力發展迅速,儼然有“小霸”之勢。同時,周邊諸侯國的情況是:“西邊的秦國正在與戎人酣戰,無暇東顧;晉國內部權力爭奪不斷,同樣無暇對外擴張;當時楚國也忙于掃蕩漢陽諸姬的小國;東方大國齊國,齊襄公昏庸無能,內部矛盾重重,國力不強,同時還受到西邊‘公交車千乘’‘公徒三萬’的魯國的有力阻擋。”〔1〕日后相繼稱霸的幾大諸侯國此時尚無力角逐掌控中原的權力,而鄭國國力的強大也對周王君權形成了挑戰和威脅,故莊公之時周平王即在政治抉擇中開始疏遠鄭國而向西虢靠攏。這一過程從“貳于虢”逐步發展到“奪鄭伯政”,二者關系更是從東遷之初的“晉鄭焉依”向“周鄭交惡”乃至“交戰”發展,其中矛盾最為激化的表現即為周、鄭“葛之戰”。因此,發生在春秋初年的周王室與諸侯國之間的戰爭,在周代乃至先秦戰爭史上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意義,其中的細節、內涵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戰前周、鄭關系的發展演變
據《國語》記載,“鄭武、莊有大勛力于平、桓;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韋昭撮述鄭國之功勞曰:“幽王既滅,鄭武公以卿士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桓王即位,鄭莊公為之卿士,以王命討不庭,伐宋,入郕。”“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勠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2〕《左傳·隱公六年》亦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3〕。清華簡《系年》記載晉國迎立平王東遷時,也提到“鄭武公亦征東方之諸侯”〔4〕。鄭國在周王朝東遷中發揮作用也是較為明顯的。可見,春秋時期人們是認可鄭國對周王室的貢獻的。同時,也就在鄭莊公時期,周鄭關系開始發生變化,這集中表現在交質、交惡、易田、爭土等一系列事件中。
(一)周、鄭交質
鄭國在周王室東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武公、莊公二世都被任命為執政卿,足見東周初年王室對鄭國的信任和倚重。鄭國君主兩世為卿,權柄之重,也令周王不安,故平王五十一年(前720),“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5〕從《左傳》記載可知,鄭莊公雖為王室卿士,但他的強勢和專權也令身為周天子的平王忌憚不已。平王雖然想以虢國制衡和分散鄭國國君的卿士權力,但這種行為招致了鄭莊公的怨恨。不僅如此,作為卿士的莊公還敢僭越以質詢周平王,而在面對質問時,平王僅以“無之”兩字作答,慘淡無力,天下共主的威嚴不存。為了安撫和取信鄭國,周王室還與鄭國交換“質子”。《荀子·大略》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楊倞注曰:“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能固 也。”〔6〕這也點出了周、鄭交換“質子”的實質是二者之間互不信任,雖交換人質,但并不代表他們親密無間。從歷史進程看,“周鄭交質”是王室與諸侯之間相互交換質子的開端,這種僅存在于諸侯之間的政治活動打破了身份與地位的限制,不僅一定程度上削弱和挑戰了周王的權威,也使得諸侯與周王朝之間的力量和地位悄無聲息地發生了轉變。〔7〕至此,曾經“晉鄭是依”的鄭與周王間的關系出現了不可彌合的裂隙。
(二)周、鄭交惡
周桓王繼位后,延續平王分化、削弱鄭莊公卿士權力的政策,遂有“周人將畀虢公政”的政治試探。桓王擬任命虢公為卿士的舉動,讓鄭莊公感到危機,這隨即招致了鄭國的報復,即莊公派兵搶奪了周王室的糧食。《左傳·隱公三年》記載,“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楊伯峻注曰:“四月,夏正之四月,麥已熟,故鄭人帥師割取之。”“秋,亦是夏正之秋。”〔8〕鄭國抓住時機,兩次派人在王室糧食成熟之際奪取糧食。糧食在任何時候都是重要的物資,對于個人生活和國家戰略極其重要。〔9〕鄭國奪取王室麥、禾的行為,給予周王室以經濟懲罰,因為糧食的減少對于王室賦稅以及物資供給、消費和穩定都有不小的影響。此次王室的試探仍以失敗告終,他們也沒采取對鄭國的反制措施。一方面,周王室可能出于平王喪禮的原因沒有出兵。《左傳·隱公元年》曰“天子七月而葬”,這一點石井宏明已指出:“如果東周王朝在‘隱公三年’的事件中沒有反抗的原因只是懼怕鄭國的軍事力量的話,其后東周王朝的活動就不好解釋了……周王朝沒有反抗的原因不只是懼怕鄭國,最重要的是‘隱公三年’平王去世,《春秋經·隱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由于這件事情,當時周王朝沒有余暇對付鄭國。”〔10〕《司馬法·仁本》曰:“戰道:……不加喪,不因兇。”〔11〕此即先秦的戰爭之道,要求不趁敵人國喪和兇荒時去進攻它,這樣做是體恤對方的民眾,體現了戰爭的仁義之處。反過來說,處于國喪的國家一般也不會主動發起戰爭。同時,天子之喪禮禮節繁復,所需時間長,在以禮樂文明相尚的周代,非常重視喪禮,作為周禮的倡導者的王室,堅持完成儀式的意義,比應對鄭國割取糧食更為重要。另一方面,周、鄭雙方仍在禮制的框架內制造摩擦,周王室借著平王喪禮削弱鄭莊公的卿士權力,鄭國則借著國喪縱兵奪取王室糧食,他們都沒將沖突放在正式層面上,也都還沒有將緊張的關系訴諸武力,實則是雙方在禮樂制度下一場隱晦的角力。當然,從此前平王面對莊公質詢的表現推斷,周王室沒有立即展開反制以維護王室威嚴,可能也有周王忌憚鄭國實力的因素在內。然而,這次雙方較量的影響甚大,《左傳》以“周、鄭交惡”四字書之,鄭國在桓王三年(前717)才前去朝覲,未得周王禮遇,故在周桓王五年(前715)魯、鄭易田事件后,周王室任命虢公忌父為右卿士,平王時分化、削弱鄭國國君在王朝中樞權力的布局至此實現。
(三)鄭、魯易田
周代禮樂文明之破壞,自姬周內部始,周王行事率先不遵儀軌,遂有諸侯相繼而起挑戰禮樂制度。以桓王五年(前715)魯、鄭易田為例:“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12〕周王室將祊地封予鄭為助祭的湯沐邑,然而隨著王室衰微,放棄了泰山之祭,《史記索隱》解釋道:“祊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祊易許田,各從其近。”〔13〕楊伯峻先生也在注解中指出鄭、魯“祊、許”之易出于周王室廢泰山之祭的可能性。若非如此,假如在王權強大、禮樂制度嚴整的時候,僅憑魯、鄭兩諸侯國公然置換王室賜予的祭田,無疑是對禮樂體系的絕大挑戰,這種行為帶來的后果自是非常嚴重的。盡管泰山之祭已廢棄,魯國也沒敢立即答應鄭國交換的請求。直至桓王九年(前711),“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14〕。至此,歷時五年的鄭魯易祊、許祭田之事方才算告一段落。鄭、魯兩國繞開了周天子而進行土地置換,從深層上看也是王權松弛、對諸侯控制和影響力減弱的表現。吳愛琴先生認為,“鄭國的做法表明不從王祭祀及朝王,意即現在的天子已沒有能力祭泰山及接受諸侯的朝 拜”〔15〕。雖然天子廢棄泰山祭祀、實力衰落是事實,如《左傳·隱公十年》所言“王室而既卑矣”,但這也沒表明周王失去諸侯朝拜的資格,至少終春秋之時,諸侯“尊王”仍是時代之大義。
(四)周、鄭土地之爭
繼周鄭交質、交惡,鄭魯易田等事件后,周王室還在次年任命虢公為執政卿士之一,分散了鄭國國君作為王室卿士的權力。春秋時期,人們對土地等資源的重視程度進一步增強,有所謂的“土地國寶論”〔16〕,即《左傳·成公六年》所言“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而成熟的土田則更是國家生存賴以依靠的資源。在桓王八年(前712),周王室還從土地方面入手,以削弱鄭國的經濟實力,這也是二者關系走向破裂的一大 因素。據《左傳·隱公十一年》載:“王取鄔、劉、、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樊、隰郕、茅、向、盟、州、陘、、懷。”〔17〕這次周王室主導的土地“交換”有著深刻的政治目的和隱喻在內。清華簡(陸)《鄭文公問太伯》簡7 曰:“及吾先君武公,西城伊澗,北就鄔、劉,縈軛、邘。”〔18〕鄭國的鄔、劉、、邘四邑不是周王室分封賜予的,而是鄭武公時期一步步開拓而獲得的,對鄭的政治意義極其重要。從現實層面看,周王置換鄭國四邑,解除了鄭國西部、西北部的防守態勢,損害了鄭國的經濟利益,進而對鄭形成了新的戰略威懾。周王室置換給鄭國的十二邑中的溫、原、、樊、向、盟、州、陘等都將處在被周的新獲四邑分割中,戰略威脅意圖明顯。此外,周桓王用來置換鄭國四邑之田的溫、原等十二邑,并不完全屬于周王。其中,樊、向已分別在宣王、幽王時期改封給仲山甫、皇父,溫地可能還在蘇氏手上。王室在這些地方具有產糧之田〔19〕,與鄭國聯系緊密的四邑相比,周王拿出的土地位置較為分散,且還需跨黃河而在東北境處理農事,反而比之前更不便。鄭國即使完全擁有此十二邑,也很難對其實行有效的治理,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鄭與其他諸侯國的邊境緊張關系。周桓王此次易地之舉,與其天下共主的身份不符,也令他飽受爭議。《左傳》編纂者批評道:“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杜預注解道:“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為桓公五年從王伐鄭張本。”〔20〕總體來看,周、鄭土地之爭是由周王室主導的,鄭國則處在被動的位置,這也表明此時周天子手中所擁有的權力還是不小的,其在政治、經濟方面仍對諸侯有較強的約束力和控制力。〔21〕在周鄭土田之爭前后,鄭、魯還交換許和泰山祭田,周王易田也可能是王室從經濟上對鄭國私自交換祭田行為的懲罰。
周、鄭矛盾經過累積,終于在周桓王十三年(前707)爆發。其一,是年夏,周桓王褫奪了鄭莊公卿士之權,莊公因之不朝王。其二,是年秋,桓王召集虢公、周公及蔡、衛、陳等諸侯國征伐鄭國,戰爭正式爆發。至此,周鄭關系徹底走向決裂。其三,周鄭“葛之戰”也。至于戰爭的詳細經過,《左傳·桓公五年》有記載:
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御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后伍,伍承彌縫。
新近整理刊布的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簡7-8 也對鄭莊公史事有所記載,其中即包括“葛之戰”:
世及吾先君莊公,乃東伐齊酄之戎為徹,北城溫、原,遺陰、鄂次,東啟、樂,吾逐王于葛。〔23〕
相較于《左傳》而言,清華簡的記敘是非常簡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逐王于葛”之前,還有“北城溫、原,遺陰、鄂次,東啟發、樂”的鋪墊,分別指周、鄭易田(溫、原等十二邑),曲沃代翼,開發“”(周王用以交換的蘇忿生田)“樂”之地,旨在說明鄭之所以“逐王于葛”,是由于桓王步步緊逼所致。〔24〕這則資料的出土為人們認識“葛之戰”提供了史料上的支撐。當然,要詳細認識和剖析這場戰爭,仍當以《左傳》為主。
鄭國被迫卷入同周王室的戰爭之中,鄭人雖然處在被動作戰的境地,但鄭公子元在戰前謀劃、戰時軍陣、策略運用等方面均十分成功,打敗了以周王為首的蔡、衛、陳聯軍。面對桓王率領諸侯聯軍的攻勢,公子元在分析聯軍內部情況后,指出“周王軍隊本身是比較強的,但是陳、蔡、衛這幾個仆從的諸侯國軍隊戰斗意志、戰斗力是比較弱的,先打敗這幾個弱敵,再集中兵力包圍、合擊王軍,就可以取得勝利”〔25〕。莊公采納了他的意見并進行了有針對性的部署。
首先,鄭國采用以方(拒)陣和“魚麗之陳”相結合的戰陣迎戰敵軍。鄭派祭仲、曼伯分別為左、右拒,原繁、高渠彌為中軍拱衛莊公,采用“魚麗之陣”對戰周天子所在的中軍。“魚麗之陣”的“魚麗”指的是戰陣形態,楊英杰先生認為“考其形應如‘魚麗于罶’之 ‘罶’”,即為“大口、窄頸、腹大而長的撲魚竹籠。即是說魚麗之陣應是兩頭大而中間細的戰陣”。〔26〕《左傳》記載其特點是“先偏后伍,伍承彌縫”,杜預注引《司馬法》“車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缺漏也”〔27〕,即戰車居前,步卒居戰車側后彌補兩輛戰車間的縫隙。對于這種陣形,楊先生還引《武經總要》“罘置前后橫,中央縱,張其四翼,利于相救”,即“前后為橫隊,中間為縱隊,形如‘工’字 。縱隊兩側的橫隊如翼”〔28〕。此陣形適應了復雜的戰場環境,實現了車兵步卒協同作戰,便于彼此呼應,有利于戰場攻防。其次,注重金鼓、旗幟在軍事指揮中的作用。《左傳》記載鄭國以大旗為號,擊鼓進兵,“金鼓旌旗”的作用如《孫子兵法·軍爭篇》所言“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六韜·虎韜》曰“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 音”〔29〕。此即要求行軍作戰中,哨兵手持旗幟,通聯營壘內外,以相互傳遞信號,同時要保證傳遞信息的金鼓之聲不要斷絕,保證信息傳遞的通暢。再次,集中優勢兵力擊潰敵軍主力。鄭國按照戰前既定的方針,先以左、右方陣將周桓王左、右軍的蔡、衛、陳諸侯聯軍擊敗,而左、右翼的潰軍在潰逃時,引起中軍混亂,鄭國左、右方陣遂與莊公所在的中軍對周王中軍形成合圍,在力量對比上,形成了局部優勢兵力,周軍最終被打敗。這種安排符合《孫子兵法·虛實篇》講求的“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30〕。周軍戰場失敗,就連桓王也被祝聃射中了肩部,但他還能統兵作戰。祝聃向莊公請求去追逐桓王,此時鄭莊公及時阻止了這個行為,并將戰爭定位為“自救”,當晚還派祭足去慰問周王及其臣屬,以緩和雙方緊張的關系。鄭國國君審時度勢,在自保的基礎上,處理此次戰爭后續問題時,盡可能地維護了周王室的權威。至此,周、鄭“葛之戰”以鄭國勝利而結束。
作為周王發動的一次征討諸侯的戰爭,它既是東周時期周王室和諸侯間的矛盾,也是周王同執政卿之間矛盾激化的表現,亦如克勞塞維茨所說,“戰爭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31〕。面對日益坐大的鄭國,王室出于維護自身的權威和統治地位的需要,遂開啟了一場討伐鄭國的戰爭。周、鄭“葛之戰”首開天子與諸侯交戰的先河,此戰之后王室的權威進一步衰落,諸侯的權威日漸興盛。而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這場戰爭雖是王權對諸侯挑戰的回應,最終以王權的失敗而告終,又呼應了“諸侯爭霸”時代的到來。相對于主動發動戰爭的周王室來說,鄭國對這次戰爭的處理是非常得體的。盡管為了自衛,鄭人也向周王室的聯軍發起反擊,但他們將戰爭的影響降到最低,基本上維護了周王的臉面。畢竟鄭國的權威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來自周室的王權,“尊王”有助于鞏固鄭國的權勢和地位。縱使周、鄭雙方兵戎相見,鄭仍出于周禮“尊王之義”,迅速地控制戰爭的規模,減輕戰爭的影響。同時,“鄭國打敗周王以后,勢力格外強盛……鄭國當莊公時代,憑借‘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采用了‘遠交(交齊、魯)近攻(攻宋、衛)’的政策,努力經營,‘國際’地位就蒸蒸日上。到了莊公末年,幾乎就成為春秋最初期的伯主”〔32〕。而在“葛之戰”后,鄭國經受住了政局動蕩帶來的考驗,其后鄭又幫助齊國等抵御北戎侵犯,維護姬周正統,得到了諸侯的認可,實力臻至鼎盛,成為春秋初期的小霸。
盡管鄭國已采取積極措施應對戰爭帶來的消極影響,但經此一役,周王室的戰敗已然使得王權威嚴掃地,此后周王再也沒有實力征討諸侯,其政治、軍事影響力也隨著戰敗而急劇萎縮。其實,早在周王室平定攜惠王和東遷之后,實力已大不如前,加之東遷后封賞諸侯以土地,更是削弱了周室的國力,經濟上也只有依賴諸侯國的貢賦才勉強得以維持日常運轉,故早在周桓王八年(前712),鄭莊公就已認識到,“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天而既厭周德矣”〔33〕。這種觀念上的變化,說明曾經強大的周王朝已經日漸萎靡,姬周封國體系內部也日漸喪失統緒,就連上天都厭棄周的德行。這種思想觀念的背后,折射出春秋時期隨著諸侯國實力的膨脹,已經形成“本小而末大”的格局,如晉國僭越等級行使了天子才擁有的“建國”之權、曲沃代翼“小宗”取代“大宗”等,皆在不同層面上瓦解了周王的君權。而周王室征討鄭國的“葛之戰”的失敗,也使得早先“眾星拱之”的周天子跌落神壇,繼鄭國之后的其他諸侯國看清周王室的真正的實力,進而在春秋五霸崛起的過程中,專屬于天子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向“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變,春秋晚期更有卿大夫的權勢興起,甚至還出現“陪臣執國命”的局面。凡此,均在進一步地瓦解周王的權威,直至專制君主時代的到來而最終廢除了周王、斷絕了周室的國祚。〔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