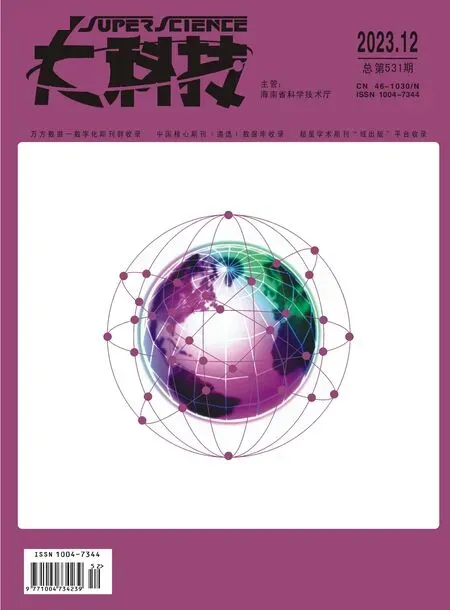小微城市公共開放空間設計改造的在地性策略研究
李蔚
(重慶工商大學藝術學院,重慶 400000)
0 引言
小微城市公共開放空間改造是當下城市建設的熱點之一,它是符合當下的社會發展背景的建設模式,也已經涌現了很多實踐項目。數量雖多,但質量參差不齊,脫離社會需求與場地記憶,缺乏社會人文關懷,是這類小微城市公共開放空間改造所面臨的一個現實困境。在地,可以成為一種研究土地、解決問題的有效手段。將在地性設計拆分成個4 層面:①土地的層面,公共空間的載體。②人物的層面,公共活動的載體。③事件的層面,公共記憶的載體。④管理的層面,公共參與的載體。且每個層面都在時間尺度上相互聯系。研究以渝中區白象街心公園為研究對象,以在地性的角度進行了長期的觀察研究,歸納了在地性改造策略的要點,為未來的城市開發改造提出了一種可行的思路。
1 研究背景
城市公共開放空間作為城市公共生活的舞臺與城市文脈的空間載體,涵蓋了街道、公園、廣場甚至一些城市空地與縫隙空間,是城市空間中最具活力的場所,也是城市改造研究與實踐的重點,如地理學、社會學、建筑學、風景園林學等不同學科均對城市開放空間有大量的研究。基于現階段存量式發展的城市建設背景,大尺度新建城市開放空間已經難以見聞,見縫插針式的小微公共開放空間設計以及其改造更新項目逐漸增加,這是現階段城市更新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城市新陳代謝的必然過程,即由點帶面的微更新模式。
2016 年,住建部啟動“社區空間微更新計劃”,通過活化社區內部的閑置用地,整體提升老舊區域的生活舒適度[1]。這一計劃把與日常生活聯結最緊密的小微社區公共開放空間作為抓手,靈活目標,提倡公共參與。目前國內已經有豐富的微更新實踐,這種模式符合我國國情,是持續、漸進的更新[2]。
2 小微城市公共開放空間改造的困境
從空間分布上來說,小微城市公共開放空間散布在街頭巷尾的城市肌理中,分布廣泛且呈片段式;從需求來說,這類空間的使用率極高,且往往呈現出多功能復合的特性。這就造成了現階段小微城市公共空間改造的一個困境——量大但質量參差。
微更新常見的低成本、短周期模式,有時演變成簡單粗暴的拼貼設計,例如,不分場合的通通加入健身器材,一味增加綠量,批量化且無意義的場地雕塑等。以此為代表的粗糙設計將場地指標化、同質化,降低了場地的利用率,抹殺了場所的獨特性。從使用需求來看,居民對公共開放空間的需求不僅停在物質層面,還有精神層面,部分改造設計只片面強調地域性自然材料、當地氣候與建造工藝,設計語匯徒有其表,空間構造猶如打補丁,無法表達地方依戀需求與場所精神。小微城市公共開放空間改造設計需要質量的提升。張萍等[3]提出,在地性敘事在被忽視的人居生態環境中,以文化符號、民族歷史等藝術直覺導向的設計方法研究就尤為必要。這也是解決小微城市公共開放空間改造困境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強調改造設計的在地性,并以此為基礎進行場地的調查分析與設計,制定在地性改造策略。
3 在地性設計的4 個層面
全球化發展背景下的地域文化的興起,激發了設計者對地域特征的強烈追求,地域性強調區域的整體特征,對場地尺度的微小特征研究不夠深入。在地性區別于地域性,強調場地本身的獨特性而非區域共性的總結,尺度更小更精準,以一種“在現場”的方式進行設計研究。20 世紀90 年代已有臺灣建筑師在“社區總體營造”中進行了在地性的研究[4],此后內地建筑師受其影響,以在地設計理論的特征和方法為出發點進行在地實踐的相關研究。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王路教授[5]在《在地:華黎的建筑之道和他的建造痕跡》文章中也表達了對“在地”的見解,他認為所謂的“在地”是指在地實踐的建筑應將現代技術、民風民俗和群眾生活結合在一起,使建筑融入群眾的生活之中,猶如在該土地生長出來一般,并且在當地養分的滋養下不斷地成長和發展。在地性創作手法是基于地方的生活、公民的參與所產生與當時政治條件和社會經濟平衡的產物,所以需要對特定的地方和地點特征理解,然后歸納出它深層價值觀[6]。
從藝術創作的視角來看,在地性改造設計的關鍵在于土地與時間,以及人物與事件,即以一種扎根現場土地的狀態進行長期性的、周期性的在地觀測,深入挖掘場地的獨特性,力求在設計改造中將真實的社會需求反饋到土地上[7]。因此,每個場地的在地設計手法都是獨特的,是場地特性與社會人文集結與此的精準表達。對社區的小微開放空間而言,生動的在地生活是改造的良好基礎。
可以將在地性設計拆分成4 個層面,每個層面都在時間尺度上進行表達,如圖1 所示。

圖1 在地性設計的4 個層面與時間尺度
具體如下:①土地的層面。土地是公共空間的載體,也是場地的物質面,包括地形地貌、氣候環境、動物植物等要素,是場地對自然的回應。②人物的層面。空間是公共活動的載體,猶如舞臺上演各色人群朝夕往復的生活,社會生活得以鮮活真實的反饋在空間中。③事件的層面。場地是公共記憶的載體,包括了祖先記憶、父輩記憶、兒時記憶等,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在空間上的縮影。④管理的層面。場地的能量流動與運轉是全體公共空間使用者公共同參與的結果,每一次場地“組織-營建-維護-改造”的循環的背后,都有公共參與這只無形的推手,既可以是自下而上的推進,也可以是自上而下的推進。此外,每個層面并不孤立,在時間尺度上相互作用聯系。
4 場地分析策略
基于在地設計的4 個層面,研究設定渝中區白象街心公園為對象,從在地性的角度進行了長期的觀察研究,總結歸納了在地設計策略,可以成為后續城市更新的一種思路。
白象街心公園位于重慶市渝中區望龍門社區,解放東路——白象街兩條道路交叉口,兩條城市道路相夾形成了略南北向長三角形的用地形態。白象街心公園是一個典型的口袋公園,場地面積約2500m2,南北向長約85m,東西向最寬處約40m。白象街心公園所在的解放東路沿線分布著大量的歷史文化建筑,向南連接了象征著重慶開埠時期經濟中心的白象街歷史文化風貌區(圖2),象征著傳統城市營建文化的人和門、太平門、鼓樓等遺址公園,向北連接著象征移民文化與開埠文化的東水門-湖廣會館歷史文化風貌區(圖3),白象街心公園與重慶母城眾多地標名片均在10min 步行范圍。白象街心公園的歷史文化屬性明顯。白象街心公園周邊界面豐富,有商住混合的老舊高層住宅樓群,以零售和餐飲業態為主。此外,場地對面現存一處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聚興誠銀行舊址(圖4);場地在白象街一側臨白象居大型生活社區(圖5),白象居由六幢塔樓構成,每棟24 層,但因其多標高的接地方式以及貫通的公共交通廊而沒設電梯,其獨特的建筑與山地高差的結合方式極富山地建筑魅力,成為城市旅游的新打卡點。

圖3 湖廣會館歷史文化風貌區

圖4 聚興誠銀行舊址

圖5 白象居
在土地層面,記錄并關注場地所有物質層面。例如,場地的地形條件呈現出西南高、東南低的態勢,制高點與最低點高差達到3.6m,現狀以綠化放坡的手法簡單的解決了高差,反映出場地設計的粗糙。場地有具有地域代表性的大喬木——黃葛樹,且呈現出有趣的季節變化,夏季豐茂,冬季進行修剪后呈現明亮的空間效果。此外,場地以大量的硬質鋪裝為主,缺乏層次。
在人物層面,記錄場地中活動的各類人群與各類活動,形成人-空間-活動的關系表。人群的活動頻率呈現出高密度、高強度的特性,活動類型呈現多元性、復合性,空間分布呈現自發性、依靠性,活動人群涵蓋全年齡段。在長達一年的觀察調研中發現,廣場活動人群有明顯的領域性行為,例如不同的舞蹈隊伍固定占有場地不同的區域,樹下空間長期被打牌下棋的居民長期占用,這類人群會對領域產生防衛行為如驅趕陌生人等;由于廣場的座椅類設施不足,人群會自發的攜帶板凳占領空間,插牌或旗進行空間個性化的標注。
在事件層面,采訪并記錄作為使用者的周邊居民對場地的各種回憶。在調查研究中發現,白象街心公園的場地記憶可以追溯到白象雕塑的傳說,“青獅白象鎖大江”的傳說以一種口口相傳的形式進行傳承,部分老年使用者清晰的口述這一故事,對場地中有白象雕塑表示十分自豪。白象街心公園的地標性雕塑如圖6 所示。此外,場地承載了城市建設的變遷記憶,關于老渝中曾經繁華的下半城的上山下水、爬坡上坎、大碼頭的集體記憶,關于城市快速開發帶來的消失的白象街與大量建設商品房的集體記憶,以及關于空間老化衰落的不甘和城市旅游興起的帶來突然的人氣的驚訝、欣喜、煩惱等情感。

圖6 白象街心公園的地標性雕塑
在管理層面,場地的公共參與潛力巨大,在走訪中發現老舊社區的改造意愿明顯。
由此提出對場地的設計改造目標:在物質層面,保證場地原生活動的持續性,打造全年齡友好與無障礙的社區公共生活空間;在非物質層面,回應集體記憶,用解構、拼貼、隱喻的方式,調動五官感覺,將文脈的承接反應在景觀中,增加民俗與商業活動形成有記憶點的場所,延續場地在時間尺度上的活力。
5 結語
伴隨著更為復雜的世界環境,風景園林學科所面臨的研究與實踐不僅要著眼于曠奧的“庭園”和“園林”室外空間環境,還要面對氣候與生態環境、綠色基礎設施與建成環境、公共空與全人類福祉、國家公園評價與管護等宏大行動,致力于解決社會文化自信、民族歷史與藝術發展、場所認同與依戀等諸多問題。小微城市公共空間的改造設計這一類型的項目,以小見大,用在地性去解決社會文化、歷史、藝術的傳承與發展,同時為民生幸福提供助力,在地性設計改造策略為未來的城市開發提出了一種可行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