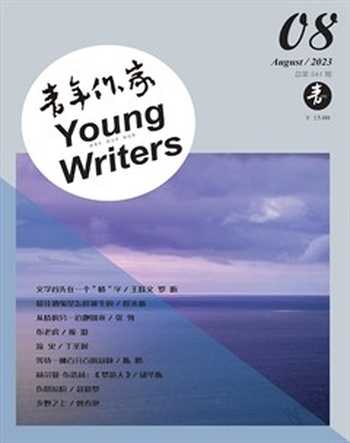走進(jìn)同一條河流
一
如果一個(gè)村莊有一條河流,有一條像荊河那樣,把宋家泊村半抱在懷里的河流,那么村莊里的每一個(gè)人,包括每一個(gè)牲類,每一棵莊稼,背依河流的庇護(hù),勤勞、生長(zhǎng)、檢點(diǎn),遵循著村莊的品格和原則,從不打破一條河流和人類之間相守相在的默契。
村莊與河流,水土交融呀。一個(gè)女人卻因?yàn)榍О倌陙?lái)的風(fēng)俗,從一個(gè)村莊來(lái)到另一個(gè)村莊,從一條河流來(lái)到另一條河流,都是掙脫不開的命運(yùn)。嫁一個(gè)好男人,做夢(mèng)都會(huì)偷著樂(lè);嫁一個(gè)二郎八蛋,一輩子都是一地雞毛。
姥爺當(dāng)過(guò)封家?guī)X村長(zhǎng),當(dāng)過(guò)浯河區(qū)區(qū)長(zhǎng),終因大字不識(shí)前程到此為止。母親與父親相識(shí),難道是姥爺做的媒?父親退伍后來(lái)浯河區(qū)工作。姥爺看中了父親的哪一點(diǎn)?肯定是可憐他孤身一人。
封家?guī)X老村,無(wú)獨(dú)有偶被渠河半抱著。1974年發(fā)洪水,老村才從渠河沿上搬到206國(guó)道邊。對(duì)老村,我只有模糊的記憶,甚至記不清姥娘家的門口,因?yàn)槟菚r(shí)我只有6歲。秋末,所有的莊稼顆粒歸倉(cāng)后,空氣里的味道有了一些改變,除了炊煙的味道,就是牲口糞的味道,如果還有就是風(fēng)的味道,一股股粗喇喇吹來(lái),村里的男人立馬在家準(zhǔn)備繩子、鐮刀和小車,不用問(wèn),要準(zhǔn)備收樹行子了。封家?guī)X總是捷足先登,我和大姐被大舅家的表姐提前一晚叫去,大姐是主力,我是湊熱鬧的。渠河灘比荊河灘寬,槐樹、楊樹、平柳、栗子、棉槐條子、蠟條,還有很多叫不出名的植被,唯一多的就是一片片的細(xì)荻,淡紫淡紅的荻花,在渠河的水聲里飛舞著。荻稈收回去做箅子,荻花塞到棉鞋里取暖,還有拿回去做枕芯的。
每一個(gè)女人不過(guò)被動(dòng)地按照祖輩的生活方式生存下去。17歲的母親從渠河邊上的封家?guī)X,嫁到荊河南的六爺家,據(jù)說(shuō)是用父親給的高粱換回了我的大妗子,這樣說(shuō),姥爺就不是單純可憐父親,他內(nèi)心里同樣隱藏著貪婪,當(dāng)然更多是無(wú)奈。和我爺爺是親兄弟的六爺,招贅到一河之隔的曹家泊,同意母親進(jìn)門,同樣是因?yàn)榧Z食,還有父親那點(diǎn)退伍金和寡淡的積蓄。當(dāng)時(shí)部隊(duì)給了多少糧食,主人公早就遠(yuǎn)去,很難搞清楚,再說(shuō)能有多少呢?
姥爺也許覺得對(duì)不起父親,給他們準(zhǔn)備了回宋家泊蓋新房子的梁檁木料,六奶正好借此給大叔蓋了新房。當(dāng)父親的糧食財(cái)物和母親的陪嫁完全被六奶據(jù)為己有,六奶就不是原來(lái)的六奶,她的心變了顏色,只要到了飯點(diǎn)就罵罵咧咧,若是父親不在家,只要母親拿起一個(gè)地瓜煎餅,就會(huì)啪的一筷子打掉原本在姑姑手里的飯食,指桑罵槐。母親在晚上點(diǎn)著煤油燈想做點(diǎn)針線活,六奶躲在母親的窗戶下學(xué)鬼叫,直到母親吹了燈嚇得蒙到被子里。黑暗中,母親瑟瑟發(fā)抖,冰涼的土炕上,她做夢(mèng)都想回自己的老家。
也許荊河是母親回家的唯一通道,每次來(lái)河里洗衣裳,母親都會(huì)癡癡地望著對(duì)岸,它延伸著母親對(duì)生活最大的希望。滴水成冰的冬天,父親去城里開會(huì)順便回家添件衣裳,看到母親癱坐在石磨旁,她從凌晨?jī)牲c(diǎn)就起來(lái)獨(dú)自推煎餅,她的雙腳早就凍成了木頭。他把她抱到炕上,把她的腳放到火盆上,她已經(jīng)感受不到熱度了。無(wú)盡的絕望,像一波波河水,從母親的心里涌出來(lái),回宋家泊吧,至少有老少爺們幫襯著。
二
清晨,太陽(yáng)從荊河的水面上掠過(guò),水鴨撲棱棱飛起來(lái)。盡管母親不知道荊河從哪里來(lái),但姥爺告訴過(guò)她,荊河和渠河最后是匯集到濰河去的。僅這一點(diǎn),就讓母親哀愁的面龐上露出笑容來(lái)。終有一天,她和她的親人都會(huì)在濰河集結(jié)。父親和母親,都會(huì)變成荊河的守望者。
村里人提起母親,才多大呀,就受了這么多罪。他們剛回宋家泊時(shí),借住在和豬為鄰的放置犁耬耙具的閑屋里,說(shuō)是屋,其實(shí)就是一間敞棚子。母親不當(dāng)回事,過(guò)日子還有不受罪的?只要能有自己的家,吃再多的苦也值當(dāng)。
準(zhǔn)確地說(shuō),母親生了八個(gè)孩子。夭亡的兩個(gè)都是女孩,父親也算奇思妙想,給第二個(gè)女孩起名“女”,“女”是我們姐妹中長(zhǎng)得最俊的。她倆都被扔到荊河的荒阡子上,母親只要走近,就會(huì)聽到小孩的哭聲。兩個(gè)孩子在母親的歲月中,長(zhǎng)成了刺,長(zhǎng)成了流動(dòng)著的水。
幾年后,一個(gè)我叫叔叔的人偷走了父親的殘廢證,這個(gè)叔叔沒有爹娘,多數(shù)時(shí)間在我家吃住,他偷的不是殘廢證,而是夾在證里的十幾元錢。父親被撤掉貧協(xié)主席,有人上告說(shuō)他是假黨員……痛苦的父親溜達(dá)到荊河邊,河水嘩嘩流著,發(fā)出空洞的回響。我很難把父親與自殺二字聯(lián)系起來(lái),他在我們眼里太堅(jiān)硬了,就像一塊石頭。母親告訴我的一個(gè)細(xì)節(jié),又讓我對(duì)父親的堅(jiān)強(qiáng)產(chǎn)生質(zhì)疑,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說(shuō)他“假黨員”,哪里都可以假,唯獨(dú)黨員要一塵不染。他決意去闖關(guān)東,沒有錢買車票,就爬火車,卻摔下來(lái)跌斷了腿。回來(lái)母親都沒認(rèn)出他,滿臉灰塵,棉襖破了幾個(gè)洞,棉花向外翻卷著。
有一段時(shí)間,父親迷上賭博,家里僅剩的半斗高粱都被賭伴收去。母親抱著大哥回到娘家,姥娘給拾掇上吃的用的,讓小姨送回來(lái)。他一個(gè)孤苦孩子也不容易,從小參加革命,被人說(shuō)出假來(lái),心里能是個(gè)滋味?小姨送了一次又一次。她的一句話擲地有聲,沒有恁姥娘,你們這些小子還不一定來(lái)世上走一遭。從父親的身上,我再次驗(yàn)證了浪子回頭金不換說(shuō)得在理,在我們的記憶中,父親勤儉、守時(shí)、悲憫,做事做人都有原則。
我從小就是個(gè)喜歡幻想的女人。經(jīng)常在荊河北崖,勾畫出三間茅屋,院子里種植著夾子桃花和石榴樹,我和他坐在石凳上數(shù)著荊河上空的星星。要是哪天我被父母挨整,就添加上一條小船,和他一起沿著荊河出逃,我倆一個(gè)坐在船頭,一個(gè)坐在船尾,船上擠滿各種聲音,水聲、鳥聲、蘆葦搖動(dòng)葉子的聲音,小麥拔節(jié)的聲音。其實(shí),我最怕的就是母親的喊叫聲。
三
我太喜歡回憶了。回憶可以說(shuō)是我逃避現(xiàn)實(shí)的一種方式。我的現(xiàn)實(shí)世界,有時(shí)是一塊破碎的玻璃,有時(shí)是一句說(shuō)不口的話,這句話或許會(huì)讓我的人生翻個(gè)個(gè)兒。
若把人生比喻成一口井,盡管我只看到巴掌大的藍(lán)天,卻把念想放飛了出去。每年我都要回老屋幾次,那兩扇老舊的木門,手剛摸上去,眼淚就出來(lái)了。父親母親的手、哥嫂姐妹的手、鄰居的手、那只黑狗的爪子,還有那只花貓的爪子、小毛驢的蹄子,包括家里的每一個(gè)物件,都從這扇門里走出來(lái)又走進(jìn)去。推開門,滿院子都是父母的氣息,只要這個(gè)老屋還在,他們的氣息就在。
土從墻上落下來(lái),木格子窗戶只有住過(guò)這屋子的人還能看出藍(lán)漆的顏色,屋山墻裂開一道道大縫。我摸摸我們用過(guò)的桌子,摸摸母親用過(guò)的風(fēng)扇,從東屋走到西屋,恍惚間,耳邊吹過(guò)母親如羽毛一樣的呼吸。二哥喊著,你怎么敢進(jìn)去。老屋若是倒了,我的心就該徹底流浪了。
父親十三歲那年,在荊河邊遇到一支帶槍的隊(duì)伍,同行的小伙伴都嚇跑了,只有他留下來(lái),給隊(duì)伍指清楚要去的地方,從此,他就與隊(duì)伍建立了聯(lián)系,成了縣大隊(duì)通訊員。甚至可以說(shuō),荊河在某個(gè)節(jié)點(diǎn),把父親推向一條光明的道路。1946年的宋家泊戰(zhàn)役,因寡不敵眾,在得到命令時(shí),父親和幾個(gè)小戰(zhàn)士借助荊河樹林的掩護(hù),安全撤退。縣大隊(duì)和區(qū)中隊(duì),有多名官兵犧牲。每次來(lái)荊河,父親蹙起眉毛,那些在戰(zhàn)斗中犧牲的戰(zhàn)友,在他的心里,一直活著。
我家的幾塊地都在荊河灘上,憑父親的“干部”身份,是可以選好地塊的,當(dāng)時(shí)母親沒少發(fā)牢騷。直到今天,我才明白父親對(duì)荊河的感情。那些回憶,包括奶奶渡過(guò)荊河改嫁的辛酸,在父親的光陰里,都是痛呀。
每次寫到荊河,才覺得自己最像父親,他倔強(qiáng)的性格遺傳給了我,最重要的是那些信念,一輩子都不會(huì)改變。
父親在一塊田里從不單純地種植一種莊稼,要么種兩種,要么種三種,地頭上還要埋一些爬豆、紅豆種子。地里出現(xiàn)最多的往往是母親的身影。我高中畢業(yè)那年,南河灘上種植著花生、地瓜;東河灘上種植著玉米、高粱、大豆。秋假里掰玉米,一到天晌,母親就讓我回去做飯,吃了給她捎點(diǎn)來(lái)。這是她一貫的做法。我竟然一個(gè)人回了家,留母親在滿坡的玉米地里。收玉米的季節(jié)太陽(yáng)多毒呀,玉米葉子刷拉刷拉,劃在臉上像刀子。等我捎飯回來(lái),母親的臉曬得通紅,咕咚咕咚喝下半壺涼開水,地上攤著一堆堆黃玉米。
多少年后,母親在我的夢(mèng)里穿行,荊河灘上的玉米也在我的夢(mèng)里穿行。
四
兒時(shí)的荊河像童話。春風(fēng)刮過(guò)田野,荊河的精神從內(nèi)里迸發(fā)出來(lái)。布谷鳥抑揚(yáng)頓挫的叫聲回蕩著,慢慢地,布谷鳥的叫聲從荊河灘去了村莊,人們傳送著,該播種了。河灘上葉子細(xì)長(zhǎng)、葉廓上帶一絲紅邊的“簸箕柳”,隨著布谷的鳴叫,鼓著勁長(zhǎng)。孩子們掐下來(lái)一截做成柳哨,柳笛的聲音把春天所有的繁華推向高潮。大人采了簸箕柳嫩芽,揉捻、炒制成簸箕柳茶。麥?zhǔn)諘r(shí)節(jié),家家會(huì)燒上一大鍋,用水筲挑到地頭,茶香麥香攪合在一起,人們?cè)诹胰障聯(lián)]著鐮刀,喜上眉梢。母親總會(huì)在荊河灘上找到大片的篷子菜,回家焯了,用蒜拌著吃,有時(shí)也做成菜餅。篷子菜吃起來(lái),有點(diǎn)生硬的感覺,母親卻對(duì)它情有獨(dú)鐘。
荊河灘上的百草皆可入藥,哪個(gè)孩子不舒服,母親挖來(lái)蘆根、車車菜、婆婆丁、野茄子,熬水喝下,孩子又活蹦亂跳了。她把莎草的根莖挖出來(lái),用火燎去根須,曬干收藏起來(lái)。莊里的女孩月經(jīng)不調(diào),母親讓她們配著艾葉熬水喝,喝下去肚子也不痛了。她一個(gè)普通農(nóng)婦,竟然從大自然中找到中醫(yī)之道,都是被孩子多逼出來(lái)的。
到了夏天,香蒲、水蔥、蘆葦、薄荷、荇菜把荊河圍起來(lái),孩子們泥鰍一樣在河中心游來(lái)游去,用小抄網(wǎng)就能把鮮活的魚兒打撈上來(lái)。母親們?cè)诤舆呄粗律眩爸⌒难剑⌒难健臇|河拐個(gè)彎,南河里的水流子相對(duì)細(xì)一些,在父親的陪伴下,半個(gè)鐘頭就能拾一水罐米蛤蜊,拿回家洗凈,打雞蛋做湯,鮮美的味道會(huì)飄滿半個(gè)村莊。端午節(jié),從荊河里摘一抱葦葉,家家都包三角粽子,即使放進(jìn)粥里幾片,濃濃的粽香也會(huì)讓你立即“崩潰”。母親總忘不了將香蒲葉子和艾草一塊放在屋檐下,說(shuō)可以辟邪。盛夏的早晨,荊河灘被一層層的水霧籠罩著,低矮的灌木叢邊,到處是找幼蟬的孩子,回家的時(shí)候,長(zhǎng)硬翅膀的蟬兒吱吱叫著。
秋天的河水總會(huì)變瘦,那些香蒲卻蔓延成一片海。水鳥從蒲根處鉆出來(lái),天空綠得發(fā)亮。冬天的河水才真正安靜下來(lái),槐樹、柳樹、楊樹、榆樹掉光了葉,任憑人們欣賞一棵樹的骨感。這個(gè)季節(jié),對(duì)于母親來(lái)說(shuō),是種煎熬。大姐經(jīng)常瞞著父親,和村里的一個(gè)姐姐去東河拾干樹枝子,樹行子那時(shí)是公家財(cái)產(chǎn),掉落的樹枝也不能拾。可燒火柴又是燃眉之急,大家想盡各種辦法鉆進(jìn)樹行子摟草,拾樹枝。
母親擔(dān)心兩個(gè)女孩害怕,站到東嶺上喚狗。一聲聲“乖、乖”,叫得刺耳。
父母是如何把我們兄妹六個(gè)養(yǎng)大的?捉襟見肘的日子,他們能受的都受了。他們永遠(yuǎn)是我的榜樣,遇到難事,我從來(lái)沒想自己是個(gè)女人,只想到我是一個(gè)母親。
父親去世那年,經(jīng)常說(shuō)一句話,人啊,死了后還得去荊河趴著。一個(gè)病痛到身心不能忍受依然不喊一聲痛的人,照樣沒有做好面對(duì)荊河的準(zhǔn)備。荊河,在父親心里,不單單是一條河了。
父親走后十一年,母親也葬在了荊河邊上。他倆匯合,讓我堅(jiān)信,荊河是生命的解碼者。天地一體,荊河流淌成一條看不見的線,連著父親的命運(yùn),連著母親的命運(yùn),甚至連著我的命運(yùn)。此刻,在我毫無(wú)察覺間,荊河波濤洶涌,父親母親長(zhǎng)成了河水,從荊河,一路向北,匯集到濰河里。
【作者簡(jiǎn)介】宋兆梅,山東諸城人。著有散文集《老家》《在時(shí)光的身后》,長(zhǎng)篇小說(shuō)《相州王》《古琴》,傳記《王愿堅(jiān)》《李仁堂》等,現(xiàn)居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