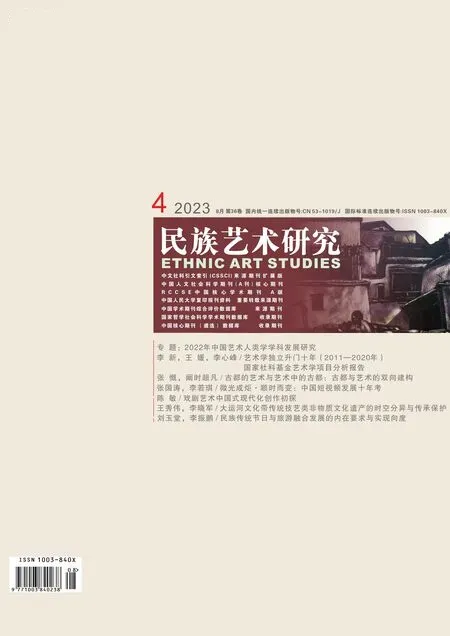時空·肖像·樣式:戲曲現代戲視閾下的服飾新特性
徐敏思,潘健華
時空性、肖像性、樣式性成為戲曲現代戲服飾藝術的新特性是時代使然。戲曲現代戲舞臺角色裝扮,因時代所生、因劇目而變,其裝扮形態及功能價值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戲曲現代戲重在表現現代生活,這是新時期大眾價值觀與審美觀的重要詮釋途徑。作為角色形象載體的現代戲曲服飾與傳統戲曲服飾相比,在性質特征與行為主張的特性層面上,漸漸生發出新的內容和樣貌。
戲曲現代戲與傳統戲在文本與裝扮上存在著根本的差異,從而催生出戲曲服飾裝扮的不同特性。傳統戲曲服飾的“三特性”,即程式性、可舞性和裝飾性,是長期以來業界公認的裝扮概念,它是經過行業內 “角兒”們不斷積累、長期沉淀后逐漸凝聚而成的特性。戲曲現代戲服飾特性的生成,是在傳統戲曲服飾特性基礎上的進一步擴展,從而形成戲曲現代戲視閾下的服飾新特性。
要進行戲曲現代戲視域下服飾特性的新思辨,有必要先審視傳統戲曲服飾的“三特性”。
傳統戲曲服飾的程式性,源于戲曲藝術高度凝練的規范法則。程式一詞原本出自《荀子·致仕》的“程者,物之準也”,故引申而出“法式”“規程”之意——“定立一定的規‘程’,以之作為法‘式’‘樣式’。”①陳多.戲曲美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118.吳乾浩先生在《當代戲曲發展學》中寫道: “程式,包含了歷代藝人的創造,歸結為包容許多方面,能適應多種戲劇情景,運用多種藝術技巧和手段的表現手法。‘程式’就其個別的存在形態來講,是凝固的、不可變的,規定性很強。”②吳乾浩.當代戲曲發展學[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276.傳統戲曲服飾的程式性同樣如此,通過服飾對角色身份、地位、性格等人物特征進行規范的外化呈現。例如傳統戲曲服飾中,明黃色蟒、帔為帝王后妃專用,紅色蟒為地位較高的王侯、宰相、元帥、欽差、駙馬等穿用,秋香蟒多為一品誥命夫人、貴夫人、太夫人等老年女性角色的日常裝束。
傳統戲曲服飾的可舞性,也是源于戲曲藝術表演的需要。陳多先生在 《戲曲美學》中寫道:“傳統戲曲的服裝既不是生活服裝的模仿與再現,也不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一般服飾藝術的加工,而是如李笠翁所稱,實質上是‘歌舞之衣’。色彩的鮮明調和、花紋的豐富精美,本身已成為具有整齊、勻稱、節奏、線條等形式美因素的造型藝術,而水袖、雉翎、帽翅、靠旗、鸞帶等等,更是為便于加強動作節奏感、韻律感的‘舞具’,而這一切,又都是為烘云托月、增強舞蹈表演的欣賞價值來服務的。”①陳多.戲曲美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128.戲曲服飾的可舞性,是基于服飾裝扮配合演員的表演功法,為演員外化角色內心情緒而服務。例如《徐策跑城》中演員通過不同頻率抖動帽翅,從而體現角色的不同情緒。
傳統戲曲服飾的裝飾性是戲曲服飾寫意表現、抽象表達的特性,是戲曲服飾形式美的凝練。“戲曲服飾的裝飾性與其程式性、符號性和可舞性是分不開的。裝飾性既體現了可舞性、符號性、程式性的要求,又包含著可舞性、符號性和程式性。如蟒袍上的蟒紋,從程式性看它是高級文官的穿戴程式,從符號性看它是尊貴的象征,從裝飾性看它又是美的圖紋。”②宋俊華.中國古代戲劇服飾研究[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56.
對傳統戲曲服飾“三特性”的總結具有特殊的歷史價值,其形成是戲曲服飾裝扮藝術發展的必然結果。雖然隨著時代的快速發展,傳統戲曲服飾的特性已屬于“非遺”范疇,但其對戲曲服飾裝扮體系發展帶來的影響卻延續至今。傳統戲曲服飾的 “三特性”應對“空舞臺”③“空舞臺”即空臺,指傳統戲曲演出中,舞臺上只有一桌二椅等。的寫意與虛擬假定,對應“三不分”④“三不分”指的是戲曲服飾穿戴規則中的“不分朝代、不分地域、不分季節”。的抽象與程式規范,可以說傳統戲曲服飾特性的形成走過了漫長的發展歷程。
早在清裝戲服和戲曲改良時期出現的時裝戲服飾中,戲曲服飾的特性就已開始轉變。民國時期梅蘭芳穿著時裝上演的《孽海波瀾》《鄧霞姑》《一縷麻》等時裝新戲就是戲曲服飾裝扮開始打破傳統戲曲服飾的 “三特性”轉而發展新特性的典型。在當下的戲曲服飾發展過程中,對傳統戲曲服飾的程式性、可舞性、裝飾性的傳承發展,由慷慨主張變得守則溫和,共同之規變得漸隱漸約,衡定在傳統戲及新編古裝戲類別的裝扮規則之中。而戲曲現代戲服飾新特性,則體現在不同于傳統戲曲服飾的時空性、肖像性與樣式性三個方面。
一、戲曲現代戲服飾新特性的客觀性
就戲曲現代戲視閾而言,其看重現代戲的視景范圍。“我們現在所說的現代戲概念,主要是指二十世紀初清末以來的當代題材戲……以上海改良京劇和某些地方戲(如廣東粵劇‘志士班’等)為代表的現代戲,從一開始就同當時的社會改造和革命運動緊密相聯,具有鮮明的思想進步性和藝術上的革新精神。”⑤高義龍,李曉.中國戲曲現代戲史[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3.戲曲現代戲展現的是新時代、新生活,戲曲現代戲的角色裝扮也應與之匹配,如在戲曲改良時期上演的時裝新戲中,服飾裝扮大量采用當時稍加美化的生活服飾,形成了明顯區別于傳統戲曲服飾的早期戲曲現代戲服飾裝扮。隨著社會體制的變革,人們的思想精神與審美認識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體現在戲曲現代戲的文本定性、舞臺轉型與觀念革新之中,這對戲曲現代戲服飾新特性的生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時空性、肖像性與樣式性生成于當今舞臺藝術革新的大背景之下。
戲曲現代戲文本的定性,即從文本創作的角度規定了反映現實時空和塑造角色肖像的創作方向。其文本敘事以表現當下生活為主,在編排上遵循一劇一本的創作方式,在人物裝扮上注重具有肖像風格的角色呈現。例如“1981年,為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上海越劇院創作演出了《魯迅在廣州》 (陳鵬、吳伯英導演,紀乃咸、薛寶根編劇,陳利華服裝設計),第一次在戲曲舞臺上樹立了魯迅的形象。”①高義龍,李曉.中國戲曲現代戲史[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332.這部戲曲現代戲以1927年魯迅在廣州的生活經歷為創作素材,主要描寫了蔣介石背叛革命制造 “四·一五”慘案,共產黨人畢磊等兩百多名學生被捕,最終畢磊被迫害犧牲等事件。魯迅在悲悼畢磊等革命烈士的同時,省悟出只有共產黨才能拯救新中國的戲理。在這部戲中,通過服飾來對魯迅的人物形象、性格特征、內心活動進行個性塑造——一襲白布長衫將一個在時代風云中擁有堅定信念的偉人肖像式地豎立在了舞臺之上。在戲曲服飾設計中,“肖像”意識其實早已出現。“從文獻記載來看,宋金雜劇服飾多因角色類型而設。如:道士穿‘道士裝’,官員穿‘衣冠’,文人穿 ‘儒服’,宦官則穿‘黃衣’等。也有因角色而設者,如扮蘇東坡者戴‘子瞻’巾。”②宋俊華.中國古代戲劇服飾研究[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63.由此可見,在戲曲服飾裝扮的特性培育早期,其設計者就已經具備了服飾裝扮的肖像意識。直至在戲曲藝術“三并舉”的政策倡導下,這種肖像意識在戲曲現代戲中進一步得以被關注。在戲曲現代戲高度發展的十年,如京劇現代戲《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襲白虎團》中,更是造就了流傳至今的經典肖像式的服飾造型。隨后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中國戲曲藝術尤其是戲曲現代戲的發展方向,由“‘以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代替過去的‘為政治服務’作為文藝方向,重申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為現代戲指明了前進的道路,使戲曲工作者煥發出更大的創造力和積極性。”③高義龍,李曉.中國戲曲現代戲史[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323.戲曲現代戲文本的定性,彰顯了與過去傳統戲不同的角色塑造方式,戲曲服飾裝扮的特性也因此發生了改變。
戲曲現代戲的舞臺轉型,指的是現代戲舞臺空間由傳統戲曲的“空舞臺”切換到了多樣式場景空間的呈現。當下戲曲現代戲的舞臺設定不再是單純的“一桌二椅”,而是采用多種手段進行時空重塑。如將電視、電影等的技術手段與戲曲抽象舞臺結合,通過寫實與寫意交融的表現手法,呈現劇本所要表現的時間與空間。由河南豫劇院三團打造的“文華大獎”獲獎劇目豫劇現代戲 《重渡溝》④豫劇現代戲《重渡溝》:何中興、姚金成編劇,張平導演,崔婉星服裝設計。的舞美空間就與傳統戲曲的“空舞臺”不同。《重渡溝》根據洛陽市潭頭鎮原副鎮長馬海明的真實事跡創作而成,講述了一位基層共產黨員帶領百姓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發展理念的故事。劇中第二場重渡溝深山里大雨傾盆的場景通過背景LED屏幕來營造電閃雷鳴和風雨交加的氛圍。新時期的戲曲舞臺已然轉型,不再單純強調“一桌二椅”的虛擬假定使用,開始采用各種科技手段以及表現方法,完成時與空的綜合呈現,同時要求服飾也隨之產生變化。舞臺轉型是戲曲藝術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科學技術發展對舞臺造型深刻影響的結果。科技的迅猛發展正在快速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和審美觀念,當下強調的是多樣化的舞臺呈現,而非傳統戲曲舞臺相對單一的“一桌二椅”。
同時隨著戲曲藝術發展方向的轉變,戲曲現代戲的創作觀念也隨之更新。傳統程式化的表演形式以及人物裝扮已不適應當下戲曲現代戲的演繹。自改革開放之后,戲曲裝扮開始由程式化的、臉譜化的人物外在,轉向多樣化、復雜化的人性刻畫。戲曲現代戲在新觀念影響下,衍生出了 “一戲一格”⑤“一戲一格”來自北京人藝創始人焦菊隱先生的倡導,原本是指話劇藝術的一臺劇一種風格,不抄襲他人、不重復自己的戲劇理想。“一臺戲一個風格”是為著求新求變,在守格、破格、創格中創造舞臺藝術。的創作方式。可以說,新觀念對應新文本,主張的是創新,單一性被跨界多樣性所取代,由此造就了戲曲現代戲服飾新特性的生成。
二、戲曲現代戲服飾新特性的內容
戲曲現代戲服飾的新特性主要表現在裝扮理念及形態層面的厘革上,這種改變并非對傳統戲曲服飾特性的否認,而是戲曲現代戲服飾本著裝扮考量的當代認知。它的內在獨特之處集中表現在時空性、肖像性、樣式性三個方面。
(一)時空性
戲曲現代戲服飾對時空定量有著明確的要求,這體現在時代、地域、風俗等一系列造型裝扮指標上。例如:196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主辦的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上,由山東省京劇團演出的京劇現代戲《奇襲白虎團》①京劇現代戲《奇襲白虎團》:李師斌、方榮翔、李貴華編劇,尚之四、殷寶忠、方榮翔導演,馬宗甫、尚春祥服裝設計。,其服飾裝扮就是戲曲現代戲服飾以時空定量的生動展現。《奇襲白虎團》中朝鮮百姓、志愿軍戰士、韓國士兵、美國士兵的服飾各具特色,其服飾設計直接點明了故事發生的時空,即朝鮮半島的抗美援朝戰爭。志愿軍戰士的服飾裝扮依據時空定量的要求,參考時代、地域等裝扮指標的變化,生成了契合劇情發展且具有時空性的戲曲現代戲服飾。第一場志愿軍戰士與朝鮮百姓相處時穿著的服飾,就是在現實生活中志愿軍服飾的基礎上進行美化而成的。其基本的服飾樣式、胸標的處理都符合歷史真實,尤其是志愿軍的胸標更是戲曲現代戲服飾時空性的直接體現。在之后志愿軍戰士喬裝扮作韓國士兵時則穿上了當時的韓軍兵服,利用服飾的改變配合精湛的表演完成了空間切換,其灰色披風的設計暗示這場突襲是在黑夜中進行,明確了奇襲發生的時間。可見《奇襲白虎團》中的服飾裝扮具有很強的時空性。
這種現代戲曲服飾的時空性裝扮原則與傳統戲曲服飾的“三不分”中不分時間與地域的傳統裝扮原則截然不同,現代戲曲服飾強調時與空的印記。對于時空定量的把握,力求鮮明而準確。如:山東省京劇團的京劇現代戲《奇襲白虎團》中的嚴偉才身穿志愿軍服,直接點明該劇所處的時、空所在,力求典型而鮮活;上海越劇院的越劇現代戲《燃燈者》②越劇現代戲《燃燈者》:李莉、黃嬿、張裕編劇,楊小青導演,潘健華、徐琳服裝設計。中居委會干部紅袖章大媽,是上海石庫門鮮活的海派服裝文化典型。
(二)肖像性
在戲曲舞臺時空的“大舞美”觀支配下,戲曲現代戲服飾在裝扮傾向上與傳統戲曲服飾的“寧穿破、不穿錯”的規矩截然不同,除了對應性格與身份這個永恒的指標之外,更注重貼切文本對角色的肖像塑造,也就是在服飾指標上更強調外貌形象的獨特的“這一個”③“這一個”是德國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提出的術語。具體是指感官感知的具體、確定的對象,在美學上引申為具體或個別的典型形象。。例如:由河南豫劇三團打造的獲“文華大獎”的豫劇現代戲《焦裕祿》④豫劇現代戲《焦裕祿》:姚金城、何中興編劇,張平導演,陳向群服裝設計。中主人公焦裕祿的服飾裝扮就很好地突出了人物的典型形象。焦裕祿1962年調任河南蘭考縣書記,蘭考縣接連遭受了內澇、風沙、鹽堿災害,身患肝癌忍受劇痛的焦裕祿選擇深入到普通群眾中去,帶領大家共同對抗自然災害,努力保護自己的家園。他1964年病逝于鄭州時的臨終愿望是要埋骨于蘭考的沙丘,等待蘭考風沙徹底成為歷史的那一天。這也成就了鼓舞著一代又一代年輕人不畏挑戰、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焦裕祿精神。豫劇現代戲《焦裕祿》中的服飾造型參考了其真實歷史影像,服飾設計整體保留了20世紀60年代生活服飾的基本款式,色彩基調偏暗以藍色和灰色為主。劇中的焦裕祿著樸實的打底衣和毛背心,這是人們心目中的焦裕祿形象,可以說這樣的服飾造型具有很強的肖像感。
肖像性是戲曲現代戲為凸顯角色的身份、性格、年齡等個性進行藝術再加工時顯現出來的特性,以使人物形象塑造更為典型、更為真切。但是部分戲曲現代戲劇目在塑造人物形象時,缺乏對原型人物外貌特征細節的考究,角色人物造型的肖像感不強,這就導致觀眾無法與其產生情感共鳴。在戲曲現代戲的角色形象塑造中,尤其是真實的英雄人物如申紀蘭、劉胡蘭、江姐、瞿秋白、華子良等等更應注重其肖像塑造上的可信度,此方面可借鑒影視藝術中角色塑造的要求。具體來說,影視劇在塑造真實經典人物時,一般會在遵循真實人物生活原貌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的藝術化設計,也就是說首先要突出人物的真實性與形似性,爾后再考慮其藝術化的加工,戲曲現代戲的服飾設計也應同樣如此。戲曲現代戲的服飾設計,應愈發注重對人物外貌形象獨特“這一個”的塑造,凸顯戲曲現代戲服飾的肖像性。
(三)樣式性
任何藝術形態對樣式的要求均是藝術創造的考量指標之一。周本義先生曾說:“舞臺美術界的‘樣式’一般是指整個演出的風格、樣貌和形式感。我設計了很多舞臺美術作品,我不敢說都是優秀作品,但每設計一個戲,我都竭力去形成這個戲的樣式。比如說《游園驚夢》《典妻》 《明月照母心》。走心去創作,努力去尋覓適合劇本表現的樣式。有時候,找準了樣式,有些問題就迎刃而解。在這方面,沒有老舊之分,中外之分,古今之分,只要合適的,都可以為我所用。一個戲有了樣式感,似乎就有了路標……一臺戲能否創作出鮮明的有特征的有力闡釋劇作內涵和思想意義的樣式,常常是一臺戲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①上海文聯.追憶周本義:寫意舞臺,寫實人生?緬懷?[EB/OL].上海文聯微信公眾號(ID:shwenlian),2021-06-05.可以說在戲曲現代戲服飾“一戲一格”的設計中,樣式即“路標”。戲曲現代戲服飾造型中對于革命軍隊的服飾造型,就是“一戲一格”的樣式塑造。如,20世紀60年代北京京劇團出品的京劇現代戲《沙家浜》②京劇現代戲《沙家浜》:汪曾祺、楊毓珉、肖甲、薛恩厚編劇,肖甲、遲金聲導演。中的革命軍隊服飾與同一時期由上海京劇院出品的京劇現代戲 《智取威虎山》③京劇現代戲《智取威虎山》:上海京劇院集體改編;應云衛、陶雄、李桐森導演;上海戲劇學院舞美系1964級戲曲舞美專修班美術設計。中的楊子榮等解放軍戰士的服飾相比,雖同樣是在軍隊服飾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化的處理,以干凈、整潔的人物造型風格展現積極向上的軍人們的精神面貌,但是由于兩部劇目所表現的內容不同,在服飾造型設計上也因此有所區分。《沙家浜》中的革命軍隊服飾更加干凈、利落;而《智取威虎山》中的解放軍服飾則在干凈的基礎上更加粗獷,從而體現該劇“剿匪”的故事核心。由此可見,兩部戲雖排演于同一歷史時期,在現代戲服飾設計的整體風格上大致相似,但是也會因為劇本內容和立意的不同,在服飾設計上呈現出不同的特色,這就是戲曲現代戲服飾設計中的“一戲一格”,即戲曲現代戲服飾的“樣式性”。
戲曲現代戲服飾的樣式追求刻意,其直接反映著當下審美傾向與藝術觀念的側重,可以說戲曲現代戲服飾的刻意樣式是時代風尚的直觀視覺外化。戲曲現代戲服飾樣式注重的是文本“一戲一本”與服飾上“一戲一格”的對應,是編導、主創對文本敘事結構與敘事方式二度呈現的藝術追求,是場景空間整體畫面設置特性的組合。不同于傳統戲以“角兒”的影響力來支配穿戴樣式,戲曲現代戲是基于闡釋劇目內涵及思想意義的需要,創造“一戲一格”的服飾造型。
三、戲曲現代戲服飾新特性形成的路徑
戲曲現代戲服飾裝扮的視域與傳統戲截然不同,它的生成及成敗取決于對其新特性拿捏的路徑與門道。其時空性、肖像性、樣式性特性鮮明,有著區別于傳統戲的不同營造方略。戲曲現代戲服飾三大新特性的造物路徑,由兼收并蓄的“五W”原則、夯實基礎的讀本讀史、基于現實的生活體驗、揚長避短的身體改造以及豐富多樣的表現力訓練構筑而成。
確立兼收并蓄服飾設計的 “五W”原則。所謂服飾設計的“五W”原則是指“有關角色的事實,它有五個‘W’,第一是時間(WHEN),即角色處于什么時代、什么季節?第二是地點(WHERE),角色在什么地理位置、什么空間環境?第三是目的 (WHAT),為什么要有這個人物及人物如何發展?第四是身份(WHO),角色的性格、年齡、職業如何?第五是意圖 (WHY),指角色穿用服裝的意義與功利何在,是標榜還是炫耀?”④潘健華.舞臺服裝設計與技術[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166.在戲曲現代戲服飾的設計之初要先明確設計所需的基本信息即時間、地點、目的、身份及表達意圖。采用“五W”原則,可以將繁復的劇本內容進行概括,梳理出整體的創作框架,以時間、地點、身份搭建起故事所需的基本骨骼; “五W”原則的確定,為戲曲現代戲服飾新特性的呈現打下堅實基礎。
讀本、讀史。讀本是指對劇本的反復閱讀,在確定“五W”原則的基礎上,進一步研讀和分析劇情,進而掌握劇本的主題、題材與風格,鎖定劇本的核心立意,依據劇情發展走向畫出人物行動圖,提煉劇本對于角色形象的描述,為設計“一戲一格”的戲曲服飾樣式提供基礎的信息支撐。讀服裝史和文化史,是為了懂史、用史,使創作的服飾不偏移劇目人物所處年代。戲曲現代戲服飾的時空性、肖像性即建立在真實的歷史依據之上,跨越時空的演繹必然要依靠史料的支撐才能再現歷史真實。懂史是為了知曉歷史真實為何,用史則是為了明確借由歷史塑造真實的人物肖像的路徑。值得注意的是,讀史強調的是要樹立“博物館”博覽式的創作意識,絕不是“博物館”式的標本復制。讀本與讀史是在尋找設計依據,為進一步呈現戲曲現代戲服飾時空性、肖像性以及樣式性夯實基礎。
強調生活體驗,是指通過采風,收集生活中的真實素材,從而幫助設計師提煉極具代表性的服飾特征,為形成戲曲現代戲服飾的肖像性提供生活依據。只有通過生活體驗,我們方知農民在田中耕作時,為了方便勞作褲腿要挽起或扎口,這就是莊稼人在勞作時的代表造型元素,可用于塑造典型的農民形象。還有革命戰士在長途奔襲過程中,會扎綁腿,這是為了防止因步行過多,血液下積引起腿部腫脹,同時在山地叢林的行軍過程中也可以防止螞蟥、昆蟲進入褲管。可見,扎綁腿是特定年代中革命戰士的代表性造型元素。只有通過生活體驗才能為造型設計的外在面貌確定鮮明的形象特征,為服飾時空性、肖像性、樣式性的生成提供保障。
戲曲現代戲服飾設計還需考慮對演員進行揚長避短的身體改造。在傳統戲曲服飾的裝扮中,演員自身的身體條件不是關鍵,傳統戲曲服飾因其寬袍大袖,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例如一米五的演員穿上寬松的外袍及厚底靴同樣可以塑造出一個高大、英俊的人物形象。但現代戲服飾受服裝款式的制約,無法全部以寬大的服裝來遮蓋演員身形的不足,為了更加貼近劇中描述的人物形象,往往要通過修改服飾廓型、巧用服飾色彩、調整首服和體服及足服之間的比例,來揚長避短地完成演員的身體改造。例如,有的演員肩膀部位棱角不夠突出且存在明顯的高低肩問題,他(她)在戲中又需塑造豐碑式的偉人形象,單憑演員自身的身體形象,不能完全體現角色的精神面貌,就需要設計師通過服飾造型對演員的身材進行適當范圍的改造,如左右肩膀分別加設不同厚度的墊肩以使造型完成后的視覺形象更加貼近角色。又如:有的演員肩、腰比例接近,呈“I”形身材,而劇中要求演員塑造“倒三角”軍人形象,就需要服飾設計師加寬其肩部的造型,使其產生“倒三角”的效果,從而完成對演員的身體改造,使其更加貼近于角色形象塑造的需求。身體改造就像日常生活中的“穿衣打扮”,通過細節的調整,使角色的整體形象獲得改變與氣質得到提升,呈現出更貼切的角色精神面貌。身體改造是戲曲現代戲服飾肖像性的重要造物路徑之一。
戲曲現代戲服飾設計的表現力訓練也很重要,要通過訓練使設計師在技法上有能力運用不同的藝術手法結合不同工藝來生成不同的視覺效果圖,拓展效果圖由平面二維轉向立體三維的主觀能力,積累鑒別工藝效果呈現的經驗。例如:體現角色處于暴風雪的環境之中,如用寫實化的表現手法,可能會采用發泡混合丙烯的方式進行面料肌理塑造;采用裝飾化或者抽象化的表現手法則可能采用絲網印或噴繪的方式直接將抽象的、裝飾性的圖案印制在布料之上,甚至有的服裝會借用三D打印、全息投影等高科技手段進行展現。戲曲現代戲服飾設計表現力的訓練就是要讓設計師掌握相關的塑造方法,從而能更加自如地傳達劇目的核心立意,對于戲曲現代戲服飾來說,表現力的訓練是其樣式性呈現的必不可少的造物路徑。
結語
戲曲現代戲自20世紀初萌發到現今,因戲而生、因內容所需的服飾藝術特性發生了重大變革,現代戲視閾下的戲曲服飾新特性與傳統戲曲服飾“三特性”存在根本的差異。戲曲現代戲服飾新特性中,其時空性對應不同現實題材的服飾裝扮參與敘事,考量其情節線索展開的長短與發生順序,令舞臺時空更加明晰;其肖像性強化角色外貌的妙肖與靈活,使角色形象更具典型性;其樣式性追求服飾立意的“一戲一格”,貼合“一戲一本”,追求以刻意樣式反映當下審美傾向。嘗試完備戲曲現代戲服飾時空性、肖像性、樣式性的新特性建立,是百年來戲曲現代戲幾代創作者不斷探索的結果,目的在于確立戲曲現代戲服飾裝扮考量的當代認知,結合其新特性的營造方略,用實踐來檢驗其新特性的指導價值。戲曲現代戲服飾新特性是繁榮戲曲現代戲在裝扮層面上的考量尺度,也是當下力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先進文化引領的時代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