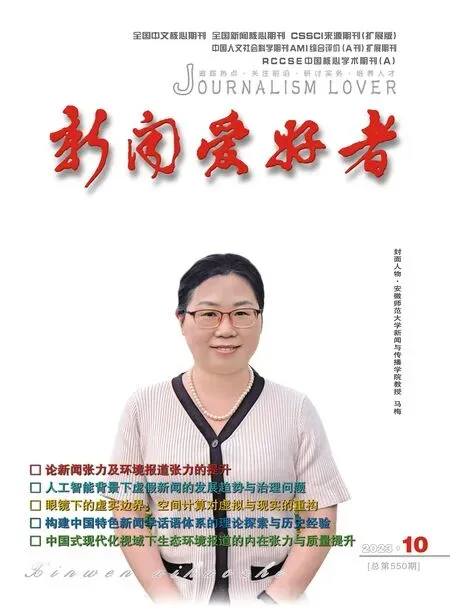從“隱憂”到“解憂”:網紅文化對青少年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風險挑戰與紓困路徑
□菅曉旭
隨著“互聯網+”和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的誕生,網絡時代的符號化催生了“網紅”這種新的媒體文化與社群現象。關于網紅的界定,學界尚未有清晰明確的定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廈門大學楊玲在《網紅文化與網紅經濟》中指出的:“‘網紅’是‘網絡紅人’一詞的簡稱,最早指的是一些因獨特的外貌或言行在網絡上走紅的普通民眾,現泛指一切主要通過網絡特別是社交媒體獲取和維系聲名的人。”[1]在資本孵化下,“網紅”被創造出更多衍生物,從人物身份到物品、店鋪、地點等一切在網絡空間中廣受歡迎的事物皆可冠以“網紅”的前綴,“網紅”逐漸擴展成為一種文化現象。網紅文化以隱秘、微妙的功能路徑全面嵌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影響并形塑青少年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帶來諸多意識形態隱憂和挑戰。因此,深入探究網紅文化所展現的意識形態圖式,對于全面把握網紅文化意識形態運作的功能路徑并提出針對性的化解策略,切實維護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網紅文化對青少年主流意識形態認同隱憂
網紅文化持續活躍的背后,離不開資本的操縱。這就造成在利益驅動下的網紅文化蘊含的錯誤思潮、資本主義強勢話語、不良價值等在日常生活中呈現出諸多意識形態隱憂。
(一)遮蔽與疏離:網紅文化虛化了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力量
首先從網紅文化內在和外界生成語境溯源,意涵了一定意識形態的網紅文化在價值觀導向生成過程中,依托網絡流量帶來的狂歡熱潮進行各種 “惡搞”“戲說”“笑談”,以淺薄化、戲謔化和娛樂化的方式對嚴肅、宏大、崇高的政治話語、傳統經典、公共議題等主流文化進行解構,削弱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性,突出呈現為物質文化超越精神文化、泛娛樂化思潮消解主流文化、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掩蓋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舶來文化侵蝕本土文化。其次從網紅文化的話語特征和青少年認知路徑來看,網紅文化本身話語具有娛樂化和去政治化傾向,在物質利益的催動下,其話語裹挾各種社會觀念和思想意識形態形成新的變體,極易造成價值越位,阻滯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傳播。同時依托算法推薦技術的網紅文化話語本身具有強烈的迎合性,定向化的推送機制會使主體逐漸喪失對價值客體的認知能力、反思能力和批判意識,導致主體變成了價值觀念的被動接收和接受者。在認知過程中,網紅文化的碎片化和快速更迭削弱了青少年的領悟力和系統分析能力,空洞和無意義的文化參與不利于青少年對文本的理解和把握,使他們逐漸淪為缺乏深度思辨意識的單向度的人。
(二)迷失與誤導:網紅文化限制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牽引作用
在多種觀念交織、多種文化交融、多種意識形態碰撞的網絡環境中,蓬勃發展的網紅文化必然具有顯著的價值多元性,造成青少年的思想紊亂和自主意識異化,引發青少年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反叛。一方面,網紅與資本的合謀表演,以“消費自由”“平等消費”等觀念試圖轉移、掩蓋、消弭現實社會的深層矛盾和階級差異,過度宣揚個人物質欲望及時滿足,讓青少年迷失在這場繁華卻虛無的消費主義浪潮中,在集體無意識中接受了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價值觀的侵蝕,解構了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念。另一方面,為了博出位,許多網紅不惜游走在道德倫理和社會公德的邊緣,不僅污染了網絡生態而且極易引發社會秩序混亂,并且,經過專業機構包裝起來的網紅的“一夜成名”以及他們不遺余力展示出來的經過美化渲染的生活方式,深深地吸引著被現實生活困擾的青少年。表象與現實的巨大落差極易引發青少年的思想困頓與精神焦灼,在人聲鼎沸的網絡狂歡中逐漸迷失自我,進而導致青少年價值立場的含糊和動搖,甚至拋棄社會主流價值觀的約束和控制,加劇網絡價值失范和多元沖突。
二、網紅文化影響青少年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邏輯理路
厘清網紅文化如何影響青少年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內在邏輯,才能進行及時正確的引導以消除負面影響、促進價值歸位。
(一)隱蔽的價值導向削弱主流意識形態的引領力
算法推薦技術是網紅文化傳播的重要助力,但由此帶來的技術偏見會使主流意識形態自身的特點和功能指向被遮蔽。一方面,信息傳播平臺為了獲取關注度和擴大影響力,過多地制造出低俗化、媚俗化、庸俗化的內容,破壞了健康的網絡文化生態。另一方面,算法推薦的資本和權力邏輯本著 “利益優先”“流量至上”的秉性助推了信息獲取差異的產生,隱蔽的技術操控引發和強化了算法偏見和算法獨裁。受眾的注意力成為衡量信息價值的唯一標準和絕對指標,信息本身的“傳播力”決定了其內容的影響力。這種“熱度”導向的信息分發模式還會誘發“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不良社會思潮肆意橫行,污染社會輿論生態,溢出負面效應。而主流意識形態要素被過濾在“信息孤島”之外,導致青少年陷入非主流話語和錯誤思潮的包圍圈,阻礙了主流意識形態的用戶抵達。網紅文化進入并擠壓青少年的意識活動,解構著主體思維和價值理性,再加上技術設計主體隱秘嵌入的價值傾向和主觀意圖,必然會對正處于“拔節孕穗期”的青少年的思想和價值選擇產生戕害。
(二)參與式文化的社會輿情表達挑戰主流意識形態權威
青少年面臨的是一個具備多種傳播與互動方式的新媒介時代,用戶參與表達成為互聯網時代輿情生成過程的重要環節。他們總能在網絡參與互動過程中找到對自己觀點、情緒、態度的認同者,并在價值觀同頻的人群中建立起社交圈層,同時圈層的強互動性也讓青少年獲得了“共同身份”的認可。但不可否認的是,網紅文化在獲取參與者高度認同感的同時,也使原本理性的自我約束能力減弱,造成參與者網絡人格的異化,把對現實生活的怨懟轉化成網絡世界里的恣意妄為,并且在同質化的圈層中容易導致價值錯位,個體的思想觀念與行為認知逐漸偏離主流,產生意識形態偏差,形成“絕對自由”的錯誤認知。甚至任何東西被安上“網紅”的標簽后,就會引起青少年群體的爭相模仿和盲目追逐。在過度追求“網紅”體驗感的過程中,參與者的思想和心理被操縱,網紅文化也由此成為異化的文化力量。這種“用戶參與內容生產”的機制進一步刺激網紅文化的再生產和更廣泛的傳播,同時受限于參與者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養以及文化監管的不到位,斷章取義的輿情表達、局部問題夸大等非理性話語也會離散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理論解釋力,多種意識形態交織而成的 “暗流”不斷向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發起沖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和凝聚作用。
(三)群體性心理下的情感宣泄擾亂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認同
網紅文化的受眾是去個性化的人,具有非理性、沖動性和盲目性的傾向,其中身心不成熟的青少年群體更是在海量的網絡信息中無力進行信息選擇和評價。很多網紅的成名體現的是群體性的認知共識,這種心理上的認同成為維系群體認知的黏合劑。群體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群集聚時的從眾效應會使得他們更容易失去理性,加劇感性化、情緒化、極端化的心理狀況,類似于狂歡式的情緒與行為表達極易受到負面的情感宣泄的浸染而失去正確的價值導向。這種集體無意識的狂歡和娛樂化世俗化的情感宣泄會導致整個群體出現規模性的價值觀“崩塌”,增強錯誤思潮的情感依附性和滲透性,給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造成嚴重威脅。復雜嚴峻的網絡生態難以形成青少年支持、認同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磁場,長期浸潤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會使正處于價值觀形塑期的青少年心中的“自我”意識、功利化特質、叛逆心理不斷生長,從而陷入“價值虛無主義”的泥潭,拒絕積極健康、昂揚奮進的主流價值觀的鼓勵和宣教,消解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信息的價值賦予。
三、化解網紅文化對主流意識形態風險挑戰的解憂之思
(一)價值引領:以主流價值觀矯治網紅文化,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引領力
網紅文化的產生和傳播具有偶然、自發的特征,呈現出紛繁復雜的亂象,需要國家建立一系列具有鮮明導向的規章制度,及時對網紅文化進行道德校準和凈化,并且督促相關部門加強甄別,相關平臺加強監控,構建起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的網絡管控體系。
(二)規范參與:科學研判、及時疏導網絡輿情,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
全媒體時代,網絡輿情關系著社會和諧穩定與意識形態安全。為此,必須從網紅文化的根源進行網絡輿情的科學研判和疏導,規范青少年的網絡參與,引導青少年群體正確關注和理性參與社會議題,促進主體意識回歸。首先,要重點關注網紅文化背后隱含的利益訴求。網紅文化往往會與社會熱點問題緊密交疊,透過網紅文化可以窺見青少年的生活狀態、社會心態和思想觀念。理解和尊重網紅文化,以包容的心態合理回應青少年的訴求。因此,一方面,國家要努力營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引導社會資源良性流動,促進機會平等,增加青少年的實際獲得感。另一方面,社會層面應切實關懷當代青少年的精神生活,盡可能地幫助他們緩解生活壓力和現實困惑。其次,主流媒體要搶占輿論陣地,牢牢把握網絡輿情引導權、主動權,有效“縫合”主流意識形態潛在的風險漏洞。通過主動設置議題、圈層輿論與主流價值共振、建立與青少年平等有效的對話機制等手段巧妙、靈活地引導網絡輿情,鼓勵青少年將關注點與主流價值觀對接,培養青少年群體的公共理性精神。
(三)情理相融:以青少年精神需求為中心,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吸引力
主流意識形態應從青少年的需求出發,深入了解青少年的情感期待,積極主動參與到網紅文化中去,在傳播實踐中適度引入網紅文化,用感性化、具體化、形象化呈現相對理性嚴肅的內容,依托網紅文化積極效應,促進青少年的情感認同和自覺實踐。因此,在理論闡述方面,注重宏大敘事與微觀表達相結合,將宏觀理念融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利用網紅文化的熱點聚焦進而增加青少年和主流價值觀的接觸,把抽象的理論變成可感知的生命體驗,激發青少年的情感共鳴和觀念認同。在生產實踐方面,主流媒體通過運用傳播效率更高、覆蓋面更廣的新媒體營造一個突破時空隔閡的開放式交流空間,打造符合青少年群體觀賞習慣的傳媒主場,設計優質內容,精耕細作,使青少年在視聽氛圍和感官刺激下對主流意識形態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愉悅的情感體驗中達到理性的升華,在視覺與精神上得到雙重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