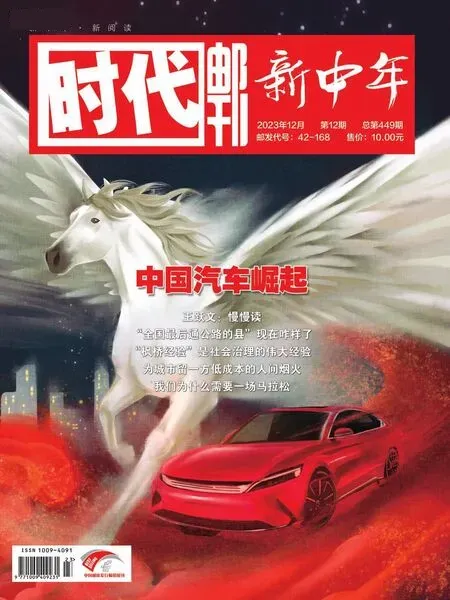“破譯”頤和園密碼的人
● 馮雨昕
比起書桌,王道成更喜歡坐在客廳的飯桌旁工作,那里緊靠著一扇窗,有陽光灑進來——他喜歡自然光勝過燈光。這位小個子的學者今年90歲了,面色紅潤,聲音響亮,有點鶴發童顏的樣子。他的四川口音很重,總是大笑。他說自己耳聰,因為有輕微白內障,目不算太明,但這并不妨礙他每日閱讀書報上的小字。

王道成的前半生研究文學,后半生研究歷史。不過總結起來說,也是“文史不分家”。
讀書、寫作,近70年的學術生涯,王道成寫出了《頤和園史事人物叢考》《圓明園研究四十年》《科舉史話》《慈禧太后傳》等著作。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闞紅柳評價,王道成是中國系統研究清史的首批學者之一,他用自己的古典文學知識素養,為清史研究留下了獨特的文化視角。
“文史不分家”
成為清史專家以前,王道成的人生還有兩種可能性。
1951年,他報名參軍。征兵要求身高1.6米,但他的身高差一厘米。帶著遺憾,他參加了當年的高考,考入重慶大學中文系,希望能實現另一個夢想——成為漢語言、漢文學的專家。“那時候同學們都想當作家,但我知道我這個人缺乏想象力,當不了作家。我就希望通過努力,成為一個專家。”
王道成從小就對古典漢語文學頗有研究。
1933年,他出生在四川省宜賓市高縣,父母開油坊,他是家中老大,被祖父寄予厚望,2歲時就被教授識字。按當地習俗,4歲,他接受啟蒙,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等。6歲,他拜到一個前清秀才門下,學習四書五經,而后“七歲作對子,十歲修文章”。
到了12歲考入中學,他開始接受新學教育。王道成記得,自己是學校里唯一能夠用文言文寫文章的,被老師評價“文如秋水”。
1952年,因為全國院系調整,王道成轉到四川大學中文系就讀。1955年大學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大學中文系任助教,次年又被調到中國人民大學,先后在國文教研室、新聞系文學教研室、直屬漢語教研室等多個研究室工作。25歲起,他就給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講古文課了。因為講得好,學校通過群眾評議給他頒獎。拿到獎金后正好是除夕夜,他去店里買了一大袋軟糖慶祝。
1972年,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教研室決定成立清史研究小組,由時任副校長郭影秋任組長,編制有40個。但當時教研室只有20個人,其余的人就從檔案、黨史、語文、哲學等院系調用。王道成也被力邀加入。
但他很猶豫:“我都快40歲了,人到中年還改行?”來邀請他的同事告訴他,文史不分家,文學也是清史的一部分。“他還和我說,我已經教了十幾年書了,應該坐下來搞搞研究了。”
也是在那位同事的解釋下,王道成明白了彼時清史研究的形勢:新中國成立初期,董必武提出要組織人力編清史,周恩來親自主持籌備編纂工作,并決定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清史研究所。后因種種原因,有關工作一直被耽擱至上世紀70年代。1972年,經北京市委批準,中國人民大學正式成立清史研究小組。
“那會兒,清史這門專業不被重視。研究古代史的人,認為清史是封建社會的殘余,沒有什么可研究的。研究近代史的人,又認為鴉片戰爭前的清史屬于古代史。”凡此種種,王道成聽后,生出一種填補學術空白的使命感。
1972年4月,他被調入清史研究小組。
研究歷史,要坐得住
清史研究小組成立之初,郭影秋提出了編寫《簡明清史》《清代大事記》《中國歷史綱要》等任務,小組的大多數人力集中在此,王道成則被分配完成外面的約稿任務。1974年,他和同組另外兩位同事接到上級要求,寫一本談《紅樓夢》歷史背景的書。
“從《紅樓夢》提出問題,進而講述清代歷史,再歸結到《紅樓夢》,這是我們的寫作方法。”三人重新并多次閱讀《紅樓夢》,結合公開的檔案及材料分析,于1976年4月出版了七萬多字的《〈紅樓夢〉與清代封建社會》。王道成說,為避免追求個人名利的嫌疑,他與同事們商定用一個集體筆名“施達青”——彼時,中國人民大學停辦,清史研究小組分配至北京師范大學,“施達青”即取自“北京師范大學清史研究小組”的簡化諧音。
后來,《〈紅樓夢〉與清代封建社會》被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吳恩裕和馮其庸稱贊見解新穎、史料翔實,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全面論述《紅樓夢》歷史背景的著作。
這被王道成視為自己清史研究歷程中走出的第一步,這本書的成功出版也加強了他對清史研究的決心與信心。
1975年,王道成受北京出版社及頤和園管理處之邀,參與《頤和園》一書的編寫。
起先,責任編輯給他們規劃了寫作方向,要求按照《定陵》一書的模式,寫“頤和園是用勞動人民血汗和才智建成的”“頤和園是封建帝王罪惡統治的象征”的主題。王道成卻覺得,這樣寫書雖容易,卻沒有生命力,“像命題作文一樣”。
他與編寫組成員花費一周的時間,到頤和園與群眾一起游園,聽他們的興趣所在。最后總結出了四個問題:頤和園是怎么修起來的?修園子之前,這里是什么樣子?建成以后,這里發生了哪些事情?頤和園的建筑和園林有什么特點?
為解決這些問題,他們去請教了更多領域的專家。聽北京大學的侯仁之教授講述海淀的歷史地理,請清華大學建筑學家吳良鏞講解頤和園的園林和建筑,也請梁思成生前的助手、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莫宗江帶他們游園和講課。
他們跑遍了北京各大圖書館,翻看已有的文章與書籍,發現原先許多的說法是不準確甚至矛盾的。“比方說,慈禧太后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到底是用了多少白銀?誰也說不清楚。”
他為此買了公交月票,每天坐車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讀一摞摞的上諭檔和奏折原件,泡一整天。任何一個篤定的歷史細節都需要翻閱海量的檔案。他舉例,只為考據慈禧的父親葉赫那拉·惠征在安徽任上時的情況,他整整看了3個月檔案。
最后,王道成與同事們為書擬出五個主題,即頤和園的前身、頤和園與慈禧太后、解放后的頤和園、頤和園是勞動人民智慧與血汗的結晶、頤和園主要景物介紹。王道成代表編寫組在審稿會上匯報情況,被批準取代原先責編定下的寫作方案。
1978年11月,《頤和園》正式出版,王道成記得,當時有關專家將這本書評為“國內關于頤和園的最具權威性的著作”。在王道成看來,編寫《頤和園》是他研究道路上的轉折點,“讓我真正理解如何才能做好研究工作。”他解釋,此前編寫《〈紅樓夢〉與清代封建社會》,參考的多是易找的公開資料,而寫作《頤和園》,他需翻閱那些不為人知的歷史檔案。
這是歷史研究的方法論,王道成說,須耐得下心、坐得住,從浩瀚文庫里尋找和印證歷史真相。寫《頤和園》的兩年多時間里,他估摸自己看了上千萬字,筆記也記了十幾本。
90歲,仍在著史
2002年,現北京燕山出版社社長夏艷到清史研究所讀研,認識了王道成。王道成雖已在上世紀90年代末退休,但仍然為所里的許多研究項目做評審或主持。
在夏艷的印象里,王道成總穿襯衫,鞋子永遠干干凈凈。他做事極認真,每每為研究所的項目寫審稿意見,總要交付二三十頁工工整整的手寫文章。夏艷也是后來才知道,王道成寫審稿意見,總是先以草書快速記下,怕同事們看不懂,會再謄寫一遍內容。他脾氣很好,“從來沒有拒絕過我的任何請求”。
從上世紀90年代起,王道成就住在張自忠路中國人民大學老校區內的一間公寓里。他的妻子前年去世了,現如今他獨居在那里。
四個房間都放滿了書,在地上、桌面上堆得和人一樣高。這些書除了用于研究外,還和授課有關。過去他給學生講課,“每講一門課,就要有一套相關的書”。而他講過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等十幾門課,藏書很雜,他估算,少說有三萬冊。
他今年90歲,除了有高血壓及前年給心臟做了兩個支架,身體還算不錯。他的睡眠好,一覺能睡8個小時以上。每天早上9點,他會給女兒打個電話,“證明我還活著”。
他覺得不能光動腦不動身體,因此不愿請保姆,自己買菜、做飯、收拾家務。煮粥時,他會同時做自己發明的保健操,從梳頭開始,到眼睛、耳朵、頸部、腰和腿,全套下來有20個動作,要花費半個小時。他仍保有一定的生活情趣。夏艷每年春節都會帶一束水仙花拜訪王道成,只因賞水仙是他過年的保留節目。
生活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仍是編書與寫書。今年夏天,王道成受燕山出版社委托,參與制作《國朝畿輔詩傳》,主要為詩文內容做注釋。全書共計100多萬字。
夏艷解釋,對北京歷史文獻研究而言,《國朝畿輔詩傳》是非常重要的一本書,“它記錄了從順治到道光年間,京津冀地區的代表性詩人的代表性作品。這對于我們研究清代文史會非常有幫助,當然,對于詩詞愛好者也是一種福利,大家所熟知的都是唐詩,但其實清代詩歌又是另外一個高峰。”
夏艷認為,王道成這樣的專家是編輯《國朝畿輔詩傳》的最佳人選,因為他既對北京的文史十分熟悉,又有極強的古典文學功底,“尤其是那些詩詞、駢文,國內能夠做精確的、恰當的點校注釋的專家非常少”。
用夏艷的話來說,王道成的貢獻相當可貴,因為做古籍文獻整理,是一個“賴漢子干不了、好漢子不愿意干”的活兒,它對學識和精力的要求都很高,但是在學者評職稱時,又不討好。“學界都認為,搞研究才是比較牛的事情,整理文獻,那都是在整理前人留下的東西。”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闞紅柳評價,王道成對于科舉史、圓明園、頤和園等等的研究,都嘗試從文化史層面去解析歷史,這在上世紀清史研究初興時,是非常有特色的視角。
或是得益于長年古籍文獻工作的積累,王道成至今仍有著讓闞紅柳佩服的記憶力。“他的邏輯和時間線總是非常清楚,比方說你問他圓明園歷史中的某一個事件,不管是再細枝末節的內容,只要他學習過,他都能立刻把每個時間點、相關人物說清楚。他就像一本活的清代歷史書一樣。”
90歲的王道成覺得,自己離“真正的退休”還很遙遠。“我讀了那么多年檔案,存下這么多材料,其中有許多,后人恐怕都是很難看見的。趁我還有精力時,只想將它們多多記錄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