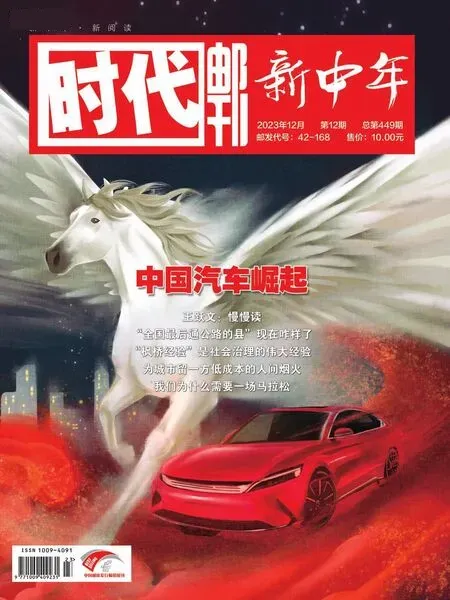地鐵口的翻譯家
● 尹海月
在重慶市中心的紅土地地鐵站,有一位男士,每天都會在這里賣書。他坐在塑料凳上,面前擺著一小摞書,書上放著白色小牌子,上面寫著“翻譯家簽售新書”。

每天下午5點,只要天氣晴朗,他都會準時出現在這里。一天,一名高中生經過,被這場沒有鮮花和掌聲的“簽售會”吸引。眼前的這位賣書人戴著眼鏡、穿著襯衫和皮鞋,看起來十分從容。她拍了兩張照片,寫了一段話,傳到短視頻平臺,沒想到引來20多萬人點贊。“這是屬于他一個人的浪漫和燦爛”“我很敬佩他,為了夢想,選擇在地鐵站銷售自己的作品”。
有人認出他是重慶師范大學校外兼職導師王川舟。年輕人在王川舟的書攤前排起了長隊。他們有的是在重慶旅游,特地趕來的;有的是受外地朋友委托,前來買書的。也有不少年輕人買完書,蹲在王川舟身旁,和他聊起人生和理想。
“他們不理解這是一種個人的文化追求”
王川舟今年63歲,開過翻譯事務所,參與過不少大型翻譯項目。2020年,他退休了,每月拿四五千元的退休金。因為過去主編了《重慶翻譯家》雜志,他決定把自己寫的文章結集成書。他找到一家出版社,自費出版1000本《翻譯往事》。期待在“社會上引起一點反響”。
沒想到,自費出書需要作者自銷。看著家里堆積如山的書,王川舟犯了愁。思來想去,他決定把書賣給“真正的讀者”。
聽說王川舟要出去賣書,家里人都反對,認為“很丟人”,也不會有什么效果。經過一番思想斗爭,他選擇在地鐵站賣書。他覺得這里人流密集,寫上“翻譯家簽售”是為了吸引路人。很多時候,他賣不了一會兒,地鐵站的工作人員就不讓賣了。他也不生氣,這個地方不讓賣,就換到另一個地方。
他覺得幸運,第一天擺攤就賣出去兩本書,買書的還都是“重慶文化界的人士”。他盤算,如果一天賣兩本,兩年多就能把書賣完,“我小小的出書夢就實現了”。
他的第一本書不到一年就賣完了,還收到不少好評,“應讀者要求”,他又印了1000本。
賣書時,王川舟遇到一位退休的大學教授。教授告訴他,自己也出過一本書,堆在家里沒處放,老婆跟他吵架,讓他把書當垃圾處理掉。教授不愿意,但多次爭吵后只能妥協。教授說,這件事是對他最大的羞辱。他后悔自己沒有勇氣,像王川舟這樣出來賣書。
還有一次,一位相熟的朋友路過書攤,注視他幾秒鐘,走了。過了一會兒,一個年輕人什么都不問,買完書就走。王川舟推測,是那位朋友托這個年輕人買的,朋友這么做或許是怕他難堪。但他并沒有。“我邁出了這一步,就不管他們的看法。”
他也遭遇過一些“冷言冷語”。有個路人經過,說翻譯家在這兒賣書斯文掃地。還有個媽媽指著他對孩子說,不好好學習就會這樣。王川舟不在乎這些聲音,他說:“他們不理解這是一種個人的文化追求。”
“他很有毅力,勇敢追逐自己的夢想。”廣東佛山的一個初二學生看到短視頻后,通過幾個網友介紹加上王川舟的微信,買了兩本書。周圍人都在拼命學習,她害怕考不上高中,覺得自己缺乏毅力。和王川舟在微信上聊了聊,她感覺自己看事情樂觀些了,“這是我開學收到最好的禮物”。
“如果不探尋出路,就會朝壞的方向發展”
賣書時,王川舟喜歡觀察來來往往的行人。他遇到過一個大學生,對方捧著書看了半個小時也沒看明白。王川舟問她最近在干什么,她說在找工作,焦頭爛額,靜不下心來看書。
茫然的年輕人希望在這個書攤前找到方向。
23歲的王同想當一名導演。他在劇組打過雜,給自媒體拍過美食,月收入兩三千元。沒有人脈,學歷不高,他覺得前途渺茫;22歲的程序員劉思剛從一家互聯網公司辭職。他喜歡看書、寫作,想轉行從事文學相關工作……在這些年輕人看來,王川舟是一位“有生活閱歷的長輩”,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生建議。
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王川舟認為自己是幸運的,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時機,又恰逢合資企業興起,轉行做了翻譯。而現在的年輕人讀了大學也不一定好找工作,“面臨很多不確定性”。
在王川舟看來,年輕人的迷茫與缺乏生活的磨礪有關,“累的工作不愿意做,好的工作又進不去”。他鼓勵年輕人多尋找出路,“如果不探尋出路,就會朝壞的方向發展”。他有一個讀者是農村孩子,沒上過大學,畢業后去中亞挖礦。還有一個讀者在印尼開重型卡車,掙了不少錢,“天地廣得很,這也是青年的一種活法”。
他年輕時也是這么摸索過來的。大學畢業后,他懷著科研夢,去一家材料研究所做科研,結果工作沒多久,單位開始“工廠化”,科研經費減少。那時,全民經商的熱潮掀起,王川舟稀里糊涂跟著潮流走,去了汕頭一家外企工作,到了發現只是坐辦公室。他覺得自己的特長是外語,便去重慶一所大學學了一年日語,轉行做了翻譯。“不能一條路走到黑,要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去尋找出路。”
他建議王同先找一份工作養活自己,“不僅僅是為了掙錢,也是為了跟社會建立聯系”,然后再利用業余時間追求自己的導演夢。對于劉思,他也是這么建議的:“必須腳踏實地,走一步看一步。看得很遠,卻一步都不走,那怎么能行呢?”
劉思覺得王川舟的建議很中肯。他打算接下來考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生,如果發現自己不喜歡這個專業,再去找工作。“趁著年輕,多找找自己的方向。”
王川舟有一位讀者,多年來都沒有工作,靠父親養活,悶在家里寫詩。他告訴兩位年輕人,不要太執著于成功,容易“鉆牛角尖”。王川舟也想過,假若自己的書無人問津,是否也會很痛苦,“我不是專業作家,不成功不成名很正常,這樣想就沒壓力了。”
“人得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賣書時間越久,王川舟越覺得這是一個“生活的窗口”。“退休之后我特別有感觸,如果不來賣書,基本跟社會脫節,整天碰不到幾個人。”
通過賣書,他遇到不少有意思的人。接觸過的年輕讀者里,王川舟更欣賞那些堅持奮斗的年輕人。“任何一個時代,如果一個人的精神垮了,就很難辦。”
他認為老年人也應該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翻譯第二本書《血浴》,就是在賣書時認識了作者陶鵬。陶鵬是重慶一位老藝術家,也是第一個把川江號子以藝術形態搬上舞臺的人。2017年春天,王川舟把書翻譯完了。看到譯稿,80多歲的陶鵬很高興,遺憾的是,還沒等到譯本出版就去世了。
他計劃以后再出版一本名叫《市井》的書,記錄他賣書過程中遇到的人和事。他還希望每個城市以后可以設立一個賣書點,讓每一位賣書人都能獲得尊重。
100多年前,他喜歡的詩人惠特曼站在布魯克林的渡口,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百年不變的航船、島嶼和大海,向世人發問:“聯系我們的是什么?聯系我們幾十年或幾百年后的又是什么?”100多年后,王川舟看到了這本書,他覺得連結人們的,是文化和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