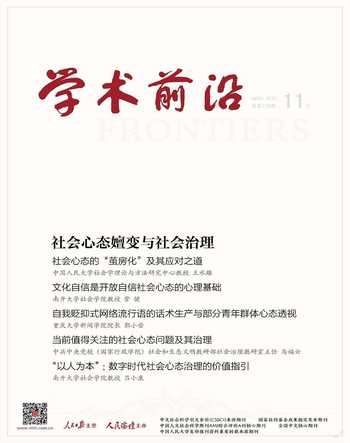社會心態的“繭房化”及其應對之道
【摘要】社會心態是指一定時間內,社會成員的利益訴求、價值觀念、行為意向與心理趨勢。它是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相互作用、互動博弈的產物,會受到形形色色的社會交往“小圈子”和信息傳播“大網絡”的影響。當前,人們社會交往的“小圈子”和“大網絡”不斷向外擴展,社會心態形成與存續方式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繭房化”的特征和趨勢,即人們在社會交往中,越來越多地編織起“小圈子”和“大網絡”的趨同性,形成一個又一個帶有一定封閉性的舒適區。“繭房化”一方面分割了原本可能匯聚的情緒洪流,一定程度上延緩了社會心態危機與失序的到來;另一方面,也容易導致社會心態邁入兩極分化的困境。“繭房化”有多種根源,且極易因為人口、媒體、群體、市場等因素自我強化。為有效應對社會心態的“繭房化”,應大力推進現代化,強化理性溝通原則,推動市場和社會力量互相制約,著力基礎教育,推動在求真程序、審美價值、表態機制等方面形成共識。
【關鍵詞】社會心態? “繭房化”? 小圈子? 大網絡? 心態培育
【中圖分類號】C912.6?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2.001
社會心態是指一定時間內社會成員的利益訴求、價值觀念、行為意向與心理趨勢,它能夠對社會生產生活及經濟運行產生影響,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人的認知、訴求和觀念與其所處的社會地位、家庭環境及獲得的學校教育、社會經驗、知識與信息密切相關。整體的社會心態,則是該社會中的個人之間、組織之間協調、互動與博弈的產物。
研究社會心態,離不開對人口、社會結構與信息技術變遷的關注。分析和研究當前中國社會心態的特點和狀況,有必要尋找人口、社會結構和微觀個體認知、心理之間的內在關聯,由此,信息技術、媒介方式等的發展變化帶來的兩者關聯模式上的變化特別值得重視。本文著眼于社會心態與人口、社會結構及信息技術變遷的關系,認為當前中國社會心態在形成與存續方式上出現了明顯的“繭房化”趨勢,這一趨勢有著多種根源,并且會自我強化,需要審慎應對。
中國社會心態形成與存續中的“小圈子”和“大網絡”
當今社會,人人都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意見表達,社會心態也越來越復雜,對社會心態的分析和研究已經越來越不宜過于籠統,而更應著眼于社會心態的形成與存續問題。學者從不同視角運用不同理論對社會心態形成相關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探討,楊宜音從個體與社會相互建構的視角來討論社會心態的結構和形成機制。[1]王俊秀從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分析了社會心態的形成。[2]周曉虹用社會表征理論、社會認同理論、社會比較理論等來解釋社會心態的形成。[3]高文珺則分析了規范如何傳遞和影響人的思想和行為,對理解社會心態的形成也有一定參考價值。[4]
本文認為,社會心態是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相互作用、互動博弈而形成的一定社會群體內部的利益訴求、價值觀念、行為意向與心理趨勢。由此,每一種社會心態的形成,都會受到形形色色的社會交往“小圈子”和“大網絡”的影響。
所謂“小圈子”和“大網絡”,首先,在最基本的意義上涉及物理空間的范圍。無論身處何地,社會個體總是在某個家庭或者特定的鄰里所處的物理空間內來感知世界。隨著社會個體的成長,其接觸的范圍擴大,這個物理空間的范圍可以相對擴大一些,但即便如此,這個物理空間也是有一定邊界的。人們可以進行較為頻繁的互動的人數是有限的,這便是物理空間意義上所謂“小圈子”。與之對應的“大網絡”,則指向物理空間意義上的更大范圍。即使是在傳統農耕文明社會中,一個村落中的村民也在其“小圈子”之外有著物理空間意義上的“大網絡”。他的“小圈子”可能是他的家族,他所在村莊的村民集體,他的“大網絡”則依賴于他的村莊所處的相對于其他村落、城鎮而言的地理位置,以及彼此間的關系。隨著交通的發展和工業化、現代化的推進,這種物理空間意義上的“小圈子”和“大網絡”,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也在發生變動。因此,個體乃至其所處的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價值觀念、行為意向與心理趨勢也會受到物理空間意義上的“小圈子”和“大網絡”的影響。
其次,“小圈子”和“大網絡”也具有社會空間意義上的內涵。所謂社會空間意義上的“小圈子”,主要是指與個人社會交往更為密切的群體,個人與“小圈子”內的成員溝通信息較多,互動頻率較高,往來的內容更多涉及情感層面,談論的話題也更具廣度和深度。社會空間意義上的“小圈子”,可以基于共同的興趣愛好、一致的價值觀念、協調的默契程度等而建立。在這個維度上,“小圈子”也受到與之相對的“大網絡”的影響。這里的“大網絡”可以是個體所歸屬的特定民族,或者在身體、心智和靈魂上被認定或自我認同其歸屬的、相對于“小圈子”而言較少或沒有什么社會交往的更大群體。“大網絡”成員有著相同的興趣愛好、價值觀念、素質能力和精神品格等。隨著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的突飛猛進,人們的通信愈加便利,社會空間意義上的“小圈子”和“大網絡”,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也在發生變動。因此,個體乃至其所處的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價值觀念、行為意向與心理趨勢也會受到社會空間意義上的“小圈子”和“大網絡”的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我們從物理空間維度和社會空間維度對中國社會心態形成與存續中的“小圈子”和“大網絡”進行了區分,也就意味著這兩個維度的“小圈子”和“大網絡”并不是完全重疊的,盡管有時它們彼此之間有一定程度的重疊性。當然,我們也可以從韋伯所強調的民族、涂爾干所強調的集體、馬克思所謂階級意識或者柯林斯所謂情感能量等維度,對社會心態形成與存續的“小圈子”和“大網絡”進行區分,不過,這些都可以置于我們已有所分析的物理空間維度或社會空間維度之內進行分析。
“小圈子”和“大網絡”除了可以從物理空間維度和社會空間維度進行劃分之外,還需要注意,無論是哪個維度,其中的“小圈子”和“大網絡”都具有相對性,并且會隨著時代進程中制度和技術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變化。例如,一個班集體中三五個好朋友,可能構成社會空間維度上的“小圈子”;而這個班集體是其相對意義上的“大網絡”。但是,從更大的范圍看,又可以說,班集體本身是物理空間維度上的“小圈子”,而整個學校是其相對意義上的“大網絡”。當然,進一步從更大的范圍看,還可以說,學校本身是社會空間維度上的“小圈子”,學校所處的教育教學系統是其相對意義上的“大網絡”。“小圈子”和“大網絡”,就是這樣一層一層地嵌套或者鑲嵌在一起。
“小圈子”和“大網絡”之所以對社會心態形成與存續有重要影響,是因為它們與人們的互動密切相關。互動對于人的意識形成的重要性,為米德、戈夫曼、柯林斯等諸多社會學家所強調,它甚至對“自我”概念的形成等都有著決定性作用。
“繭房化”:當前中國社會心態值得重視的一個特征和趨勢
社會心態形成與存續的“小圈子”和“大網絡”之間在關聯方式上有著相當復雜且值得深入分析的內容,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各類科技的發展,如軍事科技、交通科技等。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媒介方式的發展進步,對社會心態形成與存續有現實重要性的“大網絡”,已經達致了它可以窮盡的邊界——全球,或者說整個地球上的人類。盡管我們對外星文明有一定的猜想,但是,目前為止這種猜想還不足以如科幻小說中所描寫的那樣形成地球人作為“小圈子”的社會心態,因而我們的利益訴求、價值觀念、行為意向與心理趨勢,都是相對于地球上的其他人而言的。
當前,人們社會交往的“小圈子”和“大網絡”不斷向外擴展,中國社會心態形成與存續方式,卻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繭房化”的特征和趨勢。社會心態形成機制與存續方式的“繭房化”,與信息“繭房化”有一定的相關性,指的是人們在社會交往中,特別是在利益訴求、價值觀念、行為意向與心理趨勢等方面越來越多地編織起“小圈子”和“大網絡”的趨同性。也就是說,人們有意識地通過組織或加入某個“小圈子”,來迎合“大網絡”中的某種社會心態;或者,通過編織作為社會環境的“大網絡”來讓既有“小圈子”中的社會心態獲得相對應的、新編織“大網絡”的支持。
這種社會心態形成機制的“繭房化”,至少包含著如下幾個方面的特征和趨勢。
基于社會心態“繭房化”構建的“小圈子”和“大網絡”,有著不同于以往的封閉性。以往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意義上“小圈子”和“大網絡”的封閉性,往往與人際往來或信息溝通上的客觀隔離或人為斷絕密切相關。當封閉的“小圈子”和“大網絡”在交通或通信方面產生連接,以往的封閉性就可能自然而然地被打破。但是,當前社會心態形成機制的“繭房化”所具有的“封閉性”,則意味著不同的“繭房”之間不至于交通隔離或通信斷絕,也不存在“小圈子”與“大網絡”之間聯系不夠的問題。封閉性更多地表現為,人們在面對一些全球性大事件、一些大是大非問題時,往往會持有迥然相異的立場觀點、價值取向,并進行相應的話語表達,由此構成一個個同時貫通“小圈子”和“大網絡”的“繭房”。“繭房”內部在利益訴求、價值觀念、行為意向與心理趨勢上獨具特色,而又能夠具有一致性、趨同性、正當性、原則性和邏輯自洽性,能夠獲得其成員的認可、認同。由于“繭房化”有其或源于情感、歸屬、信仰方面的動機,或出于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方面的考量,所以要突破由此形成的封閉性,是比較困難的。
對舒適區的刻意經營與固守。在社會心態的“繭房”內部,人們正在形成自己利益訴求、價值觀念、行為意向與心理趨勢上的舒適區。因為不僅有“小圈子”的配合,還有“大網絡”的呼應,所以人們在這樣的“繭房”中,會有一種如魚得水、心安理得、怡然自得的感覺。從這樣的舒適區中破繭而出,去思考另一種或另一些邏輯、立場與方法,以及人生、社會與現實問題,不僅需要極強的好奇心、巨大的勇氣,還需要有良好的反思能力和敢于自我挑戰的素質。而這樣的人不是早早地離開就是根本不會進入此類“繭房”,因此,在這類“繭房”中,一種娛樂至上的傾向性或各種慢節奏會消磨人們對現實世界底層邏輯的追問。更有甚者,逆來順受的觀念與心理會蔓延開來,久在“繭房”中的人們,通常有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姿態和處事方式,不僅自己不敢站出來揭露“繭房”中的景觀與真實世界的巨大差距,而且越來越傾向于勸喻與自己關系密切的人或“小圈子”中的親人朋友少管閑事,別去費力不討好地破壞“大家”的舒適區。
“繭房”內部排斥異質性主張和取向、黨同伐異的可能性極大。社會心態形成和存續機制的“繭房化”,會導致哪怕是針對同樣的信息、完全相同的表述,也會產生差異較大的理解和解讀。同一問題通過各自“繭房”的內部溝通、交流、共振、共鳴機制,經過“篩選”“過濾”形成的“小圈子”和“大網絡”的相互激蕩,極有可能在不同的“繭房”間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在各個“繭房”之間,一些基礎性、經得起核驗的真相類信息的傳遞是可能的。但由于缺乏共同認可的信息理解和解讀程序與規則,“繭房”間的有效溝通十分困難,彼此間還會產生對方“動機不純”“人品有問題”的猜想。于是,人們寧愿被指責為“黨同伐異”,也要排斥乃至抗拒異質性主張和取向。
社會心態日趨兩極分化。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系列影響未來世界走向的大事件正在發生,而這些事件往往會引發中國社會極為熱切的關注,“繭房化”下的不同社會群體也不例外。往往是那些利益訴求、價值觀念、行為意向與心理趨勢越極端的“繭房化”群體,越傾向于以鮮明的態度和急切的熱情,來發表他們的看法。于是乎,利益、觀念、心理等立場撕裂的現象隨處可見。這種撕裂導致的一個顯而易見的結果是,一些相對溫和、中庸的立場和表達容易被忽視,或不容易引發關注,民眾的利益訴求、價值觀念、行為意向與心理趨勢可能會被裹挾著,進一步向社會心態的兩極匯聚。于是,社會心態失衡、傾斜、兩極分化的現象日趨明顯,例如,對收入差距現象的不同態度聚集出“炫富”與“仇富”兩個極端;對追求利益的不同態度匯流成的“勢利”與“佛系”兩個極端;對承擔家庭與社會責任的不同態度積淀出的“進取”與“躺平”兩個極端。社會心態失衡、日趨兩極分化的趨勢日漸顯著,而這將給社會治理帶來不小的挑戰。
當前中國社會心態“繭房化”形成的多種根源
當前,中國社會心態的“繭房化”,有著多方面的根源。有些是客觀因素導致的,有些則源于人為因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多種文明并存。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及其在生產生活領域的大面積推廣,使得十幾個世紀的文明仿佛被壓縮在一起。游牧文明、農耕文明、工商文明、數字文明在當今的中國都能找到縮影。文明不同、文化不同、時代不同,自然地會導致人們成長和心態形成的生境不同、環境不同、情境不同。不同文明的科學技術實踐主導下,不同的群體性社會心態難免會發生差異、分歧、隔離、“繭房化”,甚至是進一步的對立、沖突。
經濟社會飛速發展,貧富差距同時不可避免地有所增大。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飛速發展,迅疾的社會變動導致人們的生活境遇也隨之改變,利益訴求、價值觀念、行為意向、心理趨勢、生活方式上的異質性全面增加。社會貧富差距加大,一些民眾會建立“人以群分”的認知進而傾向于“抱團取暖”,甚至會以比過去更熱切、急迫、激進的姿態在“小圈子”和“大網絡”的支持下表態、發聲,形成一個個社會心態的“繭房”,進而演化出態度鮮明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意向。
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整體延長,不同世代間的代溝加深。新中國成立前我國人均預期壽命不足35歲,到2022年則達到了77.93歲。[5]社會學者一般認為10到15年算作一個世代。而今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青少年的生活境遇每隔4、5年就會更新換代一番,世代的劃分也因此有進一步縮短年齡跨度的趨勢,而世代之間的代溝則在加深。數個乃至十多二十個世代生活在同一個時空條件下,社會心態的差異顯而易見,基于同世代的人而形成社會心態的“繭房化”也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年輕的世代為了表達的自由和掌握一定程度的話語權,往往會在線上乃至線下突破約束,形成多種多樣的亞文化。
社會轉型帶來制度和文化的明顯改變。從新中國成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在制度和文化等宏觀層面上,發生了明顯的或松或緊的變化。不同群體潛移默化之間接受的價值觀念、權利意識、行為意向、生活方式等自然也呈現出顯著差異。某些人或許會認同“潛規則”這樣一種長期存在于中國歷史傳統中的隱性規則系統,[6]另一些人則完全可能倡導和奉行新型價值觀,強調和主張平等的合約意識和對個體權利的維護。
不同人群偏愛和接受知識和信息的渠道和媒介有明顯差異。不少中老年人可能喜歡看新聞聯播,傾向于通過電視來接受信息和學習相關知識。伴隨著中國互聯網事業的發展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則不斷地通過“匯聚—游離—再匯聚”的方式,讓新型社交媒體更新換代,博客—微博—微信—抖音—快手—ChatGPT……一個個網絡平臺推陳出新,形成縱橫分割之勢。有的人仍保留著從書本中吸收系統性知識的習慣;有的人傾向于通過瀏覽互聯網上的最新文章來獲取觀點和看法;更多的人則越來越熱衷于通過刷短視頻來了解不同的觀點和情緒的宣泄。不同世代、階層、群體、網民的多樣化、復雜化的社會心態,在縱橫分割的渠道、媒介、平臺中匯聚、激蕩,加快了“繭房化”的步伐。
對求真程序、審美價值、表態機制缺乏基礎性、廣泛性共識。中國傳統學校教育中缺少求真程序、審美價值和表態機制方面的內容。這類基礎性、廣泛性共識的缺失,導致有不同社會心態的民眾之間缺乏有效溝通交流的基礎,轉而傾向于在擁有同類價值觀念、行為意向的民眾中尋求支持、點贊和共鳴。由此,愈發導致一些人難以相信有內在一致的真相、美德和價值的存在,當他們面對不同的甚至是明顯扭曲的心態時,可能會產生強烈的無力感,也由此缺乏為尋求內在一致而進行交流、協商的努力。
當前中國社會心態“繭房化”的強化機制
當前中國社會心態“繭房化”的形成和存續,除前文所述的復雜根源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在推動其不斷得以強化。
“繭房化”社會心態形成機制的自我強化性。如前文所述,社會心態形成與存續中的“繭房化”,很大程度上是在編織起“小圈子”和“大網絡”的趨同性,是在形成某種舒適區。舒適區的存在意味著,人們留在舒適區比走出舒適區容易得多。因此,社會心態形成和存續的“繭房化”自身內在地具有自我強化的傾向性。而走出“繭房”,需要莫大的勇氣,更不必說身在其中的人破除它了。
高度可視化、算法化推送的媒體,以及視覺素養不一的社會群體并存,促使“繭房化”的自我增強。“視覺素養”是大眾文化產業在視覺形象生產端與消費端辨別美丑的價值判斷能力,它以真善美的價值判斷為依據規定了視覺主體理應堅守的價值觀,不僅涉及意識形態內容,還隱藏著不同話語形態間的復雜關系。[7]正如前文所述,當前民眾在求真程序、審美價值、表態機制等方面缺乏基礎性、廣泛性共識。“視覺素養”的不足和差異讓社會心態極易被算法推送機制所左右,陷入“繭房化”的自我強化機制之中。
對熱點事件的關注、關心和情緒化表態,使社會心態的“繭房化”進一步強化。現實生活的壓力、追求成功的期盼,易使民眾產生強烈的出人頭地的動機和焦慮情緒。但是,理想與現實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沖突。于是,一旦一些熱點事件出現,民眾就會通過各種信息渠道和媒介,對其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和關心。一些擅于使用自媒體、社交APP的人,往往會作出比較情緒化的表態。在經歷一番訴求、觀念、意向的碰撞之后,這些人往往會因其極富情緒化和頗具煽動性的表態而積累不少“粉絲”,甚至形成“飯圈”。在“我的地盤我做主”思想的驅使下,心態“繭房”的編織會日益得到強化。
市場力量有推進社會心態“繭房化”的動機,并傾向于將其付諸實踐。在對求真程序、審美價值、表態機制缺乏基礎性、廣泛性共識之時,另一種“共識”不可避免地日益凸顯,這便是消費主義在數字文明時代的新版本——流量為王。逐利者為吸引眼球、追求流量、實現流量變現,傾向于將“繭房化”進行到底,甚至希望能再通過類似“平臺算法”的機制為其套上一個只進不出的外殼。
有些地方尚未樹立重視社會心態建設的意識,進而有時會縱容社會心態形成與存續的“繭房化”。部分領導干部未能正確認識前置工作的重要性,對“繭房化”形成和存續的干預存在“不攬事”“怕擔事”的心理,在極端化社會心態發酵過程中少有作為。于是乎,“繭房化”的形勢不免更趨嚴峻,一些消極心態越來越能找到它們的庇護所乃至共鳴堂。
當前中國社會心態“繭房化”的應對之道
應對當前中國社會心態形成與存續的“繭房化”,需針對性精準施策,有些問題需要分階段著手推動改變,不能急求畢其功于一役;而有些問題則需要在當下就積極推動解決。應對好這一問題,既能為個人生活乃至社會狀況的良性變革提供可能,也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以應對潛在的社會心態危機與失序。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歷程,在這一迅速的現代化和劇烈的社會轉型進程中,潛在的社會心態危機與失序值得引起高度重視。社會心態形成與存續的“繭房化”一方面分割了原本可能匯聚的情緒洪流,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危機與失序的到來;另一方面,若“繭房化”的社會心態不能得到有效應對和疏導,將可能出現社會情緒集體失控的局面。我們當前仍需堅定不移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完善民生福祉,促進社會公平,真正有效地解決潛在的社會心態危機與失序。
強化理性溝通原則,盡可能避免社會心態的兩極分化。要加強各社會心態“繭房”間的理性溝通。應通過媒體宣傳加引導,在全社會倡導和強化理性溝通原則,提升包括自媒體在內的諸多媒體的理性溝通和引導能力,積極對社會大眾進行情緒疏導,增強民眾聆聽他人、同理同情、獨立反思、自我反省的能力。推動更多人走出心態“繭房”舒適區,敢于直面異質性信息和評價,并避免消極的心理體驗,塑造開放、進取、理性、客觀、平和、包容、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
推動市場和社會力量互相制約,有意識地避免過偏、過激地引導乃至誤導社會心態。當前我國社會心態形成和存續的“繭房化”,是由多種因素導致的。市場力量“拉偏架”,社會力量“出重拳”,都容易刺激社會心態的進一步“繭房化”。鑒于此,應摒棄簡單、粗暴的信息屏蔽、溝通隔離的作法,正確疏導社會情緒,讓不同的力量發出不同的聲音,讓基礎的共識在碰撞中產生,進一步促進民眾理性思考、作出判斷。
著力基礎教育,推動形成求真程序、審美價值、表態機制等方面的廣泛共識。在系統開放、文化多元的社會中,避免社會心態的“繭房化”需要著力在最廣泛、最基本的層面推進共識。為塑造積極、健康的社會心態,不少政策和治理措施已相繼出臺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應看到,“心態培育”不僅是一道政治題,還是一道經濟題、社會題、文化題,更是一道教育題。應從基礎教育抓起,強化求真程序、審美價值、表態機制等方面的培養和訓練。
注釋
[1]楊宜音:《社會心態形成的心理機制及效應》,《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2]王俊秀:《社會心態的結構和指標體系》,《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2期。
[3]周曉虹:《轉型時代的社會心態與中國體驗——兼與〈社會心態:轉型社會的社會心理研究〉一文商榷》,《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4期。
[4]高文珺:《社會心態研究綜述與研究展望》,《中國社會學年鑒2011-201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5]王水雄、陳虹梅、張若天:《當代中國母職行為的價值困境:由來、紓解與親職倡導》,《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23年第4期。
[6]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7]李健:《大眾文化視覺表意實踐與當代中國社會心態》,《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參考文獻
王水雄、周驥騰,2022,《中國Z世代青年亞文化的由來、發展與應對》,《中國青年研究》,第8期。
責 編∕包 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