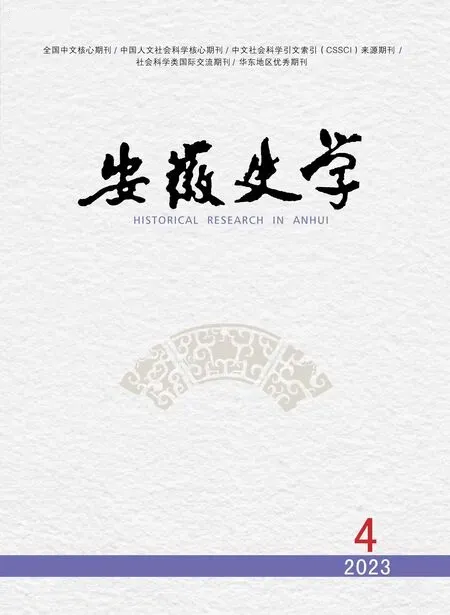論姚永樸《文苑列傳》對桐城派史的書寫
戚學民 唐銘鴻
(清華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84)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歷來記載桐城派史的官私著作較多。(1)清代的觀點,私家以曾國藩、王先謙等人為代表,馬其昶《桐城耆舊傳》亦對桐城一地的學派先賢有所記載;官方以國史《文苑傳》為主。近代以來,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等書亦極為重要。20世紀“文學史”學科誕生以來,學界對桐城派史的研究豐富多彩,桐城派的脈絡發展、文藝理論、學術特質、作品成就等本體層面的成果頗為豐碩。近年來對桐城派史的學術史研討獨樹一幟。(2)典型的研究,如王達敏:《姚鼐與乾嘉學派》,學苑出版社2007年版;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陳用光、梅曾亮、曾國藩、吳汝綸四大古文圈子為中心》,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桐城派相關研究可參見綜述類文章,如江小角、方寧勝:《桐城派研究百年回顧》,《安徽史學》2004年第6期;張晨怡、曾光光:《桐城派研究學術史回顧》,《船山學刊》2006年第1期。諸種文學史大多肯定桐城派在清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其中,如郭紹虞認為桐城派系清代唯一最大古文流派的觀點,對學界影響甚重。相對于本體層面的桐城派文人和作品的研究,在歷史認知層面對各種桐城派史的討論尚有待發之覆。
在各種桐城派史之中,清廷官方代表的清史《文苑傳》的記載有獨特價值。在清史《文苑傳》的多個稿本中,有系統的古文史記載,桐城派史一直是其中記載重點。筆者曾略論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欽定國史文苑傳》和第四次稿《續文苑底稿》對桐城派史的記載。(3)戚學民:《桐城傳人與文苑列傳》,《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4期;戚學民、唐銘鴻:《論〈續文苑底稿〉對桐城派史的續寫》,《安徽史學》2022年第1期;溫馨:《陳用光與清國史館〈文苑傳〉中桐城派譜系考》,《安徽史學》2022年第1期。桐城學人陳用光在國史館期間建構桐城派之古文正統地位,為后來的修史工作奠定基礎。而清史《文苑傳》其他檔案對桐城派史的記載內容鴻富,值得進一步研討。
清史《文苑傳》的桐城派史記載有一個特色,即嘉道時期和民國清史館時期,均有桐城派傳人參與纂修。清史《文苑傳》的桐城派史較之私人著述有正史的權威,桐城派人在清國史館和清史館參與纂修使得其中的桐城派史更加厚重。桐城后學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等對《清史稿》整體成書的貢獻,學界曾有討論。(4)目前,學界對清史館內桐城學人的研究重點在行誼、交游等事實層面,對于有關桐城派建構的工作重視不足。許曾會關注到馬其昶《文苑傳》、姚永樸《食貨志》、姚永概“諸名臣傳”等編修方面的成就,張秀玉則對姚永概《清史擬稿》做過詳盡分析。上述研究均未提及姚永樸撰《文苑列傳》稿本,亦未能對馬其昶的論述具體展開分析,未免可惜。參見許曾會:《桐城派與〈清史稿〉的編修》,《史學史研究》2016年第2期;張秀玉:《姚永概〈清史擬稿〉考論》,《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張秀玉:《清末民初桐城派士人的“倔強堅守”——以客居北京的桐城籍作家為中心》,《社會科學輯刊》2022年第4期。清史館中桐城學人對桐城派史的書寫規模更大,學界尚無深入研究。具體到姚永樸對清史《文苑傳》中桐城派史的撰述之功,更不為人知。姚氏曾纂成《文苑列傳》,涉及對桐城派史的書寫,但其成果長期以檔冊形式保存在清史館檔案全宗之中。本文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姚永樸擬清史《文苑列傳》稿本檔案為中心,討論他對桐城派史的書寫。
一、姚永樸與清史《文苑列傳》
姚永樸,字仲實,安徽桐城人,姚瑩之孫,曾師事同鄉方宗誠、吳汝綸,對近代教育事業為功甚巨,所撰《文學研究法》《史學研究法》等書影響重大,與姻兄馬其昶、弟姚永概均為清末民初桐城派代表人物。馬其昶和姚氏兄弟是民國初年知名桐城學人。姚氏兄弟為“姚門四杰”之一姚瑩之孫,馬其昶之夫人姚氏為二人之姊,姚永樸則迎娶馬其昶之妹,桑梓情誼與姻親聯結,使得三人關系緊密。姚永樸于1914年至1922年期間在清史館任職八年,由協修升至纂修,擔任列傳、《食貨志》纂修工作,《清史稿·食貨志》中《鹽法》《戶口》《倉庫》《茶法》等為其所撰。但是他對清史《文苑傳》的纂修亦有貢獻,涉及桐城派史的書寫,卻不為人知。
如前所述,桐城學人對《清史稿》成書的貢獻,學界已經有所考察,但是他們具體纂修工作有待深入討論。姚永樸曾對清史《文苑傳》的桐城派史記載有貢獻,但當事人回憶未及此點。如曾師承姚永樸、馬其昶的李誠記述,“幫助馬通伯撰寫光緒、宣統兩代列傳的,有纂修姚永樸和鄧邦述”。(5)李誠:《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館》,《江淮文史》2008年第6期,第79頁。朱師轍也說姚永樸曾經編纂光宣兩朝列傳,卻并未提及其纂修《文苑列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史館檔案全宗揭示了姚永樸在《文苑傳》中的工作成果。臺北故宮博物院館文獻編號701006315的《文苑傳目》檔冊,記載了清史館內諸纂修官的《文苑傳》分工情況。據此,姚永樸曾為《文苑傳》撰戴名世、方東樹、梅曾亮、吳德旋、湯鵬、包世臣、馮桂芬、吳汝綸、方宗誠等9人傳,并上呈史館。
前述《文苑傳目》中所載姚永樸所撰的9個傳記,以題名《文苑列傳》的四個檔冊存世。按照內容,實際上被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多人傳記匯稿本。這包括文獻編號701006791朱絲欄抄本《文苑列傳》,是戴名世、方東樹、梅曾亮、吳德旋、湯鵬、包世臣、馮桂芬、吳汝綸8人傳記匯稿。另外包括文獻編號701006792的紅格抄本、署名《文苑傳》的檔冊,為戴名世、方東樹、梅曾亮、吳德旋、包世臣、吳汝綸6人傳記的清繕本。其二是《方宗誠傳》檔冊。這體現在文獻編號701006789的《文苑列傳》朱絲欄抄本和文獻編號701006790的《文苑傳》紅格抄本,兩者均是《方宗誠傳》單傳。
姚永樸《文苑列傳》未注明纂修工作的詳細時間,但其撰著當在1914至1921年期間。按清史館開館后,繆荃孫擔任總纂,總輯《儒林傳》《文苑傳》等。他曾到館商議具體纂修事宜,在京逗留約一月(6)《繆荃孫全集·日記三》,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347,345,443頁。,與史館同仁多有互動溝通,其間亦曾與姚永樸會面。(7)《繆荃孫全集·日記三》,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347,345,443頁。之后,繆荃孫主要在滬辦理《文苑傳》等傳記的纂修工作,并曾于1916年5月入京交五卷本初稿(8)《繆荃孫全集·日記三》,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347,345,443頁。,后又于1918年7月交一卷補稿。(9)《繆荃孫全集·日記四》,第85頁。馬其昶則于1916年應館長趙爾巽之聘,入館任總纂,負責編纂《儒林傳》《文苑傳》。(10)陳祖壬:《桐城馬先生年譜》,《晚清名儒年譜》第16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頁。1921年,馬其昶纂成《文苑傳》。
姚永樸的《文苑列傳》應形成于1916年進館之后(繆荃孫已經在1915年呈繳了清史《文學傳》),1921年《文苑傳》成稿之前。兩種不同《方宗誠傳》檔冊封面上有“協修姚永樸”字樣,根據章鈺、張爾田等人回憶,在1916年馬其昶添聘入史館前,姚永樸仍為協修,而在朱師轍的回憶記載中,姚永樸最終升至纂修。(11)筆者按,馬其昶在名錄中被列為“后來添聘者”,顯然章鈺手書此名單在其被聘之前,故有此推斷。參見朱師轍:《清史述聞》,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40頁。此具體升遷時間不可考,但可以確定,至《方宗誠傳》編纂之時,姚永樸仍任協修。此條可以作為《文苑列傳》成稿時間的佐證。
清史館曾經有對清朝時已經立傳者另起爐灶的計劃,留存至今的清史館檔冊中有多種重輯的人物傳記。《文苑傳目》及姚永樸《文苑列傳》顯示,史館對繆荃孫撰《文學傳》(清史《文苑傳》第六次稿)也有所不滿,組織了重纂。趙爾巽對繆荃孫所纂《儒學傳》《文學傳》稿本曾有評價:“所惜為傳四十,而重者乃至廿人之多,未免空費日力。若如鄙見,先將欲纂之人見示,則無此弊矣。以后仍望先行抄示,館中已纂者即當另錄副呈閱。(擇要可,全錄亦難。)其文字之糾正,篇幅之分合,聽公擇定,并祈轉告絅齋,取一致之行動為要。”(12)錢伯城、郭群一整理:《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8頁。據趙爾巽意見,繆荃孫抄示的四十個傳記中,竟有二十個傳與清史館存稿重復,比例相當高。清史館因時代動蕩,常為人手不足、經費有限而苦惱,再有重復工作,降低了效率。趙爾巽提議將已纂之人整理錄副,是提高撰修工作效率的必要之舉。
清史館對繆荃孫呈繳的《文學傳》有意見,這是馬其昶任總纂,纂成清史《儒林傳》《文苑傳》第七次稿的的原因。《文苑傳》第七次稿的具體情況容本人另文研究。本文僅指出,這次重纂原有的構想可能規模較大,包括新增和重撰某些人物的傳記。姚永樸《文苑列傳》當奉史館總裁或總纂之命而作,是這次重纂的過程稿之一。姚氏《文苑列傳》多位正傳均為桐城派中人,其中的戴名世、方東樹、梅曾亮、吳德旋、吳汝綸、方宗誠更是今日桐城派史研究中的代表性人物。但是因為館務的變動,姚氏《文苑列傳》僅一位被采用,其余傳稿成為檔案史料。
二、《文苑列傳·戴名世傳》與早期桐城派史記載
姚永樸撰《文苑列傳》雖然只有9位正傳人物,但多個傳記涉及桐城派史的某些重要問題,是桐城派史的重要史料。
首先值得重視的是,姚永樸首次為戴名世立正傳,客觀上把清史《文苑傳》桐城派史向前伸展到清初。《文苑列傳·戴名世傳》是戴氏首次在清史《文苑傳》中立傳。桐城派在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纂修時即被載入(13)戚學民:《桐城傳人與文苑列傳》,《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4期。,但戴名世因政治問題并未在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獲得立傳。按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纂修工作中,因政治問題未能立傳人物不止戴名世一人,其他如錢謙益、屈大均、魏禧等明末清初重要文士也是同樣遭遇。
姚永樸纂《戴名世傳》參考了方苞《南山集序》與馬其昶《桐城耆舊傳》,主要遵循了馬其昶既有傳記的思路,但文字內容有刪減。《戴名世傳》在列述了傳主生平行誼后,主要記載了他的古文及史學成就,收錄其《答余生書》的大段原文。姚永樸記載了戴氏獲罪經歷及結果,稱其“夙負文譽,既構禍,遂無有道其為人者,或及之,輒隱其名”。(14)姚永樸:《文苑列傳·戴名世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701006791,第2、1、1頁。本文檔案皆為臺北故宮博物館藏,下不再標藏地。戴名世出身桐城,與方苞往來密切,其學“長于史” 且“天下又翕然稱其古文”。(15)姚永樸:《文苑列傳·戴名世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701006791,第2、1、1頁。本文檔案皆為臺北故宮博物館藏,下不再標藏地。
姚永樸強調戴名世的史學成就及古文成就。“其學長于史,時時著文以自抒湮郁,氣逸發不可控御。于是天下又翕然稱其古文。”(16)姚永樸:《文苑列傳·戴名世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701006791,第2、1、1頁。本文檔案皆為臺北故宮博物館藏,下不再標藏地。這是馬其昶《桐城耆舊傳》中的表述。(17)馬其昶:《桐城耆舊傳》,黃山書社1990年版,第297頁。而《桐城耆舊傳》中記載戴名世負才自傲,“負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18)馬其昶:《桐城耆舊傳》,黃山書社1990年版,第297頁。,姚永樸并未引述。戴名世對方苞之言,見方苞《南山集序》與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姚永樸撰《戴名世傳》標注將《南山集序》納入,或許便與這句話相關。《戴名世傳》主要參考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兼及方苞《南山集序》。
姚永樸并未將戴名世納入桐城派的脈絡中加以描述,全篇除了提及方苞外,未涉及劉大櫆、姚鼐,而是將戴名世視作籍貫桐城的一位獨立學人而表述。顯然,姚永樸沒有以戴名世為“桐城之祖”,此點可供學界參考。按學界對戴名世的生平經歷、文集版本,以及“南山案”始末等事實的考證等研究較多,研究重點在于戴名世是否是桐城派一員,或戴氏與桐城派的關系等。民國以來,梁啟超、柳亞子、章太炎、陳石遺、吳孟復、劉聲木等人均視戴名世為桐城派成員。然近年亦有學者提出異議,如王達敏認為姚鼐對桐城派的建構是桐城立派的關鍵,而戴名世并不位于這一體系中。
姚永樸《戴名世傳》對傳主學問成就的評價,似乎低于馬其昶《桐城耆舊傳》的說法。按馬其昶評:“(戴名世)先生生平酷慕司馬子長之文,每引以自況。”(19)馬其昶:《桐城耆舊傳》,第297頁。隨后載錄《孑遺錄》中《答余生書》的內容。姚永樸則未將戴名世與司馬遷相對比,也并未記錄戴名世以司馬遷自況之心。在正史傳記中,將傳主與過往文人名士相比擬以顯示傳主成就是典型做法。如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中,多用帝王評價來彰顯作者水平。姚永樸沒有采納馬氏對戴氏之文的評價,顯然別有看法。姚永樸《戴名世傳》也并未采用馬其昶《桐城耆舊傳》這一段話:“上嘗問文貞:‘自汪霦死,誰能為古文者?’對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叩其次,即以名世對,上亦不之罪也。”(20)馬其昶:《桐城耆舊傳》,第297頁。此文貞為李光地。按,馬其昶引此事,是為了展示戴名世之古文被康熙和李光地所肯定。姚不采納馬其昶對戴氏古文兩處高度評價,可見微意。姚永樸在《戴名世傳》最后加了一句:“名世死后,其遺稿為徒友所私寫而存之者,今尚十余卷。”(21)姚永樸:《文苑列傳·戴名世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5頁。這與目前學界所知相符。姚氏也補充記載戴名世被化名為“宋潛虛”以留存文集的情形。
如前所述,姚永樸的《戴名世傳》基本上脫胎于馬其昶的《桐城耆舊傳》,對一些具體表述有所刪減。縱覽各種《戴名世傳》,在論述其史學成就時,都參考《答余生書》的內容,強調《孑遺錄》的創作事實。或許這確是戴名世的成就重點,又或許這與他最終罹難息息相關——在這樣的襯托下,戴名世的古文成就似乎沒有那么“耀眼”了。但事實上,戴名世的古文的確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馬其昶、姚永樸將對其古文的記載放在史學之前,便是顯證。且方苞為《南山集》作序,姚永樸又引用該序,也是對戴氏古文的推崇。
姚永樸為戴名世在清史《文苑傳》立傳,是將其作為古文和史學的代表。但姚氏筆下的戴名世并沒有大書“桐城派”,全傳中只是客觀敘述了戴名世籍貫桐城的事實。盡管文字是引用自馬其昶的《桐城耆舊傳》,但是并沒有強調戴名世與桐城派的聯系。這種很克制的書寫是正史和私家著述的差異。在桐城派立場上,當然對桐城派脈絡說得越廣越好,但正史記載必須嚴謹審慎。姚永樸任職清史館,承命為桐城前輩戴名世立傳,卻不強說戴氏為桐城派,這種謙抑態度應被重視。
今日學界習知的《戴名世傳》是刊行的《清史稿·文苑傳》(卷484)中的《戴名世傳》,該傳底本是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史館全宗中文獻編號701007911無名列傳匯稿本《戴名世列傳》。(22)《戴名世列傳》,文獻編號:701007911,第191—194頁。此一匯稿本未采用姚永樸的《戴名世傳》,而是另起爐灶。后來付梓的《清史稿·文苑傳》中《戴名世傳》則在匯稿本的底本基礎上進一步刪改,記載更加簡略。姚永樸本被放棄的原因,以及這后兩個版本的《戴名世傳》作者都待考。但無論如何,姚永樸的《戴名世傳》是清史館中第一個為戴氏撰寫的傳稿,將馬其昶的私著上升為正史,客觀上將桐城文人在正史《文苑傳》的記載提前到清初。姚氏的《戴名世傳》是戴氏和桐城派史的一則重要史料。
三、《文苑列傳》與嘉道時期桐城派史的增改
姚永樸《文苑列傳》中方東樹、梅曾亮、吳德旋三篇傳記是對嘉道時期桐城派史的增補與改寫,是第二個值得關注的點。姚鼐及其門人在桐城派發展過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嘉道時期也是桐城派發展的重點。清國史館和清史館時期的桐城派史記載均強化姚鼐的地位。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中,姚鼐便已立正傳,并經欽定成稿。《續文苑底稿》對姚鼐的傳人有重點記載,梅曾亮、管同、姚瑩等立正傳。民初清史館續纂《文苑傳》,對清國史館時期的傳稿有因有革。姚永樸《文苑列傳》重纂姚門弟子數人傳記,顯示了清史館對桐城派史的重視,是正史系統中嘉道時期桐城派史的重要資料。
《文苑列傳》中的《方東樹傳》極富意義。在清史《儒林傳》與《文苑傳》纂修過程中,因受漢宋之爭的影響,方東樹遲遲未獲立傳。繆荃孫曾引張之洞之言,“南皮師云,植之本屬漢學,后自揣不能勝諸家,故反用之,以獵取名譽,為溫飽計”(23)繆荃孫:《方東樹儀衛堂集跋》,《繆荃孫全集·詩文一》,第220—221頁。,對方東樹頗為不滿。光緒年間繆氏主持纂輯《儒林傳》《文苑傳》,均沒有為方東樹立傳。特別是《續文苑底稿》(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的底本),為多名姚鼐后學,特別是姚門四杰立傳。“姚門四杰”的具體構成,姚瑩、曾國藩、王先謙等諸家說法不一,但總不出姚瑩、方東樹、劉開、管同、梅曾亮五人。《續文苑底稿》中姚瑩、管同、梅曾亮均有正傳,劉開是附傳,方東樹傳則闕如。
但方東樹終于在陳伯陶主持纂輯清史《儒林傳》中立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國史館檔案,《方東樹傳》位于七十三卷本《儒林傳》中,系上卷第二十九,為新輯傳記。該傳記有三種不同的版本,分別為編號701003929、編號701005252、編號故殿033496。雖然版本不同,但傳文內容相同。其中,701005252為成興齋稿紙版本。此《方東樹傳》國史館本傳是陳伯陶主持纂修的清史《儒林傳》第五次稿(此次纂修的具體情況本人另文研究),時間已經到了清末。
《儒林傳·方東樹傳》記載了方東樹力宗程朱,反對漢學和陽明學的學術主張和作為。重點在以《漢學商兌》為核心的理學著述,將《漢學商兌》視為“海內競尚考證”(24)《儒林傳·方東樹傳》,文獻編號:701003929,第16、20、15、19—20頁。背景下為宋學張目之作,指出該書在當時獲得學界強烈反響。有關方東樹與“桐城派”之間的關系,本傳記載與姚鼐的師承,也記載其引領了理學風氣,“然桐城自東樹后,學者多務理學云。”(25)《儒林傳·方東樹傳》,文獻編號:701003929,第16、20、15、19—20頁。本傳對傳主古文有所提及,稱其“學古文于同里姚鼐”(26)《儒林傳·方東樹傳》,文獻編號:701003929,第16、20、15、19—20頁。,“古文簡潔涵蓄不及鼐,能自開大以成一格”(27)《儒林傳·方東樹傳》,文獻編號:701003929,第16、20、15、19—20頁。,但因為是《儒林傳》,所以古文不是記載重點。清史館時期,繆荃孫再度擔任總纂,將方東樹從《儒林傳》移入《文學傳》,降為姚鼐的附傳。
姚永樸在《文苑列傳》中將方東樹從附傳升為正傳。姚氏《方東樹傳》依據國史館《儒林傳》同名傳記、《安徽通志》、馬其昶《桐城耆舊傳》纂成。《安徽通志·方東樹傳》內容極為簡單,未出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和國史館舊傳的范圍。但姚永樸《方東樹傳》記載重點發生了變化。其一,對方氏古文和詩歌的表述明顯變多,這明顯是依據《文苑傳》內容,調整了記載重點。傳文指出方東樹師承姚鼐,博覽群書,學問廣博:“師事姚郎中鼐,泛覽秦漢以來載籍,自詩文、訓詁、義理,以逮浮屠、老子之說,無不綜練。”(28)姚永樸:《文苑列傳·方東樹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7、8、9頁。詩文成為方氏最主要的成就。
其二,姚永樸《方東樹傳》強化了傳主文章堅持理學的特色。該文利用阮元漢學泰斗的身份,引用他晚年對方東樹文學的稱贊,來襯托其古文成就,“蓋其義理一本程、朱,而考證之精、文辭之辨,又足以佐之。”(29)姚永樸:《文苑列傳·方東樹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7、8、9頁。這也是《儒林傳》方氏本傳中沒有的內容,是馬其昶《桐城耆舊傳》的寫法。
其三,也是最值得重視的,姚永樸在《方東樹傳》中寫了一條桐城傳承脈絡,而這在國史館的《儒林傳·方東樹傳》、《安徽通志》和馬其昶《桐城耆舊傳》中均沒有。姚永樸挑明了方東樹師承姚鼐,這不見于《儒林傳·方東樹傳》,而引自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另姚氏將方宗誠、戴鈞衡、蘇惇元納入附傳,稱“桐城自姚鼐后,東樹為耆宿,門下知名者曰方宗誠、戴鈞衡、蘇惇元。”(30)姚永樸:《文苑列傳·方東樹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7、8、9頁。在清史《文苑傳》中,方東樹被提升為姚鼐的重要傳人,再度開枝散葉,有壯大桐城派之功。
總體而言,姚永樸的《方東樹傳》更多地參考了馬其昶《桐城耆舊傳》的內容,基本上與馬氏說法一脈相承,首次將姚鼐與方東樹間的師承關系寫入了正史,并強調方東樹是姚鼐的重要傳人。《方東樹傳》無疑在《文苑傳》中增強了桐城派的厚度。
姚永樸《文苑列傳》對《梅曾亮傳》和《管同傳》的重撰亦值得重視。梅氏和管氏作為“姚門四杰”,是桐城派史研究的重點。梅曾亮有將桐城派在京師發揚光大的重要作用,為學界重視。(31)如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陳用光、梅曾亮、曾國藩、吳汝綸四大古文圈子為中心》一書,專章論述了梅曾亮與桐城派古文在京師傳播的關系,同時分析了梅曾亮與桐城派在嶺西的發展。梅曾亮和管同均在《續文苑底稿》中立為正傳。姚永樸《梅曾亮傳》中的雙行夾注記載顯示,該文系根據國史館本傳和梅曾亮《書管異之文集后》撰成。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續文苑底稿》中,繆荃孫纂有《梅曾亮傳》(附毛岳生)和《管同傳》(附子管嗣復、劉開)。《清史列傳》根據的七十四卷本中亦有《梅曾亮傳》,管同和毛岳生為附傳。繆荃孫纂成的《續文苑底稿》中的《梅曾亮傳》和《管同傳》被沿用,七十四卷本《文苑傳》同名傳記與其區別不大。《續文苑底稿·梅曾亮傳》內容出自《正雅集》《江寧府志》《朱琦柏枧山房文集書后》《屺云樓詩話》《柏枧山房文集》《國朝先正事略》。《管同傳》內容出自《續江寧府志·文苑傳》和《因寄軒文集》。
姚永樸《梅曾亮傳》記載和前述國史館同名傳記有明顯區別。(32)姚永樸:《文苑列傳·梅曾亮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11—14、11—12、11—12頁。第一,國史館時期的《梅曾亮傳》和《管同傳》有一個突出的共同特點,大篇幅地引用二人著作中的原文——梅曾亮的《民論》《臣事論》《上汪志伊書》和《刑論》,管同的《言風俗書》和《籌積貯書》。這雖為《史》《漢》書法,但在清史《文苑傳》顯得特別。然而,姚永樸的《梅曾亮傳》寫法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對梅曾亮《民論》等文章的引用變少,把更多的篇幅放在了具體的文法理論的表述、討論和評價上。這樣的書寫方式的改變,使得傳記整體性、連貫性更強。這與繆荃孫《文學傳》和后來《清史稿·文苑傳》的同名傳記寫法均不同。
第二,管同被降為附傳。姚永樸將管同作為《梅曾亮傳》的附傳,大大增加了管同和梅曾亮之間的互動。這從對梅曾亮《書管異之文集后》的引用中可以直接體現。梅曾亮和管同合傳,且傳中僅有此二人,是《文苑傳》體系中獨特的寫法。其余版本,皆以梅曾亮與毛岳生合傳,或梅曾亮、管同、毛岳生三人合傳等。
第三,傳主古文成就,增加了管同如何勸說梅曾亮從事古文創作的經過,彰顯了桐城派為古文的思路和審美取向,并有對駢體文的批評。這些內容,是從《書管異之文集后》引用(按,《書管異之文集后》幾乎全篇被姚永樸引用)。
繆荃孫對此寫法是:“(梅曾亮)少時文喜駢儷,既游姚鼐門,與管同友善。同輒規之,始頗持所業相抗,已乃一變為古文詞。義法一本桐城,稍參以歸太仆。”(33)繆荃孫:《梅曾亮傳》,《續文苑底稿》,文獻編號:701005422,第25頁。姚永樸改寫為:“(梅曾亮)少好駢體文,與同邑管同友,同語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曾亮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固不快耶?而賤之也。’同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云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庾、徐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曾亮遂稍稍學古文辭。同不盡謂善,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駁見。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34)姚永樸:《文苑列傳·梅曾亮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11—14、11—12、11—12頁。
第四,對梅曾亮的學術史定位不同。姚永樸對梅曾亮京師經歷及從姚鼐游的表述與前人不同,把梅氏塑造成了“姚鼐傳人”,儼然是京師文壇核心。繆氏記載是:“(梅曾亮)居京師二十余年,篤老嗜學,與宗稷辰、朱琦、龍啟瑞、王拯輩游處,咸嘖嘖稱賞其才。一時碑版記敘,率其手筆。”(35)繆荃孫:《梅曾亮傳》,《續文苑底稿》,文獻編號:701005422,第25頁。姚永樸《梅曾亮傳》則載:“會桐城姚鼐主講鐘山書院,因游其門。及官京師,復交會稽宗稷辰、臨桂朱琦、龍啟瑞、馬平王拯。久之文乃深古雅潔,群推為姚氏后勁。有求古文法者,輒相詔曰,盍謁梅郎中?然曾亮于少年不徒導以文事,每接見,必以擇交游、端言行、勤讀書三者為戒。時宦官有欲納交文士者,慕曾亮名,就門請謁,曾亮笑曰:吾豈學康對山哉!卒謝之。”(36)姚永樸:《文苑列傳·梅曾亮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11—14、11—12、11—12頁。“久之”以后的話在國史館本傳和《書管異之文集后》中都沒有,是姚永樸新增。
《管同傳》在《續文苑底稿》中有為桐城派立派的重要作用。然而,姚永樸《文苑列傳》《管同傳》并沒為桐城派立派,只記載了管同從姚鼐學的事實和陳用光對他的提拔。
總體而言,在姚永樸的筆下,梅曾亮被塑造為了姚鼐之后的重要傳人,是“姚氏后勁”,是桐城派在京師的核心,有著關鍵的學術史地位。而管同和梅曾亮一樣,都是姚鼐后一輩的桐城派代表人物。姚永樸的《梅曾亮傳》中,未像繆荃孫《續文苑底稿》一樣明言“桐城派”,但卻處處展示著桐城派的學派脈絡和古文家法。姚永樸撰《方東樹傳》和《梅曾亮傳》都記載了姚鼐后學的傳承。盡管重撰《方東樹傳》和《梅曾亮傳》沒有被后來的《清史稿·文苑傳》采用,但仍然是記載嘉道時期桐城派史的重要文獻。
四、《吳汝綸傳》與晚清桐城派史的書寫
姚永樸《文苑列傳》對桐城后期傳人吳汝綸(其附傳人物張裕釗、范當世、朱銘盤、賀濤)的記載更加重要。這一組人物均為晚清桐城后學,清史《文苑傳》此前的稿本《續文苑底稿》等成形于光緒年間,下限是咸同時期,對在世的吳汝綸等人無法立傳。清史館時期,已經有條件對清史進行通盤考察。就桐城派史而言,清末去世的吳汝綸等人有必要寫入。但是吳汝綸等人是否在清史《文苑傳》中立傳,史館諸人意見不統一。姚永樸《文苑列傳》的《吳汝綸傳》反映了清史館內部對此爭論的一個處理方式。
今日學界對吳汝綸的研究,除了關注吳氏文學觀念、文學活動、學術成就、與桐城派末期古文的關系外,對其教育活動,以及晚清中日之間近代教育交流的關系非常重視。除了吳氏現實活動,其身后形象的書寫本身也是晚期桐城派史的一個事件,而學界尚無討論。(37)作為中國近代教育改革過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吳汝綸的教育思想受到重視,包括他在蓮池書院及京師大學堂中的活動、赴日考察的經歷,以及對西學的態度等。同時,作為二十世紀初文學轉型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相關研究亦很豐富。此外,吳汝綸與嚴復、林紓等人的關系也受到關注。
姚永樸撰《吳汝綸傳》載:吳氏與張裕釗同出曾國藩門下(38)姚永樸:《文苑列傳·吳汝綸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36、34—35、34、35、35頁。,并在政治上承其照拂,多任學堂教育事業,吳汝綸亦得李鴻章提攜。清末民初西學輸入的背景下,吳汝綸的態度頗為開明,他一方面飽讀經史,固守古文根基,“汝綸好文出天性,凡周秦(原文泰,誤,引者注)古籍,太史公、楊、班、韓、柳,以逮近世姚、曾諸家書,丹黃不去手。其治經,由訓詁以求通文辭。以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我國所獨優。”(39)姚永樸:《文苑列傳·吳汝綸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36、34—35、34、35、35頁。又積極研習西方新學術。“語其實用,則歐美新學尚焉”(40)姚永樸:《文苑列傳·吳汝綸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36、34—35、34、35、35頁。,強調對西方博物格致之學的吸納,并曾赴日本考察學制。在姚永樸筆下,吳汝綸不僅是一位思想并不拘泥的傳統學人,在中西交往的過程中,其同樣受到西方好尚文學者的禮遇與追捧,“而日本之慕文章者,亦踔海來請業”(41)姚永樸:《文苑列傳·吳汝綸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36、34—35、34、35、35頁。,“其國自君相及教育名家皆備禮接欵,求請題詠,更番踵至”(42)姚永樸:《文苑列傳·吳汝綸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36、34—35、34、35、35頁。,可見吳汝綸及桐城派在文章上的造詣蜚聲海外。整個傳記,凸顯出了清末數千年未有的變局下,西學東漸,桐城派代表人物對西方思想的積極接納。而吳汝綸的同門張裕釗雖未曾出洋,但在國內亦謹守桐城義法,加以教育傳播,“中歲后主講江寧、河北、直隸、陜西各書院,成就后學甚眾,嘗言學文不從桐城諸先輩緒言入,終難免龐雜叫囂之習”(43)姚永樸:《文苑列傳·張裕釗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36、37、36、36頁。,對桐城派的文學理論多有歸納傳播,且影響深遠,“世以為知言”。(44)姚永樸:《文苑列傳·張裕釗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36、37、36、36頁。知新與守本,均是桐城派的特色。
姚永樸《吳汝綸傳》系根據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姚永概所撰《行狀》纂寫;張裕釗以下諸人事據《濂亭集》、吳汝綸《文集》《尺牘》纂成。該傳的附傳人物為張裕釗、范當世、朱銘盤、賀濤,附傳人物的組合安排是獨特的。多個《吳汝綸傳》稿本中,馬其昶、繆荃孫擬的附傳人物是蕭穆,《清史稿》最終的版本則是蕭穆、賀濤、劉孚京。
在描述吳汝綸和附傳人物之間的關系時,姚永樸用了如下表述,這是他的創新:“初汝綸與張裕釗皆從曾國藩游,以文學相友善。裕釗門下最知名者,有范當世、朱銘盤;汝綸門下最知名者有賀濤。”(45)姚永樸:《文苑列傳·張裕釗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36、37、36、36頁。這句話顯示了姚永樸設計這個傳記的思路,以及這個傳記內部的人際邏輯,這是與馬其昶、繆荃孫等人不同的。總的來說,《吳汝綸傳》是將吳汝綸、張裕釗作為曾國藩門生記載,同時又集中收入了他們的傳人。《張裕釗傳》載:“嘗言學文不從桐城諸先輩緒言入,終難免龐雜叫囂之習。”(46)姚永樸:《文苑列傳·張裕釗傳》,文獻編號:701006791,第36、37、36、36頁。強調了對桐城文法傳承的重要性。同時收錄了張裕釗論作文的一些觀點,其中如“因聲求氣”等,都是對劉大櫆等人的傳承。
在吳汝綸身后的眾多傳狀中,姚永樸引述了姚永概所撰者,不僅因為二人兄弟親緣且共同師承吳汝綸,更因為姚永概所擬本來就是為了國史采擇而寫:“謹就闿生所述,參以見聞,稍加撰次,以待名公卿上聞,付史館垂編錄。謹狀。”(47)姚永概:《吳摯甫先生行狀》,《吳汝綸全集》卷4,黃山書社2002年版,第1147頁。目前《吳汝綸全集》中收錄的傳狀有:李景濂《吳摯甫先生傳》、賀濤《吳先生行狀》、姚永概《吳摯甫先生行狀》、賀濤《吳先生墓表》、張宗瑛《吳先生墓志銘》、馬其昶《吳先生墓志銘》、吳闿生《先府君哀狀》《先府君事略》、李剛己等《祭桐城先生文》、谷鐘秀《祭桐城先生文》、早川新次《在安慶寄邦人書》。序跋則有賀濤《桐城吳先生經說序》、籍忠寅《桐城吳先生日記序》、吳闿生《記先大夫尺牘后》、吳闿生《跋先大夫日記》。
馬其昶《桐城耆舊傳》中的《吳汝綸傳》是清史館《吳汝綸傳》的基礎。清史館時期,繆荃孫、李景濂、馬其昶、姚永樸等人都曾纂輯過《吳汝綸傳》。根據繆荃孫《文學傳》的雙行夾注可知,其《吳汝綸傳》亦是根據馬其昶的《桐城耆舊傳》所修,正傳傳主吳汝綸,附傳蕭穆,在引用既有文本的基礎上,自己新增了一句話,表明了人物組合的邏輯:“而汝綸通西學,蕭穆通考據,在桐城為別調,在文學則為通材也。”(48)繆荃孫:《吳汝綸傳》,《文學傳》,上海圖書館藏本,無頁碼。
姚永樸的《吳汝綸傳》的價值,在上述諸文中可見。按清史館系統中共有四種《吳汝綸傳》。版本一,1918年6月14日《大公報》載李景濂所撰《吳摯甫先生傳(清史館稿)》。該版本僅見于報刊之中,并未出現在正式的《文苑傳》稿本內,且報紙中收錄并不完全。這一傳記,收錄在了今日的《吳汝綸全集》中。
版本二,系繆荃孫《文學傳》(清史《文苑傳》第六次稿)中所收錄的《吳汝綸傳》。從雙行夾注中可見,繆氏所用文字本諸于馬其昶所撰《桐城耆舊傳》。馬氏《桐城耆舊傳》撰成于光緒十二年,其中有吳摯父、蕭敬孚二先生合傳。(49)⑤馬其昶:《桐城耆舊傳》,第444—448、445頁。逐字對比,繆氏《文苑傳》第六次稿系對于《桐城耆舊傳》文本的縮寫,部分地方完整謄錄,部分地方縮減內容,極少地方增添信息。《文苑傳》第六次稿中,增加一句評判性的語句,在《桐城耆舊傳》文本中未見:“桐城之文,名冠天下,悉研理學,摹聲調以為古。而汝綸通西學,蕭穆通考據,在桐城為別調,在文學則為通才也。”(50)繆荃孫:《吳汝綸傳》,《文學傳》,上海圖書館藏本,無頁碼。
版本三,即最為人熟知的《清史稿》中所收錄之《吳汝綸傳》。這一版本,在第八次稿中出現,在吳汝綸正傳下,附傳人物由僅有蕭穆一人,擴充至蕭穆、賀濤、劉孚京,其中蕭穆、賀濤均與吳氏有學緣關系。版本三的文字,與版本二在語言組織等方面截然不同,應為纂修官(馬其昶,抑或金梁,待考)棄前稿不用,重新纂輯而成。
版本四,為姚永樸所撰《吳汝綸列傳》。姚永樸繼繆荃孫之后重撰《吳汝綸列傳》,對繆氏文做了修改。同時對馬其昶同名傳記的行文作了刪改,精簡內容,比如刪去了吳汝綸自日本歸國后在桐城縣興辦教育的事跡,“桐城學風大起,自先生也。”(51)馬其昶:《桐城耆舊傳》,第444—448、445頁。與之相對的,繆荃孫對吳汝綸興辦教育的事情比較重視。在對吳汝綸教育成就的評價上,這一寫法的區別是值得重視的。
總之,姚永樸第一次為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人物吳汝綸在清史《文苑傳》中立傳,是晚期桐城派史的一次重要書寫。清史《文苑傳》中的桐城派史下限由此被延展到清末。桐城派中人不僅能固守理學傳統,堅持古文,更能在激變的時代中設法接納西學,迎接新世。作為《文苑列傳》的最后一位人物,意味深長。盡管姚永樸的《吳汝綸列傳》最后未被《清史稿》采用,但它是正史系統內的《吳汝綸傳》之一,對晚期桐城派史的記載仍然值得注意。
結 語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對桐城派的記載是清代古文史的重要內容。在多種桐城派史之中,清史《文苑傳》的記載相當重要。在歷時百年的清史《文苑傳》纂修歷程所形成的多個過程稿中有系統的古文史記載,而桐城派史記載居于主導地位。本文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國史館和清史館全宗相關檔冊為基礎,討論民國初年清史《文苑傳》纂修過程中,姚永樸對桐城派史的纂述之功。
清史館檔案中存有姚永樸纂《文苑列傳》4個檔冊,其中有多位桐城派人物,涉及對桐城派史書寫的多個方面。姚永樸在清史《文苑傳》中為戴名世立正傳,把正史內的桐城派史向前延伸到清初。姚永樸又重纂了方東樹傳和梅曾亮傳,對到清史《文苑傳》第六次稿為止的嘉道時期的桐城派史進行了重寫。姚永樸為吳汝綸新立傳,把《文苑傳》中的桐城派史拉長到清末。姚永樸在清史《文苑傳》中書寫的桐城派面貌,再次強調了桐城派在清代古文界的正統地位。盡管姚永樸《文苑列傳》的9個正傳,最后只有《沈桂芬傳》《湯鵬傳》被收入匯稿的《清史稿·文苑傳》中。但是他關于桐城人物的傳記保留至今,仍然是桐城派史珍貴資料。
清史《文苑傳》中的桐城派史書寫有一個特色,即桐城派中人深度參與,以桐城人說桐城文。姚永樸繼陳用光之后,延續了桐城士人在清史《文苑傳》中纂寫桐城敘事的傳統。就本文所論《文苑列傳》而言,姚永樸本就是桐城派中人。他擬的《文苑列傳》有多位桐城派傳人,而其文獻多參考馬其昶為表彰記載鄉里先賢所撰寫的《桐城耆舊傳》。馬其昶對桐城諸人的記載和評價,對于姚永樸的纂修有重要影響。除《桐城耆舊傳》外,姚永樸在纂修工作中亦多方引用桐城人士所撰之傳狀志銘等文本,如方苞為戴名世所撰《南山集序》、梅曾亮《書管異之文集后》、姚鼐《惜抱軒文集》、陳用光《太乙舟文集》等。姚永樸所引用的大多數的論述均出自桐城派人士,或者桐城派圈子。桐城文的纂述小傳統經桐城人之手,深度滲入到正史撰述中,強化了正史中桐城派記載。
姚永樸《文苑列傳》反映了桐城派史的豐厚內蘊,本文僅僅在文獻層面考察其桐城派史記載的部分問題,更多的意蘊尚有待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