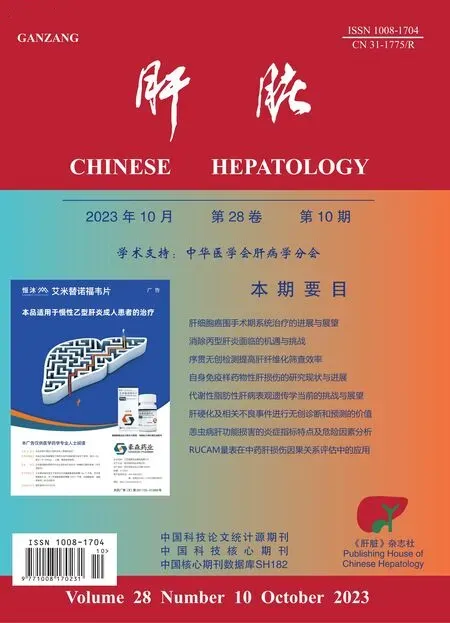肝細胞癌圍手術期系統治療的進展與展望
邵衛青 欽倫秀
肝細胞癌(簡稱肝癌)是高發病率、高死亡率的消化系統惡性腫瘤,每年全球有90.6萬新發病例數和83.0萬死亡病例數,我國的這一數據分別為37.0萬和32.6萬[1, 2]。外科手術是肝癌最主要的根治性手段。然而,肝癌術后短期復發率較高,5年復發率高達80%[3]。此外,我國約七成肝癌患者初診時已屬于中晚期,不宜首選手術切除[4]。因此,經新輔助治療或轉化治療后行手術切除,以及術后行輔助治療,有望擴大手術指征,降低術后復發風險,延長生存期。
近年來,肝癌治療新藥層出不窮,以抗血管生成藥物為代表的靶向治療和以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為代表的免疫治療均取得一系列進展[5]。靶向、免疫等系統治療在圍手術期的應用已成為創造手術機會、降低術后復發風險的重要途徑。
一、化不可切為可切
如前所述,我國肝癌以中晚期為主,絕大多數患者喪失了手術機會。針對這一難題,我國專家對肝癌轉化治療領域進行了積極探索,并于近幾年形成了初步的共識[6-8]。轉化治療旨在消除肝癌不可切除因素,達到能夠安全施行R0切除的手術標準。其主要包括兩個內涵:一是向外科可切除性的轉化,二是向腫瘤學獲益的轉化。轉化治療的具體策略包括消融、經肝動脈栓塞化療(TACE)、經肝動脈灌注化療(HAIC)等局部治療和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KI)、ICI等系統治療以及各種治療手段的聯合應用。以下將對肝癌轉化治療的關鍵問題進行簡要介紹。
(一)AATD聯合ICI為晚期肝癌的轉化帶來希望 近年來,AATD和ICI在多種腫瘤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治療效果,索拉非尼、侖伐替尼、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度伐利尤單抗聯合替西單抗等治療方案憑借其良好的治療效果已被我國指南推薦作為晚期肝癌的標準治療[9]。多項研究證實,AATD聯合ICI可達到“1+1>2”的治療效果,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帕博利珠單抗聯合侖伐替尼、卡瑞利珠單抗聯合阿帕替尼的靶免聯合方案治療不可切除的中晚期肝癌,客觀反應率(ORR)達33.2%~46.0%,遠超AATD或ICI單獨應用的ORR[10, 11]。此外,一項前瞻性臨床研究發現,侖伐替尼聯合PD-1單抗和TACE的靶免聯合局部治療方案ORR達78.9%,轉化切除率(CRR)高達50.7%。盡管還需要大樣本、前瞻性、高級別的證據支持,AATD聯合ICI已然成為目前晚期肝癌轉化治療最具前景的明星方案。
(二)轉化治療反應的評估 影像學檢查是評估腫瘤治療反應的核心依據,mRECIST更適用于晚期肝癌轉化治療的影像學評估。對肝癌而言,肝臟強化MRI檢查具有獨特優勢,而18F-FDG PET是評估肝外轉移病灶的重要依據。動脈期強化完全消失是提示腫瘤病灶完全壞死的決定性特征。據此,應優先選擇腫瘤進展率低、暴露時間短、緩解程度深、持續時間長的轉化治療方案。甲胎蛋白(AFP)和異常凝血酶原(PIVKA-Ⅱ)明顯下降提示轉化治療有效,下降至正常并長期維持提示病灶可能壞死。一項納入76例初治肝癌患者的臨床研究發現,侖伐替尼聯合PD-1單抗治療早期(2~3周),AFP或PIVKA-Ⅱ減少超過50%可作為肝癌患者接受靶免聯合治療客觀緩解的預測標志[12]。
(三)轉化后手術的指征 轉化治療后外科手術是達到根治目的的重要保證,可以使患者獲得更長的無瘤生存期和總生存期;同時,轉化后切除可減少藥物暴露,減少耐藥性及藥物不良反應;此外,術后病理檢查可以明確轉化治療效果,并指導后續輔助治療。因此,轉化治療后手術切除是必要的,當晚期肝癌降期至CNLC-Ⅰ或已轉化為技術可切除且連續2次評估不能進一步影像學獲益時應考慮手術切除。術前是否需要停用AATD和ICI尚無定論,一般建議根據藥物半衰期提前停藥,并在術后1個月開始參考原方案繼續給予輔助治療6~12個月。
轉化治療的發展為晚期肝癌治療提供了新的思路,ICI聯合AATD方案單獨或聯合適合的局部治療有望進一步提高轉化治療的成功率,使不可切除的晚期肝癌患者獲得根治性手術機會,改善長期生存。
二、新輔助治療:降低術后復發
新輔助治療是指對于技術上可切除[R0切除、剩余肝臟體積(FLR)足夠]、具有高危復發因素的肝癌患者,在術前先進行系統治療或局部治療等以縮小腫瘤,盡早消滅不可見微小病灶或增加手術切緣,從而降低術后復發率。作為肝癌術前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輔助治療和轉化治療的根本區別在于治療目標不同,因此,二者在患者人群、治療方案上均有差別。我國專家在肝癌新輔助治療領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形成了初步共識。以下將對肝癌新輔助治療的關鍵問題進行簡要介紹。
(一)新輔助治療患者人群 新輔助治療以降低復發為目標。由于目前肝癌新輔助治療高級別證據有限,我國專家共識推薦CNLC Ⅰ期和部分Ⅱa期可直接實現R0切除的患者不建議行新輔助治療,CNLC Ⅱb期、 Ⅲa期技術可切除的患者因存在明確高危復發因素,建議新輔助治療后進行手術治療,以減少術后復發。明確的肝癌高危復發因素包括:肉眼癌栓、微血管侵犯(MVI)、多個腫瘤、衛星結節、淋巴結轉移等[13]。隨著CNLC分期的上升,術后復發轉移的風險升高[14]。術前應綜合多種檢測手段對術后復發風險進行評估。對于高危復發的患者人群,建議新輔助治療來改善患者預后。
(二)AATD聯合ICI為肝癌新輔助治療提供了新的思路 自從AATD聯合ICI方案成為晚期肝癌標準治療以來,將其應用于肝癌術前新輔助治療的探索從未停止。日趨豐富的治療組合已然成為肝癌新輔助治療的新選擇,其研究熱度已超過經典的介入治療和放療。更低的疾病進展(PD)率是新輔助治療選擇方案的重要依據。研究表明,侖伐替尼聯合帕博利珠單抗、阿帕替尼聯合卡瑞利珠單抗、貝伐珠單抗聯合阿替利珠單抗等靶免聯合方案PD率為12.2%~20.0%,提示AATD聯合ICI作為肝癌術前新輔助治療方案安全可行[10]。
在新輔助治療的過程中,患者可能會因病情進展或嚴重的毒副作用等手術禁忌證而錯失手術機會。因此,應嚴格限制治療周期(一般推薦1.5~3個月),選擇相對安全、對手術影響較小的治療方案。
三、輔助治療:降低術后復發
外科手術是肝癌最主要的根治手段。術后高復發轉移率是制約肝癌治療效果的一大瓶頸,有效的術后輔助治療有助于降低術后復發風險,延長患者生存。如前所述,肉眼癌栓、MVI、多個腫瘤、衛星結節、淋巴結轉移等均為術后復發轉移的危險因素[13]。目前,全球尚無公認的標準輔助治療方案,抗病毒藥物、介入治療、化療、免疫治療和靶向治療以及中醫藥治療等多種輔助治療正在肝癌中積極探索[9]。
隨著AATD聯合ICI方案成為晚期肝癌標準治療,靶免聯合治療在肝癌術后輔助治療領域的探索也日漸活躍。IMbrave 050研究顯示,與主動監測相比,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輔助治療已被證明可改善手術切除或消融后高復發風險肝癌患者的RFS,復發風險下降28%,這一方案有望成為肝癌患者的標準輔助治療方案[15]。本中心牽頭的一項多中心前瞻性隊列研究(LACE研究)發現,侖伐替尼聯合TACE是一種有前景的肝癌術后輔助治療策略,可為術后復發風險高的肝癌患者提供更好的生存獲益(12.0個月vs.8.0個月)和可控的安全性[16]。
目前我們對肝癌術后輔助治療的了解仍十分匱乏,以AATD聯合ICI方案為代表的各種輔助治療方案組合正在積極研究中,包括新輔助治療結合術后輔助治療的嘗試。期待這些研究的成果可以為肝癌術后輔助治療提供新的參考。
四、結語
肝癌是高發病率、高死亡率的惡性腫瘤,嚴重威脅國人健康。低手術切除率和術后高復發轉移率是制約肝癌治療效果的重要瓶頸。以AATD和ICI為代表的系統治療進展迅速,已成為晚期肝癌的標準治療。近年來,靶向、免疫等系統治療在圍手術期的應用已成為創造手術機會、降低術后復發風險的重要途徑。轉化治療、新輔助治療和輔助治療的相關研究有望改寫肝癌治療規范,改善肝癌患者生存獲益。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