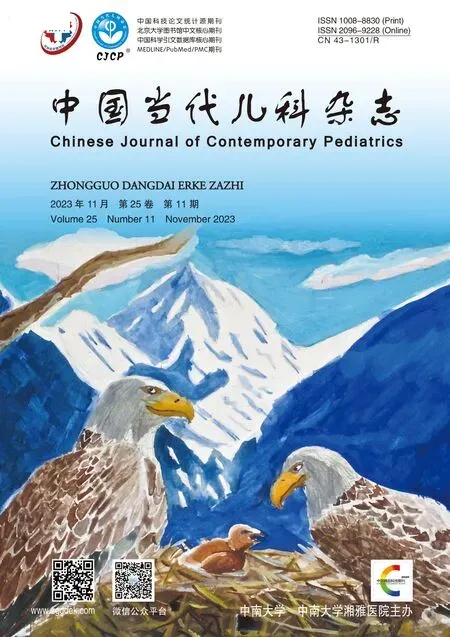高度重視兒童矮身材的科學評估
王琳
(首都兒科研究所附屬兒童醫院兒童保健中心,北京 100020)
隨著人們對生存質量的追求不斷提升,兒童矮身材已成為家庭和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矮身材是指在相似生活環境下,同種族、同性別和同年齡的個體身高低于正常人群平均身高2個標準差或低于第3百分位數。最新報告顯示,中國兒童矮身材發病率為3.2%,其中農村地區為4.7%,高于城市地區的2.8%[1]。身材矮小不僅會影響患兒身高,降低生活質量,還會導致不同程度的行為適應障礙、認知障礙、心理障礙和青春期發育遲緩等,兒童血脂異常、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發生風險也將增加[2-4]。盡早識別矮身材,并根據病因給予適當的治療干預,能為改善兒童臨床結局爭取最大機會[5-7]。《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明確提出,到2030 年5 歲以下兒童生長遲緩率要從2013 年的8.1%降低到5%以下[8]。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健康兒童行動提升計劃(2021—2025 年)》則要求將此目標的實現提前至2025年[9]。臨床實踐中存在漏診、診斷延遲、轉診延遲等矮身材診斷不充分的現象[10-13],這也反映了部分兒童保健或兒科醫生對兒童矮身材的重視程度不夠、認識不足、診斷不規范,應引起高度重視。
1 兒童矮身材科學評估的前提
1.1 充分認識兒童體格發育規律
兒童體格發育是一個復雜的動態變化過程,但遵循共同的發展規律。切實掌握兒童體格發育的基本規律,深入了解生長調控機制及影響因素,有助于兒童矮身材的早期識別。兒童不同時期的體格發育各有特點,調控機制也不盡相同[14]。胎兒期生長主要受控于營養狀況,以代謝軸調控生長軸,即營養物質促進胰島素分泌,繼之類胰島素樣生長因子分泌而促生長。嬰兒早期生長基本延續胎兒期調控模式,6月齡后垂體分泌的生長激素開始呈現促生長作用,逐漸替代生命早期營養調控模式。兒童期生長主要受生長激素調控,青春期生長則依賴于生長激素與性激素的協同作用。不同時期兒童的生長速度各不相同。嬰兒期出現出生后的第1個生長高峰,出生后第1年生長速度為25 cm,第2 年生長速度減緩至一半左右,隨后生長速度下降并于兒童期趨于穩定[15]。在即將進入青春期時生長速度會短暫減緩(青春期前下降),隨后在青春期中期顯著加速(青春期生長突增),身高突增峰速度通常發生在青春期后期,并出現第2個生長高峰,繼之生長速度下降至最后停止生長[16]。青春期男孩共增長25~28 cm,女孩共增長23~25 cm[14]。
1.2 知悉兒童矮身材的影響因素
兒童矮身材同時受遺傳和非遺傳因素的影響。遺傳是決定身高的主要因素,在身高發育中占主導地位,可導致80%甚至更多的身高變異[17]。非遺傳因素包括社會環境、家庭環境、內分泌激素、營養、運動、疾病等[15,18]。有研究表明,家庭年收入、父親受教育程度以及父母對孩子未來身高的關注度也是兒童矮身材的影響因素[17]。兒童身高發育是多種因素的作用結果,而這些因素之間可能存在復雜的相互影響,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特定因素在矮身材的發生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因此,必須從多個角度進行綜合分析,對矮身材做出正確評估。
1.3 了解矮身材在兒童群體中的年齡分布
一項納入39 項研究,涵蓋中國20 個省、市和自治區348 326名兒童的大型Meta分析顯示,6~12歲(3.3%) 兒童矮身材的發生率高于>12 歲(3.1%)或<6歲(2.4%)兒童[1]。另一項在中國兒童中開展的橫斷面研究發現,男孩矮身材的發病率在9歲時最高,女孩在8歲時最高[17]。這兩項研究表明6~12 歲是發生矮身材的主要年齡段,提示兒童保健或兒科醫生要特別關注此類高危人群的矮身材篩查,避免漏診。導致兒童矮身材的原因很多,包括生長激素缺乏癥、先天性甲狀腺功能減退癥、小于胎齡兒、Turner綜合征等,不同年齡段導致矮身材的原因可能不同。2022 年,芬蘭20年出生隊列研究首次提供了與兒童期身材矮小相關的幾種原發性和繼發性生長障礙的流行病學數據,結果顯示,Turner綜合征診斷時的中位年齡為4.0 歲,是最常見的原發性生長障礙;診斷為生長激素缺乏癥的女孩和男孩中位年齡分別為8.7歲和7.2歲[19]。這提示,在兒童早期,矮身材的篩查重點應放在原發性生長障礙上,從學齡前開始需要同時關注繼發性生長障礙。因此,對兒童進行矮身材評估時,應關注其所處的特定發育階段。
2 兒童矮身材的科學評估內涵
2.1 正確界定矮身材
隨著社會發展和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兒童身高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一旦兒童出現身高低于平均值,容易引起家長焦慮,甚至有家長錯誤認為孩子為矮身材,導致過度醫療。據報道,家長若過度關注孩子身高,矮身材發生風險反而增加1.164倍[17],心理學家將這種現象描述為“聚焦錯覺”。另一方面也存在家長缺乏相關知識和防范意識、貽誤矮身材最佳診療時機的現象,這愈發強調了教育家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時,要求兒童保健或兒科醫生對兒童矮身材的診斷標準有正確、清晰的認識,即兒童身高低于同種族、同性別、同年齡正常人群平均身高2個標準差或第3百分位數為矮身材,并進一步規范診療行為(如精確的連續測量數據、科學的結果分析),做到既不漏診也不過度醫療。需注意,部分矮身材屬正常生理變異,需加以區分。
2.2 定期監測兒童身高生長的關鍵指標
科學嚴謹地評估兒童體格發育水平需要從生長水平、生長速度、勻稱度和成熟度4 個維度進行,結合既往生長資料及單次/多次評價結果繪制生長曲線圖才能得出較為準確的結論。對疑似生長發育異常的兒童需動態連續追蹤6個月(最好12個月)以上的生長曲線圖進一步篩查,并適當增加生長監測頻率。
兒童身高生長速度是判斷矮身材的主要依據。身高生長速度需要定期(每半年)、連續、準確測量身高,獲得的生長曲線圖可篩查生長速度減慢的兒童。2021 年《兒童體格發育評估與管理臨床實踐專家共識》[14]建議,若生長曲線向下偏離跨越2條主要身高百分位數曲線,或生長速度低于以下水平,即2 歲以下兒童<7.0 cm/年,2~<4 歲兒童<5.5 cm/年,4~<6歲兒童<5.0 cm/年,6歲至青春期前兒童<4.0 cm/年,青春期兒童<6.0 cm/年,應警惕有矮身材的可能,需加以重視并及時尋找可能的原因。據調查,使用身高低于2個標準差、生長速度等指標,可以在5歲以下兒童中識別約80%的矮身材[13]。對于無癥狀的矮身材兒童,生長曲線的評估可為潛在的病理原因提供線索;矮身材兒童的體重不足提示全身性疾病或營養不良,而超重則提示內分泌疾病[20]。
2.3 明確兒童矮身材的診斷思路
國內外對矮身材診斷路徑的研究與臨床應用已處于成熟階段,對生長受損的兒童必須進行詳細的評估,包括病史詢問、體格檢查、常規和特殊實驗室檢查,找出病因,制定干預策略。矮身材的初步評估主要為病史和體格檢查。病史詢問包括家族史(父母親青春發育和家族成員矮身材情況)、母親妊娠史、出生史、生長發育史、既往史(用藥史、慢性疾病史、心理狀態)[21]。已有研究證實皮質類固醇藥物、哌甲酯可導致兒童生長速度下降,身高生長落后于同齡人群[22-23]。受到歧視、虐待等情感剝奪或近期有精神壓力的兒童是社會心理性矮小的高危群體[24]。體格檢查包括準確的體重和身高測定、身高年增長速率(至少監測3 個月)、上下部量比例、第二性征發育及分期、脊柱側彎檢查、心肺聽診、有無特殊體征(如特殊面容、頸蹼、肘外翻、牛奶咖啡斑、特殊氣味等)等[25]。篩查是否存在非勻稱性、比例失調,例如上臂或前臂短小;是否有先天畸形特征,包括面部畸形、小頭畸形;是否有心臟雜音、隱睪、肌肉肥大等。
如果初步評估結果不能提示診斷,可進行實驗室檢查,包括血尿便常規、肝腎功能、血糖、血脂,疑似腎小管酸中毒、特殊佝僂病者可進行電解質分析和鈣磷代謝檢查。骨齡是反映兒童身高生長發育水平的重要指標,矮身材兒童的骨齡一般落后于實際年齡,但也可以與實際年齡接近,通過手和手腕的X 線檢測骨齡可協助篩查矮身材。必須認識到青春期兒童骨齡與實際年齡并不完全同步,身高突增前往往先有相對的骨齡加速,身高突增后骨齡增長速度隨之回落,但不能理解為生長減速[26-27]。3歲以上兒童可以結合骨齡生長情況進行分析和指導,當生長速度下降,骨齡出現加速,骨齡大于實際年齡1歲,提示存在矮身材的危險,建議轉診至兒童內分泌科進一步檢查和治療[28]。
根據患兒具體病情還可進一步開展特定的實驗室檢查項目篩查是否存在矮身材相關病理性因素,包括甲狀腺、性腺、腎上腺、垂體等內分泌功能檢查,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胰島素樣生長因子結合蛋白3水平測定,染色體核型及部分罕見矮身材的相關基因檢測,必要時可以考慮生長激素激發試驗[28]。
對于正常生理性變異,如家族性身材矮小、體質性青春發育延遲,無需特殊干預;對于矮身材且無法確定病因,以及疑診為內分泌異常的兒童,應做好及時轉診工作。
2.4 認識常見的矮身材診斷誤區
目前臨床上存在不少對矮身材診斷的誤區,常見的有:(1)簡單地通過生長水平診斷矮身材,容易導致診斷結果產生偏移。矮身材診斷應該綜合生長水平、生長速度、勻稱度和成熟度等指標,采用標準化生長曲線動態評價。(2)盲目認為矮身材就是生長激素缺乏癥,繼而盲目進行生長激素激發試驗,導致過度檢查、過度診斷及后期的過度治療。臨床醫生一定要認識到矮身材并不等于生長激素缺乏癥,矮身材的病因需要仔細甄別,尤其是特發性矮身材的診斷是一種排他性診斷,不能僅憑生長激素激發試驗的峰值正常就直接診斷,需要進行充分排查,避免漏診和誤診。
2.5 把握不同身高兒童的管理重點
基層社區醫生或初級兒童保健醫生對兒童的身高需進行分級管理。(1)對于身高高于正常人群平均身高2個標準差或第3百分位數的兒童,一般不需要特別評估,除非有特殊情況,如生長速度持續下降,或畸形,或有全身性疾病,或身高低于靶身高等[29]。(2)對于身高低于正常人群平均身高2個標準差的矮身材兒童,需轉診至兒童內分泌科,進行病因學檢查,給予規范化治療。(3)對于身高低于正常人群平均身高3個標準差的特別矮小兒童,可能存在潛在的病理因素,如嚴重營養不良、遺傳性疾病、內分泌疾病、全身性慢性疾病等,需轉診到相關科室進行病理病因評估。
3 展望
兒童矮身材的診斷仍面臨許多挑戰,漏診、診斷延遲等現象屢見不鮮。為進一步提高兒童矮身材的早期檢出率,需要形成涵蓋家長、各級兒童保健及醫療機構的長期監測體系。事實上,大多數家長對矮身材的認識不夠,過度重視孩子身高,一旦孩子“個子矮”很容易演變成“身高焦慮”“身高內卷”,導致過度醫療。通過開展相關知識教育,提高家長對矮身材的認識,了解如何就醫及何時就醫,早期發現矮身材。另外,家長應主動配合醫生對兒童進行早期矮身材篩查,定期檢測兒童身高及增長情況。基層社區醫生或初級兒童保健醫生承擔著兒童矮身材早期篩查和初步診斷的主要工作,其關鍵臨床任務是識別正常生長變異的矮身材兒童,以及需要進一步診斷或轉診的兒童,同時引導家長對矮身材有正確的認知。目前基層兒科醫生對兒童矮身材的早期篩查意識不足、認識不充分,其對矮身材認識的常見誤區包括:(1)認為父母高孩子一定高;(2)認為現在矮是晚長,以后就長了;(3)認為補點鈣、吃點保健品就行;(4)認為男孩沒變聲、女孩無月經不算發育,不急[30]。這恰恰反映了矮身材的不規范診治,將會直接影響患兒的及時就診或轉診,進而影響矮身材的早期發現和干預,亟需加強基層兒科醫生相關專業能力的培訓和提升。
盡管矮身材的診斷和管理標準已較為成熟和完善,遺傳學及分子生物學新技術的不斷發展顯著提高了兒科醫生對矮身材遺傳病因的認識和診斷水平,進一步推動兒童矮身材疾病的早期精準篩查和診斷。目前發現越來越多的基因與矮身材相關,兒童保健門診常見與矮身材相關的遺傳學疾病包括Turner 綜合征、Prader-Willi 綜合征、Russell-Silver 綜合征、Noonan 綜合征[31]。建議對如下矮身材兒童進行致病基因檢測[32]:(1)極度矮小,且生長激素缺乏;(2)多種垂體激素缺乏;(3)明確對生長激素不敏感;(4)身高低于正常人群平均身高3 個標準差;(5)合并小頭畸形;(6)特殊面容合并矮小;(7)有骨骼發育不良的證據;(8)伴有智力障礙;(9)未達到追趕的小于胎齡兒。在未來,遺傳學新技術的普及應用勢必會為兒童身材矮小的早期精確診斷添磚加瓦。
除了常規的矮身材評估方法外,近年來有不少研究探索早期篩查矮身材的新方法[17,33-35]。例如,在深圳市12 504 名兒童中構建預測矮身材風險的列線圖模型和風險分類系統[17],通過將矮身材危險因素可視化,可以預測兒童矮身材的發生風險和身材矮小程度,初步顯示出良好的臨床實用性和便利性,未來需要在外部隊列中進一步驗證。印度學者基于年齡、輔助檢查(身高、體重指數和校正標準偏差評分)和骨骼成熟度開發了一個移動應用程序[35],其診斷與臨床診斷一致性達99%,有望輔助臨床矮身材評估,減少診斷錯誤。此外,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改變醫學各個領域的診斷工具,包括兒童生長發育領域。這些工具可潛在地改善矮身材的識別,未來可能有助于提高兒童矮身材的臨床評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