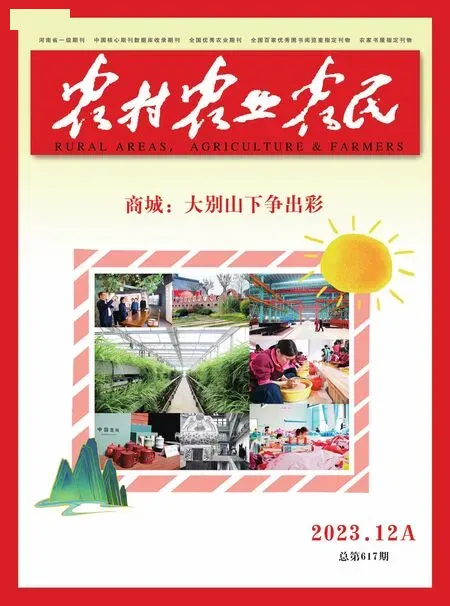“小田并大田”進程中的農地適度規模新探討
李貴芳,逯夢巖,馬棟棟
(1.河南農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2.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2023 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總結地方‘小田并大田’等經驗,探索在農民自愿前提下,結合農田建設、土地整治逐步解決細碎化問題。”于是“小田并大田”“一戶一田”成為農業農村土地整改關注的焦點問題。但是,“大田”的規模越大越好嗎?“小田并大田”又受到哪些因素影響?這是有待深入探討的農地適度規模問題。
一、文獻綜述
關于農地適度規模的研究開始于20 世紀90 年代,學術界研究的焦點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關于農業規模經營度量指標,通常采用農戶“耕地規模”直接指代“規模經營”(Sen,1962),然而這一指標忽視耕地細碎化影響,連片耕地規模和分散耕地規模對農戶生產效率影響是不同的(張紅宇,2023)。第二,關于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效果衡量標準,學者基于不同目標選取不同指標得到不同結論,常見評價指標包括農業生產是否存在規模經濟,土地規模經營如何影響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農業生產效率及農民收入等(黃季焜和馬恒運,2000;黃祖輝等,2014)。還有學者指出應該采用多目標來確定土地適度規模,基于單一目標得到的結論是有偏差的(李谷成等,2010)。第三,爭論的焦點。土地適度規模經營與土地產出率的關系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一些學者認為(羅必良,2022),擴大耕地經營規模會導致土地產出率降低。持不同觀點的學者認為(王建英等,2015;何秀榮,2016),耕地經營規模擴大與提高土地產出率不是相悖的,二者之間是可以雙向優化的。也有研究認為(徐志剛,2023),農業經營規模不存在最優規模,所謂的最優規模是基于不同研究方法和原則得到的,事實上農業經營規模是動態調整的,最優值是不確定的。張麗媛和萬江紅(2022)指出,地塊完全連片在提高規模戶土地生產率方面的效果明顯差于地塊適度連片。第四,研究數據和研究對象,以往采用農業生產加總數據進行分析所得結論的說服力是有限的,許慶等(2011)認為以往以農戶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結果是有偏的,只有聚焦于某種作物才能說明農業經營規模是否存在規模經濟或規模不經濟的問題。
已有研究成果提供了寶貴借鑒,但仍有待商榷和補充的地方。第一,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度量指標有待改進和豐富。以往研究多采用農戶“耕地面積”來反映農業經營規模,但是在“小田并大田”政策實施的過程中,關注的重點應該轉變為“地塊連片規模”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目前相關研究還不多。第二,農地適度規模經營的衡量標準需要突出地區稀缺資源的約束性。以往研究多以土地生產率、農業生產效率或農戶收入等作為確定農業適度經營規模的主要目標,較少考慮制約不同地區農業發展短板因素的作用,在“小田并大田”政策實施過程中,應該給予充分的重視。第三,以往有關農業適度經營規模的研究主體多是農戶,較少以作物為研究主體考察地塊適度規模的整改問題。鑒于此,本研究在介紹“小田并大田”地區實踐的基礎上,為小田適度并大田提供原則及建議,以期為政策落地提供參考。
二、“小田并大田”的地區實踐
2016 年,安徽懷遠縣按照“小試驗、大方向、作示范、探路子”的思路,開始有序推行“一戶一塊田”改革試點工作,成為最早踐行“小田并大田”的地區。2020 年以來,全國諸多縣(區)開始推行“一戶一田”政策,其中甘肅省張掖市臨澤縣、民樂縣、高臺縣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礎上,丈量耕地并進行公示,進而對細碎化耕地進行平整和歸并,并采用耕地互換和合并等方式,將原來的“補丁地”變成了能夠集中作業的“一塊田”;江蘇省鹽城市亭湖區積極探索“小田并大田”,將“巴掌田”“斗笠田”“皮帶田”變成了連片的“大田”,當地的改革經驗已經被列入農業農村部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典型案例;河南省許昌市后河鎮余莊村是河南省鄉村振興示范村,其在充分順應農民意愿的前提下,積極探索高標準農田建設和土地調整的具體方案和措施,將村里的“小田”變成了“大田”。目前,“小田并大田”政策已經在江蘇、湖北、安徽、甘肅、河南等省份開始試點推進。可見,“小田并大田”已經成為我國農村土地整改的新方向和新目標。但是,如何將政策與傳統農地適度規模理論體系融合以指導實踐是未來探討的重點問題。
三、“小田并大田”的原則及建議
(一)根據不同地區資源環境異質性來調整農地適度規模
土地資源是農業生產的基礎,水資源是農業生產的命脈。但是我國水土資源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在空間分配上都存在較大的異質性,導致不同區域農業生產面臨的資源約束邊界不同。比如就水資源而言,西北干旱區作為世界上干旱的地區之一,水資源總量僅占全國3.46%,農業用水歷年平均占比又高達90%(李貴芳等,2019),在“小田并大田”的過程中不僅要考慮水資源短缺的硬性約束,還要考慮如何在提升灌溉效率的前提下進行農地調整。就土地資源而言,目前農地細碎化已經是阻礙農業發展的因素之一,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報告,我國60%的耕地由2.3 億傳統農戶耕種,家庭承包土地面積平均為7.5 畝,戶均土地5.72 塊(韓長賦,2017)。這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來,由于按照“好壞搭配、遠近搭配”的原則進行土地分配,導致單個農戶擁有面積不等、數量較多的地塊,進而形成了農地的細碎化格局,而現階段要進行的“小田并大田”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一格局。此外,我國山區面積約占全國面積的2/3,地勢西高東低,在“小田并大田”的過程中還要考慮不同區域地形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如耕地平整程度、土壤肥沃程度等因素的影響。可見,“小田并大田”要遵循空間自然資源的異質性,即在傳統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理論研究體系的基礎上,將制約地區農業發展的短板資源要素納入其中,體現農業發展要與區域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匹配的思想。
(二)根據不同作物種植和生長特征來調整農地適度規模
我國幅員遼闊,氣候差異較大,農作物種類眾多,不同地區種植的農作物類型存在較大差異。比如西北地區以旱地農作物為主,如小麥、棉花、瓜果、土豆、大棗、制種玉米等;東北地區以高粱、玉米、水稻、谷子、大豆、小麥、甜菜和薯類等為主;華北平原以小麥、水稻、玉米、高粱、谷子、棉花、花生、芝麻、大豆和煙草等為主;而南方地區則以水稻、甘蔗、油菜、油茶等作物為主。由于不同作物的種植和生長特征存在較大的差異,在“小田并大田”的過程中要遵循作物生產管理特征,不能盲目地擴大耕地面積,忽視作物生長需求。比如在制種玉米的生長過程中,要進行抽天花和砍父本,這些是必須由人工完成的,并且要求不同地塊之間的距離大于1.5 米,以免影響授粉,降低產量。此外,還要考慮作物之間的輪作和套種情況,特別是對于那些生產環節相對復雜、需要大量人工投入的作物,可能不需要很大的地塊。可見,在“小田并大田”的過程中,要綜合考慮不同地區種植結構和作物生長特征的差異性,因地制宜、因物(作物)制宜,不能一概而論。
(三)根據不同經營主體差異化的機械動力水平來調整農地適度規模
當前,很多研究農地適度規模的成果是在假定機械化水平能夠與地塊規模相適應的基礎上得到的。但是,事實上機械化水平并不是總和地塊規模相適應,不同經營主體的機械化水平是存在差異的,同一經營主體的機械化水平也會隨著生產經營能力的提升發生改變,這就可能導致研究結論存在偏差。現實中,小農戶、種植大戶、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經營主體的機械化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小農戶大多使用的是人工或小型機械生產工具,其作業能力相對較差,現代化水平較低,生產水平不高,同樣的作業時間內小農戶能夠完成的作業量有限。而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則普遍使用的是大中型機械,其生產效率、作業強度更高。這就導致不同經營主體的生產效率不同,單位時間內完成的作業量不同。所以,在“小田并大田”的過程中,要為不同農業經營主體制定不同的生產規模,不能一概而論。需要說明的是,隨著機械化水平的提升,不同農業經營主體的生產效率會發生不同程度的提升,導致不同經營主體的地塊適度規模也隨之擴大。可見,“小田并大田”是一個動態調整和不斷優化的過程,不是一成不變的。
(四)根據不同經營主體差異化的生產管理水平來調整農地適度規模
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不同,工業生產是流水線,依靠機器可以日夜不停地工作,而農業生產則要受到自然和社會兩個層面的制約。其中,自然層面的制約主要是指農業經營主體必須遵循不同作物的自然生長規律,在固定的農時完成旋耕、播種、施肥、澆水、除草、收割等相關生產作業,這些環節不同于工業生產,其作業過程是分階段的,即農忙和農閑。而在社會層面,則要求農業經營主體在有限的農時內完成相關作業,合理安排勞動力或機械執行作業任務,錯過農時會導致農作物減產或者面臨更大的損失。所以,對于生產管理能力不同的農業經營主體,其要求的地塊規模是不同的。過大的地塊可能會受限于機械化水平和生產管理能力,其生產效率不一定會得到提高;而過小的地塊又會增加管理難度和跨地塊經營的時間成本,導致生產效率降低。因此,地塊適度規模主要是指滿足不同經營主體單位時間內工作量的規模。這就要求在“小田并大田”的過程中要統籌管理、分類規劃。
四、結語
目前,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已經成為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基本共識。“小田并大田”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在統籌推進的過程中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應該遵循“由小到大、由點到面、由少到多”和“試點先行、因地制宜、統籌規劃”的原則,根據不同地區資源環境異質性、不同作物種植和生長特征、不同經營主體差異化機械動力水平及不同經營主體差異化生產管理水平來動態調整農地規模,徐徐圖之,久久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