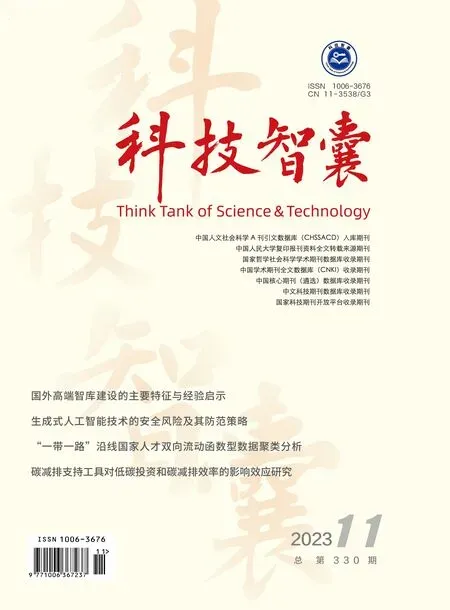“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才雙向流動函數型數據聚類分析
程 豪 裴瑞敏
1.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北京,100038;2.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北京,100190
“一帶一路”建設是沿線國家開放合作的宏大愿景,其中,科技創新合作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之一[1]。作為知識的重要載體,人才成為推動沿線國家密切交流、繁榮發展的關鍵要素,人才流動是知識傳播和流動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促進科技創新合作的重要驅動力。微觀層面,人才流動伴隨著知識、信息和能力的交流、傳播和擴散,一定程度上能實現人力資源的效率優化,推動知識和信息共享,豐富國際合作網絡;宏觀層面,人才流動能加速一個地區或國家的資源集聚,積累人力資本,直接或間接影響全要素生產率[2]。因此,不同國家間的人才流入和流出,成為備受關注的研究主題。人才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綜合影響力與吸引力,人才流出則可以顯示出一個國家開放包容的程度。從全局來看,良性的人才雙向流動對于促進國家繁榮發展、推動國際化合作至關重要。
國內外學者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發展、人才國際流動等問題進行相關研究。近年來,關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發展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曹翔和李慎婷[3]利用1996—2014年期間的中國海關數據庫并結合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貿易發展情況展開相關研究,發現“一帶一路”倡議顯著推動了沿線國家的經濟增長,而且這種推動作用會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增強。葛純寶、于津平和劉亞攀[4]基于UNCTAD-Eora 增加值貿易數據,采用SNA 法和QAP 法,對“一帶一路”增加值貿易網絡演變及其影響因素展開研究,發現沿線各國地理相鄰、共同語言、直接投資關系和產業結構差異對促進貿易網絡演變的積極效應具有階段性的差異。程豪和榮耀華[5]借助二階因子模型,利用4 種偏最小二乘估計算法,對沿線國家的科技創新水平進行評價,刻畫出影響科技創新水平的各個方面和指標的不同表現,為沿線國家科技創新水平排名提供方法支持。近年來,在人才國際流動方面,已發表的研究成果更多。陳波[6]在提出跨期工作搜尋模型基礎上,研究了人才國際流動行為規律,并從理論層面論證了移民輸出國也可能會由于移民的跨期流動而獲益。楊芳娟[7]以中國高被引學者等為研究對象,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系統研究了中國高端科技人才的跨國流動模式及影響。研究還以中國高被引學者為對象,構建高被引學者國際合著論文數據,利用科學計量分析、社會網絡分析等方法,分析了人才流動和人才合作之間的關系。龍夢晴和鄒慧娟[8]在梳理當前人才流動生態失衡現象的基礎上,從“態”和“勢”協同發展的視角,探究了人才流動協同發展的機理與路徑。程豪和裴瑞敏[9]利用Scopus 中1981—2020年的連續數據,從函數型數據分析角度,構建人才流動和國際合作之間的函數型動態效應模型,繪制全球化人才流動對國際合作效應的函數曲線,并得出全球范圍內的人才流動對國際交流與合作產生重要影響的結論。
在現有研究基礎上,本文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從函數型角度尋找沿線國家中國際人才流入、人才流出與人才流動總量不同維度下不同國家的聚類情況,以期為國家間多邊合作關系的研判提供具有較為重要的應用研究價值的參考。
一、研究設計
(一)方法選擇
人才流動和科技合作密切相關,研究顯示,人才流動和國際合作之間存在正向的演化關系,各國在流動和合作的地位方面具有趨同性。[10]人才流動是促進國際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11],研究發現參與科研合作的國家的數量與科研人員流動有很大關系,預計流動國家的增加(或減少)與國際合作的數量成正比。一些研究利用文獻計量的方法追蹤了國際流動后國內和國際合作的演變,發現學者移居國外后,將帶來國內合作的迅速增加與國際合作的減少。[12-13]此外,科學流動將給科學家的合作網絡帶來更多新的資源,例如科學家在新的機構中任職時間越久,在當前機構的合作關系就會越多。[14]還有一部分研究結果表明,科學家與新機構的合作僅在小范圍內改變科學家原有的合作關系。在宏觀層面上,人才流入、人才流出和人才流動總量,都存在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隨著時間的推移會發生連續變化,這種連續變化的特征在經過一定時間積累后會表現出函數規律,可以通過函數型數據分析的方法加以分析,以捕捉沿線國家在人才雙向流動方面的聚類情況。
眾所周知,函數型數據分析方法是指系數具有函數特征的一類方法。[15-18]其中,函數型聚類分析實現了從連續觀測數據角度出發,對沿線國家進行聚類,完整揭示了沿線國家在人才雙向流動維度下的聚類規律和特點。為方便表述,假設1981年至2020年沿線國家A的人才流動(流入、流出或流動總量)函數為xA(t),1981年至2020年沿線國家B 的人才流動(流入、流出或流動總量)為xB(t),其中,t=1981,…,2020。則定義沿線國家A 和沿線國家B 間差距的函數定義為D=∫0T(xA(t)-xB(t))2dt。將xA(t)和xB(t)用相同的K 維基函數Φ(t)展開,用xA和xB分別表示xA(t)和xB(t)的基函數展開系數向量,則有:
如果基函數是標準正交基,矩陣∫Φ(t)Φ'(t)dt就退化成單位陣,這時函數之間的距離就變成系數向量之間的歐式距離。如果基函數非正交,D 可以被理解為系數向量之間以基函數的協差陣為權重的加權歐式距離。
(二)數據說明
本文從Scopus 數據庫提取1981年至202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部分數據。經過對這4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人才流動方面的數據積累,共有38 個國家在人才流入規模、人才流出規模和人才流動總量這三個變量方面有扎實的數據基礎。38 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家名稱及代碼如表1 所示。

表1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家名稱及代碼
二、實證分析
(一)人才雙向流動數據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對1981—2020年人才流入規模、人才流出規模以及人才流動總量這三個變量的年度數據的最值(最小值和最大值)、中位數和平均數進行統計描述。受篇幅所限,表2僅展示出1981年、1991年、2001年(每10年)以及2011年至2020年(最后10年)的最值和平均數。

表2 人才流入規模、人才流出規模以及人才流動總量年度數據統計描述結果
考慮到函數型數據的特殊性,下面通過曲線圖,對1981年至2020年38 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才流入規模、人才流出規模以及人才流動總量這三個變量進行描述性分析。圖1 共包括2 個部分,左邊的圖展示出沿線國家的人才流入規模、人才流出規模和人才流動總量在1981年至2020年的變化情況。右邊的圖顯示出沿線國家的人才流入規模、人才流出規模和人才流動總量在1981年至2020年的變化速度情況。不難看出,1981年至2020年沿線國家的人才流入規模、人才流出規模和人才流動總量總體呈現上升趨勢,變化速度幾乎均大于0,而且在2000年后呈現出隨機波動的增長趨勢,而在鄰近2020年的幾年內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圖1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才雙向流動函數型數據曲線
(二)人才雙向流動的函數型聚類分析
經過對1981年至2020年沿線國家的人才流入規模、人才流出規模和人才流動總量分別進行函數型聚類分析,可將38 個沿線國家各劃分為4 類。經聚類發現,不同類各自包含的國家在數量上存在較大差異。比如,按人才流入規模進行的函數型聚類分析結果顯示,第一類包括7 個國家,而第二類包括21 個國家,這兩個類別所包括的國家數量差異較大。為解決這個問題,本文進行兩種嘗試:一是對聚類數量進行設置,比如6 類和8 類;二是對聚類數量為4 的聚類結果中包含國家數量過多的那類,再進行函數型聚類分析,將這一類所包含的國家繼續分為若干個類。受篇幅所限,本文僅展示將38 個國家劃分為4 類的聚類情況。
按人才流入規模進行函數型聚類分析,可以得到表3 所示的聚類結果,各個類在聚類時的函數型曲線如圖2 所示。需要說明的是,不同類之間是平行關系,不存在先后順序。由表3 可知,第一類包括巴基斯坦、羅馬尼亞、孟加拉國、斯洛伐克、泰國、烏克蘭和匈牙利共7個國家,第二類包括阿塞拜疆、愛沙尼亞、白俄羅斯、保加利亞、菲律賓、格魯吉亞、哈薩克斯坦等21個國家,第三類包括俄羅斯和印度共2個國家,第四類包括埃及、波蘭、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新加坡、伊朗和以色列共8 個國家。由圖2 可知,屬于同一類的國家在聚類時的函數型曲線具有相似的增長趨勢,在第一類和第二類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開展國際多邊合作時應重點考慮屬于同一類的國家間合作。

圖2 基于人才流入規模的函數型聚類分析結果

表3 按人才流入規模進行函數型聚類分析結果
按人才流出規模進行函數型聚類分析可以發現(見表4),第一類包括巴基斯坦、羅馬尼亞、馬來西亞、泰國、土耳其、烏克蘭、匈牙利和伊朗共8 個國家,第二類包括阿塞拜疆、愛沙尼亞、白俄羅斯、保加利亞、菲律賓、格魯吉亞等23 個國家,第三類包括俄羅斯和印度共2 個國家,第四類包括埃及、波蘭、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以色列共5 個國家。圖3 表現出與圖2 相似的規律,即屬于同一類的國家在聚類時的函數型曲線具有相似的規律或總體趨勢,在第一類和第二類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開展國際多邊合作時應重點考慮屬于同一類的國家間合作。

圖3 基于人才流出規模的函數型聚類分析結果

表4 按人才流出規模進行函數型聚類分析結果
比較表3 和表4 可以發現,按人才流入和人才流出進行函數型聚類分析的結果存在很大程度的一致性。比如,國家巴基斯坦、羅馬尼亞、泰國、烏克蘭、匈牙利始終屬于同一類。國家阿塞拜疆、愛沙尼亞、白俄羅斯、保加利亞、菲律賓、格魯吉亞、哈薩克斯坦、科威特、克羅地亞、拉脫維亞、黎巴嫩、立陶宛、摩爾多瓦、尼泊爾、塞爾維亞、斯里蘭卡、斯洛文尼亞、烏茲別克斯坦、亞美尼亞、伊拉克、約旦屬于同一類。俄羅斯、印度屬于同一類。埃及、波蘭、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屬于同一類。
下面從人才流動總量角度,進行函數型聚類分析,可以發現,第一類包括阿塞拜疆、愛沙尼亞、白俄羅斯、保加利亞、菲律賓、格魯吉亞、哈薩克斯坦、科威特等22 個國家,第二類包括埃及、波蘭、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新加坡、伊朗和以色列共8 個國家,第三類包括俄羅斯和印度共2 個國家,第四類包括巴基斯坦、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泰國、烏克蘭和匈牙利共6 個國家(見表5)。圖4 表現出與圖2 相似的規律,即屬于同一類的國家在聚類時的函數型曲線具有相似的規律或總體趨勢,第一類和第四類國家增長比較平緩,第二類國家增長速度較大,第三類國家包括俄羅斯和印度,增長最快,在開展國際多邊合作時應重點考慮屬于同一類的國家間合作。

圖4 基于人才流動總量的函數型聚類分析結果

表5 按人才流動總量進行函數型聚類分析結果
綜合表3、表4 和表5 可知,按人才流入、人才流出和人才流動總量進行函數型聚類分析的結果表現出很大程度的一致性。比如,國家巴基斯坦、羅馬尼亞、泰國、烏克蘭和匈牙利始終屬于同一類。國家阿塞拜疆、愛沙尼亞、白俄羅斯、保加利亞、菲律賓、格魯吉亞、哈薩克斯坦、科威特、克羅地亞、拉脫維亞、黎巴嫩、立陶宛、摩爾多瓦、尼泊爾、塞爾維亞、斯里蘭卡、斯洛文尼亞、烏茲別克斯坦、亞美尼亞、伊拉克、約旦屬于同一類。俄羅斯、印度屬于同一類。埃及、波蘭、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屬于同一類。
三、總結與展望
在當前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下,緊扣“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部署,實現與沿線國家的人才交流和合作,是我國國際科技合作中的重要議題。本文對Scopus 數據庫中1981年至202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部分數據從人才流入規模、人才流出規模、人才流動總量三個維度開展人才雙向流動函數型數據的聚類分析,發現不同國家在流動方面的差異性,形成了四組人才流動增長速度不同的國家群,這些國家群表現出相似的流動特征,與其國家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文化特征等息息相關。本研究的結論為我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才雙向流動規律的捕捉提供依據,為實施差異化的合作方案設計提供支撐。
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將繼續對人才雙向流動與國際合作展開深入研究,根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不同屬性特點,對潛在聚類關系進行深入的劃分,以期為沿線各國合作關系提供更加切實可行的方案。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才雙向流動與國際合作將呈現出不同的規律,因此需要根據時間階段,確定用于預測未來人才雙向流動與國際合作態勢的時間起點和階段性數據。在統計學方法方面,將進一步深耕當數據存在缺失現象的函數型數據聚類分析,以解決人才雙向流動函數型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缺失數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