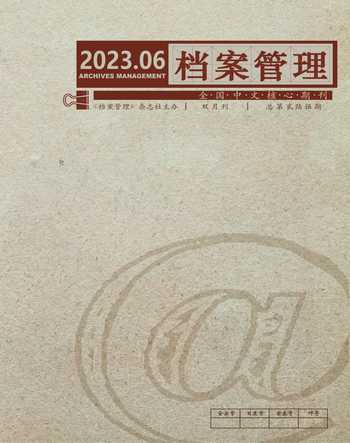電子檔案獨立證據地位確立的法理分析
摘? 要:電子檔案系經特定歸檔程序被認可的電子文件,作為獨立證據類型具有重要的意義。面對電子檔案存在的證據地位不明確、證據效力認定困難、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等問題,應首先通過制定《電子文件證據法》、完善電子檔案管理與證據儲存和保全規則體系等以明確電子檔案的證據地位;通過建立嚴格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最佳證據規則、標準化電子檔案取證程序以厘清電子檔案證據取證規則與程序;通過優化技術措施保障數據安全與個人隱私。
關鍵詞:電子檔案;電子文件;證據地位;獨立地位;數據安全;隱私保護;取證規則;證據效力
Abstract:? Electronic archives are electronic documents that have been approved through specific archiving procedures and hold significant importance as a separate type of evidence. In the face of issues such as unclear evidentiary status, difficulties in determining evidentiary weight,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irst establish the "Electronic Document Evidence Law"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archives and rules for storage and preservation of evidence, etc.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evidentiary status of electronic archives. Secondly, strict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rules and best evidence rul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standardized evidence collection procedures of electronic archiv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clarif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obtaining electronic archival evidence. Finally, technical measures should be optimized to ensure data security and personal privacy.
Keywords: Electronic archive; Electronic document; Evidentiary status; Independent status; Data security; Privacy protection; Evidence collection rule; Evidentiary weight
2012年,訴訟法將電子數據確立為一種獨立的證據類型,電子檔案作為一種特殊的電子數據,自然獲得相應證據類型的法律定位。2021年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以下簡稱新《檔案法》)進一步明確了電子檔案的法律地位和憑證作用。然而,在實踐中,仍然存在諸多關于電子檔案法律效力認定的爭議,因此有必要從法理視角對電子檔案的獨立證據地位進行系統分析,進而為電子檔案在司法中的實踐應用提供理論指導。
通過梳理相關研究文獻發現,現有成果在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方面均有涉及。其中,理論研究主要聚焦于研究動因、法律依據、研究前提等,如許曉彤、李海濤等從實踐動因視角探討了電子檔案法律效力確認對單套制的推進作用;劉冰、韓李敏等對新《檔案法》關于電子檔案法律效力的相關規定進行了探析。應用研究主要集中于對應用現狀、現實障礙、發展策略的探討,如何英昌對不動產電子檔案在司法訴訟中的應用進行了探究;郝樂、余亞榮等在分析電子檔案法律效力實現障礙的基礎上,對其發展策略進行了探討;吳品才、劉貞伶從證據價值視角對電子檔案法律價值維護提出了相關建議。綜上,現有研究多集中在電子檔案法律效力的法律依據、現實障礙等方面,缺少對電子檔案證明力問題的深入探討;同時,現有研究多是基于檔案學視角,缺乏基于法理學、證據學維度的探討。因此,本文擬就電子檔案獨立證據之問題展開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1 電子檔案及其獨立證據地位必要性分析
1.1 電子檔案相關概念的法理解讀
1.1.1 法理上的概念關系。根據國家檔案局2016年8月發布的國家標準《電子文件歸檔與電子檔案管理規范》GB/T 18894—2016)(以下簡稱《管理規范》)對電子文件和電子檔案的定義可知,只有經過特定歸檔程序被認可的電子文件才能被稱為電子檔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民訴證據若干規定》)第十四、第十五條以列舉的形式明確了民事訴訟中電子數據的范疇。《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刑事案件電子數據若干規定》)第一條以列舉形式規定了刑事案件中電子數據的范疇。對比兩部司法解釋可以發現,電子數據包括電子文件,電子文件屬于電子數據的下位概念,且司法解釋中所列舉的電子數據的范圍遠大于電子檔案的范圍。
綜上可知,電子檔案區別于電子文件和電子數據。在訴訟中,電子檔案作為證據的證明力如何,是要采取相較于電子文件和其他電子數據更為嚴苛的證明方法,還是采取更為寬松的證明方法,對于提升案件審理的質量和效率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1.2 法理上的概念特征。電子檔案若要作為獨立證據,則必須滿足證據“三性”,即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根據新《檔案法》第三十七條規定,電子檔案應當來源可靠、程序規范、要素合規。來源可靠是電子檔案具備與傳統載體檔案同等效力的基本前提,程序規范是電子檔案合法性的根本保障,要素合規是保證電子檔案完整性、可用性的關鍵所在。雖然在實踐過程中電子檔案的真實性還存在認可度問題,但隨著先進技術的深入應用以及基礎設施、制度的不斷完善,電子檔案的真實性、可靠性將得到有效保證。
根據國家標準《管理規范》中的電子文件歸檔程序與要求,電子文件歸檔應對其真實性、可靠性、完整性和可用性進行鑒定,鑒定合格率達到100%才能成為電子檔案。由此,電子檔案自然具備證據的真實性和合法性特征。至于電子檔案作為法律證據的關聯性,只要電子檔案滿足與相關案件的存疑事實存在實質性的邏輯關聯就具備關聯性特征。因此,電子檔案的真實性、可靠性、合法性、完整性等特征與證據“三性”具有密切的映射關系,電子檔案具備成為獨立證據的核心要求,這是顯著區別于其他證據的重要特性。
1.2 電子檔案的現有證據地位分析
1.2.1 電子檔案在新《檔案法》中的地位。依據新《檔案法》規定,電子檔案與傳統載體檔案具有同等效力,可以電子形式作為憑證使用。因此,依據新《檔案法》,電子檔案是區別于傳統載體檔案形式且以一種新型載體存在的檔案,且具備傳統載體檔案所應有的證明力。
1.2.2 電子檔案在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一方面,民事訴訟法已將電子數據確立為一種獨立的證據類型,其中包含電子檔案,即電子檔案可以作為電子數據類型在民事訴訟中適用。同時,《民訴證據若干規定》第九十四條明確規定,電子數據以檔案管理方式保管的,人民法院可以確認其真實性,但有足以反駁的相反證據的除外。這一條款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電子檔案在民事訴訟中的證明力。
1.2.3 電子檔案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依據《刑事案件電子數據若干規定》第一條,電子數據是案件發生過程中形成的,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傳輸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數據并對其類型進行了列舉。筆者認為,其一,該條所列舉的網頁、手機短信等要成為檔案需要經過專門的程序;其二,數字化形式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不屬于電子數據范疇,其是否屬于無紙化辦公的電子檔案,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能否被直接作為證據采納,尚無定論。
綜上,第一,電子檔案是檔案的下位概念,電子檔案應與其他載體形式的檔案一樣具備在訴訟中的地位,只是由于電子檔案載體的特殊性,需要界定電子檔案在訴訟中是直接適用還是需要特定的認定程序;第二,電子檔案當然是電子數據的一種,并且相較于法律規定的各種電子數據更為嚴謹,問題在于,對電子檔案證明力的認定是否也要遵從普通的電子數據,還是要另有其專門的認定程序。
1.3 電子檔案作為獨立證據的必要性。《“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強調提升電子檔案管理與應用水平、《“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對加強電子檔案管理提出了具體要求。在這一背景下,明確電子檔案獨立證據地位更加必要。
1.3.1 電子檔案內容的專業性。新《檔案法》第三十九條和國家檔案局起草的《電子檔案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電子文件歸檔與電子檔案管理規范》(GB/T 18894-2016)都對電子檔案的內容做出了詳細的規定,確保了電子檔案內容要素的專業性。
1.3.2 電子檔案程序的嚴謹性。新《檔案法》和國家檔案局辦公室秘書處于2017年12月29日印發的《電子檔案管理系統基本功能規定》《電子檔案移交接收操作規程》(DA/T 93-2022)、《電子檔案證據效力維護規范》(DA/T 97-2023)等對電子檔案的規定,其目的在于確保電子檔案的真實性,而這是電子檔案能夠作為獨立證據類型的根本所在。
1.3.3 無紙化辦公的必然要求。黨政機關,尤其是一線服務窗口落實數字政府無紙化辦公的政策要求而形成的電子數據,經歸檔程序即為電子檔案。這里,明確電子檔案的獨立證據效力,也是數字化時代無紙化辦公的必然要求。
2 獨立證據地位確立的主要問題
2.1 電子檔案的證據地位不明確。截至目前,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對于電子檔案是否屬于獨立的證據類型,尚無明確的觀點和界定。
2.1.1 理論研究缺乏。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側重于從電子檔案法律效力確認與檔案學發展互促互動的基礎上討論如何通過檔案管理機制的完善提升電子檔案的真實性或者證明力;二是從證據構成的三要件探討電子檔案是否具備證據的條件及其法律效力。
縱觀現有研究,一方面,現有研究側重從理論上探討電子檔案法律效力的相對較多,較少關注電子檔案在實際工作中的應用情況;另一方面,大多數研究將電子檔案等同于一般電子文件歸于電子數據證據類型進行論述,尚無將電子檔案作為獨立證據類型進行探討的成果。因此,有必要從理論上明確電子檔案作為獨立證據類型的價值、意義、內涵界定及其作為證據的法律效力等,進而確立獨立的電子檔案證據類型模式。
2.1.2 實踐樣本較少。在司法實踐中,電子數據作為證據被適用的頻率越來越高。在這一背景之下,如何實現紙質檔案證據規則到電子檔案證據規則的過渡也是法學界必然面對的問題。早在2004年,為了適應數字社會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明確了符合條件的電子簽名等同于紙質簽名的法律效力,破除了電子數據作為證據適用的制度障礙。20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陸續將電子數據作為獨立類型的證據列入證據范疇,并賦予其法律效力。2020年,新修訂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既明確了電子數據能夠作為證據適用的條件,也提出了電子數據推定真實規則,明確了除有足以反駁的相反證據外,對于特定情形的電子數據,人民法院可以直接確認其真實性。
縱觀有關訴訟證據的現有法律法規,盡管訴訟法已經將電子數據作為一大證據類型進行了明確確認,并明確了相應的適用規則,但現有法律法規并未提及電子檔案的具體證據地位及其效力,而是將其與一般的電子數據作為同一類別的證據進行適用。
通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現有法律法規對于電子檔案作為證據的處理于檔案本身的價值的發揮和檔案事業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反觀紙質環境時代的訴訟法,無論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2001),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2002)均明確了紙質檔案在訴訟過程中作為證據的證明力優于其他書證、視聽資料和證人證言等證據類型,紙質檔案在證據適用中具有一定的獨立地位,而現有的法律法規對于電子檔案的證明力卻未予以明確。
實踐中,涉及電子檔案的案例并不少見,但多數案件所謂檔案并非新《檔案法》所明確的檔案,而是相關主體在正常業務活動中形成的電子檔案材料,或者是相關企業事業單位自身保管的內部檔案材料,對于這些材料作為證據的適用,實踐中僅作為一般的電子數據進行質證和認定。除此之外,實踐中也涉及以檔案管理方式保管的電子檔案作為證據適用的情況,也多將其等同于一般的電子數據進行證據質證和認定,不過實踐中對于此類證據直接采用的較多,但是采用的前提也是建立在相關電子檔案所存儲的載體安全可靠、所管理的系統安全可信的基礎上。
未采信的案例中未采信的原因,主要在于對相關電子檔案難以證明其是否以“檔案管理方式保管”且存在電子檔案系單方制作并保存管理難以避免主觀性情況。例如,在天水市第三人民醫院與石某、劉某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2020)甘05民終435號)中,上訴人主張天水市第三人民醫院提交的“出院意見”等電子檔案不具有真實性,法院經綜合判定而不予采信。
綜上可知,實踐中多數將電子檔案放在電子數據證據類型之下,并適用電子數據認定的規則對電子檔案進行質證和認定,并未明確電子檔案與其他電子數據之間的區別,在證明效力上也未與其他電子數據進行區分,因而將電子檔案作為獨立證據類型進行認定的案例較少。
2.2 電子檔案的證據效力認定存在困難。筆者認為,未將電子檔案作為獨立的證據類型予以討論或者適用的原因主要在于相較于紙質檔案,電子檔案在作為證據進行認定時存在多方面的困難。
2.2.1 內容真實性保障的法效不足。新《檔案法》明確:“電子檔案與傳統載體檔案具有同等效力,可以以電子形式作為憑證使用。”但在實踐中,相較于紙質檔案作為證據出示時的易于被采納,作為證據出示的電子檔案卻容易被認為內容可能存在不真實而不予認可其效力。
傳統的紙質檔案記載于紙質載體上,檔案信息一旦被篡改或者涂抹,便會留下痕跡,因而形成了紙質檔案的不易改動性特點。而新《檔案法》也明確規定了禁止篡改檔案。這便為紙質檔案作為證據采用的真實性提供了技術保障和制度保障。相對于紙質檔案的穩定性,電子載體上的信息具有易改性特點,技術上的障礙使得電子檔案難以擁有如紙質檔案一樣的在公眾心中的地位。再者,在制度的實施過程中,整個電子檔案管理制度體系的構建還跟不上實踐需求。所以,相對于紙質檔案的穩定性和真實性,電子檔案形成和保管方式存在不穩定性,電子檔案的內容真實性缺少充分保障。
2.2.2 查證屬實相對困難。在司法訴訟中,只有內容真實的證據材料才能被采用,對于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如果對方當事人對證據的真實性有異議,需要法院通過證據采用規則確定證據的真實性。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對于紙質檔案的認可度較高,在司法實踐中查證屬實相對容易。在司法實踐中,電子檔案信息改動后直觀上難以被發現,訴訟主體提供的電子檔案是否真實、可信,很難通過一般技術手段進行查證。法院并未賦予電子檔案與紙質檔案同樣的證據效力,一旦當事人對電子檔案提出異議,在確定電子檔案的證據效力時,司法機關相對謹慎。
2.3 可能引發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問題。目前,運用云端資源進一步提高電子檔案管理的效率,將電子檔案數據托管于云端(電子檔案管理者)是一種有效的途徑,這就造成電子檔案數據支配權與管理權的分離,使得電子檔案在大數據環境下面臨更多的安全風險和隱私泄露風險,包括隱私泄露、云存儲數據泄露、數據損毀等。其中,隱私信息中的社會信息部分對于地區發展或者社會制度建構而言屬于不公開的信息,個人信息也歸于個人隱私的部分,依據相關的檔案管理規定,除非經過特定程序和條件,這些信息是不允許被其他人隨意查看的。
在紙質檔案時代,檔案信息的查閱需要經過嚴格的手續,但電子檔案是以數據的形式存放在云端,在現有的研究中,云服務提供商被定義為半誠實的,即其按照既有規則或協議為用戶提供服務,但在不背離協議的情況下會盡量挖掘用戶的隱私數據。此外,由于大部分案件的裁判文書會在網上公開,在相關檔案信息公開的同時,一些不法分子可能會根據公開的信息,推定特定人群的特定屬性,進而造成用戶數據的隱私泄露。
云存儲存在數據泄露和數據損毀問題。電子檔案的大規模使用,會造成檔案數據的過度集中,集中的數據可能會吸引數據攻擊者的關注,如信息流監聽等,這些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會對電子檔案數據保存造成威脅,損毀數據的完整性。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電子檔案內容的真實性,而這正是電子檔案能夠作為證據使用的重要標準,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保障電子檔案內容的真實性,是當下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3 電子檔案獨立證據地位確立的法理策略
3.1 完善立法明確電子檔案的證據地位。前文已述,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新《檔案法》等并沒有明確電子檔案的獨立證據地位,甚至電子檔案是否具有優勢地位仍然是不明確的。法律規則的權威性、明確性及穩定性使立法成為確立電子檔案證據地位的必然的首要路徑。法律規范應具有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法律同時也具有抽象性,規定不能過于繁瑣。因而,在新《檔案法》《民事訴訟法》剛修訂不久的情況下,不宜通過再次修訂這兩部法律的方式確立電子檔案獨立證據地位。在當前情況下,可通過完善其他方面的法規、規章、標準等方式完善相關立法。
3.1.1 通過制定《電子文件證據法》確立電子檔案獨立證據地位。為確立電子檔案獨立證據地位,可以制定專門的《電子文件證據法》,在全面規定電子文件證據完整規則體系的同時,對電子檔案的證據地位問題進行明確規定。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建立電子檔案證據的規則體系:其一,在《電子文件證據法》中明確電子文件、各類電子文件,包括電子檔案的確切定義。其二,固定電子文件證據的確切分類,明確電子檔案的證據構成,通過規定電子檔案的原始、可靠及完整性確定其證據效力,明確電子檔案的證據界限。其三,規定電子檔案的審查制度,系統明確電子制度的客觀、合法、關聯性的審查標準。其四,明確規定電子檔案的復制標準及其證明力等。
3.1.2 通過完善檔案管理的法律法規確保電子檔案的內在證明力。電子檔案的內在證明力來源于電子檔案具有三個方面的構成特征,即“來源可靠、程序規范、要素合規”。在新《檔案法》與《民事訴訟法》均未對上述要素進行細致規定的情況下,可通過制定檔案法相應的實施辦法將其具體化。
首先,明確電子檔案的形成、保存和使用等規則,使其與法律法規中對電子證據“檔案式管理”的具體要求相銜接,例如,明確規定來源可靠、程序規范、要素合規的具體含義;并以此為根據,規定各類機構應對電子檔案實施全生命周期管理與維護的要素。
其次,對于更為細節的要素,可通過制定《檔案管理方式保管電子數據具體辦法》等更為具體的規范性文件,規定具體標準和管理要求,銜接司法機關對“檔案管理方式”的具體要求。具體而言:一是在來源可靠方面明確規定具有兩方面的要素,即主體可靠、環境可靠,并明確其具體標準。二是在程序規范方面,明確保管階段、涉案取證階段等程序規范的具體標準;三是在要素合規方面,不僅要規定檔案材料本身“主”證據的合規標準與條件,還要規定軟硬件等技術方面的合規標準與條件。
3.1.3 完善電子檔案證據的儲存與保全規則體系。建立嚴密的電子檔案儲存與保全體系是保證電子檔案真實性與可靠性的關鍵。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部門規章的立法形式規定電子檔案服務機構與司法機構相鏈接的共同平臺,實現電子檔案證據的無縫鏈接。一是建立檔案服務機構、電子服務平臺,以及公證、鑒定機構共同參與的平臺,實現電子檔案、法律文書的跨平臺傳遞;二是將電子簽名、可信時間戳、哈希值校驗融入電子檔案的管理中,對電子檔案進行日常真實性保全;三是運用區塊鏈技術將電子檔案管理系統接入司法區塊鏈應用,形成電子檔案與司法應用實踐環節的順暢鏈接,同時可通過責任鏈制度實現電子文件管理痕跡的記錄責任分配與精確到人的責任追溯。
3.2 理清電子檔案證據的取證規則與程序。盡管《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范及相關司法解釋等對證據的取證規則與程序有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有關電子檔案證據所適用的取證規則是散見于不同種類的證據程序之中,有關電子檔案證據的取證規則與程序是不成體系的,電子檔案證據在司法程序效力發揮中也存在各種障礙。因此,可以從建立電子檔案證據的取證規則與程序兩個方面完善。
3.2.1 建立嚴格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最佳證據規則。其一,建立符合電子檔案證據實際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內容包括:適用于電子檔案的非法證據排除原則;電子檔案證據的儲存及環境要求、真實性要求以及網絡、信息系統、計算機技術性要求等;取證是否非法的具體判斷標準及非法證據的排除界限等。同時,還要構建以電子檔案“原件”為中心的最佳證據規則。其二,基于“電子檔案證據”的特殊性,構建最佳證據規則的內容主要包括:在標準層面上,電子檔案證據原件的定義及其必備的內涵、形式、技術要求,電子檔案證據原件的具體化標準,例如原件與復制件的區分標準、原件丟失毀損情況下復制件的適用條件等;在操作層面上,確立電子檔案真實性規范的鑒定流程,具體包括跟蹤記錄集鑒定、操作處理權限核對等核驗要素等。
3.2.2 建立標準化的電子檔案取證程序。標準化的取證程序是實現電子檔案證據程序規范要求的重要保障。其一,電子檔案的取證原則。這些原則包括規范取證流程和具體操作的過程規范原則、方便操作原則、取證全面原則,以及檔案維護的安全保密原則。其二,電子檔案證據的取證程序。取證程序包括取證前的準備,取證步驟及取證結果的保全等。其三,電子檔案證據的驗證程序。從技術角度而言,可以通過建立基于時間戳的逆向解碼過程實施驗證。
3.3 優化技術措施保障數據安全與個人隱私。由于電子檔案保障數據安全與個人隱私的側重點不同,其優化技術保障路徑也有區別。
3.3.1 優化技術措施保障數據安全的策略。首先,在電子檔案管理中引入區塊鏈技術。區塊鏈技術具有不可偽造、全程留痕、可追溯等特征。區塊鏈的加密算法、時間戳等技術手段使得過程清晰可追溯,且區塊機構相關聯,篡改難度極大。區塊鏈的加密算法可實現傳輸過程的安全,分布式儲存和共識機制能夠最大限度防止文件損壞丟失。同時,區塊鏈技術能夠實現電子檔案儲存的完備性與安全性。區塊鏈能夠對應電子檔案管理安全的四個方面,為電子檔案管理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護。其次,建立電子檔案信息安全風險評估機制。通過技術建立電子檔案信息組織層更好地實現電子檔案信息的風險防范。最后,通過加密強化檔案信息云儲存安全保護,同時通過技術手段防止非授權用戶訪問。總之,需要強化技術的保障作用,通過各類技術的運用構建完善的電子檔案信息技術安全防護系統。
3.3.2 優化技術措施保護個人隱私安全的路徑。對照《個人信息保護法》,在電子檔案的形成、儲存與使用中,可以通過以下方面保護個人隱私:首先,通過技術設置規范數字檔案館個人信息收集。通過技術設計明確落實“告知—同意”規則。例如,在電子檔案館的初始使用頁面明確設置告知的信息,并設置是否同意被獲取個人信息,保障用戶的知情權;依據法律法規將收集的檔案個人信息通過前端技術控制分為一般個人信息、敏感個人信息與非個人信息,通過技術設置不同信息的獲取和使用規則。其次,規范數字檔案館個人信息管理,例如通過技術手段對個人信息進行脫敏處理,嚴格管控數字檔案館與使用人員權限。最后,建立完善數字檔案館的評價體系。
4 結語
數字時代,明確電子檔案的獨立證據地位,有效解決電子檔案的證據取得、證明力維護、公共安全保障問題既是完善訴訟證據規則、提高司法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做好新時代檔案工作,提升政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信息化效能的應有之義。如何在單軌制、單套制的背景下完善電子檔案證據法律體系,需要檔案管理界和法律界的共同努力。基于此,本文更多從法律層面上進行考量,擬通過完善電子檔案管理與證據儲存和保全規則體系、建立嚴格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最佳證據規則、確立標準化電子檔案取證程序等路徑明確電子檔案的獨立證據地位,完善相關的法律規則體系,以期為電子檔案作為獨立證據的實施和規則構建提供有益參考。
*本文系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依法治理視域下高校巡察制度研究”(項目編號:2023BFX023);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黨風廉政建設研究課題“大數據驅動的“三不腐”一體推進機制及實施路徑研究”(2023LZYJ02);2023年河南省檔案科技項目“數字化戰略轉型背景下紀檢監察檔案信息化提質賦能研究”(項目編號:2023-X-036)研究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許曉彤.組織機構電子文件證據效力保障研究[J].檔案學通訊,2020(06):109-112.
[2]李海濤,郭靜.單軌制視角下國內外電子文件證據立法研究[J].檔案學研究,2021(01):70-77.
[3]劉冰.新《檔案法》背景下電子文件管理立法建議[J].檔案學研究,2021(06):72-77.
[4]韓李敏.電子檔案與傳統載體檔案具有同等效力[J].浙江檔案,2021(01):16-18.
[5]何英昌.“互聯網+”背景下不動產電子檔案管理探析[J].蘭臺世界,2020(10):62-65.
[6]郝樂.人民法院應用電子卷宗的理論基礎?實踐考察與制度完善[J].檔案學研究,2022(02):40-47.
[7]余亞榮,吳振宇.從數據備份走向數據保全:基于憑證效力維護視角的電子檔案保管[J].檔案管理,2022(01):18-19.
[8]吳品才.從證據“三性”看電子檔案真實性維護[J].檔案管理,2022(06):21-23.
[9]劉貞伶.電子檔案法律證據價值的維護研究[J].檔案與建設,2020(01):38-41+33.
[10]許曉彤.電子文件證據性概念模型研究[J].檔案管理,2021(02):27-31.
[11]裴佳杰,郭若涵.電子檔案法律效力問題研究綜述[J].檔案學刊,2022(05):21-31.
[12]許曉彤,章偉婷,唐瑩琪.“檔案管理方式保管”與“正常業務活動中形成”電子文件證據效力保障:調查與思考[J].檔案學通訊,2022(05):73-82.
[13]戴玲,彭延國,彭長根.大數據環境下的電子檔案信息安全問題及對策[J].蘭臺世界,2015(29):25-26.
[14]李詹宇.數據挖掘隱私保護綜述[J].信息安全與技術,2012(9:47-51)
[15]李海濤,郭靜.單軌制視角下國內外電子文件證據立法研究[J].檔案學研究,2021(01):70-77.
[16]許曉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2019修正)對電子文件管理工作的啟示[J].檔案學通訊,2021(03):98-105.
[17]許曉彤.電子檔案憑證價值保障需求研究——基于電子證據審查判斷的視角[J].檔案與建設,2021(07):14-19+13.
[18]余亞榮,張照余.基于可信時間戳服務的電子檔案證據取證和驗證方案設計[J].檔案管理,2020(01):66-68.
[19]金麗雙.區塊鏈技術在電子檔案安全管理中的應用[J].黑龍江檔案,2022(04):55-57.
[20]王臻.數據轉型背景下的電子檔案信息安全研究[J].蘭臺世界,2022(04):109-111.
[21]燕雙雙,張丹.《個人信息保護法》視角下數字檔案館個人信息保護的問題與對策[J].檔案與建設,2022(08):20-24.
(作者單位: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 鄭毅,碩士,副教授 來稿日期:2023-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