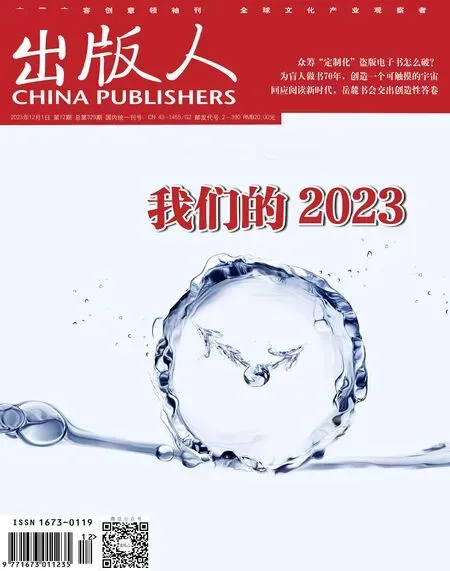敖德:簽下跨國IP永久版權,我們就要啃硬骨頭
記者|張競艷 “我們想做成體系最完備最先進的教材級‘百科全書’,成為未來通識教育的引領者。”
“我們簽的是永久版權。”“我們就要啃硬骨頭!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氣和能力去啃硬骨頭的。”
剛剛完成了一項重要國際合作項目的簽約,耕林童書總編輯敖德的聲音里滿懷喜悅。11 月20 日,擔任項目負責人的敖德代表青葫蘆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青葫蘆”)與英國 What on Earth 公司及基金會CEO 克里斯托弗·勞埃德(Christopher Lloyd)簽訂了聯合開發創作“百科全書類”圖書的戰略合作協議。畢業于劍橋歷史系的勞埃德,曾是英國《泰晤士報》科學版的資深記者,其團隊創作并出版的“墻書”系列風靡歐美。此次戰略合作,雙方將采取聯合開發的合作模式:由勞埃德團隊與青葫蘆團隊共同確認“百科全書”的各本選題及圖書的文字風格、插畫風格。青葫蘆團隊也會選擇合適的中國創作者(插畫、設計、作者等)參與到選題的創作中。最終出版的作品不僅僅在中國出版。青葫蘆擁有上述作品的中文全球永久版權、英文版的中國(含港澳臺)永久版權。“從2016 年底耕林引進推出第一本墻書《地球通史》至今,我們跟勞埃德團隊已經持續合作多年,之后我們的合作將更加緊密,這種合作是兄弟之間的合作,是在相互充分信任和欣賞的前提下展開的。”敖德說。
創建于2010 年12 月的青葫蘆,近年來致力為全球優秀的創作者搭建創業平臺,6 年打造了20 支優秀原創團隊,創作了《小羊上山兒童漢語分級讀物》《打開故宮》《走近三星堆》《爆笑作文》等優質版權超1000 項,且保持每年200 多個新品的快速增長。值得一提的是,青葫蘆此前跟勞埃德團隊合作推出的全新《大英兒童百科全書》目前單本銷售超14 萬套,總碼洋超3480 萬元。青葫蘆在2019 年獲得該書及系列圖書的中文全球永久版權、英文版的中國(含港澳臺)永久版權。

11月20日,敖德與勞埃德簽署了聯合開發創作“百科全書類”圖書的戰略合作協議
作為項目的見證者之一,青葫蘆副總裁張麗認為,青葫蘆能夠在國際版權合作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青葫蘆在圖書電商領域有扎實的運營銷售能力,可助力圖書的策劃和創作。勞埃德對青葫蘆及其創始人林柄洋在商業能力上非常信任。二是敖德了解中國讀者和文化,能為創作提供客觀、真實的讀者需求和狀態信息,勞埃德對其專業能力非常信賴。張麗表示,青葫蘆以中國原創童書為主要的內容創作原點,此次合作,青葫蘆要融合世界的力量,為中國原創童書的發展做出貢獻。“一方面使圖書能夠更好地融合進悠久深厚的中國文化中華文明,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另一方面這種共同創作會極大地推動中國創作者走向世界,讓世界文明相互交流,不同文化相互借鑒。”
“我們想做成體系最完備最先進的教材級‘百科全書’,成為未來通識教育的引領者。”在接受《出版人》專訪時,敖德如是說道。就在不久前,耕林與青葫蘆成功聯姻。對項目團隊編創能力的自信,再加上青葫蘆以自營為主、分銷為輔的全域銷售渠道加持,敖德對這個跨國IP的打造信心滿滿。
《出版人》:近幾年大家普遍看好非虛構類童書市場,進入這個賽道的人也特別多。您對此次戰略合作研發的“百科全書類”圖書在內容層面有怎樣的定位?
敖德:在做這個項目前首先要清楚的是,我們是站在哪一個賽道上。其實,在非虛構的百科類童書賽道背后還有不同的賽道,我們是把它定位在未來中國的教育跟世界接軌的賽道上去做的。
我們知道,中國的基礎教育比較完善,但是這些年很多家長也越來越認識到我們在教育上需要更加具有開拓性,教育部已經明確提出的教育改革措施之一就是開展通識教育,打破學科之間的壁壘。當今社會各方面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很多人開始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現在的教學方式和教學內容可以更有突破性和開創性。兒童圖書是教育的啟蒙工具也需要更加具有開創性。閱讀對于孩子的重要性是帶給孩子思維上的改變,而不是說無窮地拓展他的知識結構或者提高他的分數,因為分數和能力是不掛鉤的,所以我們跟勞埃德團隊的合作是基于未來教育改革的賽道上,去做的這樣一個“百科全書類”的產品。這就和目前在我們國內市場上已有一定影響力的單一學科分類的百科類圖書品牌有了一個巨大的區別。它們是在傳統教育的格局下做的圖書類目,而我們的產品要把所有的學科融會貫通在一起,這在思維上徹底顛覆了我們原有的學習方法。擁有這種學習思維的孩子,未來一定能高質高效地完成工作。這是我們產品的核心競爭力。而且世界科技在飛速進步,百科類圖書其實怕的就是過時,我們的產品是緊跟各學科領域的最前沿知識。
和互聯網提供的碎片化知識不同,我們這套產品的另一大特點在于它不但是跨學科的,還給了讀者一個類似蜘蛛網一樣的思維網,你站在這個網面前就會發現,每一個節點都可以向四面八方與各個節點產生連接。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單一的跟任何事物都沒有關系的東西。知識也是這樣,所有知識之間都是有緊密的聯系的。我們要做的工作就像給讀者提供一個開車的導航,我們的產品就像一個巨大的知識地圖網,讀者的腦海里有了這個網,就可以輕松地連接各領域知識,從而在未來能夠應對跨行的挑戰,輕松勝任多變的工作。
《出版人》:這樣的產品在策劃理念上很有前瞻性,但實際操作會很難吧?
敖德:難就對了。我能做你能做誰都能做,我們就沒有壁壘了。出版業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跟風,當一個好的構思出來以后,很多人迅速跟風,然后用低價格把你“打死”,真正的好東西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我們就要啃硬骨頭,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氣和能力去啃硬骨頭的。
能夠啃硬骨頭的原因是,我們早在“墻書”出來的時候,就已經引起全國的轟動,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同行去模仿我們的“墻書”。我知道“墻書”背后的邏輯有多難。你不要小看那一張2.4 米的長卷,它不是簡單地把所有的圖放上去就行了,而是需要制作者具備龐大的閱讀量和掌握整個學科的知識結構。
我們就想做有很強壁壘的產品,才能實現自我的保護,才會有這個產品真正的核心競爭力。
做教育產品的核心是我們要把市場最好的產品給讀者,我覺得出版事業是一件功德之事,出版物是文化消費品,但應該把“消費品”三個字去掉,它是文化就應該是能夠真正去改變這一代人的。如果基于這個邏輯去做事情,結果就一定會好,而不是奔著錢去,什么好賣就賣什么,什么題材火了就做一把賺一把錢,然后下一個題材火了又跟著做一把,這樣的公司往往都不長久,可能中途哪一天就一下子夭折了。
耕林在這方面一直非常穩健。我曾經跟同行開玩笑說,“我們耕林二婚了還有人愿意娶我們,是因為老男人也有價值”。別看我們只是由20 個人組成的團隊,但我們有很強的編創能力、策劃能力及對市場的前瞻性,我們愿意去做有創造性、引領性的事情,而不是去跟風。這些年,我們一直在不斷地自我變革,自我成長,這可能是跟其他同行不一樣的地方。

耕林“墻書”系列作品
《出版人》:耕林團隊之前與勞埃德團隊共同合作“墻書”的經歷會給此次合作帶來怎樣的幫助?
敖德:我們從2016 年11 月推出第一本墻書《地球通史》后,連續5 年邀請勞埃德來中國巡講,每年上半年講半個月,下半年再講半個月。我們幾乎跑遍了中國的一線城市,最震撼的是在曾作為春晚舞臺的武漢漢秀劇場,我們采取賣票的形式,一場的觀眾人數高達2000 人。我們迅速通過地推的方式,讓更多的消費者看到這樣獨特的內容。我們給自己的定位始終不是一家出版公司,而是一家教育公司,用教育的理念去選教育的產品,這是其一。
其二,在跟勞埃德合作的過程中,我們邀請他來中國僅僅是為了地推,僅僅是為了演講嗎?不是,其實我們是在深度地走近對方,磨合協作。我會知道他的每一本書背后的呈現形式,他的出發點是什么,他是怎么構思的,為什么要這樣做,書出來以后我們要以怎樣的形式去給讀者講得更清楚,讓他們認識到這本書的真正價值。同時我們通過巡講溝通前期的策劃,也找到了做這類書的方法和路徑,然后我們就可以共同來策劃這樣的書,所以在做第一本墻書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做原創墻書的布局了。其實相當于我們在引進產品的同時,就把它的編輯理念也同時引進并且付諸實踐,做出了自己的產品。經過8 年時間的深度磨合,中英兩個團隊都有了豐富的合作經驗,我們可以相互啟發,未來的百科類圖書合作也同樣是這種邏輯。
青葫蘆有強大的渠道運營能力,知道中國市場的消費者是什么樣的喜好,什么樣類別的書能夠賣得好,在這種強大的市場數據的基礎上,我們就更加清楚應該策劃出什么樣的產品更能夠讓消費者接受。
如今,距離我當初創辦耕林已經16 年,這16 年里用戶和渠道全變了。如果一個出版公司還守著10 年前的經營思路肯定是不行的,你都不知道書賣不好的原因究竟在哪兒,因為你沒有考慮當用戶和渠道改變后,你的產品跟著變了嗎,你的營銷手段跟著變了嗎,你的圖書編寫體例和內容呈現方式跟著變了嗎?而我們的團隊就是要緊跟市場的變化做出相應的改變。
《出版人》:和勞埃德團隊的合作,受到過文化背景差異、專業背景差異、語言溝通問題等因素的影響嗎?
敖德:我們在合作中并沒有遇到什么困難。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覺得這怎么可能?兩個團隊的磨合,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兩個團隊的理念是否一致,我們雙方團隊在理念上可以說是高度契合,這的確很難得,也許就是我們之間的緣分吧。我們團隊有很多英文水平達到口譯級別的編輯,所以在溝通上也沒有語言方面的障礙。而且勞埃德這個人非常開放兼容,在內容的合作上不會很固執和高傲,在商業的合作上也懂得取舍,這使我們的合作一直很順暢。
《出版人》:按約定,青葫蘆擁有此次合作研發作品的中文全球永久版權、英文版的中國(含港澳臺)永久版權。作為一名資深的童書出版人,您如何看待此次戰略合作的意義?
敖德:我們為什么要用永久版權的形式來做這個項目?就是因為國內出版業存在一個問題,似乎找不出像《哈利·波特》那樣基于一個產品或者一套書的成功而孵化出一個IP 的大項目。是我們缺少好的作品嗎?這個理由好像并不成立,原因就是我們任何一個項目對于出版機構而言,都是階段性地擁有出版權。這個模式就是我們這個行業做不大做不強的根源所在。比如耕林看好一個項目,它在內容上很好,有引領性,但可能暫時在一兩年之內不容易被市場所接受,我就要砸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推廣做宣傳,可是當我用5 年時間把它做得足夠好,宣傳得足夠好,賣得足夠好的時候,我的版權到期了。同時,有很多同行看好這個項目,他們拿更多的錢把它挖走了,我前期所有的努力都白白為別人做了嫁衣。像這樣,誰愿意為一個項目做長遠的規劃和完整立體的運營呢?這就導致我們的項目缺乏持久性。
青葫蘆也好,耕林也好,我們希望把企業傳給下一代接棒。是給他們留錢嗎?錯了。我們要留項目、留文化資產給下一代去繼續運作,要有讓企業延續的核心內容。當我們這一代退休干不動了,下一代接班時可以用年輕人的方式在這個內容基礎上重新整合編輯做出新的產品來,但是內容永遠都在我們手上,這樣才敢舍得花錢、舍得投入功夫去打造好的產品。耕林和青葫蘆兩家合并后,這是林柄洋和我都深深認同的一個理念。只有在這個方面有所改變,我們未來才會有機會做強做大。
要擁有永久版權,還要有底氣,就是有強大的銷售能力。如果沒有強大的銷售能力,還要“抱”渠道和網紅達人的“大腿”,這樣是根本沒有主動權的,因為有太多的不可控。尤其是今天的直播帶貨,你覺得你的書好,可達人不選就是死路一條。但我們的底氣在于,青葫蘆有強勁的全域渠道銷售能力,讓我們有充分的信心。之前我想這么干,但是我們的發行能力不足以支撐我的野心和夢想,一旦條件成熟了,我必須這么干。
我們希望通過這個項目顛覆大家的認知,為時下處于艱難迷茫期的出版業找到未來的出路,帶來一絲希望。如果能夠找到一個方向,不僅是我們受益了,能夠讓整個出版業也重燃信心,這也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