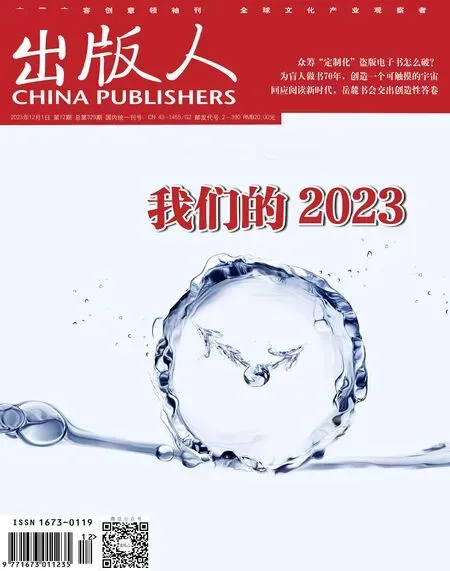“神仙譯者”有了,編輯為什么找不到
記者 | 李晶 為什么“神仙譯者”百年一遇,編輯要被“爛稿”折磨。
在圖書市場上,那些被“糟糕的翻譯”毀掉的經典好書經常被拿出來盤點,一本書的譯者有時候與原創作者同等重要。與編輯一樣,譯者的工作也同樣具備“幕后”“隱匿”的特點,不過他們的能力同樣決定了圖書的質量。
正所謂“好譯者是笨蛋編輯的救星”,編輯眼中的“神仙譯者”,既要有優秀的語言能力,又要有深耕垂類領域的專業背景;既要有與編輯詳盡、靠譜、親切、體貼的溝通能力,又最好有一定社會影響力能為圖書的營銷宣傳提供助益……都說編輯是一個高門檻的職業,現在看來圖書翻譯的門檻一點也不比編輯低。
既然在圖書出版工作中,譯者的身份如此重要、對譯者的要求如此之高,那么圖書譯者能否在這個行業獲得合理的報酬以及相應的職業榮譽感呢?編輯找到心目中的“神仙譯者”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嗎?《出版人》采訪了6 位圖書譯者,他們都是從編輯到翻譯的跨界譯者,希望通過雙重視角重新看看圖書譯者在出版行業中的真實情況。

翻譯點什么不好,干嗎要去翻譯書啊!
首先跳出出版行業,看看其他行業的譯者收入。以英語語種為例,市面上正規翻譯公司的旅游、展會、解說口譯報價為每天1000 ~4500 元;電影字幕筆譯報價為每分鐘30 ~300 元,按平均7 分鐘千字算,價格為每千字210~2100元。而圖書翻譯報價一般在每千字60~120元。這相當于做幾天口譯就能賺到一本書的翻譯稿酬,而電影字幕翻譯的價格竟然是圖書翻譯的十幾倍!
一位稿酬在行業平均范圍內的全職圖書譯者,按照一年一百萬字的翻譯量來算,全年收入也只有10 萬元左右,這個收入真的能養活自己嗎?
身為給譯者開稿費的外國文學編輯,黃建樹自己也覺得圖書譯者的付出與回報比并不合理:“報酬提高了一些,但跟CPI 相比,感覺增長幅度很小。”2000 年前后,譯者就能拿到千字80 元的稿酬,如今絕大多數圖書譯者還是拿這個數。去年“天才譯者”金曉宇被爆出稿酬千字僅五六十元,引發了不少爭議,而像金曉宇這樣拿“入門級”稿費的譯者在行業內比比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物價翻了近兩倍,期間圖書譯者稿酬被拿出來反復爭論過,也產生了小幅增長,不過“稿費漲一倍到千字160元才是合理的”,譯者何嘯風認為。
國內按版稅計費與譯者簽約的出版方不多,大多數情況下譯者獲得的圖書翻譯稿酬不會因為圖書銷量而產生變化,然而一本書的銷量真的與譯本質量毫無關系嗎?大多數拿一次性稿酬的譯者看到自己翻譯的書暢銷了,內心多少都會摻雜著驕傲和失落并存的復雜情緒。
據黃建樹觀察,翻譯行業內能拿版稅的條件比較苛刻,只有少數知名譯者能拿到版稅,而且一般只有在譯公版書的時候才會給版稅。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譯者早一步進入圖書翻譯領域,自然會先成為“站在塔尖上的人”。然而在一些編輯眼中,現在的年輕譯者可以通過網絡或出國留學等方式與最新學術文化動態接軌,所以年輕一輩譯者的翻譯水平整體不僅在提高,甚至可以超越老一輩譯者。但他們并沒有獲得與同樣的知名度以及水平相當的報酬。
另外公版書也在考驗著年輕譯者的定力。由于首譯版權書面臨著未知市場的風險,一次性稿酬對出版方和譯者來說都更加保險,也成為普遍的稿酬結算方式。然而引進版權書的首譯往往比公版書難度更高,需要譯者付出更多與編輯的溝通成本,而獲得的回報比公版書低,這自然會折損做當代外國文學、學術、社科等艱深領域圖書譯者的信心。
剛入行沒多久的譯者董紓含告訴《出版人》,她給自己的定位是“成長型菜雞”,很多事情都還在學習階段。在與出版方簽訂合同時,除了稿費結算方式、千字多少人民幣,她還會重點看看出版方是否要買斷版權。如果出版方買斷版權后不再出書,譯者也不能把譯稿授權給其他出版單位出書,這對譯者來說是很麻煩的事。在與出版方合作的過程中,年輕譯者還有可能遇到一些類似買斷版權、拖欠稿費的“坑”,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
從行業內部來看,不對等的收入回報和職業榮譽感使圖書譯者的從業信心降低,圖書譯者在出版環節中相對弱勢的地位也給翻譯工作造成了重重阻礙。從行業外部來看,新技術的出現、競爭者的涌入也讓有志于在這個行業深耕的年輕譯者面臨更加復雜的環境。
GPT-4Turbo都出來了,書還要你來翻譯?
從業八年的出版公司編輯小墨之所以會產生做圖書譯者的想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生氣和憤怒。不少編輯都與他深有同感,任職于浦睿文化的編輯何嘯風說:“純粹是因為翻譯的稿子太爛了!我職業生涯中第一部稿子就譯得很差,當時心里就想,還不如我自己來譯!”
村上春樹《第一人稱單數》的譯者燁伊就從編輯轉行成為全職譯者。曾在某知名民營圖書公司做編輯的幾年里,燁伊譯書幾乎沒有間斷過,那時候所有的譯作都是她利用下班后的空閑時間做,但兩樣工作一起干,時間久了身體就不太能吃得消,于是只好忍痛割愛做全職譯者。
在圖書出版這個小圈子里,“今天你是譯者我是編輯,明天我是譯者你是編輯”,編輯兼職譯者的現象很常見。不過這些編輯之所以會遇到令他們“懷疑人生”的譯稿,有一部分原因也是這些譯稿的背后是大量的兼職譯者。
在燁伊看來,這些兼職譯者來自各行各業,有學生、老師、文藝愛好者,他們有的為了豐富履歷而接下圖書翻譯的任務,有的就是為了嘗試而接觸圖書翻譯,翻譯水準不一。雖然也有真正愛好翻譯、用心做事的譯者,但整體上不可避免地缺乏對行業的了解,進而也導致行業整體缺乏規范性,成了惡性循環……
兼職譯者大量涌入圖書翻譯行業的現象,和機器翻譯的出現密切相關。當被問到編輯如何處理自己并不熟悉的語種文本時,編輯小墨的答案是“借助機翻平臺”,他認為懂得怎么使用機翻平臺是現在引進書編輯的必備技能。機器翻譯的出現方便了編輯的工作,同時也降低了圖書翻譯的門檻,讓那些編輯眼中“很爛”的譯者能夠乘虛而入。
不過在機器翻譯向AI 翻譯的方向不斷發展并進化的過程中,譯者出現了兩極分化的現象。“AI 翻譯的出現對認真負責的好譯者是有好處的,當然有些不認真、不負責的譯者在AI 的幫助下可以變得更不認真、不負責。”小墨說。接受采訪的大多數譯者也認為AI 翻譯目前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取代他們的工作,而是隨著AI 翻譯水平的提高,他們從中獲得了更大的幫助。
在本次調查中,“目前來看圖書譯者最大的競爭者是什么?”這一問題得到了意料之外并且相對一致的答案:
董紓含:“是自己吧(啊,好中二的回答)。”
康海源:“可能還是自己——如何在翻譯實踐中不斷提高自己的語法、邏輯、語文水平。”
黃建樹:“也有可能是譯者自己。我個人覺得,自己和自己‘競爭’、提升自己的業務能力和經驗、時刻端正自己的態度,也是一件要緊事。”
何嘯風:“最大的競爭者就是彼此吧。總是能遇到一些很厲害的譯者,覺得——哇,這個句子我怎么想不到這樣譯呢?”
在對人本身抱有信心的年輕譯者眼中,AI 不是競爭者,最大的競爭者是自己。“有些老社編輯,一句外語不會,也能做引進書,主要就是相信譯者吧。”小墨補充道。也許現在不認真負責的譯者做的翻譯工作,從機器輔助變成輔助機器,直到有一天被機器取代后,最終這些相信自己也值得編輯相信的譯者會留下來。
因為這是很好玩的事,會盡力把這件事做好!
雖然圖書譯者在工作上面臨重重阻礙和復雜的環境,不過仍有不少年輕譯者都把這樣一項超高難度的工作當作“好玩兒”或者激勵自我成長的事情,愿意在各自感興趣的專業領域和語種上鉆研,敢于挑戰更具創造性的引進版新書的翻譯工作,并在不同類型的圖書翻譯市場上生發出自己的見解。
在圖書譯者圈里,大家公認文學翻譯對譯者的語言和文學功底要求最高,文學翻譯中的頂級譯者可以說是翻譯界的天花板。編輯黃建樹本科和碩士學的都是英語,碩士具體方向是英美文學。在他看來,英美文學翻譯“用時下比較流行的語言來說,已經非常‘卷’了。當然也有一些空白地帶,但相對較少”。
2014 年碩士畢業以后,黃建樹先做了3 年的出國留學咨詢相關工作,然后轉行做編輯一直到現在。他說自己之所以兼職做譯者,是因為喜歡文學、喜歡英語、喜歡翻譯。他翻譯的書有《成為母親》《超凡脫俗的鳥》《早春》《四面風》《承諾》等,其中不乏獲布克獎等國際重要文學獎項的當代作家的作品,因為譯稿質量高,被同行稱為“樹師”。
因為本職就是歷史社科類圖書編輯,小墨翻譯的圖書也以歷史社科為主。以他的經驗來看,歷史社科類引進版圖書以前市場翻譯需求很大,現在似乎在萎縮。不過主攻海外學者對中國歷史研究的康海源卻發現:“從版權貿易的情況看,歷史社科類中海外學者對中國歷史研究方向的選題競爭卻越來越激烈了,國外有些新書事實上還沒正式出版,版權就被國內機構買下了,有時令人吃驚。”
上學的時候,康海源所讀的專業幾乎人手一套“海外中國研究叢書”,這套書對他的影響非常大。當時他沒想到畢業后會來到江蘇人民出版社,成為這套叢書的編輯。進入學術翻譯的領域讓他體驗到不少樂趣:“它讓你‘跳出椰殼碗’,與更大的世界(包括古代的世界)發生聯系;讓你像闖關一樣,去破解一個個長難句;讓你用語言還原前后句、前后段的邏輯關系,感受思維的樂趣。作為譯者,我會盡力把這件有趣的事做好。”
關注法語翻譯的何嘯風認為:“法語圖書和英語圖書一樣已經和國際接軌了。雖然有些書出版時會宣傳‘被遺忘的法國大師’,但是至少就社科領域而言,基本上口碑不錯的新書,很快都會引進到國內。”他主要關心的是社科領域中的精神分析和女性主義:“我認為二者是有關聯的,它們都關心那些‘被壓抑的聲音’。”同時他也發現社科書的翻譯需求近幾年明顯增加了,“看這類書的人越來越多,因為人們更關心社會了”。
專業是戲劇的董紓含讀書期間兼職做戲劇相關的活動,比如寫劇本、參加戲劇節的制作和翻譯。畢業后短暫做過一段時間圖書編輯,在做編輯期間找到了譯書的樂趣,于是開始了“非專業翻譯”的生活。轉行成為全職圖書譯者后,她喜歡和編輯們聊天、學行業知識,在各種出版行業聚會的場合,她都會拿出精致的名片,向大家鄭重地推薦自己的譯者身份。今年9 月,她翻譯的上野千鶴子和水無田氣流的對談集《結婚由我》正式出版,新書上市后,她開心地給業內女性友人贈送這本書。
為什么“神仙譯者”百年一遇,編輯屢受“爛稿”折磨?
“神仙譯者”百年一遇,編輯屢受“爛稿”折磨,原因到底是什么?
小墨曾經遇到一本一度難產的書。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編輯著急催稿,兩年過去了翻譯費卻遲遲不給支付。他有些生氣了,比較嚴厲地發郵件向負責的編輯“發飆”,后來接手的編輯抱著同情與理解妥善解決了問題。最后他和編輯成為特別好的朋友,正所謂不“罵”不成交。編輯對“神仙譯者”的第一個訴求就是不拖稿,那么出版方至少也要做到不拖欠稿費。
黃建樹回憶,翻譯《早春》時,編輯和改稿過程都很愉快,編輯郭歌將兩人關于譯文的商討整理成了一個四萬多字的文檔,專門請朋友設計做成了一冊“小書”,在后來見面時送給了作為譯者的黃建樹。這才叫專業編輯與“神仙譯者”的雙向奔赴。
燁伊認為,目前兩種情況可能會導致譯者稿酬不容易提高:假如出版機構對文本質量要求很高,要求編輯具備非常優秀的改稿能力,并給編輯大量時間打磨內文,那么他們沒必要買那么好的譯稿,因為他們可以“屎上雕花”;假如出版機構對文本質量根本不在乎,只追求效率和碼洋轉化,30 分的譯稿和70 分的譯稿對他們來說區別不大,在既定下限的基礎上不愿花錢買質量,只追求利益最大化。
將翻譯成本轉移給編輯,或者主動降低文本標準,這些壓縮圖書成本的傾向都會讓優質譯者很難出頭。近年來,從電商崛起到直播賣書,掌握新渠道似乎成為出版機構的制勝法寶,但在“渠道為王”的觀念驅使下,圖書破價等亂象層出不窮,退讓的是價格,壓縮的是成本,錢省在了文本上,花在了流量上。留給好書的空間似乎越來越小了,優質圖書譯者的空間自然也越來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