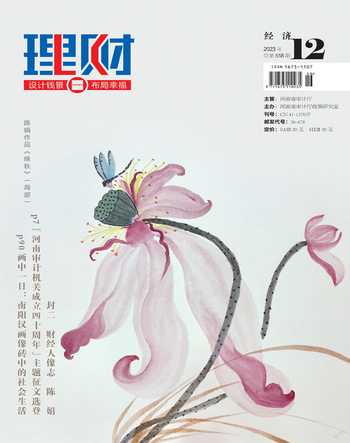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孝行圖像釋義初探
王君 榮昱森
孝行圖像也稱孝子圖像,是中國古代墓葬中比較常見的一種圖像。孝行圖像形成于漢代,多見于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貴族墓葬中。這一時期比較著名的孝行圖像有山東嘉祥縣的武氏墓群石刻、山西大同司馬金龍墓出土的彩繪漆屏、波士頓美術館藏北魏孝子石棺床和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北魏孝子石棺等。國內外學者對其研究也較多,主要從考古學、圖像學、文獻學等角度進行探討,且極少有學者對其釋義進行研究。筆者認為,孝行圖像是歷史時代的產物,對孝行圖像的解讀還需要從當時的社會環境出發,通過對當時人們的孝行觀的考察,來解讀孝行圖像的含義。
孝行圖像最早流行于兩漢,而這與漢朝“以孝治天下” 的治國理念密切相關。“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使得統治者深信:維護統治,離不開孝治,進行孝治,就必須推廣《孝經》。《漢書·藝文志》便有記載:“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孝經》),各自名家。”漢平帝時“立官稷及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東漢時期,《孝經》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其后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孝經》作為基層學校的通用教材,經過多年的教育傳承,成為兩漢以至南北朝時期人們孝行觀的指導性書目。
《孝經·開宗明義》寫道:“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臥冰求鯉的王祥在其去世前告誡子孫:“……揚名顯親,孝之至也;……立身之本。”可見,漢魏時期,人們理解的最大的“孝行”就是要“揚名顯親”。如何才能“顯親”呢?《孝經·感應篇》中明確提出:“宗廟致敬,鬼神著矣。”魏文帝曹丕也曾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祭祀宗廟成為“顯親”的重要內容。
東漢武氏祠是武氏家族墓地所在地,是武氏子孫祭祀祖先的地方,其后世子孫在此修建祠堂就是為了“昭孝事祖”。現武氏祠保存有碑三通,其銘文所記皆為武氏官位顯赫的子孫,這就是漢人所說的“揚名顯親”。
武氏祠石壁上刻畫有孝行圖像十三幅,“武梁碑銘”上記載:“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蛇有章。垂示后嗣,萬世不亡。其辭曰:……身歿名存,傳無疆兮。”由此可見,武氏祠畫像石上的孝行圖像的目的有二:一是“垂示后嗣”,即教育意義;二是“身歿名存,傳無疆兮”,即“揚名顯親”。但武氏祠畫像石上還刻畫有帝王和列女圖像,巫鴻在其專著《武梁祠》中便提道,帝王、列女、孝子的排列順序和《孝經·感應篇》中的“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相對應。所以,武氏祠中孝行圖像具有教育子孫、忠孝持家、“揚名顯親”的作用。
除了推崇《孝經》,兩漢南北朝時期還通過選官鼓勵孝行。兩漢施行察舉制,魏晉之后流行九品官人法。漢武帝時規定“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謂善事父母。廉,謂清潔廉隅”。此后,以“孝”作為選官的重要標準。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中護軍夏侯玄言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今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可見魏晉時期崇孝之風不減,依然以“孝行”作為衡量人才的重要標準,是中正官“考行”的重要內容。但由于舉孝廉缺乏明確的評比標準導致大量的“愚孝”“偽孝”的產生。“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贏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世說新語》也記載: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后,遭母童夫人艱,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吊省,號踴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凄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后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這些不顧生命安危的“愚孝”行為其實已經背離了《孝經》的宗旨。《孝經·喪親章》中說:“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圣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孝經》也是不主張這種愚孝行為的。更有甚者,為了博得“孝”名弄虛作假。“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馀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頤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觿,誣污鬼神乎?遂致其罪。”而社會氛圍也樂于評價、比較別人的孝行。“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倶以孝稱。王雞骨支床,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正是在這種弄虛作假、相互攀比的社會氛圍下,孝行日益形式化。
“孝行”的形式化直接導致選官制度的失效,階層不斷固化。北魏韓顯宗曾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不復彈坐。”一些以“孝行”著稱的大臣也不再恪守孝行:“于時雖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郤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通典·選舉二》中評論道: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至此,“孝廉”成為世家貴族等社會上層子弟的榮譽頭銜,成為他們進入官場的通行證和“揚名顯親”的資本,孝行和身份緊密相連。
因此,南北朝時期,墓葬中出土的孝子圖像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子孫孝順墓主人,而應理解為對墓主人品格的贊揚。而且如前所述,漢魏南北朝時期人們對至孝的理解就是“揚名顯親”,所以孝行圖像實際上也是在表達墓主人顯赫的身份和家族的榮耀。與此同時,漢代及其以后的各代,神秘主義彌漫于整個社會。漢武帝時就有巫蠱之禍,讖緯之學也在民間泛濫。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宣傳君權神授,《白虎通義》又進一步將儒家思想神秘化。作為十三經的《孝經》也被經學家斷章取義,或神秘化解讀。《孝經·感應篇》中“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的觀點被人們深信不疑,即使到了兩宋依然被人認可。而作為《孝經》“孝能通神”理論具象化的孝行圖像自然成了通神的符號。漢魏南北朝時期,墓中的圖像多是為了表達死后升仙的主題,而墓中的孝行圖像實際上也是表達同樣的含義。